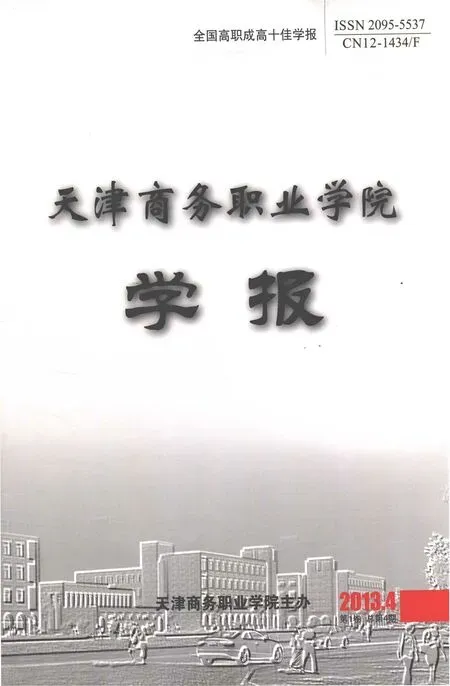等级含义认知机制研究对语用教学的启示
李 然,李 焱
1.2.天津农学院,天津 300384
等级含义认知机制研究对语用教学的启示
李 然1,李 焱2
1.2.天津农学院,天津 300384
“教语用”是在国际外语/第二语言教学界新兴的教学观念和方法,正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发展。本文先简要讨论等级词项的语用认知;然后着重分析等级含义认知实验对语用教学的启示,继而探讨怎样在课堂上教授语用知识、培养学生语用能力。作者介绍了两项(“隐性教学法”和“显性教学法”)具体的语用教学形式、内容和步骤,以说明教语用是提高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语用能力;课堂教学;等级含义;认知机制
一、荷恩等级
学者荷恩(Horn)于 1972年在格赖斯(Grice)会话含义理论数量准则的基础上率先提出了“等级”这个概念。自此以来荷恩等级(Horn Scale)作为新格赖斯语用学派(Neo-Girce)会话含义理论的重要推理契机倍受关注,并被语言学家列文森(Levinson)引进其理论,成为“列氏三原则”中等级数量原则会话含义推导的主要依靠。等级含义产生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荷恩等级<S,W>(S指强项,W指弱项)。构成荷恩等级关系的词项要满足以下三点:①在一个任意的句子框架A内必须实现A(S)蕴含A(W);②S,W词性性质相同;③S,W涉及的是相同的语义关系或来自相同的语义场。Levinson列出了常见的等级词:不定代词<all, most, many, some, few>; 连接词<and, or>;数词<… three, two, one>;情态词<must,should, may>;频度副词<always,often, sometimes>;程度形容词<hot, warm>;动词<start, finish>等。等级含义指的就是人们通过使用构成荷恩等级关系的词项,依靠语言规约,通过等级推理而得出的会话含义。简言之,这种等级含义就是选择弱项意味着否定强项。以最典型的荷恩不定代词等级词项<全部,有些>为例:“今天有些网页打不开。”那么对弱项“有些”的选择则构成了对强项“全部”的否定,因此该句的等级会话含义是“不是所有网页都打不开。”由此可见,“有些”的等级含义是“有些,但不是全部”。这则不同于其逻辑含义(有些,可能是全部)。如 “今天我上网时发现有些网页打不开。经检查发现是网线坏了,那所有网页就都打不开了。”此句中“有些”的等级含义则被撤销,显示的是其逻辑含义。但这个等级推论仅停留在假说阶段,质疑声不断。因此教师不能凭直觉判定词项的等级含义来进行语用教学,学生更不可能凭直觉习得语用能力。因此,外语教师需要在具体的语用学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地培养学生的语用意识和理解“等级会话含义”的能力。在语用教学之前,我们应该先弄清楚学生对等级含义的认知机制是怎样的。
二、等级含义认知模式之争
以Levinso为代表的新格赖斯派(neo-Griceans)认为等级含义属于一般会话含义(GCI),是正常自然交际语言中某词语形式通常带有的无标记的、高频使用的甚至是默认的含义。除非遇到特殊语境将其撤销或阻止其产生,否则GCI将是此词语形式的首选的乃至默认的含义。Levinson认为人们对GCI的理解依靠的是 “默认语用推理 (default pragmatic inferences)”。
Bach将此默认含义命名为 “会话隐意(Impliciture)”,并认为隐意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意义层面而存在,人们对隐意的理解要经过对话语形式的认知,但无需语境参与而依靠的是一种“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的常识和习惯。例如:
Some elephants have trunks.
在正常情况下,听话人会对例句感到困惑。因为根据常识所有的大象都长有长长的象鼻。听话人感到困惑说明他\她优先反应了“some”的等级含义“some but not all”,而且是无意识地、自动地反应了甚至是默认了“some”的等级含义。
以Sperber和Wilson为代表的关联理论派认为等级含义是所言(What is said)的一部分,因此对等级含义的认知不完全是语用推理。关联理论派认为等级词项具有语义不确定性 (semantic underspecification)。换言之,等级词项具有语义多样性。具体语义的选择和确定需要具体语境的参与。在特定语境中,听话人并非将词项的一系列语义一一反应出再选择最合适的,而是直接反应与当前语境最为相关的一条语义,其他语义不做反应。例如:
Some of our neighbors have cars.
Some but not all of our neighbors have cars
Some,in fact all of our neighbors have cars
The speaker doesn’t know whether all of his/her neighbors have cars.
听话人在听到上述句子时不会优先反应出“some”的等级含义,也不会将 “some”的三个语义全部做以反应,而是直接反应出与语境具有最佳关联的词项含义。语境具有最终决定权。
综上所述,对于等级含义的认知机制主要存在两种意见:
(1)Levinson一派认为等级含义通过认知的默认机制 (Default Mechanism)推理出来。“常规”(stereotypology)是话语理解的依据。默认推理模式假设词项的等级含义是首先被认知的,如果得不到恰当的意义,再参照语境撤销等级含义,进行新一轮的语用理解并认知出其特殊会话含义。
(2)Sperber和Wilson支持的语境驱动理论则认为,等级含义具有语境依赖性。此模式假设词项的逻辑含义、等级含义及其他会话含义都没有被优先处理的特权,最终由语境因素决定是哪种含义出现。
哪种模式真正还原了学生认知等级含义的真实图景呢?还是学生的等级含义认知模式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
三、西方等级含义认知机制的实验研究的教学启示
Noveck,和Posada以及Bott和Noveck的在线实验基本是通过对比受试者对句子真值判断的时间来推测受试者是否看到“some”就同时反应了该词项的等级含义(some but not all)。 例:“Some elephants have trunks.”或者在测试句子前面加上 “Mary says the following sentence is true/false”。 结果显示对此句判断为“错误”的受试者的平均反应时间显著慢于判断为“正确”的平均反应时间。实验者认为这恰恰说明了“some”的等级含义不是它的语言编码意义,其等级含义的得出需要结合语境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因此反应时间加长。这一结论支持了语境驱动论。研究人员随机选取了30名会计专业大二学生重复上述实验,结果将近40%的受试者判断此类句为“正确”。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意识到等级会话含义的存在。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等级含义并不是高频使用的默认含义,不能通过语言学习而习得成功,等级含义的推导需要特别的学习和指导。尤其是对于二语和外语学习者。Trosborg的研究发现,母语语用能力强的学生并不一定二语语用能力也强。有些学生在母语语境中深谙规则、言谈得体、恰到好处地以言行事,但在第二语言语境中却言语唐突、处处碰壁,因为他们不能把熟悉的母语语用规则和模式(比如礼貌用语)恰当地套用到二语中以取得同样的礼貌效果,而且有时还适得其反。同理,学生们可能能在母语中意识到等级含义的存在并加以利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这种语用能力可以自然迁移至外语学习中。所以,英语语用教学就应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除了学习机械规范的语法和单词的字面含义外,更明确地分析自己母语中的语用常识和规则,自觉对比母语和英语的语用异同,鼓励他们正确地进行“正迁移””,克服“负迁移””。
Richard Breheny,Napoleon Katsos 和 John Williams的研究为含有等级词项的单句设定了两种具体语境(支持等级含义的语境和不支持等级含义的语境),结果显示受试者对“some of the Fs”的反应时间在支持等级含义的语境中要显著长于在不支持等级含义的语境中。这说明受试者只有在支持等级含义的语境中才会推理“some”的等级含义,所以反应时间长。在不支持等级含义的语境中,受试者不会反应“some”的等级含义,所以时间短。实验二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语境驱动论。这一实验启发教师在教授等级含义时不可一概而论,应区分不同语境具体探究相同词项的不同等级会话含义。例如:
Some of our neighbors have cars.
a) Some but not all of our neighbors have cars.(等级含义)
b) Some, in fact all of our neighbors have cars.(逻辑含义)
c) The speaker doesn’t know whether all of his/her neighbors have cars.(特殊会话含义)
教师不仅要提供具体等级语境让学生理解到“some”的等级含义,还应该提供非等级含义语境使学生同时领悟到“some”的逻辑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
国外有教育者认为,语用教学的对象应该是目的语语言水平高的学生,对语言水平低下的学生实施语用教学是杯水车薪的。所以他们建议,语用教学应该是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词汇量、句法知识和语法以后再逐步实行。但是,Wildner-Bassett在研究中发现,语用教学对于初学者来说,也是有效的。语言实践与语言学习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换句话说,语言表达和理解的需要增强了学习语言使用规则(即语用)的动机。以上句为例,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如果他们能知晓如此简单地词项“some”都可以表达三种会话含义的话,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字典中的单词活起来;另一方面确实可以强化学生对于词汇学习的好奇心以及提升学生的语言使用能力。语言学习并不在于学生可以使用多么艰深的词汇和句法,而是利用简单的词巧妙自如地表达合适的意思。
Huang和 Snedeker运用眼动记录仪 (visualworld eye-tracking paradigm)结合图片来为受试者建立一个不常见的低频语境并记录受试者眼球运动轨迹及在目标图片上(target)的停留时间。研究者重点观察记录受试者在听到“some/all/two/three of the soc-”处眼球的停留位置及时间。如果受试者优先默认了“some”的等级含义,那么在听到“some of the soc-”时就如同听到“all/two/three of the soc-”时一样,即使没有听完全是“socks” 还是“soccer balls”眼球都会迅速定位在目标图片上。如果等级含义不是默认含义,那么此时受试者的眼球将徘徊在右面有两个女生的图片之间,即眼球停留在这两张图片上的时间应该没有显著差异。直到听完全句,听到“socks”或者“soccer balls”时,眼球才会定位在目标图片上。
实验结果显示受试者在听到“some of the soc-”时不能迅速将眼球定位在目标图片上,其定位所需要的时间显著长于其他词项(two,three,all)。研究者就此认为“some”的等级含义不是默认的,而是需要人们额外付出认知努力才能推理出来的。这说明在低频语境或低频心理语境中,等级含义的认知更为费力,趋近于特殊会话含义的推导。在高频心理语境下,等级含义或许可以独立于现实语境,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默认属性;但在低频心理语境中,其认知模式与特殊会话含义的语用推导模式相同。在高频心理语境下,如“Some elephants have trunks.”还存在超过50%的受试者能推导出等级含义的存在;在低频心理语境下,绝大多数受试者都不能反应出词项的等级含义。所以在低频语境中更需要英语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并推导词项的等级含义。如:
A:Is there any evidence against them?
B:Some of their identity documents are forgeries.
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推导:有一些,并不用全部的身份证件是伪造的就足以成为对他们不利的证据。日本教育家Kubota针对教授“会话含义”开展的教学实验发现目的语的“会话含义”是可教的,但反映出的问题是学生们只能够理解实验材料上所表达的“会话含义”,但讲授之外的、对没有接触过的材料中所表达的“言外之义”就不能推导出来。所以要提高外语学生的语用能力,我们更需要教他们语用,并且要持续不断,循序渐进,课堂教学中,对于语言使用的情景进行充分的描述,尽可能真实地模拟外语使用效果,让学生自觉地对语用学理论有直观的理解,激发其对语用知识的学习热情。
四、语用教学方法
在课堂上教语用是对英语教学的尝试和创新。在此,我们具体分析北美Bardovi-Harlig&Mahan-Taylor语用教学实验改革的情况,对语用教学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方法、步骤进行深入探讨。
在课堂上,语用教学方法可以分为“隐性教学法”(implicit teaching) 和 “显性教学法”(explicit teaching)两种形式。“隐性教学法”并不直接地讲授语用学理论,而是通过在学习材料的选用中,使用具有典型语用知识的内容,让学生对语料的理解突破字面含义表达的内容,准确地找到语言交流的真实含义。同时启发他们有意识地对语言表达中各种语用模式进行总结、归纳和吸收。“显性教学法”是通过教师系统、细致地讲述语用学理论、目的语语用模式,使学生掌握具体的语用技巧,同时辅以大量的有针对性的练习,对语言进行模拟真实场景的演练,从不同的角度体现语用过程中语言含义的变化。
从课堂教学的基本形式和内容入手体现语用教学:
(1)利用真实的目的语语料充当教材。语用教学首先要强调教材中语料的真实性。因为语言教学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的教学目的常常关注于语言的模仿,语法结构,或者修辞问题。长期的训练可以造就语言形式和语法直觉,但是这些机械训练,对于语用直觉的培养几乎没有作用。仅仅依靠教师对设定资料中某些细节上的语用直觉来教学生是不稳定、不科学的。所以,在选择外语语用教材时,就更应选用有真实使用环境的原文语料。例如:外语新闻广播、电影原声、原版书籍、以及国外公开课等。
(2)利用双语活动的方式激发学生的语用意识。语用课堂的教学语言可以使用双语,这样可以使学生自觉体会母语和目的语具体语用规则和方法并且进行对比,利用母语校正对于外语词汇的歧义理解,或明确等级含义的理解。比如教师可以利用汉语和英语的日常信件进行对比教学。
(3)对语言材料的理解和表达,由学生自己在活动中进行。与明确的语法规则相比较,在课堂教学中完成教语用的任务要繁锁得多。他需要更多的情景对照,更多的练习分析。教师不能仅凭直觉来教授零星的语用知识。这就是说,在组织学生进行双语活动之前,教师要系统地“教”给学生语用知识。学生依靠自己的理解,通过活动实践自主地运用外语设计活动,完成活动,并从中体会真实环境下的语用含义,将语用知识转化为语用能力。
本文讨论了等级含义实验研究对语用教学的启示并由此总结出的语用教学的基本方法。由于交际功能是语言的主要功能,目前我国的外语教学改革也越来越重视对学生英语实际使用能力的培养。要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必须要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在外语教学中,教学生有效地“理解”和“使用”外语,真正形成有效的交际能力。教语用是目前国内外广泛推崇的交际教学法之一。我们借鉴国外 “教语用”的课堂实践,再通过实际工作中大量的教学试验,不断摸索各种教学活动,分析和比对各种活动对语言能力形成的影响作用。此外,要系统地教好语用,我们还需要一套取自英语真实语料的甄选编撰的教材。希望我国的外语教育者能共同来完成繁重的语料收集工作和语用教材编纂的工作,共同探讨外语语用教学新模式。
[1]蔡翠云.从语用失误谈学生语用意识的培养[J].高教论坛,2003,(2): 93-95.
[2]项成东.等级含义的语用研究综述[J].当代语言学,2006,(4): 334-344.
[3]鲍曼.论荷恩等级的不适用性[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7): 125-127.
[4]Bach, K.Conversational Impliciture [J].Mind and Language,1994,(9): 124-62.
[5]Noveck, I.A., & Posada, A.Characterizing the Time Course of An Implicature[J].Brain and Language, 2003,(85): 203-210.
[6]Bott, L.and Noveck, I. A. Some Utterances Are Underinformative: The Onset and Time Course of Scalar Inferences[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4,(51): 437-457.
[7]Trosborg, A.Apology Strategies in Natives/Nonnatives [J].Journal of Pragmatics, 1987,(11): 147-167.
[8]Breheny, R.Napoleon, K.and John, W.Are Generalized Implicatures Generated by Default? An On-lin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enerating Pragmatic Inferences [J].Cognition,2005,(100): 434- 463.
[9]Wildner-Bassett, M.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and Proficiency:“Polite” Noises for Cultural Appropriateness [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4,(32): 3-17.
[10]Huang, Y.T., & Snedeker, J.Online Interpretation of Scalar Quantifiers: Insight into the Semantics -pragmatics Interface [J].Cognitive Psychology, 2009,(58): 376-415.
[11]Kubota, M..Teachabilit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o JapaneseEFLLearners[J].IRLTBulletin, Tokyo: TheInstituteforResearch in Language Teaching.1995,(9): 35-67.
[12]Bardovi-Harlig.K.& R.Mahan-Taylor.Teaching Pragmatics[EB /OL].http: //exchanges.state.gov /education /engteaching/pragmatics.htm 2003.
A Study o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Scalar Implicature and its Elicitation to Pragmatics Teaching
LI Ran1,LI Yan2
(1.2.Tianj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4)
As a fresh idea regarding TEFL/TESL methodology, “Pragmatic Teaching” is emerging developing worldwide.Firstl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studies of scalar implicature, and then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calar processing study on “Pragmatic Teaching”.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conduct Pragmatic Teaching in class to train the students’ pragmatic ability.Two types (“implicit teaching” and “explicit teaching”) are introduced in terms of mode,content and procedures to explain that pragmatic teaching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help enhance students’ communicative ability.
pragmatic competence;classroom instruction;scalar implicature;cognitive mechanism
H319.3
A
2095-5537(2013)04-00048-04
2013-10-23
[课题项目]本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C740059)的研究成果。
1.李然(1981—),女,汉族,天津市人,天津农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用学教学与科研。
2.李焱(1971—),女,汉族,天津市人,天津农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责任编辑:周晓华 张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