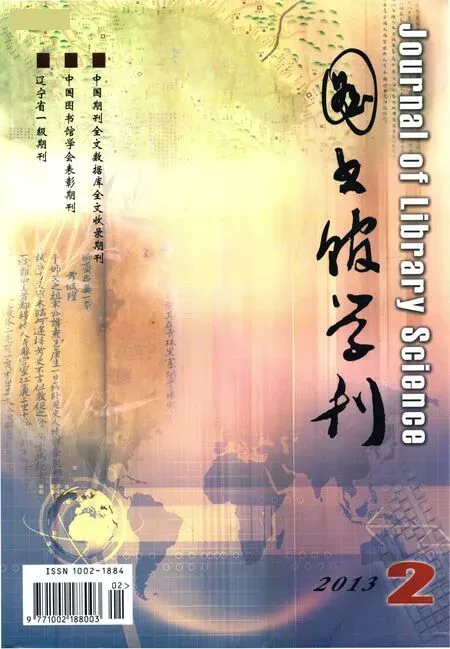《隋书·经籍志》编撰思想探源*
周文博 傅荣贤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周文博 男,1987年生,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目录学及文献学。
傅荣贤 男,1966年生。在读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目录学及文献学。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我国现存的第二部官修史志目录。它“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上承前代目录的优良传统,下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之先河,并一直为后代目录奉为圭臬,在中国目录学史上享有承上启下的崇高地位。而它所运用的分类、著录方法也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一直影响着唐代及其以后的官私修目录,对后世目录增补、补撰方法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1]。从这一角度来说,《隋志》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研究价值极具代表性。对《隋志》编撰思想进行分析,不但有助于探明其成书的内在规律,也能为推究中国目录学发展的思想脉络提供借鉴。
1 教化之具,尊经尚儒
《隋志·总序》第一段,即从“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至“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重点都在讲典籍的功能。根据对其的理解,可以得出典籍的功能主要是政治教化作用,那么作为对典籍进行梳理的史志目录,《隋志》自然也担当着重视人文教育传统和道德教化、重视社会有序与和谐的“为治之具”[2]的角色。而“经”作为“阐圣学,明王道”的“文之源也”①,在《隋志》中的重要地位更是不言而喻,除了将其列为四部之首外,《隋志》的尊经思想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 统一经典,维护“经”的正统权威地位
自孔子及七十弟子以降,不仅六经“典文遗弃”,内容理解上也是“各为异说”、“多立小数”,尤其经历前朝政权的频繁更迭后,作为初唐统治思想和指导思想的“经学”更是处在南北对立和学派纷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经学和经学思想进行统一成为《隋志》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在同类文献的排列上,《隋志》大致在《易》、《书》、《礼》等各个二级类目中沿袭着“传”、“注”、“音”、“论”、“义”、“疏”的排列顺序,这本身就以编撰方的权威地位,按照文献题材和内容的重要性大小,人为地为“经”的排列规定了一套森然的逻辑秩序,以反映统治者意志。其次,在著录书目的内容上,“音”都占有一席之地,如“《周易音》一卷 东晋太子前率徐邈撰”、“《今文尚书音》一卷 秘书学士顾彪撰”等,这主要是因为南北经读音声差异较大,作者希望以规范音韵来实现南北经学的统一。最后,在著录书目著者的选择上,《隋志》多选取了前朝或当朝著名的经学家来凸显其所收书目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如梁代皇侃、褚仲都,北周沈重,南陈周弘正、张讥,隋代刘炫及当朝的孔安国、马融、郑玄、王肃等。这些做法都是在统一经典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并维护了经的权威地位。
1.2 还原“经”的本质,重视教化功能
引述《汉志·六艺略》序言的观点叙圣人抒作之意,《隋志》作者认为经学的实质在于“知道”和“畜德”②。而当其面对“虚诵问答”、“不能究其宗旨”的后(经)学风尚时,必力图还原“经”的原义,维护其“阐圣学,明王道”的教化功能。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通过著录、销毁之别确定文献价值高低[2]。《隋志》作者认为,经学自“后汉好图谶”、“晋世重玄言”、至“近代”更“无复师资之法”,“专以浮华相尚”②,因此对那些“文义浅俗、无益教理”的文献“删去之”,那么保留下来的文献实质上就类似于官方规定的导读书目,以求达到其“弘道设教”之功效。其次,通过类序安排体现文献教化意义的大小。如在经部类目的排序中,“六经”被认为是“大道”故排列在前,单从每个类目看,“义”、“疏”类文献均排列靠后,可见作者对经学体例上以“注疏”取代传记、以解字说经为务的做法颇有质疑②。最后,通过撰写“序”来对文献价值进行评价。由于《隋志》不似《四库全书总目》书名下有题解,因此对于文献价值的判断要通过“序”来说明。如在易类小序中,《隋志》作者认为《归藏》一书“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在图纬类小序中,认为这类文献“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这些都表明了《隋志》在编撰过程中力求还原“经”的本质,发挥其教化功能。
除经部之外,《隋志》其他部类设置上也大都按上述原则维护其正统地位和教化功能,如史部列“正史”以突出正统性,并列“霸史”与之做区别;子部总序中认为儒家属“圣人之教”,而小说则属“小道”等。对于其他部类本文不做深解,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尊经重教的编撰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方技”类文献的地位,如《鲁史欹器图》、《器准图》等技艺类文献在著录时不得不附类于其他部类,而由此产生的“重道轻术”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
2 离其疏远,合其近密
“离其疏远,合其近密”是《隋志》主要的分类方法,意为“如果书与书之间在内容上毫不相干,差别较大较远,这样就把它们分离开来,各入其类。而内容上很接近、很密切的就把它们合在一起,归为一类”[3]。由于《隋志》的著录是分类著录,因此笔者认为也可将其作为编撰思想之一进行探讨。对《隋志》“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研究可从“存书”和“亡书”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傅荣贤先生在注释②一书中对“亡书”的著录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笔者仅参考其范式对“存书”做如下两方面的探讨。
2.1 根据文献内容“离其疏远,合其近密”
如果说西方的图书分类采用“归纳”的逻辑方法,那么《隋志》在书目分类思想上则内含“演绎”的逻辑思维,预先设置“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后根据文献内容按分类主体的主观判断“以义归类”。因此,所谓“书类不全,勉强附类”[4]的现象是存在的。例如:按照今天的分类标准看,《易》、《论语》、《孝经》属于哲学类;《尚书》、《春秋》、《礼》属于历史类;《诗经》属于文学类,而这些经典却因为“教化”功能被统一划为“经”类。其次,在小类设置上,“尔雅”类文献属训诂类却因其教化意义附丽于“论语”后;“奏议”类文献附丽于“刑法”类;“怪志”类文献紧随“佛”“道”类附入“杂传”类,“产乳”类文献紧随“婚嫁”类入“五行”类;“棋”类文献却因其对弈性质著于“兵法”类。最后从单本文献看,《竹谱》、《钱谱》、《钱图》被附入“以纪世族继序”的“谱系”类;《相马经》、《相贝经》等跟随《相书》入“五行”类;《夏小正》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事历书[5],却因原为《大戴礼记》第四十七篇而随其附入经部“礼”类。可见,这种针对于文献内容“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分类标准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都贯穿于《隋志》始终。
2.2 根据作者关系“离其疏远,合其近密”
《隋志》的“离其疏远,合其近密”并不只针对所著录文献的内容而定,在同类文献作者的排列关系上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例如:“《礼记讲疏》九十九卷 皇侃撰”和 “《礼记义疏》四十八卷 皇侃撰”合著,是同类文献中同一作者所撰书目“合其近密”;“《尚书》十一卷马融注”和“《尚书》九卷郑玄注”,将马融和郑玄合著是因为郑玄师从马融;“《周易》十卷晋散骑常侍干宝注”和“《周易》三卷晋骠骑将军王暠注,残缺。梁有十卷”合著,这是根据两位著者官阶相近。除此之外,这种“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作者合著原则还涉及学派流别,如“《礼记义疏》四十八卷皇侃撰”和“《礼记义疏》四十卷沈重撰”,其中皇侃为当时经学流派中“南学”的代表人物,沈重为“北学”代表人物;“《春秋汉议》十三卷何休撰”和“《驳何氏汉议》二卷郑玄撰。梁有《汉议驳》二卷,服虔撰,亡”,何休为今文经学代表人物,而郑玄则为古文经学代表人物;“《丧服经传》一卷郑玄注”和“《丧服经传》一卷王肃注”,其中郑玄是“郑学”的开创者,王肃则创立“王学”一派。可见,所谓作者关系的“离其疏远,合其近密”也是多重所指。
如果说西方的图书分类思想是科学而机械的,那么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内在逻辑则是人文而写意的。以《隋志》为例,它的分类并不拘泥于对文献外部特征的描述,也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它更注重根据文献内容或作者亲疏关系而进行“类”与“类”在“语境”上的划分,以达到“以形写神”③的艺术效果。按照今天的评判标准,这种分类方法虽然不是十分科学,但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却是十分合理,而这种“合理性”的思想精髓对于本土化目录学的构建是大有裨益的。
3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如果说“尊经重教”是《隋志》主要的编撰思想,“离其疏远,合其近密”是《隋志》主要的编撰方法,那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是《隋志》在编撰过程中想极力体现的价值所在,除“序”阐明学术源流之外,这种价值还主要通过“小注”表现出来。《隋志》所著录的每条书目信息后基本都著有小注,“约文绪义”、“各列本条之下”,以对文献作者、内容等诸多方面进行解释说明。笔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效。
3.1 说明文献来历,揭示学术渊源
《隋志》小注注重记叙成书过程,以便读者了解文献蓝本,知晓学术渊源。如“《春秋公羊传问答》五卷,荀爽问,魏安平太守徐钦答”,据此可知成书的零次文献来源;再如,“《史要》十卷 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可知《史要》是根据《史记》删减得来;再如,地理类《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注:“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见存别部行者,唯十二家,今列之于上。”可知《地记》乃是以“陆澄之书”为蓝本。《隋志》的这种著录方式起到了“(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古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通志·校雠略》)的效果,较好地发挥了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3.2 著录亡佚之书,揭示学术流变
《隋志》不仅著录隋代“今存见考”之书,还通过附注的方式对前朝残缺、亡佚之本进行梳理,这也使《隋志》区别于其他目录,更使得其小注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如“《周易》二卷魏文侯师卜子夏传,残缺。梁六卷”,可知今《周易》残本在梁代原有六卷;再如子部《张公杂记》一卷注:“张华撰。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有《杂记》十卷,何氏撰,亡。”据此可知现存仅1卷的《张公杂记》在梁代原有5卷,内容与《博物志》相似,而已亡佚的何氏《杂记》也与二者旨趣相同。《隋志》这种“见存”和“亡佚”之书相互呼应的著录方式有助于相对完整地揭示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发展状况、渊源演变等信息,对古籍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
3.3 指出文献真伪,别白学术源流
文献与学术源流的关系最为密切,若不能辨明文献的成书年代、作者是否为假托、内容是否为伪造等情况,学术源流就会混淆,学术的发展历史也会错乱[6]。《隋志》小注着力甄别文献真伪,以使“学术透彻,源流明晰”[7]。如“《古文孝经》一卷孔安国传。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古文孝经》梁末已亡佚,因此著者对“见存”之本提出异议;又如“《广成子》十三卷商洛公撰。张太衡注,疑近人作”,可知著者对《广成子》作者提出质疑;再如,医方类《疗马方》一卷,注“梁有《伯乐养马经》一卷,疑与此同”,表明著者对《疗马方》的内容和版本有所怀疑。《隋志》小注的这种标明文献真伪的著录方式不但能对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效产生积极影响,还能让读者在参考书目信息时“取而明辨之”,完成“读书第一义”④。
除小注之外,《隋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互著”的著录方法上,即“对内容上跨学科通两义的书目在两个类目中相互著录”[8]。如《春秋土地名》既见“春秋类”又见“地理类”、《战国春秋》既见“古史类”又见“霸史类”、《周易玄名》既见“易家类”又见于“五行类”等,这种著录方式可以减少文献著录的纰漏,完备著述源流。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在《〈隋书·经籍志〉的错讹及其改订复原法》一文中将这种互见著录的方式判定为“重复著录”所产生的“矛盾”现象,有失公允。首先这种著录方法在《汉志》中已然兴起,《隋志》效法《汉志》沿袭其著录方法在情理之中;其次,所列“重复”文献按今天的著录标准来看均可用“互著”思想来解释,并无巧合之嫌。因此笔者认为,《隋志》的“互著”并非“重复著录”,而是其为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效而进行的科学著录。
众所周知,文献是文化的载体,目录作为梳理、检索文献的工具,在追寻文化发展脉络的同时,也能动地整理和规范着文化的走向。《隋志》以其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诸多分类、著录的创见之功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探明《隋志》的编撰思想无论对研究中国目录学思想史还是中国古典文化发展史都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据此,笔者所论3方面内容可归纳如下:《隋志》的编撰思想以“尊经尚儒”为逻辑主线,以“为治之具”为限定目标,采取“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分类著录方式,力求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价值。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对《隋志》及其他中国古典目录的相关研究应限定在特定的文化范畴之内,多关注并挖掘其“合理性”而非“科学性”,这样一来,相信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所带给我们的启迪将是构建“中国图书馆学”(梁启超语)的巨大财富。此亦为笔者立意所在[2]。
注 释:
①乾隆皇帝曾将经史子集的关系比喻为:“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
②参见傅荣贤手稿《史志目录》,该文是来新夏主编的《目录学读本》第五章,该书待版于上海交大出版社。
③“以形写神”这一论点最早出于东晋画家顾恺之,是指画家在反映客观现实时,不仅应追求外在形象的逼真,还应追求内在精神本质的酷似。笔者认为这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编撰思想异曲同工。
④清代辨伪名家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有云:“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
[1]张冬云.《隋书·经籍志》对目录学与学术研究之贡献[J].天中学刊,2000(1):66-67.
[2]蒋永福.尊经重教以成”为治之具”——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的思想宗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2):1-2.
[3] 子厚.什么叫”离其疏远,合其近密”[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3(2):12.
[4]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百度百科 [EB/OL].[2012-11-21].http://baike.baidu.com/view/39626.htm.
[6] 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17-318.
[7] 傅荣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诂[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53-54.
[8]子厚.“互著”与“别裁”[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3(4):26.
——以谭瑟勒的《目录学概论》课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