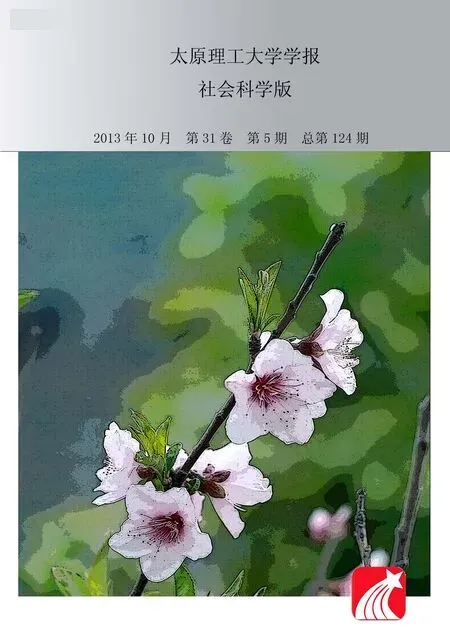“沉郁顿挫”与杜诗风格关系之批判性再认识
张 杰
(北京语言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083)
自古诗人创作风格,或出于后人总结评介,或出于诗人自身体察。杜诗可堪中华诗史中最重要的象征符号之一,古来议论甚多,因其于《进〈雕赋〉表》中自言“沉郁顿挫”,后世论杜诸家多奉之为不刊之论。今日学者凡论“沉郁顿挫”,定会先入为主将其定义为杜诗的整体风格,然后再去讨论其中内涵。乔象钟、陈铁民主编《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是集中概括了他诗歌的主要特征的。具体地说,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涵义。”[1]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杜诗的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2]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杜甫诗歌的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家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3]王辉斌《杜甫“沉郁顿挫”辨识》:“从接受史与演变史的角度讲,沉郁顿挫作为对杜诗风格的总体概括,乃是既确切而又恰如其分的。”[4]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对于杜甫诗歌风格的讨论,众家阐述愈多,而真相似乎愈加模糊。一个小小的“沉郁顿挫”负载了过多的诗学内涵,还原其本身诗学指向会有助于今人更加全面的认识杜甫的诗歌创作风格。
一、“沉郁顿挫”之缘起
说起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由来,就不能不提《进〈雕赋〉表》。诸多论文中多截取以下一段文字:
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也,约千有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派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为臣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呼?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把泥途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5]
诸论家见“诗笔”二字,便将老杜心意归入律诗创作。然而详查此文,疑点诸多,其一,杜甫所言“今贾马之徒,得派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贾马”者,贾逵、马融也,此二人为汉之经学大儒。其成名之作,亦在传经注经。此时连珠体方兴未艾,文人五七言之诗作初登诗坛,后世声律诗篇更无从谈起。杜甫若在此有意显示诗才,为何不以同代“建安”、“太康”为例。其次,在此段文字之前,《进〈雕赋〉表》尚有前文: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於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视於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於今而师之。[5]
杜甫在文中自述家世,由魏晋以降,士人求取功名之时,喜言自家往昔显贵故事,故对于前代先人事迹的选取,亦可以透射出士人自身的价值取向。杜甫在文中用“奉儒守官”来形象概括自己的家门传统,在此传统的大前提下,杜甫列举出三位具有典型意义的先辈族人:杜恕、杜预和杜审言。其中杜恕为曹魏时期杰出的儒臣,著《体论》八篇,又著《兴性论》一篇。《隋书经籍志》又有《笃论》四卷,亦称恕撰。《魏略》:“恕在弘农,宽和有惠爱。”[6]《三国志·杜恕传》:“恕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恕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终致此败”、“恕屡陈时政,经论治体,盖有可观焉”。[6]从以上文献可知,杜恕其人于当时并不以诗赋得名,其为人称道之处或为忠厚宽爱之品行,或为治国理政之才能,其文也多为“经论治体”。杜预其人,以平吴注律之功成为西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其同时还兼具经学家的身份,杜预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收入《十三经注疏》中。《晋书》有赞曰:“昔之誓旅,怀经罕素。元凯文场,称为武库。”[7]可见其文武之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彪炳史册的能臣,也恰恰没能留下任何值得称道的诗赋作品。文中最后提到的杜审言,往往会被研究者拿来作为杜甫诗歌创作的源头。不可否认,在魏晋隋唐之际,家数传统是文学继承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在同一文学世家内,特定文体也会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在此文中,杜甫充分肯定了审言为官修文的业绩,却对其诗歌创作只字未提。而唐人对于杜审言文学成就的评价也更集中于文章层面,故将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一起合称“文章四友”。由此可见,杜甫并不是要去集成以上三位宗族先辈的诗歌创作传统,而是把他们作为自己“奉儒守官”的效法榜样。在《进〈雕赋〉表》的结尾处,杜甫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赋,实望以此达於圣聪耳。”[5]子美将自己比为鸷鸟,取三闾大夫“鸷鸟之不群兮”之意,愿一己之宏愿可上达天听,早解释褐之愁。综上可知,杜甫全文所言皆为抒泻心中政治抱负,“沉郁顿挫”不可以简单等同于杜甫诗歌的总体风格,杜甫在文中认为自己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是针对前文所列前辈学人而言的。在老杜眼中,传承圣人经典学说才是自己人生正途,只是因为自己才德浅薄无法达到前辈的水准,但是自己起码可以做到的是像“扬雄、枚皋”一样“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西京杂记》:“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8]《汉书·枚皋传》曾载:“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9]从以上两段文献不难看出,枚皋的创作风格是以速度著称,但同时也存在“时有累句”的弊病,这也直接导致了枚皋的创作只能局限于“飞书驰檄”,“临机草诏”。而真正高质量文学作品的创作仍需依靠司马相如、扬雄一类的深思型作家。有关扬雄“沉郁”的说法,最早见于刘歆的《与扬雄书从取方言》:“非子云澹雅之才,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10]诸家对此文献皆不查之下用于证明子美诗风,然刘歆所言扬雄“沉郁之思”非常明显的是指向其《方言》一书的写作。扬雄虽为汉代辞赋名家,然《方言》一书却实与诗赋创作没有实质性的关系,《方言》一书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朝廷遣“輶轩使者”至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然随秦末战火,材料至扬雄时多已丧失。扬雄在前代学人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经过27年的艰苦努力终成此书。杜甫以扬雄为例,并取“沉郁”之语,显然是要学习扬雄朴实深厚的治学精神,而不简单是扬雄诗赋创作。杜甫在这段文字中也指出“臣之述作”是“至于沉郁顿挫”,很显然“述作”所辖的范围绝不仅仅是诗歌,而是一切可以承载儒家精神的文体。
从以上的材料中不难看出,杜甫并没有在《进〈雕赋〉表》中强调自己的诗风就是“沉郁顿挫”,而是把“沉郁顿挫”看成一种用来达成“奉儒守官”目的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过程应该具有先后两个阶段,其中“沉郁”更多的指向思考的过程,而“顿挫”则是思考结果在文本中的反映。
对于“沉郁顿挫”应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论述,前人其实已经有过类似的认识,只是模糊未清而已。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
不读全唐诗,不见盛唐之妙。不遍读盛唐诸家,不见李、杜之妙。太白胸怀高旷,有置身云汉、糠秕六合意,不屑屑为体物之言,其言如风卷云舒,无可踪迹。子美思深力大,善于随事体察,其言如水归墟,靡坎不盈。两公之才,非惟不能兼,实亦不可兼也。杜自称“沉郁顿挫”,谓李“飞扬跋扈”,二语最善形容。后复称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推许至矣。[11]
在此文中,贺裳将李杜二人之诗比而言之。笔者认为二人的诗才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不可兼得。如果按照文章逻辑结构来看,“沉郁顿挫”相对应的是这样一组论述“子美思深力大,善于随事体察,其言如水归墟,靡坎不盈”。很明显,这句对于“沉郁顿挫”的解释分为上下两个层面。首先,贺裳指出杜甫的思考模式是“思深力大,善于随事体察”。其次,在这种思考模式下的写作结果是“其言如水归墟,靡坎不盈”。贺裳对于“沉郁顿挫”的把握还是相当到位的。贺裳将“沉郁”定义为思维的形成过程并无太多创新之处,但是过于“顿挫”的书写,“如水归墟,靡坎不盈”的比喻却极为的传神。苏轼曾将自己的文风比作泉涌,不择地而出,因山川曲折,而随物赋形。而贺裳在这里也用水来比拟杜甫的诗风,只不过和苏轼强调其流动性不同的是,杜甫诗风中更加突出了水流的兼容性。这与“沉郁”的文思是相称的,“顿挫”的内涵更应指向真实的客观世界。子美之诗有“诗史”之称,乃是在称赞其以时事入诗,并有“不虚美、不隐恶”之风。杜甫在其种种文体中为我们展现的就是一个充满艰涩与幻灭的真实世界,“顿挫”就是这个世界的最真实定义。
二、“沉郁顿挫”之历史性变迁
既然杜甫自己在提出“沉郁顿挫”时并没有把这一概念强加为自己的诗风,那么后世的文论家们又是出于怎么样的一种思考要把“沉郁顿挫”认定为杜甫的诗风了?目前所见,最早把“沉郁顿挫”与老杜诗风联系在一起的是宋人葛立方的《韵语阳秋》,该书卷八有云:
老杜高自称许,有乃祖之风,上书明皇云“臣之述作,沉郁顿挫,扬雄枚皋可企及也”,《壮游诗》则自比于崔魏班扬,又云“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赠韦左丞》则曰“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甫以诗雄于世,自比诸人,诚未为过。至窃比稷与契则过矣。史称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岂自比稷契而然邪。至云“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其忠荩亦可嘉矣[12]。
葛立方援引《进〈雕赋〉表》《壮游诗》《赠韦左丞》中的相关材料,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甫以诗雄于世,自比诸人,诚未为过”。其中存在两点问题:其一,这三段材料中提到的诸位人物,并不都是以诗歌著称,《进〈雕赋〉表》所列诸儒不再重复,而其中“崔魏”二人,崔尚为武则天久视二年(701)进士,魏启心为中宗神龙三年(707)才膺管乐科及第,二人皆以异才登第,而不以诗赋闻达。文学并不等同于诗歌,所以葛立方实际上是使用世人已经公认的“杜甫”为“诗雄”的事实来“反推”自己的论述过程。其二,葛立方对于杜甫的评价在于对前人的说法的反动。在他看来,杜甫虽然“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而其忠君悯民的精神却是非常可贵的。此时,葛立方还没有断然把老杜诗风和“沉郁顿挫”等同起来。
通过对这段材料的批判和肯定,不难看出无论是自我定义还是后世评价,杜甫都首先是一个儒臣,而非诗人,“沉郁顿挫”也绝不仅仅指向的是诗歌。
在元明两代,“沉郁顿挫”不再是杜甫的专属。方回《瀛奎律髓》:“刘蕴灵(刘仓)大中八年进士,其诗乃尚有大历以前风味。所以高于许浑者,无他,浑太工而贪对偶,刘却自然顿挫耳。”[13]脱脱《金史·文苑传》:“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14]胡应麟《诗薮·杂编》:“赵秉文,字周臣,磁州人。幼颖悟,自壮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所著《滏水集》三十卷。七言长歌笔势放纵,近体壮丽,小诗精绝。五言沉郁顿挫,字画遒劲。”[15]文史论家似乎更加倾向于把“沉郁顿挫”用来定义刘仓和赵秉文的诗风。化用前人妙语来描述诗风的做法本无可指摘。孔子妙引“思无邪”,同音转义,开启了最早的儒家文学批评,如黄庭坚“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本出佛道内典。
如同汉字“六书”之“假借”一般,某一文学定义在提出之时拥有固定的指称范围,但是在经过不同叙述者的使用后,其内涵往往会发生变化,也就是所谓“本无其事,依声托事”。“沉郁顿挫”在元明清三代就是被缩小了定义范围后,用来专指诗歌风格。
清人开始固定并高频地使用“沉郁顿挫”来定义杜甫诗风。田雯《古欢堂杂著》:“子美为诗学大成,沉郁顿挫,七古之能事毕矣。《洗兵马》一篇,句云‘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犹是初唐气格。王、李、高、岑诸家各有境地。开元、大历之间,观止矣。”[11]贺贻孙《诗筏》:“子美诗中沉郁顿挫,皆出于屈、宋,而助以汉、魏、六朝诗赋之波澜。”[11]翁方纲《石洲诗话》:“杜五律虽沉郁顿挫,然此外尚有太白一种暨盛唐诸公在。至七律则雄辟万古,前后无能步趋者,允为此体中独立之一人。”[11]袁枚《随园诗话》:“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16]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汉槎(吴兆騫)阅历,倘以老杜之沉郁顿挫出之,必更有高一格者。”[17]方东树《昭昧詹言》:“后山之祖子美,不识其混茫飞动,沉郁顿挫,而溺其钝涩迂拙以为高。”[18]“杜公所以冠绝古今诸家,只是沉郁顿挫,奇横恣肆,起结承转,曲折变化,穷极笔势,迥不由人。山谷专于此苦用心。”[18]综合以上论述,清人对于沉郁顿挫的认识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关于“沉郁顿挫”应该指向的是子美的何种诗体。田雯和翁方纲各执一词,前者认为“沉郁顿挫”非七古之风莫属,后者认为老杜七律能当此嘉誉。第二,“沉郁顿挫”的成因。贺贻孙认为“沉郁顿挫”是杜甫诗歌对于屈宋及汉魏六朝诗风的继承,而袁枚则把“沉郁顿挫”当成杜甫“芬芳悱恻”诗情之外化。第三,“沉郁顿挫”被作为一种杜甫代表性的诗歌创作手法。方东树认为“沉郁顿挫”是与“混茫飞动、奇横恣肆、起结承转、曲折变化、穷极笔势、迥不由人”相并列的众多杜诗风格中的一个元素。沈德潜则把“沉郁顿挫”符号化,将其与杜诗风格直接划了等号。他认为吴兆騫既然拥有和杜甫类似的人生境遇,如果采用“沉郁顿挫”作为自己的诗歌创作风格,“必更有高一格者”,但是清代仍有稍显例外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如杜少陵之诗,包罗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19]“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19]“词至美成,乃有大宗。然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19]陈廷焯诗法论词,以周邦彦为词中子美。其言“沉郁”兼取子美深思怨情之意,“顿挫”才以杜诗笔断意连,若隐若见之法。情法统一,恰恰暗合子美之意。
三、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清人完成了对“沉郁顿挫”概念理论的构架,从此时起“沉郁顿挫”开始成为了杜甫个人的固定标签。
环顾“沉郁顿挫”概念形成的过程,不难看出,今日的“沉郁顿挫”与其说是杜甫对其诗歌的自评,不如说是后人对杜诗经年接受而形成的积淀性观念,其不可以作为杜甫诗歌风格的总体概括。然而将“沉郁顿挫”视为杜甫整体的治学作文理念还是比较恰当的,又因为诗歌作为杜甫客观上最为重要的文学形式,所以必然也会受到杜甫整体文学观念的投影,但同时也不至于简单狭隘到只有一个“沉郁顿挫”。对于“沉郁顿挫”的认识是一个无限变化中的连续统,其有开始时较为明确的界定范围,然而随着文学接受的历史性发生,连续统开始发生“变异”和“迁移”,今人对于这个概念的论述也从必然变成其中的一个节点,所以武断地进行概括性定义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从前文所引可以看出,清人谈“沉郁顿挫”,或言诗体,或言诗情,或以此喻彼,或讽评古体,却从不一概而论,这一点是值得今人学习的。
[1]乔象钟,陈铁民.中国文学通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515.
[2]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90.
[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19.
[4]王辉斌.杜诗“沉郁顿挫”辨识[J].杜甫研究学刊,2009(1):15.
[5]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2173.
[6]陈 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64:489,501.
[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25.
[8]葛 洪,成 林.西京杂记[M].程章灿,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19.
[9]班 固.汉书·枚皋传[M].颜师古,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689.
[10]严可均.全汉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349.
[11]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74,315,1382.
[12]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546.
[13]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15.
[14](元)脱 脱.金史·文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721.
[15]胡应麟.诗薮·杂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28.
[16]袁 枚.随园诗话[M].顾学颉,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80.
[17]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75:80.
[18]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31,379.
[19]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卷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