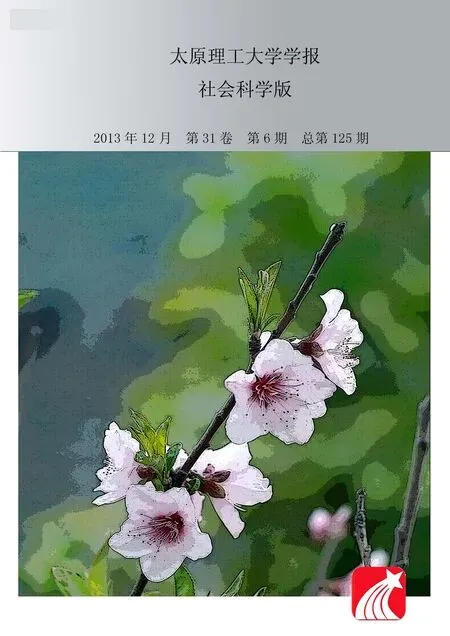论子孙“违犯教令”罪对亲属间人身侵害的启示
刘海波
(山西大学 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子孙“违犯教令”罪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长期存在,是因为它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适应。站在血缘关系的视角,透过历史的尘封,我们看到了各个朝代法律之间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我们在为中华法系的伟大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为近代法制改革无视传统法律文化而感到痛惜。
一、我国历史上的子孙“违犯教令”罪
(一)子孙“违犯教令”罪的沿革
《唐律疏义》疏云:“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犯……若教令违法,行即有愆,……不合有罪。”
清律规定,“凡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1]。对于不肖子孙,法律除了承认父母的惩戒权,可由父母自行责罚外,法律还给予父母以送惩权,请求地方政府代为执行。唐宋的处罚是徒刑二年,明清时则杖一百。至于违犯教令的范围是很宽泛的,只要父母提出控诉,法司无不照准。 这相当于我们现在刑事诉讼自诉案件中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这就把管束、控制子孙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尊长亲属。礼法将尊长亲属教育子孙的义务变成强制的权利,尊长亲属一旦感到难以控制子孙,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求助于礼法,靠道德教育解决不了的问题诉诸礼法便可迎刃而解了。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赋予了尊长亲属管教子孙的绝对权利,子孙从出生那天开始,在尊长怀抱中享受抚爱和温暖的同时,头上也戴上了纲常伦纪的“紧箍”,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尊长一念“违犯教令”的“紧箍咒”,他们就不得不俯首帖耳[1]。“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惩戒权是绝对的,子当“有顺无违”,这不是是非的问题,而是伦常的问题。在我国古代的等级伦理之下,子女受到父母责骂,和父母分辨讲理甚至顶撞不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家庭中,父母永远是正确的,“是非”毋宁说是系于身份的,我错了因为我是他的儿女;他的话和行为是对的,因为他是我的父亲[2]。
(二)子孙“违犯教令”罪的作用
儒家思想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注重“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伦理秩序,其实质是君权至上、家族至上、父权至上,社会关系是以垂直服从的身份等级为基础构筑起来的。在中国古代,没有个人观念,只有家族,家族是社会的组成单位。子孙“违犯教令”罪设立的作用实际上是加强父权的,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家族的首脑,家族中所有人都在他的管治之下。只有法律赋予家长强大的管治权力,家族才能稳定,继而社会才会稳定。另外,移孝可以作忠,判断一个人能否忠于君主,首先看他在家能否行孝悌。孔子曾说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这是法律规定子孙“违犯教令”罪的深层目的。
二、我国清末修律时子孙“违犯教令”罪的废除及反思
(一)子孙“违犯教令”罪的废除
1904年(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修订法律馆开馆,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莫瑞等充任修律大臣,主持修律。沈家本在《修正刑律草案》按语中称:“修订刑律所以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地步,刑律中有一、二条为外国人所不遵奉,即无收回裁判权之实,故所修刑律专以模仿外国为事。”[3]以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为代表的法理派认为,违犯教令出自家庭,从教育不从法律,可以设立感化院一类的机构加以教育。历来所控子孙“违犯教令”案件,大抵因游荡荒废、不务正业引起,先行的违警律与游荡不务正业已有明文,足资引用。礼教派则认为,天下刑律无不本于礼教。事物合于礼教,彼此相安无事;不合礼教,必生争端;争端一生,必然妨害治安。如果子孙触忤祖父母、父母,官府没有惩治之法,祖父母、父母没有呈送之所,大拂民情[3]。礼教派一再强调法律当与国家的风俗民情相吻合,方不至人心涣散,天下大乱;收回领事裁判权,毋须脱离中国风俗民情,(完全)效仿西法;中国风俗民情以礼教伦常为主,相沿数千年,久则难变,所以法律应该也必须全面照顾和考虑到中国国情。经过激烈的论战,最终以法理派的胜利而收场。1911年(宣统二年)1月25日,朝廷下令颁布《钦定大清刑律》(一般称为《大清新刑律》),子孙“违犯教令”罪没有被规定在《大清新刑律》中,被彻底废除了。
(二)对完全废除子孙“违犯教令”罪的反思
由于晚清修律是在列强环逼、内外交困的情势下开展的,修律的首要目的是要收回治外法权,即所谓“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4]。采用西法以补中法的变法路线是必然的选择。无论是清政府“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的变法谕令,还是沈家本“折冲樽俎,模范列强”的修律主张,或张之洞“采用西法”“所以为富强之谋”的变法路线,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西化的法制近代化路线。
当时的法律精英殚精竭虑改革法律,以期早日实现法律的近代化,其修律速度可谓是世界奇迹,就连当时日本的民法专家中岛玉吉都自叹不如。当时日本民法中的亲属、继承两篇已经修订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完成,相比之下,中国修订法律的速度之快,足以让世人惊叹。但是在这种修律速度的背后有着巨大的隐忧,那就是过度追求西化,而没有审慎地对待本国自己的法律传统,没有处理好传承法律传统与引进西法之间的关系。国民政府聘请的民法创制顾问法国人宝道就曾指出,中国的家族制度虽然弊端颇多,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是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废除该制度前,首先应该考虑建立起来的新制度能否适应将来的中国;旧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民众的生活习惯,舍旧谋新可能会引起民众的反抗;外国在修改家属法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民众对该制度的看法。废除旧法律,必须谨慎;创制新法律,必须符合民意。用强制力建立道德和家庭的新观念,事实上不可能,政治上也是错误的。颁布民众不赞同的亲属法,“则叛逆之气焰,将弥漫全国,其结果不独妨碍此法令之实行,且与中央政府以种种不利,而其他重要工作之实施,亦必因此而感受困难”[5]。也许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中国人还在为机械地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而乐此不疲时,作为旁观者的法国人宝道却认识到,法律文本制定之简单,不考虑法律能否融入中国的社会文化,这是极为草率、不妥的。一直参与清末民初法典创制的当事人董康以前也是极力主张废除传统礼教的,然而经过他多年的修律实践、游历东西和考察比较世界各国的法律状况后,指出中国在修律时对传统的东西弃之如敝帚是错误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建设整个法制大厦的基石,如果把基石完全抛弃掉,那么整个法制大厦就将有倾塌的危险[6]。这并不是董康司法理念的倒退,而是基于对法律制度与社会实际的对照,目睹法律制度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与社会实际产生龃龉后,对当年的修律时过于蔑视法律传统、罔顾社会实际的一种检讨和反思。
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不像工艺技术的引进或生产方式的转变那么简单。法律是否有用,取决于法律是否与社会相适应;移植外来法律文化,也要有能使其植根的社会土壤,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态等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7]马克·布洛克也说过,“小小的橡子只有在遇到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这些条件完全不属于胚胎学的范围)时,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没有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橘子就会变味,橡子就难以成材。橘橡如此,法律制度亦然。
子孙“违犯教令”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它必定是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等是相符的。所以,它不应该在1911年被武断、草率地彻底废除,这不符合我国社会实际,应该循序渐进地加以改良,最终达成我们的目的。
三、对现行刑法亲属间人身侵害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以“六法全书”为代表)一夜之间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在打破“六法全书”体系之后,并没有及时建立一套新型法律体系。1949年对“六法全书”的彻底废除,不仅仅是对旧法制的摧毁,更为重要的是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为法制近代化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从根本上予以抛弃,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中断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
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从这两条法律规定来看,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没有考虑到亲属之间人身侵害的特殊性。儿子打老子,在家庭成员看来,是教育的失败,家门的不幸,只能是无可奈何的一声轻叹;在邻人的眼里,人家毕竟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于是避而远之;在公安和司法机关看来,这是家庭内部纠纷,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是大事,也出不了大事。这里司法机关虽然考虑了亲属间人身侵害的特殊性,但是作了错误的理解,把亲属之间非重伤、死亡性人身侵害的危害性忽略了。
有人说,刑法第260条就是对亲属间非重伤、死亡性人身侵害的规范[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0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现行刑法并没有漏洞。 法律规定了虐待罪,但是又把此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并没有注意到被虐待的人往往在精神上处于被强制的状态,体力也很衰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自诉的能力,因此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很难实现。此外,这里还需注意虐待的定义,以及长时间、持续的暴力行为,假如是儿女非持续性地殴打父母,是否应该和普通人之间的故意伤害有所区别呢?现行刑法用调整一般社会关系的规范调整亲属间的关系,忽视了亲属间人身侵害的特殊性和层次性。现行刑法这样规定的意图是明显的,对子女主要归于道德教育,如果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子女必定是孝顺的;如果家庭教育是失败的,则很有可能出现不赡养老人,遗弃父母,甚至造成子女将父母杀死或者父母杀死不肖子孙的悲剧。
中国古代规定了子孙“违犯教令”罪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护君权,“未有不能尽孝而能尽其忠者”。在此我们强调的不是那种封建的愚忠思想,但是这个理论仍然是有效的,一个连养育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的人是很难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对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冷漠的人能对身边的朋友真诚吗?答案是否定的。对此,极其重视修身的林则徐就曾说过,“父母不孝、奉神无益;兄弟不睦,交友无益”。2012年3月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规定了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之间的拒证权[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说明立法者也注意到了中国传统的亲情伦理这个问题,相关立法也在不断地予以调整。综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现行刑法第232条、第234条和第260条进行修改,且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要强化对亲属间非重伤、死亡性人身侵害的法律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笔者就曾亲眼见到儿子三番五次把自己的亲生父母打得头破血流,父母却又对其无可奈何的事例。对此,应该分情况处理,如果只是辱骂父母,情节较为轻微的,经父母申请,可以经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介入对子女进行说服教育;如果经说服教育屡教不改的,出现动手殴打父母行为的,则应该由《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将这类行为明确规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如果殴打父母构成轻伤以上,则应归于刑法管辖范围。
2.要明确亲属间人身侵害中当事人的血缘关系。一般来说,血缘关系愈近则制裁愈重,比如一个人杀害其父亲当然比杀害其叔叔更为严重,一个人杀害其叔叔当然比杀害普通人更为严重;反之亦然。
3.要充分考虑引起亲属间人身侵害的具体背景。比如子女顽劣不化,经常辱骂、殴打父母,父母将其伤害或者杀死则应低于同类普通刑事案件的量刑。因为无论在法律还是道德上,儿女均有孝敬父母的义务和责任,如果不履行这个义务和责任,那么子女在法律和道德上已经存在严重的过错,即被害人首先违反了法律和亲情伦理。又如为了诈骗保险金而杀死自己儿女的行为,比杀死普通人要严重得多,前者既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权,又侵害了亲属之间的亲情伦理,冲破了两道防线,所以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要大得多。
历史是发展的,也是永恒的;现实是全新的,也是陈旧的。以血缘立法,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血缘关系是亲情的载体,有时也是冲突的根源,我国刑事立法必须面对这一矛盾,也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四、结语
钱穆先生曾说过,“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绝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8]。对于我们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在法制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加以吸收和改造,如果全盘否定,我们会在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迷失自我,我们的法制建设就像一支无根的浮萍,漂泊不定而找不到归宿。
在今天东西方文化交融日趋紧密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转型和制度重构。社会的转型和制度的重构,说到底是民族精神的重生。我们要在摒弃西方文化本位论的前提下,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本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础,对自己的法律传统予以反思,其目的不是决裂,更不是丑化,而是开新与超越。
参考文献:
[1] 大清律例:卷30[M]//张仁善.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99.
[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74.
[3] 劳乃宣.新刑律修正案汇录[M]//张仁善.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70.
[4] 沈家本.删除律例内重法折[M]//历代刑法号:寄簃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宝 道.中国亲属法之改造[J].张毓昆,译.法学季刊,1936,1(1).
[6] 董 康.民国十三年司法之回顾[J].法学季刊,1924,2(3).
[7]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M]//张仁善.中国法律社会史的视野.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
[8] 钱 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7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