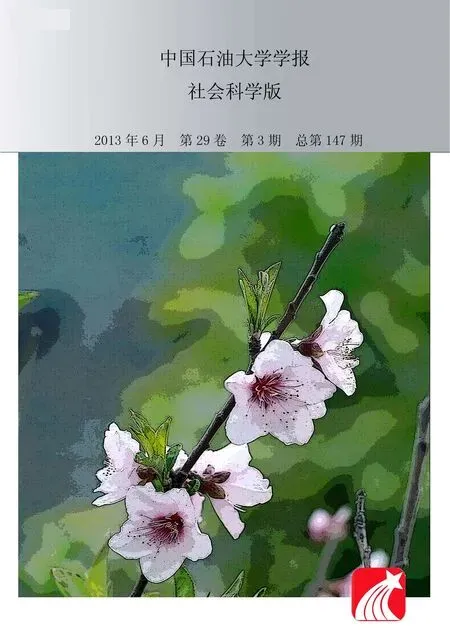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探析
——对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之解读
陈 杰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探析
——对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之解读
陈 杰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中国新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意在加强对民事诉讼中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规制。《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中国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通过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制度以及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等进行,但这些制度都存在相应问题。本次新增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于第三人权益保护上有诸多亮点,例如扩大了保护主体、衔接了事前保障程序及明确了提起事由等,但也存在着制度瑕疵、缺乏相应配套制度及与相关制度界限不明等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良好运行还需要通过完善制度构建、协调配套规定等对策进行。
第三人撤销之诉;虚假诉讼;事后保障程序;第三人权益保护
2012年8月31日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56条增加了第3款规定,即非因本人原因而未能参加原诉的第三人,可以原审法院作出的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致自身权益受损为由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撤销或者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这被认为是在中国《民事诉讼法》上建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对实践中案外第三人权益受侵害而救济措施不力困境的呼应。[1]然而,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所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款却仅此一条,且规定简陋,暴露了该项程序设计的不成熟和可能产生的问题。
一、《民事诉讼法》修订前后中国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状况
在新《民事诉讼法》生效前,中国立法对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有事前及事后的程序保障两类,前者主要指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后者则指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制度、申请再审制度。新《民事诉讼法》则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一)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
原《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2款规定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可细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制度,两制度均存在一定缺陷。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依据过于狭窄,以对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为限,而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则还赋予因权利可能受到原诉结果损害的第三人参加诉讼[2],因此,中国的“独立请求权”仅限于实体权利,对第三人的保护范围过小。另外,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参加之诉中虽然有着相当于原告的诉讼地位,但其对程序的参与度要明显弱于本诉原告①,也不利于其程序权利的保护。
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最为学者所诟病的便是其虽然移植自大陆法系的“从诉讼参加人”或者“辅助参加人”制度,却不遵照它们的立法基础。②在中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中往往处于实质上的被告地位,法院可以判决其承担义务,但对于该类第三人的权利保护却远不及当事人。[3]同时,中国立法允许法院依职权通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明显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理。另外,制度作用的前提是第三人在本诉进行中即知道该诉的存在,且可以参加诉讼,但实践中却存在着诸多第三人因不知情而未参加的情形。[4]62因此,第三人制度在实践中运用率相当低,即使启用也容易被扭曲为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的工具,对案外第三人权益的保护效果不甚明显。
(二)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异议制度
原《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修订后为第227条)规定了案外人异议制度。该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首先,该制度的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执行程序,且损害第三人权益的诉讼结果必须为给付判决;其次,程序设计有重复审查之嫌,异议审查程序与异议之诉相比并不具有决定异议的效力,可能导致异议审查的形式化;再次,异议审查与执行异议之诉裁判的机构并不相同,前者一般由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作出,后者则由法院的裁判机构作出,而不同法官面对相同事实亦可能作出不同的裁判,有损司法公信力,也不利于案外第三人权益的有效保护。[5]
(三)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监程序解释》)第5条规定,案外人对原裁判、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却无法提出新的诉讼的,则可在原裁判、调解书生效后两年内或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受损后三个月内向作出原裁判、调解书的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③
该条即规定了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司法实践中对案外人特别是非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利益保护的迫切需求,赋予了案外人一定的正当程序请求权。但该项制度亦存在缺陷。第一,对可提起再审申请的案外人设定过于宽泛,未体现再审程序的补充性原则。[6]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作为一种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事后救济制度,应当是在第三人非因本人原因而未参加原诉的前提下发挥价值的,而此项制度并未对案外第三人是否需满足未获得事前程序保障的条件加以限制,可能导致本可以在原诉中通过第三人参加诉讼解决的案外人,却仍滥用再审制度,有违再审程序的补充性救济程序的原则。第二,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可适用于执行程序之外的阶段,但是却仍仅限于给付之诉中,对于实践中常见的形成判决之案外人权益如何救济问题④,仍然没有规定。第三,申请再审仅是一项申请权而非诉权,再审的启动难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再审条件较为严格,再审决定权在法院手中⑤,且再审事由不以裁判侵害第三人权益为依据,因此第三人进入再审程序难度较大,即使法院收到案外第三人的再审申请,也可以裁定不予再审。[4]63
(四)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正是由于中国之前对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缺陷,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在参考了大陆法系各国、各地区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吸收实践诉求,在第56条新增第3款规定,建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⑥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要内容如下:(1)适格主体。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是第56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范围十分明确。(2)提起事由。需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该第三人须因不能归责于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即第三人因无从知道而未参加诉讼或者因不可抗力等原因而无法参加诉讼的。其二,须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书、调解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3)管辖法院。管辖法院为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4)诉讼时效。第三人须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提起诉讼。
二、对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的评析
(一)立法亮点
1.扩大了主体范围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是第56条前两款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此处的第三人不同于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制度及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中的案外人,其范围要大于后两者,不仅包括对原诉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的案外人,也包括对原诉标的物不享有实体权利但与原诉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案外人。
2.衔接了事前保障程序
第三人撤销之诉须因不能归责于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事实上弥补了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中未对是否已寻求事前救济作出限制的缺陷。若第三人参加过原诉的审理,或者知道原诉会损害自身权益但怠于行使权利而未参加原诉的,则不得再提起撤销之诉。如此修改,可“督促能够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参加诉讼,及时解决纠纷,避免权利的消极滥用,以致使得原生效裁判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影响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4]64。此外,对第三人原告主体适格的规定,也很好地体现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与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在权益救济上的自然延伸。
3.明确了提起事由
在立法修正之前,许多学者主张建立再审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⑦,其中在第三人撤销事由上多认为可以参照申请再审的事由,而将其界定为申请再审中的实体事项。该设想存在一定的实践难度,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中国,再审程序都是分阶段性的构造。法院首先对申请事由进行形式审查,符合条件的,才进行重新审理。只有原裁判确实错误的,才作出撤销原判的裁判。因此,再审程序的阶段性特点区分了申请再审的事由和撤销原裁判的事由,生效裁判的撤销事由不在于申请再审的事由而在于对原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重新认定。[7]
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存在类似再审的阶段性特点,相对于一般纠纷而言,虽具有次生性,但其仍是第三人对自身实体权益的第一次救济,而非对解决纠纷的过程的不满。因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应当且仅应当是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而不存在类似再审的申请事由。此次立法的明确规定,厘清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独立的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非独立性的区别,使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得以明确化、专门化。
(二)立法缺陷
1.制度瑕疵
(1)客体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仲裁日益成为商事争议领域的重要纠纷解决手段,仲裁作出的仲裁裁决书和仲裁调解书也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也可能损害案外第三人的权益,在这一点上与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仲裁机构作出的相应法律文书也应当包括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之中。[8]
(2)审理范围问题
理论上普遍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旨在除去或变更原裁判或调解书中对第三人不利的部分,无须全面否定原判决的效力,即取消部分与原诉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无关的部分则不对原诉当事人发生效力。⑧这种解释也与法国、中国台湾地区等立法例的观点相近。⑨虽然本次立法并未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判决的效力范围作出明确规定,但相关立法部门似乎倾向于认为法院应当“同时对第三人与原审当事人之间、原审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重新作出裁判”[4]66。如此,显然与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仅影响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分配的原理相冲突,不利于原审裁判效果的固定,甚至可能造成第三人滥用起诉权致使原诉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迟迟无法稳定的后果。
2.缺乏对第三人滥用撤销权的配套惩罚机制
新《民事诉讼法》增加第112条,对处罚虚假诉讼、调解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了规定,其还是强调对虚假诉讼、恶意调解加强规制,是从处罚的立法目的出发,侧重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原诉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保护则相对受到忽视。同时,新《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以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为恶意诉讼、调解的构成要件,缺乏对一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单方自行滥用起诉权或者上诉权的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情形的规制。虽然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和当前的实践状况更应当解决的是第三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问题,但对于原诉当事人因第三人撤销之诉而权益可能受到侵害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无视,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规制,以免造成顾此失彼的问题。
3.与相关制度界限不清
(1)与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执行过程中,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与案外人异议制度可能存在适用竞合。案外人第三人提起异议之后,法院依法予以审查,作出相应裁定,若是与原诉裁判有关,当事人、案外人可以申请再审,若与原诉裁判无关,当事人、案外人则可以另行起诉,对案外人而言也即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在与原诉裁判无关的情形下,案外人提出异议仅仅是围绕被执行的具体财产权利归属而发生的争议[9],与原诉裁判仅有事实上而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同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倘若与原诉裁判有关,案外人提出的异议便可能与第三人撤销之诉重叠。如何协调,立法未予明确。
(2)与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之间的关系
《审监程序解释》第5条规定,对原判决等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的案外人,须以“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为条件,那么,如果符合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情形,是否就不符合“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条件而无法再提起再审[9],还是说两者可以任由案外第三人选择,甚至案外第三人可以在一种程序无法解决之后,是否能选择另一种程序,值得思考。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实践运行对策
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虽然在中国立法上已经确立,也体现了不少对第三人权益保护的亮点,但是正如上文分析的,该制度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陷,这些都需要理论界对该制度进行更深刻的研究和反思,也需要实务部门在未来执行该制度时予以注意。
(一)完善制度构建
1.出台司法解释,细化立法规则
(1)客体
考虑到商事仲裁的广泛应用性,应将仲裁裁决书和仲裁调解书亦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虽然立法部门认为通过仲裁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属于仲裁庭的职责,宜由仲裁法及仲裁规则予以规定[4]156,但从法律修改的滞后性及法律实施的配套效果考量,应当将仲裁裁决书和仲裁调解书纳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
(2)审理范围
相关立法部门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应当包括原诉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范围[4]66,这导致原诉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迟迟无法稳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判范围应限定于第三人受到侵害的权益范围,不应包括原诉当事人之间的与第三人无关的部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在于规制原诉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而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第三人提起该诉意在恢复受原诉当事人不法侵害的合法权益,至于原诉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要不涉及第三人,第三人便不会关心,法院也没有必要主动进行审查,如此既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同时也是对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理的尊重。
(3)适用范围
以法国、中国台湾和澳门地区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缓解民事诉讼与民事实体法制在理论和实践运用上的矛盾,即缓解既判力的相对性以及既判力主观范围仅及于诉讼双方与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多元化之间的矛盾,为民事诉讼可能在程序合法的前提下作出损害案外第三人权益的裁判的情形提供救济。而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方式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日益频发。[4]61另外,近些年中国法院系统强调调解工作后,当事人通过提起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并借助调解的高度合意性和自愿性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更便利地获取法院调解书以达成侵害案外第三人目的的恶意调解的数量也愈发增加了。[10]因此,中国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目的即在于整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恶意调解等的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司法顽疾。⑩第三人撤销之诉立法目的的不同直接影响该诉提起事由的不同进而影响制度运行的范围不同。正如前文分析的,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质提起事由应当是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而非第三人对原审享有的程序利益未得到保障。若是依照大陆法系保护第三人程序利益、缓解判决既判力过于刚性的立法目的,则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范围相对较大,第三人只需证明非因本人原因未能参加原诉即可;而若依照中国遏制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需求的立法目的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范围则受限许多,因为第三人非因本人原因未能参加诉讼并非第三人撤销之诉得以提起的实质事由,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才是其中的关键。故而,鉴于上述立法目的的差异,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在实践适用时务必需要明确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即只能以法律规定的第三人民事权益受损为唯一提起事由,由此才能达成限制滥用诉权、侵犯第三人权益的制度设计的初衷。
2.制定配套制度,明确程序界限
(1)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
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对原生效法律关系的重新裁判,涉及既判力的稳定和原诉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因而其更易被滥用且被滥用的后果亦更严重,有必要建立对第三人滥用撤销之诉的惩罚机制。中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49条之一规定,第二审法院驳回上诉时,认为上诉人之上诉显无理由或仅系以延滞诉讼之终结为目的者,得处上诉人新台币六万元以下之罚款。虽然该条文规定的是对上诉人滥用上诉权的惩罚机制,但中国大陆也可以借鉴到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建议在其后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受理法院驳回起诉的,认为第三人的起诉显无理由或仅以拖延执行为目的的,得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罚款数额可参见新《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如此才能够使得第三人更加审慎、更加诚信地利用该项制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第三人撤销之诉造成的原诉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迟迟无法稳定的问题。
(2)与案外人异议制度的界限
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异议制度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存在重叠。至少从立法的规定而言,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比提起案外人异议之后再依照再审程序处理来得便捷,而从立法本意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也更关注第三人权益保护。因而可以在之后的司法解释中明确此种情况下只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即在执行程序中,若案外第三人认为原诉裁判有错误的,须直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予以解决,而不能再提起执行异议然后另行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解决。
(3)与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的界限
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与第三人撤销之诉也有着功能上和适用上的重叠性,两者保留其一即可。同时,因为前者在适用主体上的过分宽泛、启动上的实质困难以及第三人申请再审的理论缺陷,建议当两项制度竞合适用时,规定优先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
(二)协调配套规定
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除了新增第56条第3款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外,事实上还有其他相关条文涉及相关内容。作为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有效运行,必离不开这些相关制度的配套协调实施。
1.协调适用对恶意诉讼、调解行为进行司法处罚的规定
事实上,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很多情况下是对第三人合法权益受侵害后的事后救济,其努力也是在于如何恢复受破坏的正常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如果能配合第三人合法权益受侵害前的事前救济措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这种事后的努力便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新《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恰能满足这种要求。需要注意的是,两项规定的协调实施中,法院应当注重在诉讼中发现虚假诉讼、调解行为,将侵犯第三人权益的结果尽早遏制。具体而言,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调解行为的,应当首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次还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拘留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2.协调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
新《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设立的目的在于规制民事诉讼活动中滥用诉讼权利,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4]14,而对于通过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恶意调解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的规制,则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可以说,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以对恶意诉讼、调解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行为进行司法处罚的规定为保障,以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为核心,新《民事诉讼法》构筑了一个规制恶意诉讼、调解,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诚实信用原则是基础,是其中的纲领性、原则性的规定,不仅应当贯穿于第三人权益保护和恶意诉讼、调解行为规制的始终,还应当起到弥补制度不足的补充适用作用。在原诉中,诚实信用原则应配套对恶意诉讼、调解的司法处罚规定,在事前规制该类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法院也应当监督第三人本着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诉讼,以自身合法权益保护为限,禁止滥用第三人撤销权;在第三人撤销之诉后,原诉当事人或第三人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配合法院履行执行或者执行回转的义务。在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或者对恶意诉讼、调解的司法处罚制度存在缺陷、漏洞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发挥诚实信用原则的补充作用,使其真正成为切实适用的刚性原则。
注释:
① 诸如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事实上无法依据参加之诉的管辖来参与诉讼。
② 该第三人按照大陆法系制度设计应当不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缺乏相应的当事人权利,也无须承担当事人的义务。参见章武生《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53-62页)。
③ 新《民事诉讼法》第205条修改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规定,不再规定为一般情况下的客观标准两年,特殊情况下的主观标准三个月,而规定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由于该期限的修改与本文探讨内容相关性并不大,故在此不作分析,仅作简单说明。
④ 典型的如离婚诉讼等涉及身份关系的诉讼判决。
⑤ 法院决定再审及检察院提起抗诉引发再审的方式,在实践中则因为法院自身纠错的悖论和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监督的相对薄弱而运行效果不佳。
⑥ 该制度的具体评析详见下文。
⑦ 此观点可参照肖建华、杨兵《论第三人撤销之诉——兼论民事诉讼再审制度的改造》(《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4期,第38-42页);江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
⑧ 相关观点参见胡军辉《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建构——以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为参照》(《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第146-151页);郑夏《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构建》(《兰州学刊》,2012年第8期,第175-180页);陈贤贵《论第三人撤销之诉——以台湾地区立法例为中心》(《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6页等)。
⑨ 法国学者认为当判决可分时,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仅对第三人产生效果,在原判当事人之间则仍保留效力;仅当判决不可分时,第三人取消判决异议的效力才及于原判所有当事人及第三人。相关观点详见[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下)》,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5-1296页。中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07条之四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有理由的,仅撤销对第三人不利的部分,原判决于当事人之间仍不失效力;仅当原判决诉讼标的对于原判当事人与第三人须合一确定时,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判决效力才及于原判当事人之间。
⑩ 据相关调查,北京某基层法院因虚假诉讼而导致案件申请再审的数量仅2007年就比2006年增加4倍多,其中7件被提起再审,达到该院全年提起再审案件数(12件)的58.3%;又,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5月份,浙江省已经法院审理的虚假诉讼案件多达107件,有虚假诉讼嫌疑的更是远多于此;而自2004年至2007年,据上海某基层法院统计,该院已发生8件当事人利用调解侵犯第三人利益的案件,其中有4件被提起再审。以上调研数据详见钟蔚莉、胡昌明、王煜珏《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中发现的虚假诉讼的调研报告》(《法律适用》,2008年第6期,第55-58页);魏新璋、张军斌、李燕山《对“虚假诉讼”有关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浙江法院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的实践为例》(《法律适用》,2009年第1期,第64-68页);陈慧《当前民事诉讼中的恶意调解现象及防范研究》(《法律适用》,2007年第5期,第60-64页)。
[1] 陈丽平.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济程序[N].法制日报,2012-8-28(2).
[2] 王保民,王泊达.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之完善[J].行政与法,2011(12):96-99.
[3] 章武生.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法学研究,2006(3):53-62.
[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2012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解[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5] 陆福媛.民事执行异议制度的不足与完善[M]//陈锋.法学论丛——诉讼法卷(2009).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218.
[6] 王合静.案外第三人之申请再审权——对《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解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23-126.
[7] 崔玲玲.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与再审之诉的事由比较[J].社科纵横,2011(9):76-79.
[8] 郑夏.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构建[J].兰州学刊,2012(8):175-180.
[9] 王亚新.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解释适用[N].人民法院报,2012-9-26(7).
[10] 李浩.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问题研究[J].江海学刊,2012(1):138-143.
[责任编辑:陈可阔]
OntheSystemoftheThirdPartyDischargingtheJudgmentofChina:AnAnalysisoftheArticle56Item3oftheNewCivilProcedureLaw
CHEN Jie
(GraduateSchool,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0042,China)
In reality there are massive acts such as fraud litigations, malicious litigations and vicious conciliations, which seriously infringe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ies. The previous Civil Procedure Law had certain systems regulating such phenomenon but resulted poorly on account of some reasons. The new Civil Procedure Law establishes the system of the third party discharging the judgment aiming to enhance the regulation of acts of infring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ies.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analysis the concrete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in order to find some defect and present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and suggestion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evious system and the new one and the reference of foreign legislations.
the third party discharging the Judgment; fraud litigations; malicious litigations;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y
D925.1
A
1673-5595(2013)03-0040-06
2013-03-16
陈 杰(1988-),男,浙江宁波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