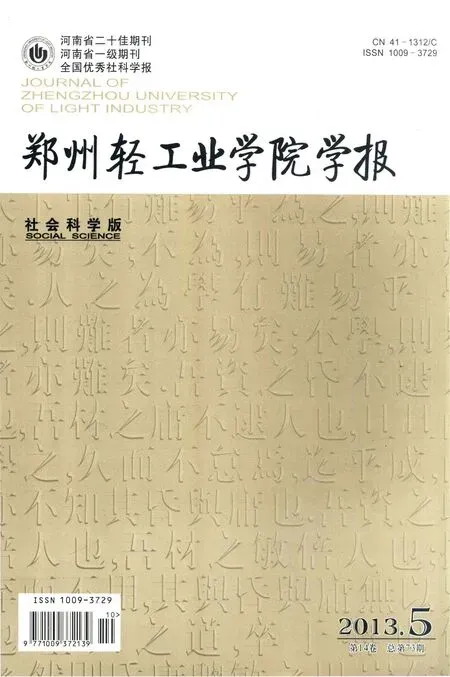民国时期河南省灾荒救助体系措施及成效
孙训华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河南 郑州450015)
1928—1937 年,河南省灾荒发生的频率及其所造成影响,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尽管国民政府的救灾工作相对前清而言,无论是其重视程度还是动员力度,都有明显的增强,但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等诸多因素,灾荒救助工作并未取得预想效果。作为近代灾荒最为频发的地区,河南省的情况是国民政府灾荒救助的一个缩影。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灾荒的成因及其影响层次,而对于地方灾荒救助体系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拟通过分析1928—1937 年间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的框架及存在问题,深入了解民国时期地方灾荒救助体系的特点及成效,以期为今后的救灾工作提供参考。
一、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体系与运作
1.构建救灾组织体系
(1)建立救灾组织机构
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灾害,更好发挥政府对于灾荒救助影响,河南省政府奉命于1929 年4 月成立河南省省赈务会,隶属于省政府,“盖合省政府委员二人,省党部委员二人,民众团体五人组织”。[1](P560)赈务会成立以后,成绩显著,3 个月时间,各种捐助及中央、地方所筹集的赈款已达275 850 元。大部分用于散放各县急赈,部分款项用于办理工赈和平粜。1935 年,成立河南省水灾救济总会,主要办理急赈、工赈、收容等事宜,并且在各县设水灾救济分会共计35 处。河南省政府设立的赈灾机构,多为临时筹设性质,由于政府财政专款的支持,赈灾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发放急赈、设粥厂、工赈等措施,灾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救助。
(2)制定救灾运作规范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河南省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救灾法规和办法,以规范救灾工作的各种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筹集平粜基金,针对灾荒期间省内受灾地区缺粮的现状,先后颁布了《筹购款粮及运输办法》《以富养贫办法》等,以稳定市场粮食供给,后又陆续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调剂民食办法》《节食救灾办法》《收养灾童办法》《牲畜保育办法》《开仓贷谷及散放办法》《专员、县长办理救灾奖惩办法》等规定。上述种种救济措施,采用中央赈灾与地方自救相结合的救灾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对于社会民生的破坏。
2.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1)大力整顿仓储
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积谷备荒显得尤为重要。早在清朝乾隆时期,全省常平仓、义仓、社仓,贮谷256 万石有余,劝捐民社仓贮谷73 万石有余[1](P552)。仓储量相当可观,有效地发挥了防灾备荒的功效。但近代以来,积谷量逐年下降。民国初年,仓储制度几近废弛,“清时虽不时开仓赈济,然犹时借时还,仓储常满。自民国以来,民乏隔岁之粮,官无期年之任。仓政废弛,只有支出,未有偿还,早已一粒无存。”[2]南京政府成立后,政治形势渐趋稳定,政府开始重建仓储。河南省政府要求各地严格整顿仓储,“由厅规定查报二麦收数、秋禾收数、谷价并旧仓状况,及新仓筹设情形,印成表册,交由查禁烟苗委员,附带查报,以为责成之标准,而杜藉词延宕之弊”[3]。1933 年,鉴于各县整顿仓储未能划一,河南省政府提出了具体的仓储整顿办法大纲,要求“于最短期间,以最低限度,将县仓区仓分别成立,一面督饬区保甲长宣传仓储必要,俾各协力举办义仓,即以办理仓储为各该县长之考成。自经通令之后,本厅当随时派员考查,倘仍有玩忽情事,一经查明,定行严惩不贷”[4]。据统计,1932 年河南省全省仓储粮为1.1 万石左右,经过数年的整顿,1935 年全省积谷已达29 413 石,连同旧谷共45 816 石。[5](P331)
(2)开展植树造林
为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河南省政府制订了一系列防灾造林的制度,并出台许多植树绿化措施,积极开展各种造林活动。1927 年10 月,河南省政府将原北洋军阀时期所设的林务监督改为森林办事处,加强对全省林业建设的管理,全省林务开始有了统一管辖机关。1928 年5 月,省政府公布《承领荒地造林暂行条例》,又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植树造林的法规条例,如《拟定林业合作社规则》《订定强制人民造林条例》《订定各级林务行政人员奖惩条例》等。在这些法令条例的指导下,河南省先后组织营造了中山纪念林、各县模范林等,进行河岸造林、坟地种树,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强制人民造林。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人工林面积较以往有了明显的增长。据当时的河南省政府统计,1929 年,全省共植树3 469 964 株,1930 年为3 879 102 株,1931 年更是达到5 330 551 株,三年合计全省共植树造林12 679 617 株。[6]可见,河南省当时的森林覆盖面积有了较大的提升,对防灾减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3)重组水利机关,兴建水利设施
河南省水利管理机关早在民国初年就已设立,却因经费欠缺、政局动荡,纯属有名无实,水利设施已逐年老化,“河渠蓄泄无度,以致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汪洋一片”,尤其是民元以来,战乱频仍,水利建设已经严重滞后于农业发展的需要,以至于“十年之内,旱者七,潦者二,年谷顺成者,不过十一耳。欲救济之,水利自不可缓也。”[1](P687)1928 年1 月,河南省政府按照河流大小、水利设施具体情况,先后将全省水利机构整合为48 个水利分局。1932 年,又改组为4 个水利局。1935 年,又改组为河南省水利处,隶属于省建设厅,负责管理全省水利建设事务,水利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据统计,仅1931 年一年,全省有54 个县共疏浚及开挖大小沟渠232 处,有31 个县疏浚大小河流51 处,有22 个县凿井共4 088 口。[7]
3.开展实施灾荒救助措施
(1)调配散放赈粮
饥荒之年,灾民最急切盼望的是赈粮。由于灾荒不断,人口众多,河南省粮食本就不充裕,如遇上饥荒年景,粮食缺乏便成为了困扰当局的迫切问题。1929 年1 月,因灾荒严重,河南省决定向江苏购米10 万石。1932 年鄢陵水灾,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郑州办事处“拨给美麦一百二十吨,计一千四百九十四包,重十八万斤,按全县一百八十二乡镇,每乡镇分八百斤发给”[8]。1933 年,黄河大水,泛滥成灾,国民政府在河南省兰封、滑县等21 县共散放救济赈粮201 万余斤。[9]从救灾应急效果而言,赈粮无疑是最为理想的方式。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与交通设施、天气状况以及社会政治形势有关。对于交通便利、政治相对稳定的地区,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战火纷扰、交通不畅的地区,赈粮必然不能及时运往灾区,一旦出现积压、耽搁时日,不但延误救灾时机,赈粮也会出现霉质,进而造成损失,影响到灾荒救助效果。
(2)筹集拨放赈款
除赈济粮谷外,拨放赈款也是一种常用的救灾手段。灾荒发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便会立刻拨放赈款,开展救灾。1931 年河南省大水,泛滥成灾,国府水灾救济委员会下拨赈款10 万元救济河南省灾民。[10]1936 年河南省全省大旱,经多方呼吁,财政部前后共拨给公债票面30 万元,售后现款为18 万元左右,用于救济豫灾。[11]拨放赈款,一直是政府赈灾的主要手段,可以实现快速高效的救灾效果。但由于受灾区域较广,赈款数额有限,难免在赈款分配上出现各种矛盾和纠纷,程序上的繁琐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救灾的良机。同时由于经办赈款、参与赈灾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侵吞克扣赈款的违法案件层出不穷,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成效。
(3)开展以工代赈
工赈作为传统荒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灾荒救助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民元之后,政治动荡,经济衰败,政府当局仍然将急赈放在了灾荒救助工作的首位,对工赈没有给予足够的投入。1928 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工赈逐渐引起了各级救灾机构的重视,“古言荒岁役民,原出于不得已,而未始非良法也。浚河筑堤诸务,受其值,救目前之饥荒;藉其劳,免将来之水旱。故筹办工振,实救荒最善之策也”[10](P21)。1932 年,西华境内沙河暴涨,泛滥为灾,绅民“向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呼吁,蒙准拨发赈麦赈款分别办理沙颖工赈……复以余款设立颍河下游桥工委员会,建修沿河桥梁十一处,植树十万株”[12]。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政府已经开始将防灾与救灾进行了初步的结合。虽然从救灾成效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考虑到当时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这种灾荒救助的举措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通过分析河南省政府所采取的种种灾荒救助措施,可以看出尽管政府已经意识到防灾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又只能将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到灾后的补救上来,缺乏防灾救灾的长效机制。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虽然构建起了灾荒救助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并未掌握近代灾荒救助的科学方法与先进的救灾思想。因而,面对无法抗拒的灾荒,只能疲于应付,以致于无法取得救灾的明显效果。
二、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的特点及其在灾荒救助中的作用
1.河南省政府所构建的灾荒救助体系趋于近代化
(1)运用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宣传赈灾
民国时期,河南省政府在救灾方面采用了大量的近代化技术手段,比如通过近代化的媒介手段及时向外界传播救灾信息。报纸和电报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式,以1931 年江淮大水灾为例,作为当时中国社会影响力度较大的《申报》连续刊登了呼吁赈济豫灾的报道和通讯,诸如《济生会豫赈主任出发》《济生会豫赈纪要》《河南省刘峙主席急电乞赈》《河南省赈务会恳拨款粮赈灾电》《豫省赈务会电告水灾》《张钫电张学良乞赈》《豫省府请拨赈灾公债》等。在当时全社会范围内,让国民更加及时、真实、全面了解河南省的灾情,对于动员社会各方赈济豫灾产生了较好效果。
(2)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
官方赈灾一直以来就是传统荒政的主要内容,但民国时期,政局混乱,财政匮乏,政府应对灾荒力不从心,于是动员民间力量参与救灾,“本省灾区广袤,灾情惨重,又值库款支绌,募赈有限,以之散给各乡,其为数直等于杯水车薪,而各县不乏殷富之家,慈善之士,劝捐义赈,实属要图。一方可免办赈不善之弊,同时灾民得受实惠”[10]。民间救灾开始快速的兴起,1930 年河南省大水,灵宝乡绅张重仁于本地“散粮二十余石,全活颇众”[13]。1931 年,河南省水灾,沙河两岸各县受灾较重,“现该处士绅组织沙河水灾救济会,实地调查,筹款疏浚,以期免除永久灾患”[14]。1932 年7 月,“霪雨为灾,漳河决口六十余丈”,“邑绅王孝德、李建勋会同临漳绅士倪建勋等组织临时河防局,堵塞决口”[15]。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专门的救灾赈灾机构,主要包括华洋义赈会河南省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在河南省的各分会、旅平河南省赈灾会、旅京河南同乡会。这些机构通过筹募粮款、移民垦荒等措施,在河南省灾荒救助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扩充赈灾资金
在整个的灾荒救助体系之中,救灾资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国时期,政府财政支绌,而灾荒又异常严重,仅靠政府的赈款,无疑是杯水车薪。据国民政府统计,1932 年河南省受灾面积14 万多平方公里,灾民1 480 万人以上,因灾外迁者35 万多户,死亡34 万人,财产损失1 893 万元以上,而全省所得公私赈款不过23 万元[5](P312)。面对巨大的救灾资金缺口,河南省政府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如发行赈灾公债、发动政府机关捐薪助赈,组织社会知名人士开展义演、动员省外慈善团体募捐及提倡政府机关开展节约助赈等。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所采取的赈款募集方式,已经打破了传统荒政的单一模式,体现出民国时期河南省救灾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进一步改善了救灾环境,提升了救灾成效。
2.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体系中的作用及其救灾成效
(1)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救灾体系的运作中,政府在灾荒救济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河南省政府组建的专门救灾机构——河南省赈务会,负责救灾工作的统筹与协调。灾害一旦发生,政府便会立刻启动救灾工作,并通过政令以及新闻媒体等各种渠道,向全社会发出最为权威的赈灾呼吁。虽然富绅积极参与当地赈灾,但政府依然保持着对民间救灾力量的引导与控制。尽管在近代救灾体系中,民间救灾力量异军突起,但其从属于官方救灾体制的模式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种民间无法取代的官方主导式的赈灾体制,有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保障救灾有效运行。
(2)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成效有限
尽管灾荒来临之时,河南省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民间人士都采取了众多的救灾措施,但在当时政局动荡、经济衰败的背景下,政府的灾荒救济在灾害频仍的现实面前,其救助效果依然是非常有限的。1935 年偃师境内河流满溢、山洪暴发,省赈务会拨洋1 000 银元,连同其他各种方式所募集的赈款共计8 000 银元,赈粮6 万斤,这些即便是完全无余地发给灾民,人均也只能得到8 两粮食,1 角钱。1936年临汝旱灾严重,省政府拨振款2 000 余元,灾民每口仅能分的五分钱,尚不够一餐之用[16]。据国民政府统计,1931 年,河南省全省各河决口长达8 600 余华里,灾民949 万人以上,死亡11 万人,物产损失约计22 955 万余元[5](P304-305)。1934 年,河南省受灾田地共3 469.4 万亩,占田亩总数的37%[5](P326)。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河南省政府尽力救济灾荒,但其救灾成效并不十分明显。
三、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成效发挥的限制性因素
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成效发挥的限制性因素,除了自然因素之外,政府自身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首先,苛捐杂税众多,民间经济负担沉重。民国时期,政府当局对广大农民加捐加税、重捐重税的现象极为严重。作为传统田赋征收大省的河南省,人民经济负担更为沉重,据统计,1902 年,全国最好的稻田每亩税不过四角,而到1929 年,豫南稻田平均每亩赋税负担增至1.196 元,较1902 年平均额上升近3 倍[17]。各地驻军“吃地面”(饷项及一切军需、草料全让地方供应)十分普遍。辉县、滑县见于册籍的一年就分别为100 万、400 万元以上,人民实际负担数倍于此数。1932 年,据国民政府统计,河南省20 个县水田每亩平均负税5.6 元左右,43 个县旱地每亩平均负税5.6 元,均相当于清末地丁之14倍[5](P312)。1934 年,《东方杂志》曾报道,今大灾之后的河南省附加税名目就高达42 种,居全国前列[18]。鉴于河南省捐税名目繁多,有超过征税十倍以上者。1934 年6 月份省政府先后免去300 余种捐税,10 月召开财政会议后又免去县杂捐21 种,各县私收田赋附加查免46 种。尽管如此,未上报的捐税还不知有多少。由此可以看出民间负担何其重[5](P326)。
其次,赈灾过程中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民国时期,财政支绌,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救灾助赈机构的赈款也仅仅是杯水车薪,但即便如此,仍有人在赈灾过程中,营私舞弊,侵吞赈款,从中渔利。1932 年,河南省省民政厅指出,“查河南省各县,自去岁以来,被灾奇重,分配赈款,亦不在少数。惟各属散放人员,及各区绅董,往往经人控告,有吞食挪用情弊,自非切实查察,认真整顿,不足以维赈务”[19]。汝南县十九店以往所积累之社仓积谷,数年来一毫未动,合计应有积谷1 500 石,灾荒严重时,各方决定开仓赈济,当开仓时才发现所积仓谷早已被仓库主任“都信手挥霍,或者经营了买卖,现在是一点没有”[20]。遭遇蝗灾更是一些地方贪官发财的大好机会,“这正是各省、各县政府中靠‘吃蝗虫’肥胖起来的贪官污吏们所大为高兴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年年除之不尽的严重的蝗灾中得到更多更多的‘奖金’,而使自己更肥更胖”[21]。
最后,农民日益贫困,抗灾自救能力严重不足。因灾致荒,因荒成灾,近代以来社会灾荒的演变一直没有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灾荒的打击极度地增加了农民生存的负担,造成了农村社会的日渐破产。即便勉强熬过了一个灾荒,在濒临破产的农村社会,农民在下一次灾荒面前依然毫无抵抗力。1936 年,经济学家朱其华曾把中国人群按照经济生活状况进行了分类,其中处在贫穷线的人口为18.7%,饥饿线的人口占62.5%,死亡线的人口占到12.5%,全国人口的93. 7% 已经基本上无法维持最低生活了[22]。而在这个群体中,农民的人数显然占绝大多数。农民在灾荒和农村经济破产的夹击之下,其对灾害的防御和自救能力已达到了极为脆弱的地步。大灾自不必说,即便小灾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场与死亡展开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政府官方的灾荒救助体系中,农民抗灾自救基本上无从谈起,进而加大了政府当局救灾的难度,成为影响政府灾荒救助体系发挥其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结语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河南省政府在构建灾荒救助体系方面进行了良好的组织和引导,也陆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防灾救灾工作,但是灾荒救助的成效并不明显,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的苛捐杂税、政治腐败,表现出政府当局在构建地方灾荒救助体系框架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制度性缺失,而这种体制上的缺陷又是国民政府自身无法克服和弥补的,结果必然导致救灾成效大打折扣。
[1] 河南省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民国)河南省新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2] 〔清〕张嘉谍. (民国)西华县续志(卷五)[M]. 潘龙光,修.台北:成文出版社,1938:10.
[3] 讲演[J].河南省民政月刊,1933(1):88.
[4] 重要公牍[J].河南省民政月刊,1933(2):35.
[5] 王天奖.河南省近代大事记[M].郑州:河南省人民出版社,1990.
[6] 河南省各县最近三年造林成绩统计表[J]. 河南省省政府年刊,1931:558.
[7] 全省二十年水利进行之统计[J].河南省省政府年刊,1931:587.
[8] 苏宝谦.(民国)鄢陵县志[M].靳蓉镜,晋克昌,修.台北:成文出版社,1936:39 -40.
[9] 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R].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MG4.3 -50).
[10]工作报告[J].河南省省政府年刊,1931:19.
[11]工作报告[J].河南省省政府年刊,1936:140.
[12]〔清〕张嘉谋. (民国)西华县续志(卷一)[M]. 潘龙光,修.台北:成文出版社,1938:27.
[13]张象明.(民国)灵宝县志(卷十)[M]. 孙椿荣,修. 台北:成文出版社,1935:24.
[14]报告[J].河南省政治月刊,1931(4):2.
[15]〔清〕贵泰,武穆淳. (民国)安阳县志(卷末)[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33:1683.
[16]武艳敏.民国时期社会救灾研究——1927—1937 年河南省中心的考察[D].上海:复旦大学,2006.
[17] 李作周. 中国的田赋及农民[J]. 新创造,1932,2(1):1.
[18]邹枋. 中国田赋附加的种类[J]. 东方杂志,1934,31(14):312.
[19]计划[J].河南省政治月刊,1932(11):3.
[2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十三辑)[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44.
[21]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137.
[22]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M].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