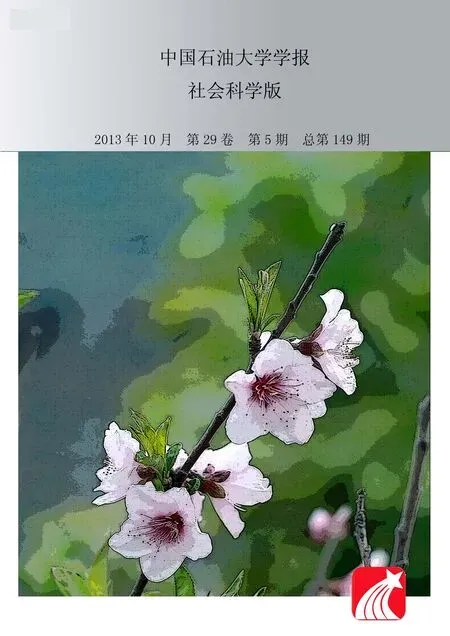善恶之辩与管理之道
——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析论
纪光欣,向松林
(1.中国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580;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人性观或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建构和管理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点。“人性假设”这一概念是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在1957年的《企业的人性面》中首次提出的,但人性观实际上隐含于每一种管理理论或管理政策之中。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主要围绕“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观点而展开,与此相应,“德治仁政”和“严刑峻法”就成为两种对立互补的政治统治主张和社会管理政策。正如“新生的管理科学事实上只是古老的治理艺术在当代的延续”[1]一样,传统的人性观依然是当代管理人性观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当今探求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管理模式必须面对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一、管理理论的人性观基础
人性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问题。“人性的不同概念导致对于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何以能够做它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2]对人性的不同信念即人性观必然反映在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之中。所以,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总是以一定的人性观为前提的,管理理论更是如此。
管理是通过他人达成组织目标的活动。任何管理都是对人的管理或由人来进行的管理,也是利用人性的管理,人始终处在管理理论的中心位置。麦格雷戈说:“每个管理决策和管理行动的背后,都有一种人性与人性行为的假设。”[3]人性假设是对人的本性和共有行为取向的认知与判断,也可以称之为人性观。纵观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百年历程,各种管理理论都是从特定的人性假设或人性观出发,逻辑地展开其管理理论构建的。如以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都把人看作“理性经济人”,主张通过严密的组织结构、严格的规章制度、明确的职位分工、有效的物质激励等管理方式控制人的行为;而以梅奥、马斯洛为代表的行为科学理论则把人看成“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主张通过情感关怀、参与管理、充分授权、工作丰富化等管理方式激发人的积极性。麦格雷戈总结性提出的“X理论”、“Y理论”两种不同的管理理论则充分揭示了人性与管理的内在关联。埃德加·沙因对管理理论中的人性观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出广为流传、已成经典的四种人性假设,即“理性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4]49。当代管理理论对人性的丰富性、层次性和可变性的认识愈益辩证,它不再追求固定不变的抽象人性,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人性及其变化探求更为有效的管理方式。
人性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先秦时期的儒、道、法、墨等各家都有对人性问题的独特认识。尽管各家各派的思想观点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对立,如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的“修己安人”、“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利人”,法家的“唯法为治”,兵家的“运筹定计”、“应敌而变”等,但各家学说最终的落脚点则是共通的,即“富民安邦”、“平治天下。”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所以,中国传统哲学整体上具有鲜明的政治管理或社会管理哲学的意蕴。冯友兰曾明确指认“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5]25这样,传统哲学的人性观实际上成为先秦各家学派构建治国理政的思想主张和实践策略的理论基础,韩非子就明确地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所以,传统哲学的人性观也是一种管理人性观。如儒家“为政以德”的道德管理与孟子的性善论、“礼法合一”的和谐管理与荀子的性恶论,法家“循法而治”的制度管理与韩非的“自为”人性论,道家“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与老庄“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等,都是基于人性观而形成的管理思想。其中,儒家、道家、法家之间的“不同而和”与协调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面貌。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历来是传统中国哲学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5]80,也是贯穿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的中心线索,对中国传统管理之道影响深远。
二、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中的善恶之辩
中国传统人性观的善恶之辩肇始于先秦,孟子时就有“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善”四派之争。 (《孟子·告子上》)自《国语》提出“忘善则恶心生”(《国语·鲁语下》)开始,先秦诸子各派、两汉经学名家、魏晋玄学名士、隋唐佛学名僧、宋明理学名贤都曾阐论人性善恶问题,并由此提出治国理政的管理主张。这里,笔者仅就先秦时期的“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四种典型人性观进行讨论,以展现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的主要特征。
(一)性善论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中国人对人性的这种朴素认知源自儒家性善论的深远影响。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子对人性的善恶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他只是肯定人具有相近或相似的本质,由于后天环境习染和教化不同,才有了品性上的差异,因此人性是可变的、可塑的。但是,在孔子对“仁”、“义”、“忠”、“恕”等人性品质的推崇中,包含着对人性为善的肯定。①正是基于对人性的正面评价,孔子才明确提出了“修己安人”、“为政以德”的德治主张,奠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调。
孟子是中国传统人性观中“性善论”的代表。在他看来,人性是人的天性,是人的本初才质,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天生的生命本能,即形质神貌。孟子说:“形色,天性也。”(《孟子·尽心上》)又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二是天生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下》)这种“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与良知(即仁义)构成了人的本初才质,也就是人的天性。
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高于禽兽,不在于人具有形质神貌的生命本能,而是根本在于人所独有的道德良知良能,它们构成人后天道德践履的“善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进一步说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里,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相对的是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而且它们“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道德善端是人人生而皆有的善性,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当然,人性善端虽然为人的道德善行或圣贤人格提供了“可能”的理据,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或道德境界还是要取决于他能否自觉扩充自己内心的善性以及扩充的程度如何。孟子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途径:一是认识人性善的道理。“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下》)人性有其所以然之故,只有明白人性之所以为善的道理,才能顺其自然而不断实现自我道德完善。二是自觉保存善心、培养善性。“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有意识地扩展善端、修养身心,就能使自己的道德践行符合天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里,孟子提倡的尽心知性知天,着眼点都在于强调人在道德修养上的自觉性。
孟子依其性善论而提出了善教与善政的管理之道。[6]“善教”,即修养心性,方法是“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唯有将人的物欲减少到最低限度,才能恢复人所失去的善性本心。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管理中的自我管理。“善政”即“仁政”,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强调统治者要行“以德服人”、“尊贤使能”的王道政治,“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是儒家“为政以德”道德管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性恶论
儒家的荀子是“性恶论”的最早提出者。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性是人先天就有的自然本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这里的人性具体是指人的利欲之心。“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既然人人都有“这种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的感性欲望,自然会追逐利欲,从而导致社会上争夺、残贼、淫乱、暴虐等现象发生。所以,恶是人之本性,善是后天人为。社会的教化、礼义、法度就是要防止和节制人性之恶,“化性起伪”,使人向善。“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在礼义的约束之下,人们能够相互合作,有秩序地进行生产和生活;对于那些不学礼义、不自觉按礼义行事的人,则必须用刑罚来制服。这样,荀子基于性恶论而提出了礼法兼治、王霸并用的治国思想,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社会阳儒阴法统治模式的思想始基。
传统管理人性观中性恶论的代表是法家。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在力行变法、“为秦开帝业”的商鞅。他从人性的自利论证法治的必要:“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就是说,好逸恶劳、追名逐利是人的本性。针对“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商君书·错法》)的特点,商鞅为统治者开出了以“导之以利、刑之以法”为核心的“垂法而治”的统治之策。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他继承老师荀子的性恶论,提出了更为明确的“人性自利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败矣。长行殉上,数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难二》)他甚至极端地认为“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就是说,连有血亲关系的父母与子女之间都只有利害计算而无亲情友善,何况君臣、主奴等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韩非子从当时的经验中观察到,“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妊,然男之贺、女之杀之者,虑其后便,计其长利也。”(《韩非子·六反》)韩非子还强调指出,人的这种本性是天生而非后天学习得来的。“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韩非子·显学》)这里的“智”,仍是人的自利算计之心。基于人性的“自为”“好利”,韩非子认为,君主要驾驭臣下、控制百姓,就必须用刑赏法治来应对臣民趋利避害的本性。“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定法》)“法者,王之本也。”(《韩非子·心度》)他竭力反对儒家的“以仁治国”,主张“以法治民”,系统地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国家管理思想,“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为传统社会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当然,在韩非子那里,真正发挥管理效能的其实是“君人南面之术”(《韩非子·内储说上》),即统治者对客观之法的主观运用策略,而最高统治者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就此而言,法家的“法治”不是当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而是君主即统治者的“以法治民”,本质上仍是“人治”。
(三)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
性有善有恶论是与孟子、荀子同时代的世子(名硕,生卒年不详,为孔子弟子的学生)提出的。《汉书·艺文志》记载,世硕著有《世子》21篇,但书已佚亡,世硕的思想是根据王充的《论衡》而流传下来的。世硕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情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论衡·本性篇》)这里的人性有善有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性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质性,有“善”和“恶”的差异,这使得人后天的思想行为有向着两种方向发展的可能。因此,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善恶道德差异都能从人性中找到缘由。但人性中的善质与恶质具体是什么、人为什么生而具有善恶质性等问题,尚无确切资料证明世子对此有详细论说。二是人的后天善恶道德形成的关键在于“养性”。如果一个人能够把握自己的善性并加以培养扩大,就可成为有德的善人;如果一个人放纵自己的恶性并任其蔓延,就可能成为无德的恶人。世子有善有恶思想实际上强调了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以及社会教育在道德养成中的作用。所以,王充称赞说:“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唯世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论衡·本性篇》)
与世硕相对,告子(公元前420—前350,名不害,稍早于孟子,著作亦遗失)提出了性无善无恶论,在先秦人性论争辩中成一家之言。告子也认为,性是人天生而有的资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生之谓性。”(《孟子·告子上》)人的这种自然资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饮食男女之欲。“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这是人的生物本能。二是人的仁爱之心。“告子曰……仁,内也,非外也。”(《孟子·告子上》)这表明,仁爱之心也是人的天生资质,而非外力所加。但是,告子并没有把食色之性等同于恶,也没有把仁爱之心等同于善,而是主张人的道德善恶都是后天形成的。根据孟子的记载,“告子曰:性无善无恶也。”(《孟子·告子上》)告子以水为例予以形象说明:“性犹湍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人性的善或恶,就像水的东西流向一样,是环境熏陶和后天教育的结果。东汉王充在评价告子这一思想时指出:“夫告子之言,亦有缘也。”“不善不恶,须教成者也。”(《论衡·本性篇》)显然,告子的人性论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了人之仁爱之心的天然存在,但告子通过将仁爱之心与道德品质相区别,从而更加突出了后天的教育和道德修为的重要性。
三、对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的评析
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独特性看,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高度重视人性问题的,认为管理最根本的是要发挥人的作用,强调“因人设事”、“事在人为”,是一种“以人为本”②的文化管理理论。这与西方管理以“事”(效率)为中心、“因事找人”的科学管理理论明显有别。[7]所以,相信人的精神和道德力量,重视对人的精神引导和道德教化,重视培育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团队意识,着力提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道德自觉与自律,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特质。中国式管理,首要的是一种自我道德管理,所谓“以人为本”,最根本的是以“人心、人性”为本,重在“修己安人”、引人自觉。所以,尽管先秦儒家基于性善的“为仁由己”的“德治”或“仁政”因其理想性而难以成为现实社会的管理政策,而法家基于性恶的“唯法而治”的“法治”也因其严酷性而为统治者所诟病,中国传统社会在不断试错中最终确立起反映性恶兼容性善人性结构的“阳儒阴法”或“儒表法里”的统治秩序或管理模式;但是,儒家以人为本、注重道德自觉自律的思想却对后世中国社会的管理之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孔子说的“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论语·哀公问》)。
从中西管理人性观的差异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型文化或“德性文化”,在人性观上的表现是侧重于从价值(道德)评价的角度阐释人性。这与西方管理理论有明显的差异。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主要从人的“自然”或“客观”角度理解人性及其行为,无论是“经济人”、“社会人”,还是物质利益、社会情感甚至权力追求,都是从人的需要的角度来阐释人性,因而认为人性是“价值中立”、无所谓善恶的,也是不可改变也无须改变的,管理只能顺应和加以利用,即通过满足和提升人性需求激发人的动机、引导人的行为。正如德鲁克曾说的,管理者的任务不是改变人性,而是如何利用人的长处为组织绩效服务。中国传统管理思想重在从人的“道德”属性界定人性及其内涵,无论性善、性恶,还是有善有恶、无善无恶,以“善恶”表达人性本身就包含着明确的道德评价意味,着眼点在于人性是可以改变的,通过礼仪教化,可以使人达到向善的目标,进而通过有德之人实现社会善治。这对孟子这样的性善论者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即人生而具有的善端使“善教仁政”成为可能;即便是荀子这样的性恶论者也认可“化性起伪”,即人天生的恶性使“隆礼重法”成为必要。因此,中西方人性观及其管理方式各有其特点和问题:中国传统管理重在塑造人性、抑制物欲、成就人格的德性过程,但往往忽视效率或效果;西方现代管理重在顺应需求、提供激励、制度规范的理性过程,但又过于功利或机械。从管理实践的角度看,管理唯有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性特点而构建与此相适应的管理模式,才能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开发人性潜能的效果;从管理理论的角度看,只有在充分认识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与西方管理人性观的差异与互补特征的基础上,才能促进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创建中国式管理理论奠基。
从管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看,儒家人性观重在对管理者人性的判定,“仁、义、礼、智、信”首先是对管理者素质的要求,即为政以德、推己及人,就是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然后以自己高尚的德行引导和激励被管理者的道德行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一个通过管理者的“自律”而达到被管理者的“自觉”,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内圣外王”的过程。所以,正己正人、修己安人既是伦理,也是管理,而且是更自觉更有效的管理。而现代西方各种管理人性论重在对被管理者个体人性的判定,据此寻求控制和激发被管理者行为的管理制度或方式,如“经济人”基础上的物质激励、“社会人”基础上的情感沟通、“自我实现人”基础上的工作挑战性等。儒家管理的特色在道德管理、自我管理,西方管理的重点是制度管理、管理他人。这是中西方人性论的不同所带来的管理方式的重要差异。当然,当代西方管理理论与实践呈现的柔性化、人文化以及重视价值观引导、伦理领导等趋势,又凸显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特别是儒家道德管理弥补西方管理人性论中德性伦理缺失的实践价值。
从人性的具体内容看,人性不是抽象的、思辨的凝结物,而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人们的需求、动机、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组织的成长,更重要的是随着个体的成长与发展,而发生改变。”[4]43无论从社会环境分析,还是组织成长状态与阶段分析,抑或是从组织成员个体分析,都应该从具体、系统、动态的观点把握人性和人性需求,把人性看成不断生成的、向未来敞开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为构建有效的管理方式提供恰当的人性基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中的有善有恶论、无善无恶论对人性的具体性、可变性的认识,尽管有些简单直白,但更接近真实的人性,类似于西方管理人性观中的“复杂人”假设,可以为把握现代社会复杂可变的人性提供参照。随着当代组织环境的复杂多变性和组织成员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试图再像以往那样寻求一个稳固不变的人性假设,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也无论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都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当今复杂多变环境下的管理变革,要求超越中西传统管理人性观的思维范式,回归现实的人性和人的需求,在对多样人性及其文化表征的具体把握中,探寻卓有成效的管理之道。
注释:
①徐复观认为,孔子虽未言明“仁”即人性,但他认定仁为内在于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内,仁乃是善的极致,可以推知,孔子实际是以仁为人生而即有、先天所有的人性,因而是性善论者。(参阅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
②“以人为本”最早出现在《管子·霸言》中:“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1]杰伊·M·沙夫里茨.公共行政导论[M].刘俊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1.
[2]莱斯列·斯蒂芬森.世界十大人性哲学[M].施忠连,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
[3]道格拉斯·麦格雷戈.企业的人性面[M].韩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3.
[4]埃德加·沙因.组织心理学[M].马红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葛荣晋.中国管理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1.
[7]曾仕强.中国式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