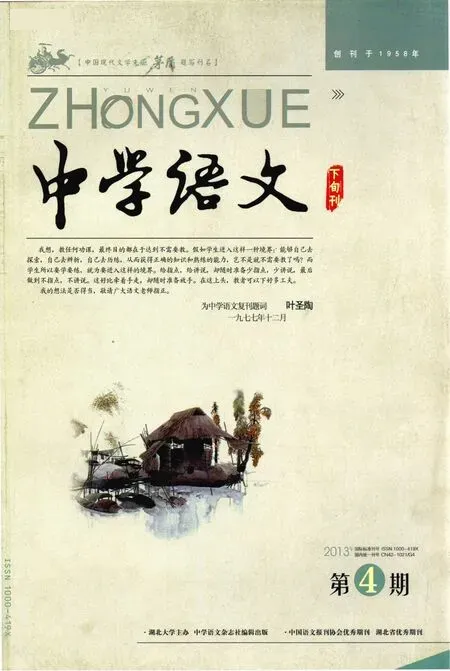把教学还给教师——徐江教授阅读教学思想启示录
韩建飞
上世纪末以来,语文教学一直遭遇“高耗低效”的责难。这种责难并没有随新课程标准的推出与实施而减少。在最近几年对语文教学的质疑者当中,徐江教授是影响较大者。
一、阅读教学不是“学生在阅读”
针对阅读教学“学生主体性”的论调,徐教授这样认为:
阅读教学不是“学生在阅读”,而是“学生学阅读”。……阅读,本身是人作为人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方式。在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中,人还要以这种方式为手段获取其他的生存资本,使自己的生存更完善。学生,作为尚未独立生活的社会成员,在学校里接受阅读教育,参与阅读教学活动是为了跟老师学习有关阅读这一存在方式所必备的规律知识和技能知识。即使他们在这一阅读教学活动中有“阅读”行为,比如阅读课文,其实那是“学阅读”活动中的一种形式。当然,在“学阅读”这种阅读教学活动中,具体的文本所有的各种积极内涵会作为一种积累储存于学生的脑库中。但这种积累还是有限的,因为他们三年下来所学课文不过百十篇而已。所以,他们在阅读教学活动中,其本质任务是“学阅读”,即学习有关阅读这一存在方式的规律和技能。
而“在阅读”强调的是这一群人就存在于这个阅读方式中,或通俗地说这一群人正以阅读这一方式活着。这种做法,使这群尚未独立的人提前进入成熟成员社会性阅读存在方式,看似是积极的,主动的,但他们失掉了重要的“学”的特性……收获是微小的,进步是很慢的。学段愈低,问题愈大。
学生“在阅读教学活动中,其本质任务是 ‘学阅读’,即学习有关阅读这一存在方式的规律和技能”。徐教授的这一说法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根据学生心智发育的阶段性和学习的实际情况而提出,有矫正“教”的分量不足、“学”的效率不高这样的时弊流俗之意。而“学生在阅读”的提法则剥夺了学生“学”的权利,结果往往是不自觉的同学不动脑耗时间,自觉的同学在浅层次上徘徊思考,收效甚微。这样让“学生在阅读”,成绩也许会不错,而对学生的成长而言,是很成问题的。这里面涉及考试评价方式的转变问题。语文考试的命题增加开放题型这一方向没错,这就要求阅卷者有足够深厚的语文素养、足够准确的研判力。
关于素养,我认为不能限于语文素养,最起码还得有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比如《〈论语〉选读》的教学。我们当然要吸取其中为人处事的智慧,但也要注意到孔子及其儒家的学说落脚点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和利益的,儒家后来为封建统治者利用的意识形态工具,以及“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无不说明这一点。这时,有批判意识很要紧,而具有现代公民意识更要紧,否则你怎么能做到批判地吸收这一点?
二、教师要讲述自己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针对“阅读教学不是语文教师讲述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和感受”的说法,徐教授认为教师要讲述自己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教”有两层意思:一是教者要努力给学生带来可学的;二是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努力”是指一个教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他要有对教育事业、对学生负责任的职业意识;“带来”,就是在阅读教学中有他独到的研究;“可学的”,就是值得学生去学的东西。
目前语文界,阅读教学的教学内容为四大类:一是所教内容根本就是错的;二是所教内容虽是对的,但却是无用的;三是所教内容是对的,是有用的,但却是学生自读即会的;四是所教内容是对的,是对学生发展有用的,学生自读不会的。我这里所谓的“教”就是指第四种内容,并且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教师要大胆地向学生讲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感受,这些理解和感受是学生自己阅读不可企及的,而且对学生有积极意义,值得学。如果教师做不到这样的“教”,那么,他就不是一个适应课改需要的语文教师。
《课程标准》指出,“教师既是与学生平等的对话者之一,又是课堂阅读活动的组织者、学生阅读的促进者。教师要为学生的阅读实践创设良好环境,提供有利条件,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判质疑,发表不同意见。教师的点拨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自己的分析讲解代替学生的独立阅读。”这里实际上学生处于教学的主动地位,教师处于被动地位。这样做改变了传统教学中教师强势控制课堂的态势,但也弱化了教师的作用。而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每堂课都如此。把学生的阅读积累想得太理想,把学生的理解水平想得太高,把阅读过程想得太完美,都不利于阅读教学顺利有效地进行。这里涉及三个概念——“教师”、“学生”、“教学”。 让我们回到原点,“教师”是教人的老师,“学生”是求学的人,“教学”是教师教学生学。教学相长是理想的教学状态,但首先一定要有教师的“教”,否则不能算是“教学”,而是师兄弟之间的切磋。“点拨”是学习者的水平处于相当高的层次上的点醒,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大多数同学而言是不合适的。尤其在各个学校或者同一学校不同班级之间生源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一律让学生自主学习呢?教师的深刻理解和体验不能代替学生的理解和体验,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可以传达给他们,这自然就需要方法。教师可以引导甚至传授,也要与启发、自主相结合,双轨运行,尤其是对中等偏下的学生而言,不能仅仅满足于低层次、低思维值的自主阅读,可以通过教师的启发引导甚至讲授提高自主阅读的层次,比如经典文本《拿来主义》很难通过自主阅读来获得其中的深蕴。总之要结合文本、学生学情而定。
三、关于教学内容的选择
徐教授是这样表述的:
“以特定文本使用者所在学年段教育目标为依据,以文本所能有的为选择范围,以相对教育值高为选择标准,选择文本所蕴相对于教育目标之达成有较大促进作用的内容为教学点。”
学情 对于“以特定文本使用者所在学年段教育目标为依据”,比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初一学生只要能读出其中的孤独与寂寞感,读出李白对敬亭山的喜爱也就可以了;高一学生,还要读出这种孤独与寂寞所自何来,以及“相看两不厌”所蕴含的哲理与禅意。我们从学生情况出发去备课的话,除了王教授所说的三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三句:一是要思考从这篇课文当中能衍生出一点儿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二是要思考从这篇课文里汲取一点儿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不能满足于让学生“读懂”它、“读好”它,而是要思考学这篇课文要用它一点儿啥;三是思考在现实生活、学习中怎样把这些从文本中所得到的东西用起来。概括说,根本的学情是认识“学什么”、“用什么”、“怎么用”。这也是由“教”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真正的生存实践智慧这一点决定的。从学情的角度去看“文本所能有的”的选择范围,“文本所能有的”既包含“文本所有的”,也包含文本“能”启发读者创造所有的。
认定根本的学情是“学什么”、“用什么”、“怎么用”,就是以特定年段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生发文本中有用的东西。比如在教学《我与地坛(节选)》一文时,可以适时拓展这样的问题:“你从史铁生身上学到了什么——假如你身处困境,你该如何自处?”通过思考讨论,能让学生叩问人生,明白每一生命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份生命的喜悦和感动这样的体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像他那样感受、品尝、体会大自然的美,读懂自然,从中获得生命的启示。这就不是一堂课的问题,而是一生受益的问题。这样的课就是大大超值的。当然在“以特定文本使用者所在学年段教育目标为依据”时,要注意高年段学生低年段水平问题,特定文本使用者所在学年段教育目标不是确定“学生学情”的唯一依据。对于我们老师而言,最好通透文本内容,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教育值 对于教育值的问题,其实是关于应教与不应教的问题。因为文本解读既然有选择问题,就意味着并不是“文本所能有的”任何内容点都可以作为教学点,都是适宜的。我们不要把“教育解读”或者说“解读教育”与常规人们的自由解读混同起来。这是特定的解读,所以,我们的选择应该是能对教育目标之达成有较大促进效应的内容。
在正常的语文教学范畴内,诸如文本解读、写作、演讲等等语文教学活动,凡属于学生发展需要的而他们自读自学又搞不明白的,就是“应教的”。学生发展不需要的,肯定是“不应教的”。即便是学生发展需要的,但学生自己能搞懂同样也是“不应教的”。
徐江教授并不完全反对以文本体式来选择教学内容,但他认为仅仅以此为依据就有点固步自封了。“我们应该奉行这样的原则:在探索事物的过程中,方法论视野应该不断开拓,应该接纳一切具有积极意义的方法论元素。”如,关于《背影》的教学。徐教授认为大部分语文教师强调的内容都是 《背影》文本内容是什么的“说明性”解释。作为《背影》的教学内容应该是“父爱伟大”和“难忘父爱”,再就是“怎样”表现这些内容。由于“父爱伟大”和“难忘父爱”这些内容学生初读即可理解,所以,它们都不是教学重点,课堂三言两语点一点也就可以了。而应该把文本“怎样”表达这些内容作为重点,这就是“解构性”教学。
形象大于思想,文学形象往往超越作家塑造这个形象时所意识到的思想意义。文本就内容而言,有浅显与深奥之分,教师对教学文本的处理一般是深奥文本(如哲学文本)浅显化,深入浅出,浅显文本(如新闻报道)深奥化,浅入深出。
以文本体式选择教学内容是形式确定教学内容,以哲学思维来选择教学内容是形而上确定教学内容。走向哲学思维,这里有个难度,要求教师铺好路,光是一些哲学概念足以吓到学生,更遑论走向思维。
强调哲学解读,培养学生智慧的过程中并未弱化能力培养,不用担心走向非语文教学。其实我们必须要正视的问题是有些课堂上不怎么听的学生也能取得较强的语文能力,考试也能不错。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语文的外延非常广阔,涉及各门各科乃至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地为牢,固守语言,排斥它类,是打不开语文教学的新局面的,反而可能提不起学生的兴趣最终连语言也学不成。要知道,语文教学本质上是语言教学,也是一种思维教学,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并重的教学。
文本体式说其实包含读写结合的理念,认识文本问题为写作提供借鉴,这也是阅读教学的目的之一,光是写作教学是教不好学生写作的,必须通过阅读,读写结合。
四、关于文本解读
要把被文本给予的东西变成被我们思维的路径和方法。按照文本体式去选择教学内容必然会导致按照文本体式解读文本。对于《安恩和奶牛》有的老师根据小说体式去解读,必然得出类似于“安恩是一位比较清贫的却富有仁爱之心老奶奶”这样的结论,安杨华老师认为这样的结论只回答“是什么”的陈述性知识,而这种非概括性的陈述性知识是无法转化成学生的智慧的。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教学就是一种无效教学,至多是低效教学,停止在“知”的层面。而徐江教授主张引导学生探究类似于“安恩为什么会好心办尴尬事”、“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行为更为合理”这样的旨在回答“为什么”“怎么办”的程序性知识,而程序性知识的获得才是发展学生能力、启迪学生智慧的关键,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教学才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的教学,其根本性的特点是落实于实践。
如果我们满足于充斥着“是什么”的课堂教学,那么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的“底子”是肯定打不好的,即使课堂上学生和老师你来我往,对答流畅,那也是伪对话。低层次的阅读教学探讨只能浪费大家的时间,一旦这样的探讨成为教学探讨的常态,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而“为什么”“怎么办”才是我们阅读教学的落点,这样的问题探讨才能真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真正促进学生心智的生长和成熟。当徐教授从空间意识的角度解读《安恩和奶牛》,让学生能够认识到“安恩不能仅仅从自己和奶牛的关系出发去到牲口交易市场‘散散心’,自己的规则只有在公众的规则之下才是合理的”这样的道理时,他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就已经得到了提高。如果学过的每个文本都有这样的一得,显然也是很可观的一种积累,这样的“底子”算是夯实了。
徐教授还认为:
我们不但要把“被给予的东西”中所含精神意识的东西提取出来变成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要把“怎样”给予的“运行机制”也变成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要特意提醒读者——把 “被给予的东西”变成认识的方法——这句话本身就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它告诉人们面对所得到的东西还要作进一步的提升。在这里我们便把它作为阅读的一种解读方法,或者说原则——把“被”文本所“给予”的东西转变为自己的认识的方法。当然,还需要读者有较好的“转变”能力。比如上面所提到的认识对象的方法:“空间意识”和“联系思维”。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徐江教授在和赵建晖老师合写的 《在叙事性联系中品读 〈雷雨〉》(《中学语文教学》)2012年第5期)一文中提到:
……在这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对金钱和地位的贪欲会泯灭一个人的人性,往往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悲剧。但金钱和地位等等身外之物却是夏夜屋内的油灯,而人则是扑火的飞蛾。油灯不灭,总是有飞蛾前仆后继而来。这是一种社会现实。《雷雨》是对周朴园式的人物进行鞭挞的寓言,以“雷雨”对他们进行警示:他们制造了一些事情,随之,后续其他事情发生了,甚至故事中充满宿命论式的因果报应氛围——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同时,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侍萍也予以讽喻。她虽经历了生死考验,但对为富不仁者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只是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会丢弃对他们的幻想。当她意识到是在周公馆时本应携鲁大海主动离去,至少免得第二次受辱。
作者或者说故事本身——周朴园、鲁侍萍一家人“分离”与“再分离”——告诉人们:只要能确定目前讨论的事件中的条件是什么——如周朴园的人性泯灭,那么,假如对于将来的事件人们能够确认有相似的条件存在,则可预见相似的事件还会发生。灭绝人性,违背人伦是要受到谴责的,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假如对于将来的事件人们能够确认有相似的条件存在,则可预见相似的事件还会发生”,这既是认识的结论,也是认识的方法,在推理上可以算是类比推理。徐教授的阅读教学理念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就是他不仅要把自己深刻的理解和体验“教”给学生,而且要把自己如何思考的思维轨迹、思想方法“教”给学生,让学生能够随时运用方法论的武器解读文本,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知道自己面临问题时该如何解决。假设鲁侍萍是徐教授的学生,她如能学以致用,就绝不会出现后面的悲剧。“授人以鱼”,以加强学生的积累;也要“授人以渔”,以加强方法论的指导,直奔他“致用”、“立人”的目的。
文本是用来质疑的。面对文本,语文教师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一般的读者,可以处于自由的阅读状态而与文本互动、沟通,那种状态往往是随意的、多样的、不确定的。而语文教师则是借助文本这个载体,来完成他的教学目标。所以,教学中的教师为最终实现教学效能的最大化,他往往要对文本做能动的开发,惟其如此,“最大化”才有保证。
教师在对文本进行二度开发时,除了对文本的隐性价值进行合理的阐释外,也可对文本的内容进行质疑。比如,在季羡林《幽径悲剧》一文中有这样一处:“抬头一看,在一团团的绿叶中——根本分不清哪是藤萝叶,哪是其他树的叶子——,隐约看到一朵朵紫红色的花,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味。”有一位名师给学生评析说“的确很美”。徐教授以为这是很糟的描述。前边说“一朵朵”,后边说“万绿丛中一点红”。“一朵朵”与“一点红”是矛盾的。
面对教材文本,我们老师缺少质疑的精神,只会按近乎完美的“好”来分析,包括语言的表达、结构思路、甚至是标点符号。这就是“认同式教学”:先无条件肯定,再由此具体分析。只讲文章好在哪,语文认同式教学带来了什么?那就是在文本权威和教师权威下,学生质疑精神的丧失,阅读个性的泯灭。
徐教授的态度是,搞课改当然是“我主教材”。他曾对经典文本《拿来主义》提出两点质疑:
(一)喻体选择质疑
根据文章开头所提出的写作背景,鲁迅先生在阐述“拿来主义”时所选择的例据应该与之相呼应,相平衡,这是文章写作应该遵循的原则。那么,与送“古董”、“挂”国画、送梅兰芳博士等背景论“拿来主义”应该选择从外拿来的东西为宜,比如与画相对介绍毕加索的抽象主义画作吧!讲一讲我们应该学人家一点什么,甚至还可讲一讲毕加索的抽象主义画法是否适合我们的审美欣赏习惯等等。
但是,鲁迅先生所选是某青年对待“大宅子”的问题。虽然,这“大宅子”里有一点儿洋货——“鸦片”——但这不是“拿来”的,是人家“送来”的,况且是在“大宅子”里面的。这就是说以如何对待“国货”系统的东西来阐释“拿来主义”,“大宅子”、“姨太太”使人想起山西的“乔家大院”或者“王家大院”,这样的喻体就背离了原来的写作背景,产生了前后不对称的问题,因而未能充分地、恰当地阐释“拿来主义”。
甚至有些读者认为对待“大宅子”的问题是如何对文化遗产的问题,由此大论特论《拿来主义》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错觉就是所选喻体——“大宅子”——这一国产货连带产生的。以国产货为喻去论“拿来主义”显然有南辕北辙之嫌。因此,由于喻体的选择失当导致了整个文本主旨发生扭曲,前后文章不协调。
(二)“不管三七二十一”质疑
鲁迅先生在以“大宅子”为喻解释“拿来主义”时,这样说——“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我以为,一般来说“拿来主义”首先就要考虑“拿什么”,就得弄准“三七二十一”之后才能“拿来”。在未拿之前,“要运用脑髓,放开眼光”,去“挑选”拿什么。比如“抢来的”或者“骗来的”还是不要“拿”的好。所以说,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逻辑上有点儿矛盾。
徐教授认为文本就是用来质疑的,以此来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和批判精神。但是批判的前提是真正弄懂文本。
质疑是对方的说法确实有错你才能提自己的看法,最起码是有争议,但你要学生接受你的看法,必须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教师的权威去压人,更不能以错误的看法引导人,比如李白《春夜宴桃花园序》一文,你从“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中读出人生短暂、光阴易逝的感受,结合后文“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两句,你认为本文起笔“抒发悲观、低沉的情绪”,这种说法就有待商榷。仔细品味“逆旅”“过客”,你会感受到这里蕴藏着李白彻底的人生漂泊情怀、深沉的人生感慨,于是才在“四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具,二难(贤主嘉宾)并”的情形下宴从弟,欲抓住稍纵即逝的美好时光。而后下文的“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也就很好理解了。“悲观、低沉”云云显然不合适。这就首先要求教师要有相当高的语文素养,练就一双慧眼,不能把白当黑,胡说八道忽悠人。其次要精研教材,不要光从好的一面去寻找其教学价值,不好的一面也可以。即使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文本,因为我们不知道修改到何种程度才是最完美的。当然不能为了质疑而质疑,质疑也要看是否符合教学的需要,也要有设计,使之成为推进有效教学的一个环节。
结语
以上我们梳理了徐江教授的阅读教学思想:教的根本目的 (培养学生真正的生存实践智慧——教是需要的——有学的需要)—→关于教学内容的选择(关于备课——教什么)—→关于文本解读(包括质疑——教什么的前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徐江教授的改革语文教学现状的心情是迫切的,研究的思路是清晰的,批判是有深度的,也是切中肯綮的。他“颠覆”的是错误的教育观念,“破坏”的是不恰当的教学理念。对此惊慌不安或者不屑一顾都不是正确对待批评的态度,只有静下心来观照,反思,深思,三思,不仅看到徐教授“颠覆”了什么,“破坏”了什么,还能看到他“匡正”了什么,“建设”了什么,我们就会有所收获。在我看来,他的阅读教学理论看似与王荣生教授的相左,实则是一种完善和修正,而不是全盘否定。在文本解读上徐教授主张运用哲学思维,在阅读教学理论批判和构建方面我们再次领略了他独到的思维品质。
徐江教授的阅读教学思想从教学本原出发,以教师素养的提升为中心,以服务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为宗旨,教学不忘教育,致力于超越现有的语文教学依据,以改变目前语文阅读教学仍然存在的高耗低效的现象。徐教授曾引用的加拿大教育哲学家巴罗所说的一句话——“把教学还给教师”是切中时弊的。是的,把教学还给教师,让教师切实承担起教学的责任,努力发展自己,提升自己,少一些花哨噱头,多一点觉解实在,那样我们的语文教育必定能再次迎来教学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