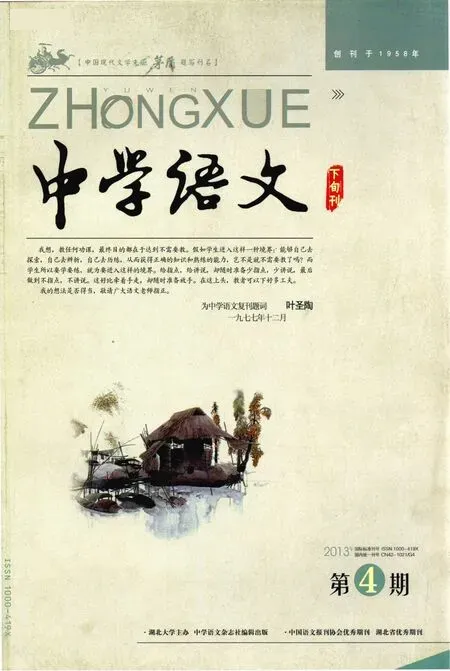怪也不怪——也释“其可怪也欤”
楼小燕 赵火夫
《师说》“其可怪也欤”句的译文可谓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常见的就有以下五种:①这真值得奇怪啊!②真可(或“值得”)奇怪啊!③这不是很奇怪吗?④难道不值得奇怪吗?⑤“哪里值得奇怪啊?”或“难道值得奇怪吗?”前四种意思基本相同,可统称为“奇怪说”,第五种意思与之截然相反,可称之为“不怪说”。笔者认为,“不怪说”比“奇怪说”更科学,更正确。
首先,从字词落实来看
“奇怪说”几种译法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问题。(1)把“其”译为“这”,不太妥贴。“其”作为指示代词单独使用时,大多为远指,译为“那”、“那些”,鲜有作近指的,因此,译作“这”,难免给人突兀的感觉。(2)去掉了“这”,不知是因为“其”很难落实就避而不谈,还是把“其”理解成表达感叹语气的副词而译为了“真”。前者是不负责任的作法,不值一议;至于后者,看似有理,但毕竟缺少依据,“其”表达感叹语气,还真没有见过。(3)把第一种的感叹语气转化成反问语气,意思不变,但把原文的肯定句随意地译成了否定句,不符合文言翻译“信”的原则。(4)应该是把“其”作为表达反问语气的副词讲,译为“难道”,但一个“不”字,不知从何而来。相比之下,三四两种译法比前两种更要不得。
而“不怪说”无一字不落实,无一处不妥贴。把“其”译为“难道”“哪里”,这是“其”作副词时最常见的用法。至于把“也欤”译为“啊”或“吗”,一为感叹,一为疑问,意思截然不同,但应作两可观;因为反问句也可表达强烈的感情。有人为句末应该用“?”还是“!”而争论,这是毫无必要的;而因为原句是感叹语气 (这是没有争议的)就否定“其”可以表达反问,这更是失之于偏颇了。
其次,从表情达意来看
“奇怪说”意思含混错谬,让人费解甚至误解。
先从字面上看,①-④都表达同一个意思,即:“士大夫们”轻视“巫医们”却比他们笨,这是值得奇怪的,是出乎人的意料的。其言下之意就是“士大夫们”应该比“巫医们”要聪明,“巫医们”天生就是低人一等的。有观点据此认为韩愈有轻视劳动人们的思想,这是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所致。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试想,韩愈提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主张,又怎么会因为“巫医们”地位低下而轻视他们?韩愈倡导从师学习,坚持“学使人愚,耻学使人愚”的观点,又怎么会怪讶“不耻相师”变得聪明而不学无术的“士大夫们”变得愚蠢?“抑彼”“扬此”,为了批判“耻学于师”的“士大夫们”,韩愈又怎么会不对作为参照物的“不耻相师”的“巫医们”表示首肯或暗许?可怜韩愈,蒙受了千年不白之冤,而罪魁祸首正是 “奇怪说”,是学者误译导致了读者错误的理解。
有人说“奇怪”的内容不是“其智不能及”的结果,而是“君子不齿”的态度,全句是对“君子”即“士大夫”的讽刺。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是一个表转折关系的复句,语意的重点不在偏句(前半句)上,而在正句(后半句)上。同理,其后的议论“其可怪也欤”主要针对的不是“君子不齿”的态度,而是“其智不能及”的事实结果。这个“事实结果”自然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前段已作充分论述),而且也不宜作为讽刺的对象,因为讽刺的对象一般是人(包括行为、态度、思想等)。如果把偏句和正句的次序对调一下,改成“君子智慧比不上巫医乐师百工这类人,却反而看不起他们”,那么,语意的重点就落在“君子的态度”上,作者对此“奇怪”也好,还是“讽刺”也好,都将顺理成章。
诚然,“不齿”的态度和“智不可及”的结果,形成明显的倒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大约这正是“奇怪说”的根本依据),但这是否意味着作者一定要对“君子们”进行讽刺呢?从全文的情味来推断,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对于“师道不复”的现象,作者感叹不已,深表痛心(两个“呜呼”);对于“耻学于师”的后果,作者委婉说理,语重心长(“其皆出于此乎”);对于错误的态度和做法,作者义正辞严,直言批评(“惑矣”“吾未见其明也”)。可见,韩愈抨击轻视师道的不良风尚,是为了拨乱反正,其态度是严正的,其用心是良苦的,如果出其不意地对“君子”进行冷嘲热讽,那才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有人说“奇怪说”还有“发人深思”的意味,可以让人思考“其知不能及”原因,也许这正是③④不惜背离原文而故意曲译成否定式反问句的原因吧,因为反问句比感叹句更具启发性。但是,跟“怪讶”和“讽刺”相比,这个意味太过含蓄晦涩,让人难以捉摸。
总之,“奇怪说”有太多的岐义,而且其义项或错误,或晦涩。对一篇议论文而言,语言岐义晦涩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弊病。
“不怪说”则表意明确无误,合乎情理。“君子们”的智力不如为他们所不齿的“巫医们”,哪里值得奇怪啊?这里,作者要传达的信息是没有一丝含糊的:不管你出身有多好,地位有多高,如果不从师学习,你都将会智不如人,甚至愚不可及。反问句的使用更是强化了这层意思:耻学致愚,理所当然,何怪之有?
第三,从文章主题来看
全文中心是提倡从师学习,本段主要围绕段首“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两句,从反面展开论述:不从师学习使人无以解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批判“耻学于师”的社会风气,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也不是简单地表达对士大夫之族的愤懑,而是为论证“要从师学习”的中心论点服务的。如“其皆出于此乎”指出“愚人之所以为愚”的根源在于“耻学于师”,“惑矣”是对“众人”“于其身也,则耻师焉”的批判,都是紧扣中心展开议论的。
“奇怪说”却游离于主题之外,表现无力。它的第一层意思是对“耻学于师”的“君子们”智力不如“不耻相师”的“巫医们”表示怪讶,明显与文章中心背道而驰,离题万里。第二层意思是讽刺“君子”,但真有讽刺的话,这里也只能理解为着重讽刺“君子不齿”的态度,而不是针对其“耻学于师”的态度,这与中心似即实离。至于第三层意思(发人深思)因为其本身的含蓄、隐晦、歧义,导致与中心若即若离。
而“不怪说”紧扣中心,论证有力。在拿“巫医们”“不耻相师”与“士大夫(君子)们”“耻学于师”的现象作对比后,作者针对“地位高的后者不如地位低的前者聪明”的事实结果进行议论:哪里值得奇怪啊!这样议论遵循着作者一贯的逻辑思维:“好学必然使人智慧,耻学必然使人愚笨”,从而成为文章中心的最有力的支撑。
最后,从上下文连贯来看
“奇怪说”与前句难以连贯。“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君子不齿巫医们却知不及人,真是值得奇怪啊!”(或“不是令人奇怪吗?”)前后两句意义上缺少明显的联系,语气上也难有通畅的感觉,可谓意断气阻。
其实,前句表面感叹“师道之不复”,实则揭示耻学之风盛行的根源在于在上位的士大夫之族(即君子)耻学之习根深蒂固。接下来直接点明“君子”智不如人的事实。两者是前因后果的关系。而“不怪说”正是对这种内在关系的揭示和评价:君子耻学不改,师道不复可知,(至于)其智不如人,也就不足为怪了。显而易见,这比“奇怪说”要连贯通畅得多了。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