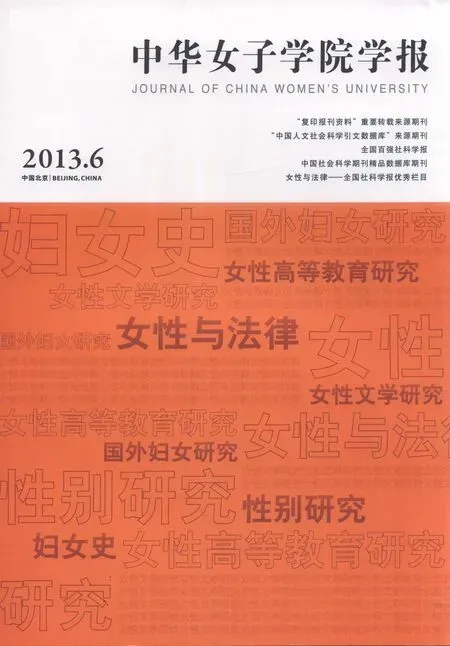人身保护令准入反对家庭暴力立法维度的困境与对策
李秀华
人身保护令准入反对家庭暴力立法维度的困境与对策
李秀华
在司法实践中,人身保护令是有效制止家庭暴力立法对策之一,但在制止家庭暴力及其执法方面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如缺乏综合、协调性立法系统,未建立有效的干预机制,举证责任制度构建困难等。因此,实施人身保护令应从建立制止家庭暴力合议庭,规范立法研究机制与合理的评估指标,完善人身保护令操作模式等方面突破障碍、改进对策,在立法与执法中,只有充分导入多元研究因素才能有效地推进人身保护令的有效实施。
家庭暴力;人身保护令;举证责任制度
一、引言
所谓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①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一条首次在立法上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家庭暴力中,女性成为权利最容易受到损害的群体。2011年,全国妇联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或性暴力的女性占24.7%,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比例为5.5%。②在国务院新闻办2011年10月21日于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领导小组组长宋秀岩代表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了该项调查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数据。调查认为,家庭暴力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对人身权利和公民尊严的一种严重的侵犯。参见陈丽平:《全国妇联积极推动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律》,2011年网络热点法治事件回顾(法律法规篇),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zt/content,2011年12月21日。2008年至2011年笔者在承担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关于“和谐社区与婚姻家庭诊所教育模式结合与功能创设”的项目时,将干预家庭暴力作为重点研究问题之一,并发现家庭暴力事件的存在成为家庭与社区和谐的隐患,如处理不当将会引发更大冲突。诸多研究显示,很多人对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手段与力度表现质疑,强调更喜欢用隐形方法悄悄处理家庭暴力事件。近年来,在探讨如何干预家庭暴力的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人身保护令的干预家庭暴力的效果受到高度关注。所谓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作为民事强制措施,是法院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做出的裁定。③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指出,人民法院做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是以民事诉讼法等为法律依据的。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首先是给当事人和社会传递了一种信息:家庭暴力不是私事,公权力要予以干预。
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制定《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审理指南》),为法院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提供了导向性指引。《审理指南》第三章专章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措施。①《审理指南》第二十三条规定,在涉及家庭暴力的婚姻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有必要对被害人采取保护性措施,包括以裁定形式采取民事强制措施,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安全,确保诉讼程序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第二十五条规定受害人保护性缺席。第三十条人身为安全保护措施的管辖。第三十一条对涉及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申请的提出时间做了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申请后,应当在48小时内做出是否批准的裁定。人民法院经审查或听证确信存在家庭暴力危险,如果不采取人身安全保护措施将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应当做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在家庭暴力公权力干预方面,人身安全保护令实现了司法理念与方法突破。其中,将人身保护令引入反家庭暴力立法系统为中国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救济措施,这在我国法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2012年3月,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发出了一份反家暴人身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曹武(丈夫)殴打、威胁、骚扰、跟踪申请人陈圆(妻子)及其亲友,禁止被申请人曹武在距离申请人陈圆现住处100米范围内活动。”[1]人身保护令使饱受家暴蹂躏的申请人陈圆及其亲友在申请离婚期间有了一定的安全感。为了保证“人身保护令”不会成为一纸空文,香洲区法院同时向当地公安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以监督被申请人对裁定的执行。如果有证据表明被申请人违反“人身保护令”,出现在禁止的特定区域对受害人造成骚扰,法院可视情节轻重对其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这是法院积极运用人身保护令的司法手段保护受害方的一项尝试,亦是法院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有效遏止家庭暴力的举措之一。2013年1月1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引入的行为保护制度使人身保护令实施有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强调,从目前司法实践看,需要通过行为保护措施有效保护当事人利益,但由于欠缺法律依据而难以实施保全的情况较多。该书指出:“在家庭暴力侵害等纠纷案件中,有时需要立即停止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实施的可能造成危害的行为。”[2]2212010年笔者提出在扬州法院系统引入人身保护令的政协提案,得到扬州法院系统的回应。目前扬州法院系统结合本土情况启动人身保护令计划且发出20余份人身保护令。“截止2012年底,全国试点人民法院已发出200多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自动履行率达98%,高居世界各国此类民事保护令之首,也居我国各类民事裁判文书履行率之首。据《审理指南》试点法院反映:绝大多数被申请人在签收人身安全保护令时,都表示服从人民法院裁定并承诺不再对申请人施暴。部分申请人因家庭暴力的停止而主动撤诉或与被申请人和解。少数被判离或调离的被申请人,也因慑于公权力而没有实施分手暴力。”[3]74笔者认为,研究发现人身保护令的制定与具体实施因国情、文化、习俗、立法背景不同有一定差异,但它毕竟带有极强的制约性与威慑力,因此对制止家庭暴力仍起到积极干预作用。事实证明,人身保护令制度彰显了法律对弱势群体生命的尊重与关注,以其仁慈的法律内涵和显著的实践效果证明其在人身保护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身保护令实施的原理在于:法院在保障人权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但目前在法院系统,全面引入人身保护令仍面临诸多挑战,如立法缺失与不足是难以有效推进人身保护令的瓶颈。在立法滞后的前提下,在相应司法举措尚未到位时,在一些法院引入人身保护令缺少有力的机制与立法的土壤支持,显然有些仓促与不成熟。显然,人身保护令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本土化,在具体操作层面应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二、实施与运行人身保护令的困境
人身保护令作为保障受害者人身自由的综合性救济途径,目的在于以公权保护方式防止公民私权被他人侵犯,从而有效保障人权。就目前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保护机制建构而言,必须了解并解构目前的法律保护难点与困境所在,才能有的放矢,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来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行为,其实施难点主要表现为:
(一)缺乏综合、协调性立法系统
尽管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审理指南》,在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上述规定过于理论化、纲要化,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审理指南》在实践中亦不能成为司法裁判的直接依据,导致司法机关难以有效干预家庭暴力。立法规范是反家庭暴力法律保护机制在世界各国确立的首要前提。以美国为例,美国法院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的最主要途径是启动民事保护令制度。美国大部分州均颁布法律,明确规定违反民事保护令的行为是犯罪。因此,要构建反家庭暴力司法保护机制,立法必须先行。为有效防治家庭暴力行为,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美国联邦及各州都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法律规范,包括《家庭暴力逮捕法》《预防家庭暴力与服务法案》《民事保护令》等。①在美国防治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民事保护令是法律赋予被害人最直接、最常用的法律救济手段。当今美国法律要求警察告知家庭暴力受害人所享有的权利及可实行的保障措施;有义务护送受害人到医疗或是庇护机构;对被害人说明如何依法定程序取得民事保护令,必要时可由警察代为申请。除人身保护令的实施,美国有关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的系统法律,为司法干预家庭暴力提供了十分充分的立法依据。加拿大许多省颁布了《家庭暴力法》和《紧急状态下保护令》,做出了有利于受害人的规定。当受害人遭到暴力威胁时,随时可打电话向警察求救,即使未获得当事人允许,警察也可以破门而入并带走施暴者。此外,加拿大许多省要求警察必须对家庭暴力案件及时做出反应,无论受害人的合作态度如何,警察都应深入调查家庭暴力案件,提交相关报告,必要时可以提起指控。在香港地区,申请人身保护令需要提供病历、照片、报警证明等表明曾遭受家庭暴力或正面临家庭暴力威胁,可在离婚诉讼提起之前、诉讼过程中或者诉讼终结后的6个月内提出,而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我国台湾地区出台了《家庭暴力防治法》,该法对民事保护令的申请、审理和执行、家庭暴力的预防及处理等做了详细规定,使得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与法制化,这样也促使相关公务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目前,我国在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上有许多举措,如《意见》重点强化了警方在反家庭暴力中的重要作用。《意见》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应及时组织受害人进行伤情鉴定,并根据家庭暴力的具体情节酌情处理。但笔者认为,无论《意见》还是《审理指南》都存在强制性薄弱、规定体系缺少统一与协调性的问题,因此难以有效制止家庭暴力。
(二)未建立有效的干预机制
处理家庭暴力,应形成由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干预机制。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居民(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妇代会等组织要认真做好家庭矛盾纠纷的疏导与调解工作,防范家庭暴力于未然;家庭暴力报警已经纳入110出警范围。公安机关要根据情节,对施暴者予以训诫或治安处罚;对于有证据表明可能构成虐待罪或轻伤害的案件,要告知家庭暴力受害人或其近亲属直接向法院起诉。必要时,司法局要给受害人提供减免服务费的法律援助。近几年,为保护家暴受害人及其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由全国各地妇联牵头建立了大约四五百家妇女庇护所,但大部分妇女庇护所都门可罗雀,无人问津。究其原因,一方面,收容式的简单庇护容易使受害妇女感到失掉尊严;另一方面,妇女庇护所的保密性与安全性、心理抚慰、法律援助等均远远达不到国际水准。[4]事实上,由于受害妇女受到“家事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等观念影响,加之公权力不应过度干预私人领域的原则及协调机制上的缺位,出现家庭暴力问题时,相关部门之间的衔接仍易断裂。囿于司法被动性局限,人身保护令一般只能在离婚诉讼期间才能提出。例如,2012年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对美国籍妻子KIM实施家庭暴力多年,正是KIM通过微博发出求救信号才使李阳家暴行为被曝光并受到媒体的关注。当KIM提出人身保护令时,受到法院的关注。②2013年2月3日11时30分,KIM诉李阳离婚一案在北京朝阳区法院最大的法庭公开宣判。身穿白色外套的KIM依然优雅地出现在法庭上,但李阳方面却只来了一名律师,未见其身影。随后,法官开始宣读长达15页的判决,听着听着,KIM流下了眼泪。审判区外,端着“长枪短炮”的四五十家媒体的记者,形成了一道人墙,颇有阵势。法院门外,还出现了反家暴志愿者的身影,宣判尾声,KIM默默地褪下了手上的婚戒。宣判之前,审判长首先宣读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据悉,2013年1月29日,KIM向法院递交了“人身保护裁定”申请,并为此提交了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手机短信等证据。法院认为,KIM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裁定禁止李阳殴打、威胁KIM。该裁定的有效期为3个月。如果李阳违反该禁令内容,将面临拘留、罚款等制裁,如果构成犯罪,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参见张蕾:《李阳离婚被发“人身保护令”》,载《北京晚报》,2013年2月3日。新民事诉讼法的创举之一,即是首次确立了行为保全制度。其中,第一百条强调,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该条款标志着两种类型的行为保全制度的确立,即确保型行为保全和制止型行为保全。人民法院针对李阳家暴行为所发出的人身保护令属于典型的制止型行为保全,这是新民事诉讼法行为保全制度实施以来的首次适用。由此李阳家庭暴力案推动了北京保护令的实施与推广。
(三)举证责任制度构建的困境
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如何收集被司法认定的证据是难点之一。在加拿大,如果施暴者暴力行为很严重,将被提起刑事控诉。在诉讼过程中,受害人仅作为证人参加审判,并没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方面,他们具有合理性的判断。笔者认为,如何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中,进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将是法律探讨与突破的难点,如责任倒置与合理转移均是探讨的重点。有研究表明,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当事人主张家庭暴力的占40%—60%,但只有不到30%的当事人能提供包括伤情照片、有关病历、报警记录、亲属证言及其他证据等。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相关证人鲜有能站出来作证的。就现实案例来说,法院目前能认定家庭暴力的,基本上是根据加害人的自认,认定率不到10%。[5]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一般只有构成家庭成员之间的轻微伤害案件及虐待案才能通过“告诉”处理,故对家庭暴力案件的认定与处理采用的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受害人提供的证据再多,只要没有加害人自认的证据,法官仍然难以认定家庭暴力的事实。有学者强调,“务实地承认在相对确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前提下,法官可基于公平正义要求对具体案件中的举证责任作出部分转移的裁定。”[6]笔者认为,就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保护而言,针对其难点所在,应向受害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与救济。《审判指南》在责任合理分配方面有一定突破,如举证责任转移至加害方。
(四)传统审判方式的困境
引入人身保护令,需要立法相应的完善与配套。我国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家事法院、设置专职家庭案件法官并且有效介入阻止家庭暴力事态扩大化。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领域不断拓宽,给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挑战。只有适应这种形势变化,制止家庭暴力才能有效推进。要捍卫法律尊严,提高审判效率,法院涉及审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就要改变传统的审判意识与方式。近年来,随着法院系统改革的深化,及法官业务素质、审判理念与专业化水平之提升,法院对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务经验,因而有能力引入人身保护令。
(五)性别与容忍文化背后的观念障碍
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传统根植于社会生活,并对人们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尖锐指出,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因而在分析文化因素的影响时必须保持谨慎。[7]以文化厚重、绚丽而神圣的色彩掩饰或淡化家庭暴力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律威严。有学者从男权视角出发,强调男性施暴与其自然特征有密切关系,认为施暴者激素较高与暴力犯罪率有联系,却未从实质上揭示家庭暴力之根源。女性主义者对生理决定论提出质疑与挑战,认为生理原因决定人类生育模式或身体结构不同,对绝大多数人类活动并无影响。这一挑战表明,婚姻暴力产生并非生理原因引发,主要是由社会环境、文化习俗、观点等不同所造成。不少学者观察到家庭暴力源自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利控制,源于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位序,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群,拥有的生活机会较少,沮丧的程度更深,再加上贫困、缺乏资源和应付技巧不够等问题,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群容易产生婚姻冲突,当压力和紧张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暴力行为。”[8]当暴力成为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时,受害者难以将施暴行为视为暴力,并最大限度地容忍暴力。
三、人身保护令准入立法的新维度
(一)建立制止家庭暴力合议庭
设立“反家庭暴力合议庭”是启动人身保护令实施机制的突破口。合议庭主要审议与家庭暴力相关的案件。合议庭应由社会阅历丰富、熟悉婚姻家庭审判和执行业务的审判员以及人民陪审员组成。还应吸收心理专家、社工等专业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人员诊断案件,从而提出最优方案。人身保护令将事后惩罚施暴者转变为事前保护受害者。受害者可通过提供病历、照片、报警等证明,在提起离婚诉讼前、诉讼过程中或在诉讼终结后的一年内向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的申请,而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1999年,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暴力防治法》(2007年修改)正式实施。针对这一法案的颁行,台湾警方改革并优化了干预家庭暴力的应对机制,如在警察系统成立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机构,推行家庭暴力安全计划,制定并完善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操作规程,建立家庭暴力数据库,加强警察处理家庭暴力能力建设的培训等。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司法统计年报》,2005年1月至2009年4月台湾地方法院共核发保护令12345件,其中禁止实施家庭暴力50604件,占总数的41%。[9]在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生效期间,人身保护令可禁止被告殴打、威胁原告或其亲友,还可禁止被告擅自处理、侵占夫妻共同财产等。根据《审理指南》的规定,紧急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有效期为15天,长期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有效期为3至6个月。确有必要延长人身保护令有效期的,经分管副院长批准,可延长至12个月。运用国家公权力主动出击是推进人身保护令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
(二)制定全国统一的《防治家庭暴力法案》
人身保护令价值在于将事后惩罚施暴者转变为事前保护受害者,开辟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防治的新维度与新途径。人身保护令制度在全国的普遍激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但目前我国现有关于维护妇女、老人、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虽然上述部分法律明确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没有考虑到社会观念对家庭暴力性质与危害认识上的偏差”[10],从而也就难以有效保护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受害人。由此,只有将“家庭暴力防治法”纳入全国人大常委立法规划,走单项立法之路,受害人权益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由于人身保护令实施需要规范性法律文件,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不利于从整体视角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司法规制。尽管《审理指南》明确提出了专门针对受害者事前保护的“人身保护令”,得到了各地法院的积极回应,但因缺少统一立法,使人身保护令的推动仍面临各种司法障碍。国外很多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均有相关较为完善的立法规范。如加拿大1994年制定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法案》、新西兰1996年7月施行的《家庭暴力法案》、我国台湾地区制定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均对反家庭暴力予以了全面立法规范。笔者建议,应考虑制定全国统一的《防治家庭暴力法案》,在法律中明确人身保护令定义、受理条件、保护内容、人身保护令启动程序与执行机构、施暴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从而做到可操作性强,执法部门明确、各部门分工合作,让人身保护令启动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应赋予受害者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权利,并将这种权利的规定予以细化,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结合《防治家庭暴力法案》,全面启动人身保护令,将有助于切实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
(三)规范立法研究机制与合理的评估指标
实施人身保护令并非单一而绝对的措施,应规范系统的立法研究机制与评估指标,避免因机制与指标不同,导致研究结论与实践指向出现过多偏差。在这方面,香港地区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如警方问询干预机制和法医检查系统、医疗服务支持、陪护服务、心理咨询与社工服务系统跟进十分协调。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防止虐待儿童等机构都会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多项有效支持服务。所以实施人身保护令与反家庭暴力干预机制必须互相协调。对不同形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程度的家庭暴力发生频率与轻重程度和年发生率进行规范性的全面科学调查,对家庭暴力进行类型化与分层化研究,评估家庭暴力的风险程度、评估其疾病、自杀、精神病及离婚甚至犯罪的风险值、评估其法律后果,从而为立法引入人身保护令提供系统而科学的经验,也为推进人身保护令的实施提供有效的参考意见。
(四)完善人身保护令操作模式
因为缺少全国统一的防治家庭暴力法案,《审理指南》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尚未上升为全国统一的法律文件或者司法解释,一些法院在操作模式上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在我国法院,“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大体有三种执行模式:长沙市岳麓区法院签发的三个人身保护令,都是由政法委协调公安机关执行的;无锡市崇安区法院签发的两个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是法院与公安机关配合执行的;重庆一中院签发的四个人身保护令,则是法院、妇联、民政三家配合执行的。”①法院在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抄送辖区公安机关的同时,会同时函告辖区公安机关保持警觉,履行保护义务。被申请人对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之日起5日内向签发裁定的法院申请复议。参见徐伟:《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全国发出11个》,《法制日报》,http://www.sina.com.cn,2009年6月15日。除此之外,在实践中还有试点法院自行执行。如陕西省、广东省与江苏省。[3]76笔者认为,要进行合理的探讨与论证,统一人身保护令的执行模式,细化保护令的内容,如有效期的规制、保护距离的界定,并扩大人身保护令的送达范围,即是否突破传统的做法,送到当事人单位、社区,甚至在网上公开人身保护令具体内容等,均是推进人身保护令有效实施的措施,有助于人身保护令在全国范围内复制与合理的本土化。
2013年8月,笔者荣幸地参加了中国女律师公益协作网于天津举办的“(华北)女律师公益、赋权、妇权交流研讨会”。由于笔者通过政协平台,推动了扬州法院系统实施了人身保护令,因此得到律师们的高度肯定。李阳的妻子KIM现场谈及当自己面临家庭暴力,提出人身保护令最初遭遇的障碍与困惑,到最终得到保护令的保护。在探讨如何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时,律师们一致认为,人身保护令是有效保护受暴者的有效手段。“反家庭暴力小组”的女律师决定近几年内将人身保护令作为反家庭暴力的突破口,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人身保护令的实施。笔者认为,上述建议将有助于各机构协调机制,有助于各级政府部门、司法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起多元协作关系,从而共同推动和有效实施人身保护令。
[1]陈治家,等.首份反家暴远离令出炉[N].北京青年报,2012-03-06.
[2]奚晓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3]陈敏.涉家庭暴力案件审理技能[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
[4]赵喜斌.家庭暴力庇护所,八年没人来[N].北京晚报,2012-03-27.
[5]孙娜娜.中国家庭暴力发生率达35.7%,女性受害者占9成[EB/OL].中新网-人民日报,http://www.gscn.com.cn,2008-10-07.
[6]程春华.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以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J].现代法学,2008,(3).
[7]高凌,李秀华,高建秀,刘婷婷.中国内地与香港针对妇女和儿童性暴力的理论及实务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8,(4).
[8]张李玺,刘梦.中国家庭暴力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史长青.台湾家庭暴力之处理机制——从公力救济到乡镇市调解[J].台湾研究集刊,2010,(5).
[10]薛宁兰.社会性别与妇女权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蔡 锋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cluding Writ of Habeas Corpus into Legislative Dimension
LI Xiuhua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one of legislation countermeasures to curb domestic violence.However,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curbing domestic viol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in reality.They include lack of comprehensive,coordinated legislation system,lack of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chanism and lack of the system of burden of proof.Therefore,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 should establish anti-domestic violence court,standardize legislation study mechanism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indicators,improve the habeas corpus mode of operation so as to make breakthroughs and find countermeasures.The paper states that full import of multiple factors can lead to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writ of habeas corpus in the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domestic violence;writ of habeas corpus;burden of proof
10.3969/j.issn.1007-3698.2013.06.001
:2013-10-05
DF55
:A
:1007-3698(2013)06-0005-06
李秀华,女,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婚姻家庭法学。2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