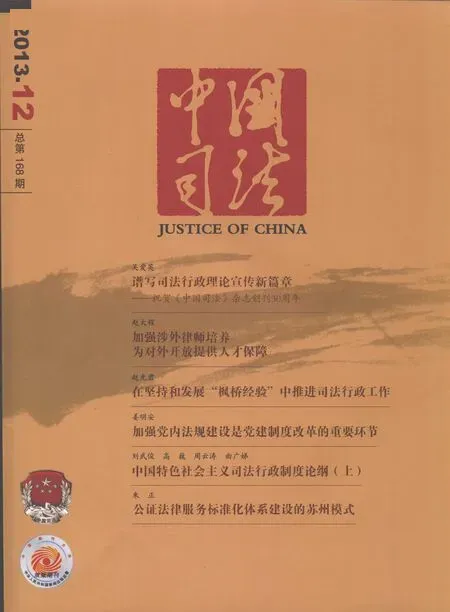试论对网络诽谤的刑法治理
■陈 碧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孙颖菲 陈斐斐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试论对网络诽谤的刑法治理
■陈 碧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孙颖菲 陈斐斐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风生水起,互联网大潮已席卷全球,我国也不例外。据统计,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已有5.38亿网民。其中,手机网民为3.88亿①数据引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址:http://www.cnnic.net.cn/cnnicztxl/hlwtj15n/。。信息的传播已不仅仅依靠传统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等公共传媒行业,动动手指,点击“转发”、“分享”,个人在互联网上完全可以轻松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可以传播,自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诚然,言论自由、网络空间开放,通过互联网络讲讲故事、晒晒心情、发发牢骚,无可厚非,不论原创或转发,总能给自媒体的主体们激起点“小感觉”。然而,2013年以来,随着网络大谣“秦火火”、“立二拆四”、中石化“牛郎门”造谣者傅学胜被抓,让众多网民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网络谣言无处不在、网络诽谤就在身边。如何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有效地规范网民的网络行为,成为政府、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刑法上关于网络谣言入罪的条文,主要规定于第246条的诽谤罪和第221条的侵犯商誉罪。当然,个别内容特殊、后果严重的谣言还可适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罪名。为遏制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空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两高《解释》”),本文主要围绕网络谣言可能涉嫌的诽谤罪,着眼于从证据法角度解析诽谤罪名的成立。
一、网络诽谤的入罪标准
我国《刑法》246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众所周知,诽谤罪通常情况下对社会的危害性较轻微,民法处理即可。只有在达到“情节严重”时,才应当按犯罪来处理。并且,此罪的最高量刑也仅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此罪如仅仅涉及个人,则属于亲告罪,如果没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通常情况下,如被害人不控告,司法机关也不主动追究。上述各方面都体现了刑法在此类行为追究上的谦抑态度。
通过网络谣言构成的诽谤行为上,笔者认为,证明应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主观故意。通说观点认为诽谤罪的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并具有贬低、损坏他人人格、名誉的目的。这也应用于网络诽谤。两高《解释》第一条规定中的“捏造”、“篡改”也印证了网络诽谤的主观方面应是直接故意。但是,在网络诽谤案件中,构成诽谤罪的主观是否只限于直接故意?有人认为,可以包括间接故意。因为造谣者对自己帖子的影响力是不能确定的,这种主观故意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多认为是间接故意的典型形式之一②丁一览:《网络诽谤中名誉权的刑法保护——以网络诽谤个案为考察对象》,《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2期。。对此观点,笔者难以认同。对于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始作俑者、或者在网络上散布诽谤信息的组织者、指使者,对于该信息将被点击、浏览、转发,将起到贬低、损坏他人人格、名誉的效果,在主观上是持希望态度,而非仅仅为放任态度。对于不明事实真相,不加甄别、随意转发他人散布的虚假信息的自媒体“传播者”,其主观上才真正为“放任”,但却不应是刑法打击的对象。对犯罪主观方面的把握必须严格,否则可能误伤舆论。刑法是保护法益之法,但也应考虑网络的特点。
(二)侵害对象。诽谤行为必须针对特定的自然人,既包括具体的指名道姓,也包括虽未具体指明被害人,但通过已知信息可以推知的特定人。如有的虚假信息中,为增加可信度,为实际不存在的被害人编造了真实的学校、工作单位,虚假信息通过网络转发后给真实的学校、工作单位造成极大影响。如,2010年的合肥“女教师诱奸门”网络事件,发帖者编造安徽省合肥四十二中英语组女教师“孔菲艳”利用补课的机会,诱奸学校900名学生。而事实上,合肥四十二中根本没有“孔菲艳”其人,但该网络谣言却给合肥四十二中造成极大负面影响③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063/11837204.html.。此类行为不宜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诽谤。这是因为,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诽谤罪的犯罪对象。尽管民法规定法人享有名誉权,捏造事实对单位的恶意攻击确实可能导致单位名誉受损,但鉴于诽谤罪属于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该罪保护的法益只能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不包括单位的相关权益。
(三)情节严重。有人指出,网络谣言的传播方式本身就是情节严重的表现,因为影响者众,帖子如在天涯、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等知名网站刊出,点击、浏览、转发极易以万、十万计,这和传统的诽谤相比,情节绝对严重。两高《解释》也将情节严重明确到“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互联网的信息更新速度相当快,人们对于信息的关注往往不具有持久性。虽然可以利用网络铺天盖地散布对他人不利的言论。但当出现另外一个热点问题,受众眼球立即又转向他处。并且自媒体天生的“自我纠错”功能也能起到抵消效果。因此,笔者认为,不能仅仅从传播方式和次数方面考量情节,而只有当侵犯行为造成他人名誉、人格的严重毁损,才可动用刑罚工具。美国法院曾经受理过某知名牧师状告《好色客》杂志的案件,该杂志在一幅色情漫画中直指原告牧师与母亲乱伦,这是何等严重的一个诽谤!然而,法院认为,所有阅读该杂志的读者都只是一笑了之,谁也没把这种事情当真。被告律师说,当年华盛顿总统何等神武,还被杂志丑化成一头毛驴。而此案也无关格调,只关言论④Hustler Magazine V.Falwell,485 U.S.46,48,51-55(1988).。
(四)区别对待。谣言滋扰的个人,可以分成两类,普通人和公众人物。对于公共人物的刑法保护应该有所节制,在诉讼法上,应从证明程度上加大难度,体现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司法实践中,已经体现出这一审慎态度。2010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指出,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这些规定都表明,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害人是公众人物,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诽谤案件,在证据规格和定罪标准上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如果不能证明网络上的谣言行为、抹黑行为出于蓄意造假,那就应当推定该抹黑是正当的批评和善意的监督。
如此严格限制,主要原因是:名誉保护与言论自由的价值冲突,以及与刑法保护功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后文将详述之。
二、诽谤与言论自由之冲突:以美国诽谤罪发展为例
美国是一个深以言论自由为荣的社会。但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建国之后各州刑法中都存在刑事诽谤罪名。1962年,美国州法院还给诽谤罪下过一个很宽的定义:“任何刊出的文字只要有损被诽谤者的声誉、职业、贸易或生意,或是指责其犯有可被起诉的罪行,或是使其受到公众的蔑视,这些文字便构成了诽谤”⑤【美】安东尼·刘易斯著,何帆译:《批评官员的尺度》,北京大学出版社。。按照这个解释,很多批评行为都可能被判定为诽谤。
但从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之后,美国司法系统在言论自由与名誉保护的天平上明显站在言论自由这一边。目前在美国各州刑法中,仅在规范私人对私人名誉侵害的范畴内,刑事诽谤法依然有效。而对于公众人物的名誉侵害,刑事诽谤法几乎已经放弃作为了。他们的假设是,公共人物享有足够资源在言论市场里为自己的名誉辩护,并不需要给予太多法律救济的途径。
以美国的诽谤去罪化进程为参照,笔者认为,我国司法界在处理网络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时应当审慎。借助互联网,网民通过自我组织成为主动向公众发布信息的信息源,网络得以成为公共事件的重要策源地。网民们的发言互动,构成了个体间特殊的“全民传播”,这与Gregory Ulmer提出的“第五权”(The Fifth Estate)概念不谋而合⑥翁家若、徐玉红:《自媒体时代的全民传播现状与舆论困境》,《天涯》,2011年4月。。在此种意义上,网民的自媒体言论权力应当得到保障。他们通过此种媒介表达对某一事件的诉求,对某一人物的评论,对某一事件的态度,无论言辞激烈粗鄙与否,只要并非以贬低、损坏他人人格、名誉为直接目的,只要不会带来即时的明显的危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障。
如果在涉及到网络谣言参与事件中,采取严格定罪的立场,很可能使得诽谤罪成为压制言论的工具。在网络诽谤案件中,刑法规则要兼顾秩序和自由这一刑法的两大基本价值,同时也要兼顾网络这一新生领域的特点和我国现阶段政治民主的趋势。刑法乃国之重器,应警惕成为公民言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在以诽谤定罪之前,必须考虑民法是否足够保护名誉权,而不用刑法越俎代庖。它包含了两个假设:一是民事手段已经能够提供有效的名誉保护;二是民事手段不像刑事手段那样过度侵犯言论自由的边界。如果民事法律能够提供这样的保护,刑法应慎用。
三、诽谤罪于证明责任的难题
(一)谁来承担诽谤事实的举证责任
诽谤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捏造或篡改事实,也就是虚构不符合真相或者并不存在的事实。只有假的事实才构成诽谤罪的事实,因此,此罪证明的重点之一就是证明虚假的事实是否成立。换言之,诽谤罪名之成立,关键不在于证明自己名誉是否被抹黑,而在于所言之事实是否存在。前者证明起来容易,而后者的证明是煞费苦心的。
在普通法传统里,名誉侵权责任的成立,采取严格责任制。普通法的基本思维是,任何人的名誉,在被相反的事实证明之前,都享有法律保护⑦徐伟群:《论妨害名誉权的除罪化》,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博士论文。。在具体案件中,也就是说,被告只有自证陈述事实的真实性,才有可能脱罪。很明显,普通法更倾向于保护诽谤案件的原告,至今英国仍在沿用这一传统,因此被称为“诽谤之都”,意思是在那里诽谤定罪太容易,一告一准。
普通法里把名誉侵害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而有别于一般侵权法里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这实际上考虑了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未考虑对于言论的压制后果。或者说,只考虑了技术,而未考虑价值取向。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这个普通法原则颠倒过来,增加了证明的难度。其结果当然对于言论自由有利。原告负举证责任问题到了刑事诉讼里面就更加明确,基于被告人权保护的要求,自诉人或公诉方负举证责任的原则几乎不可能动摇。而且不管被害人是公共或者非公共身份都同样适用。并且刑事诉讼使用的证明标准明显高于民事诉讼,因此对于原告的负担加重。
于是,举证责任问题会造成一种两难处境:如果适用原告负担举证责任原则,可能造成过度压缩名誉保护的不公平现象;如果适用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则我们不愿见到的有罪推定的恶果也可能真正发生。不仅如此,无论哪一种原则,都可能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待遇⑧徐伟群:《论妨害名誉权的除罪化》,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博士论文。。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名誉侵害行为应该尽量交给民事法来处理,而非刑法。
(二)故意内容如何证明
网络谣言诽谤罪名的成立,要考察主观故意是否为直接故意,并具有贬低、损坏他人人格、名誉的目的。故意内容的体现在于行为人明知自己是捏造、散布虚假事实诽谤他人,并且会造成他人人格、名誉受到严重损害的后果,却希望这种结果发生。仅仅是“恶搞”,明显地能使受众感觉到“不可能”、 “不真实”,“娱乐而已”的虚假信息,没有产生对他人人格、名誉的严重损害,即使被点击、浏览五千次以上、或者转发五百次以上,也不应认定为构成诽谤罪。针对普通人的网络诽谤,如果行为人将虚假事实误认为是真实事实加以扩散,也就是造势,不构成诽谤。
在证明时应当注意:一定要区别事实和意见。故意散布的应当是不实事实,而非意见、评论。纯粹的观点评论,即使言语过激,一般认为是不受到诽谤罪的制裁的,即使有目的进行造势传播。
(三)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如何保护
受网络谣言滋扰的公共人物的名誉权,刑法的保护应该有所节制,在诉讼法上,应从证明程度上加大难度,体现对言论自由和网络第五权的保障。
前文已述,无论是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认为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应该受到言论自由的限制。因此,对公众人物的批评即使有不实言论,追究也应慎重。如果不能证明网络上的造势行为、抹黑行为出于对方的蓄意造假,那就应当推定批评和抹黑是正当和善意的。
涉及公众人物的诽谤案件,必须由公众人物自己提起告诉,同时由其证明对方明知所言不实,还罔顾真相地进行传播,方有胜诉可能。由于自诉人身份的不同,证明的内容存在差异:作为公众人物,证明诽谤者的故意内容包括:首先,事实不实;其次对方明知所言不实,仍然罔顾真相,怀有确实的恶意。
总之,刑事法律对于网络谣言的打击应当有所为,更应当有所不为。其行为虽恶,但言论自由的价值取向值得保护,而网络谣言远不值得妖魔化,其离“网络黑社会”之实差距甚远。即使对簿公堂,也可以用证据法加以区别对待,以平衡言论自由和名誉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
(责任编辑 张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