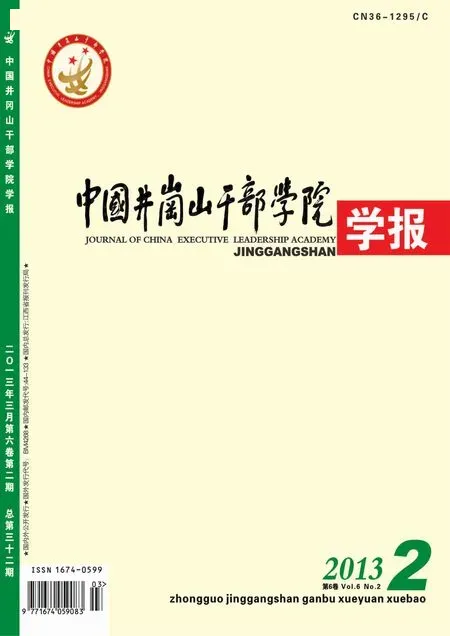论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及其内涵
□王新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一研究部,北京 100080)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产生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一种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与此前产生的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一脉相承,又对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遵义会议精神产生的土壤
精神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来自深厚的基础。探讨遵义会议精神,首先要对遵义会议精神产生的土壤进行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下旬,遵义会议召开于1935年1月,距党的成立已达13年半。期间,经历了从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党已经同大革命失败时大不相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党内已形成一批善于从实际出发、有实践经验、有威望的领导者
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离开领导岗位,党在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帮助下,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但是,党中央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党内盛行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因此,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然而,七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有实践经验、有威望的领导干部已成长起来。
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工作过,大革命失败后,婉言拒绝了瞿秋白要他在中央工作的要求,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受挫后,率领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树立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1929年1月至1930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创建了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年秋至1931年秋,毛泽东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创建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建设党与红军的经验,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很大影响。1928年10月,中共鄂东特委曾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1]P277。习仲勋在谈到西北革命斗争时曾说:“以刘志丹、谢子长为首,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的八个年头内,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道路,锻炼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2]P165可见,毛泽东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周恩来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是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者:1927年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9年给中共红四军前委发出“九月来信”,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维护毛泽东、朱德对红四军的领导;1930年10月负责制定全国红军发展计划,决定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活动的区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底到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3年春,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周恩来是在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上成长起来的既有组织、军事工作丰富经验,又深孚众望的领导人。
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与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粤赣湘边界坚持游击战争。1928年4月,他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红四军)。从此,朱德与毛泽东的名字就紧紧连在一起,他们领导的红军以“朱毛红军”著称,是令国民党军闻之胆寒的部队。朱德先后任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先后取得了中央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被称为“红军之父”。鉴于朱德在红军的威望,1933年10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提议他为六届五中全会新一届政治局委员。[3]P542朱德由此开始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
陈云在中央领导层中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他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委员,在中央苏区时曾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针对中央苏区存在的照抄《劳动法》、对商店、作坊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的作法,陈云批评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认为“这种‘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4]P9
刘少奇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早在1931年至1932年间,他主管中央工运工作时,就同实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发生争论,并在此期间写下了十几篇文章,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工人运动的正确策略思想。刘少奇的这些主张被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2年3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他所担任的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
这时,在党内一些执行过“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其危害性,开始从实际出发看待革命问题,并成为有威望的党的领导者。
张闻天是1931年9月下半月成立的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之一,虽然也跟着王明犯过“左”倾错误,但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左”倾错误对革命的危害性。1932年10月,张闻天在《斗争》杂志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强调要打击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张闻天同博古的分歧日益加深。博古认为,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是宣传口号。张闻天认为宣言提出的三个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主张建立统一战线也包括上层。福建事变发生后,张闻天主张给十九路军以军事上积极的配合,博古则持反对态度。张闻天同博古发生的公开冲突是广昌战役之后。他批评博古:“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博古则指责张闻天是“普列哈诺夫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5]P77此后,博古与张闻天的关系更加疏远。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起行军,谈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同毛泽东的意见逐渐一致。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并且是中央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的转变对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王稼祥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候补委员,曾执行过“左”倾错误方针,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开始认识到李德的军事指挥的错误,多次同李德发生争论,“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是打不破敌人‘围剿’的,还是要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战法。”[6]P126长征开始后红军处境日渐危急,王稼祥更加认为李德的瞎指挥是把红军引向绝路。
除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外,在各根据地也涌现出一批注重实际、有能力、有威信的领导干部。在中央根据地还有陈毅、彭德怀、林彪、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林伯渠、李富春、邓小平、毛泽民等,在赣东北有方志敏等,湘鄂西有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鄂豫皖有徐向前、邝继勋、曾中生等,湘赣有任弼时等,陕甘边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闽北有黄道等。
总之,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锤炼出一批求真务实、有实践经验、有领导能力、忠诚党的事业的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二)党内已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七年多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经过苦苦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党内普遍认为革命应以城市为中心。但是,所有以占领为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转移到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僻农村和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迫使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与朱德等率领红四军出击赣南后,在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2.形成了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
随着红军和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经过土地革命实践的摸索,党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这些路线、政策和方法的实行,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极大地激发了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的就是因为紧紧地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
3.找到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把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途径。
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由于白色恐怖党在城市的斗争遇到严重困难,而农村革命斗争却得到迅速发展。这种情况使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发生很大变化。1928年党的六大时,党员成分农民占总数的76.6%,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又下降到7%。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党员主要是农民成分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变成农民党,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产业中心发展工人党员。农民是小生产者,大量涌入党内会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共产国际的担心虽然不无道理,但在实际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工人数量很少,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大量发展党员,农民占党员多数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等经过艰辛探索,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4.红军进行了各方面建设,形成了作战的基本原则。
由于红军的发展和反“围剿”斗争的多次胜利,以及战争形式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红军普遍加强了各方面的建设。一是建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各区党委、军委分别颁布了一系列条例、条令,初步统一了红军的编制,加强了红军相对的正规化建设。二是加强了红军中党组织的建设,建立了战时政治工作,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了思想政治保证。三是建立了后勤机构,做好部队供应,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了物质保证。四是加强了地方武装建设,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五是创办了各类红军学校,加强军政训练,学员最多时曾达6000多人。在反“围剿”作战中,形成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一是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二是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三是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四是不失时机地实施进攻,扩大战果或将敌之“围剿”打破于计划实施之前;等等。
从以上两方面看,在遵义会议之前,尽管“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但正确的力量发展已经超过错误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已逐渐成熟,有能力独立正确解决自己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与逐渐成熟,已使中国政治力量发生重大变化,与七年前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
如前所述,经过13年半的斗争,尤其七年多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已由幼年走向成年。因此,遵义会议精神必然体现出成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特点。笔者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包括以下内涵:
(一)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应该把独立自主放在首位。为什么如此,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着最危险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军事指挥的原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开始后,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又采取了大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丧失了有利时机,遭受惨重损失,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不仅如此,在蒋介石判断出红军行军的方向,并命令构筑了新的碉堡线后,博古、李德仍不顾敌情坚持原定的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计划,使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面临着灭顶之灾。这时,党中央所面临的危险程度远超过了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大革命失败时,党中央转入了地下,还未面临随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一网打尽的危险。这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着国民党军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又无根据地作依托,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无数险关要隘,如果一着不慎,不仅中央红军主力被敌人消灭,党中央和红军中枢指挥机关也将被一网打尽。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只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存在,革命就有复兴和发展之时;如果党中央领导机关彻底被敌摧毁了,中国革命事业受到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因此,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挽救革命危机,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作为严重的任务摆在了党的面前。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党内先后出现陈独秀右倾错误和瞿秋白、李立三“左”倾错误时,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才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然而,这时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不存在共产国际干预的客观条件。但是,敢不敢在未得共产国际的同意下,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对党来说是一个挑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召开的,政治局的组成也是经过共产国际同意的,不经共产国际同意对其进行改组需要极大的胆略和勇气。即这个改组必须是成功的改组,新的中央用事实证明它的领导是正确的,才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否则的话,将会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处罚,
从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红军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许多干部就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如彭德怀等,多次在作战电报和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多次提出正确的主张,但都没有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的不断失利,广大干部、战士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了顶点。
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毛泽东利用此机会,向他们反复分析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王稼祥向毛泽东表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6]P127
召开遵义会议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尤其是周恩来,他主持黎平会议,不顾博古、李德的激烈反对,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红军战略进军方向。杨尚昆曾说:“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还转述毛泽东的话:“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7]P119
可以说,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已经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领导干部中普遍的要求。
毛泽东后来在谈到遵义会议时,多次提到独立自主问题。他指出:“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引者),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8]P51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开始的。”[9]P55“1931年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就是国产国际给我们起草的,并强加于我们。”“以后我们独立自主。在长征路上,我们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10]P55
可见,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最大特征,体现了已经长大并逐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独立自主是和实事求是密切相连的,没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就成为无原则的党内争斗。尽管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实事求是”四个字,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在实际斗争中,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如前所述,经过七年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辛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逐渐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倾向和正确方面、正确力量的发展呈现出反向发展趋势,即教条主义从强到弱,教条主义的市场逐渐萎缩,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由于在工作中取得成就、革命根据地得到发展的事实,而越来越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认同。党在过去积累的宝贵经验尤其是作战原则,是纠正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基础。
博古在遵义会议上作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并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反帝反蒋介石国民党的运动没有明显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各苏区呼应配合不够紧密,等等。
与会者认为,按照博古的报告,“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这个“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大家指出:“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来源是由于对于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于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批评博古、李德“在转变战略战术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11]213-214,225
遵义会议肯定了过去行之有效的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重回军事指挥岗位。此后,红军摆脱被动挨打局面的事实充分证明,遵义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闪烁着实事求是精神的光辉。
(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造成的恶果,遵义会议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问题,而是一般地肯定了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之所以这样做,是从当时的大局出发。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虽然把国民党“追剿军”甩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打下遵义,取得了12天的休整时间。但蒋介石不可能让红军有更多的休整时间,中共中央必须高效地利用这短短的十余天时间,解决面临的事关党和红军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着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胜利实现战略大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创斗争新局面,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革命的大局。而这时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中,对于纠正军事指挥错误的认识比较一致。但对于政治路线问题,大家还没有取得一致。比如,“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关门主义的方针,把中间阶级视为“最危险的敌人”。遵义会议上,大家虽然批评了博古、李德没有“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但又认为十九路军“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的统治”[11]P222。很明显,当时大家对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性质判断是错误的。这说明,对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的认识,还需要一个对过去的是非问题进行讨论,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这在军情紧急,只有短短的十余天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如果对政治路线进行讨论,不仅很难统一大家的认识,而且会产生新的分歧。一旦新的分歧产生,中央领导层争吵个不停,必然会使军事问题无法解决。那么,党和红军的前途与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曾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路线,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5]P80正如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的:“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12]P234可见,遵义会议只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不对政治路线进行讨论,反而一般地肯定了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体现了大局意识和顾全大局的精神。
顾全大局是和团结一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博古等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根本纲领是一致的。李德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革命,其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在到中央苏区之前,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军事顾问组成员,也为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做了一定工作。尽管他们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仍然是革命队伍中的成员。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大家对他们犯的错误尤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还是当作同志对待的,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帮助的方法,而不是“残酷斗争”的方式。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曾说:“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12]P235尽管如此,后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后,博古仍然是中央常委,并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的重要职务。李德在遵义会议后虽然被解除了指挥权,但有时让他参加一些军事会议,并征求他意见。至于凯丰,没有因他对“毛张王”有不同意见而解除职务。
毛泽东后来同外宾谈到遵义会议时指出:“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8]P51
遵义会议所体现的团结一致精神,还表现在会后新的党中央领导班子之间的团结。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但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否能够团结,对于红军能否走出困境,开创新局面,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博古受到大家的批评,再继续领导下去是困难的。张闻天提出变更领导的问题时,毛泽东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来领导。当时,从党内、军内的威望、能力和经验来讲,毛泽东是最合适的。而毛泽东却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做一个时期。”[13]P68对此,周恩来后来曾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增强了党中央新领导班子之间的团结。此后,在坚持党中央的北上决策,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博古,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11]228可见,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刻,党中央尤其重视全党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认为团结一致才能度过难关,才能取得胜利。
笔者认为,正是遵义会议坚持顾全大局和团结一致的精神,为长征的胜利,开创抗日斗争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三)坚信必胜,勇往直前
遵义会议是在革命处于最困难的境遇下召开的,当时严峻的形势以及红军因错误的军事指挥遭受的惨重挫折,容易使一些人产生张皇失措和悲观失望情绪。遵义会议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错误时,特别注意反对张皇失措和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发生和蔓延。因此,会议指出:虽然“由于我们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了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党的正确的领导,……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的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
针对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闽浙赣苏区相继变为游击区的情况,会议认为这“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前途表示张皇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会议分析了国民党政权面临的困境,认为“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增加了,我们活动的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的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崩溃”[11]P228。而中国共产党则由于纠正了军事指挥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纠正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由此,会议得出的结论是:“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胜利必然是我们的。”[11]P228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看到光明,坚信革命必胜是遵义会议的重要特征之一。
摆脱国民党军的重兵围追堵截、建立新苏区、开创革命的新局面是需要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奋斗来实现的。遵义会议召开时,蒋介石部署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经过了短暂的休整之后,中央红军又面临着严峻的局面,需要以崭新的精神状态迎接新的战斗。
1月19日,中央红军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为了鼓舞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士气,1935年2月15日,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在指出“全国革命形势的尖锐化”,“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之后,号召:“全体同志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14]P262从1935年的1月末到3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针对部队大踏步进退、转移,时东时西,时而走大路,时而走小路,时而渡河,时而翻山越岭,战斗环境十分紧张的情况,红军总政治部于4月1日发出指示,要求红军政治工作:“不仅在胜利情的况下,能更加提高士气,而且要在困难的条件之下团结红色战士,不灰心,不丧气,坚定的为着我们光荣的任务,为着中国的工农解放而斗争到底”[15]P307。4月30日,在中央红军准备渡过金沙江之际,总政治部又在训令中提出:“最大限度的提高我们特有的迅速、敏捷、坚决、勇敢”;“最大限度的提高吃苦耐劳、坚持不倦的精神。”并要求“我们要永远的保持与提高我们的旺盛的作战热忱,以歼灭阻拦与侧击之敌,必要时回击追敌。”[16]P3245月初,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接着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如铁流滚滚势不可阻挡。对此,博古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一文中说:“金沙江与大渡河的天险,我们履险如夷地渡过了,邛崃山脉之高峰,四川军阀的兵力,当然更不足以阻止奔腾的铁流之合流。”红军以“更高的吃苦耐劳,更高度的机动与巧妙,更勇猛的作战,以一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勇气与力量,克服了一切人为与自然的困难,而达到了我们的目的。”[17]P382
显而易见,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一直要求中央红军以坚信必胜、勇往直前的精神战斗,去实现党中央的战略目标。中央红军正是贯彻和发扬了遵义会议要求的坚信必胜、勇往直前的精神,才得以纵横云贵川,斩关夺隘,终于跳出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实现了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之势。并在此后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取得长征的胜利。
纵上所述,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概括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坚信必胜,勇往直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A].习仲勋文选编辑委员会.习仲勋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A].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4]陈云.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A].陈云文选: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A].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王稼祥.会议参加者的回忆:王稼祥[A].吴德坤.遵义会议资料汇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7]杨尚昆.会议参加者的回忆:杨尚昆[A].吴德坤.遵义会议资料汇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8]毛泽东1963年4月17日同外宾的谈话[A].吴德坤.遵义会议资料汇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9]毛泽东1963年9月3日同外宾的谈话[A].吴德坤.遵义会议资料汇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0]毛泽东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的谈话[A].吴德坤.遵义会议资料汇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1]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12]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13]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A].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15]总政治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的指示[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16]总政治部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17]博古.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