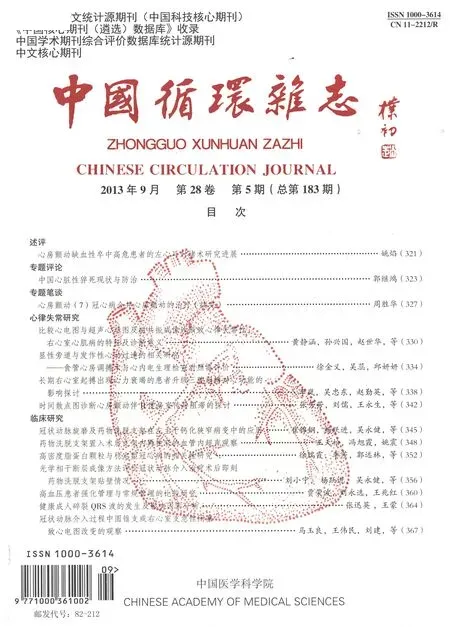儿童扩张型心肌病的病因及预后
郭潇综述,张健审校
儿童扩张型心肌病的病因及预后
郭潇综述,张健审校
儿童心肌病是儿童发生心力衰竭的常见原因,其中扩张型心肌病约占各类儿童心肌病的50%,在儿童心血管疾病中死亡率最高。儿童扩张型心肌病可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心肌炎、神经肌肉疾病、家族性心肌病、遗传代谢病等。起病时年龄<6岁,射血分数较高和诊断心肌炎提示预后较好。
儿童;扩张型心肌病;病因;心力衰竭
心肌病是一组以心肌直接受累,影响心室收缩和(或)舒张功能为特征的疾病,它是儿童发生心力衰竭的常见病因。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心脏的形态和病理生理特点将心肌病分为肥厚型心肌病、扩张型心肌病、限制型心肌病、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右室发育不良和未定型心肌病。其中扩张型心肌病以心脏单个或双心室腔扩大和收缩功能减退为主要特征,通常会引发充血性心力衰竭。
根据报道,在18岁以下人群中,心肌病的年发病率约在1.13/100 000到1.24/100 000之间,男孩发病率略高于女孩(1.32/100 000 vs 0.92/100 000)[1-3]。扩张型心肌病年发病率约为0.58/100 000左右,在各类型心肌病中约占50%;确诊时患儿的平均年龄为1.5岁,约41%-50%的患者确诊时年龄不足1岁,初诊时6~12岁年龄组最少,约为14%。约70%~90%的患儿在确诊时以心力衰竭以主要表现[1,2]。
扩张型心肌病这个术语描述的是以心腔扩大和收缩功能减退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征,而不是单一的疾病。多种病因可导致“扩张型心肌病”样的临床表现。各种心脏疾病,如冠状动脉缺血、高血压、瓣膜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心包疾病等均可以累及心肌。一些全身性疾病,如感染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结缔组织疾病、内分泌疾病、神经肌肉疾病、先天性疾病、过敏性反应及毒素作用等,也可累及心肌[1,4]。表现为扩张型心肌病的患儿中,仅有30%~40%可明确诊断病因;其中最常见的是病因是心肌炎(16%)和神经肌肉疾病(9%),其他原因包括家族性心肌病(5%)、遗传代谢性疾病(4%)和先天性畸形等[2,5,6]。
1 心肌炎
儿童心肌炎的临床表现轻重不一,轻者可仅有心肌组织的炎症性改变而没有临床症状,重者可出现心力衰竭、心原性休克甚至心原性猝死等。如果患者有典型病毒感染症状,如发热、肌肉疼痛、呼吸道或消化道症状,同时合并超声心动图提示心脏扩张及收缩功能下降的表现,多考虑诊断心肌炎。超声心动图提示仅有左心室收缩功能下降,不合并室壁变薄及左心室扩大的心肌炎预后较好[7]。
与特发性扩张型心肌病相比,心肌炎患儿需要心脏移植或死亡的风险较低[2,3]。但目前,尚缺乏诊断心肌炎敏感性及特异性均好的临床检查或诊断标准。在出现症状的前4周内,心肌损伤标志物如肌钙蛋白I、肌钙蛋白T及病毒抗体血清学检查可协助诊断病毒性心肌炎[8]。心内膜活检“Dallas标准”曾作为心肌炎诊断的金标准,但敏感性较低,仅有约30%怀疑心肌炎患者的活检结果符合Dallas标准。结合临床表现和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方法检测病毒基因组学也可诊断心肌炎;但有文章报道,用PCR方法在26名心肌炎患儿及13名扩张型心肌病患儿心肌细胞中均可检测出病毒基因组,心肌炎患儿中检出12例(46%),而扩张型心肌病患儿为6例(46%);腺病毒在心肌炎患儿中多见,而肠病毒在扩张型心肌病患儿中更多见[9]。心脏核磁可以发现灶性的心肌肿胀、水肿、微血管渗出等炎症表现,釓增强显像可以发现不可逆的心肌损伤[10];在鉴别心肌炎及扩张型心肌病方面有一定作用。
尽管病毒性心肌炎和扩张型心肌病预后不同,但许多临床观察发现部分病毒性心肌炎患者最终会发展为扩张型心肌病[11,12];因此,病毒性心肌炎和扩张型心肌病可能代表同一疾病的不同阶段。
2 神经肌肉疾病
与神经肌肉性疾病相关的心肌病患儿多数患Duchenne或Becker肌营养不良,二者均为抗肌萎缩蛋白编码基因dystrophy基因突变所致,遗传方式为X-连锁遗传[13]。抗肌萎缩蛋白Dystrophin是一种肌细胞骨架蛋白,具有保持肌细胞细胞膜和肌质网完整的功能;dystrophy基因的缺失或突变可导致肌肉变性坏死。典型肌营养不良患者的肌活检可见肌纤维不同程度增大、变性坏死以及结缔组织增生和脂肪浸润。
肌营养不良患儿出现扩张型心肌病的表现多在青少年时期。Duchenne肌营养不良患儿常以骨骼肌表现为主,1岁以前运动发育基本正常,5岁左右起症状明显,至约20岁时大多数患者因咽喉肌和呼吸肌无力死亡。患儿在出现心功能不全的临床表现之前数年,患者即可出现潜在的心电图异常,或组织多普勒超声、心脏核磁发现心肌功能异常。
Becker肌营养不良患儿多在5~10岁起病,至20~25岁丧失行走能力,可存活至40岁左右;其心肌病常比骨骼肌表现更重。有报道无症状心肌损害在Becker肌营养不良患儿中的比例可高达67%,主要表现为心电图的束支传导阻滞、II、III、avF、avL及V6导联出现Q波;及无症状性肥厚型心肌病。40岁以后,约1/3的患者逐渐出现心悸、晕厥、呼吸困难和下肢浮肿等症状,表现为扩张型心肌病、肥厚型心肌病、严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或心原性猝死。青少年男性扩张型心肌病患儿如果合并肌酸激酶升高,需警惕Becker肌营养不良的可能[14]。
Dystrophy基因的其他变异还可能表现为X-连锁遗传的扩张型心肌病(X-linked dilated cardiomyopathy,XLDC),但没有骨骼肌受累。这类XLDC临床表现轻重不一,多数患者在15岁后至20岁发病,多因为快速进展的心力衰竭在起病一年后死亡。女性XLDC基因携带者也可出现心肌病表现,但起病较晚,预后较好。患者和携带者均可检测出肌酶升高;虽然临床没有骨骼肌受累表现,但骨骼肌活检可见轻度肌病样表现,如肌纤维增粗、细胞核增大及间质结缔组织增生;而心肌活检则提示典型肌营养不良样表现。免疫组化方法发现,抗肌萎缩蛋白Dystrophin在骨骼肌中表达水平仅轻度降低,而在心肌组织中完全不表达。目前共发现有10余种与XLDC相关的Dystrophy基因变异热点[13]。
3 家族性心肌病
扩张型心肌病家族史或一级亲属中有35岁以下不明原因猝死的病史,提示患儿可能存在基因缺陷,为家族性心肌病。仅14.7%~19%的患儿在诊断扩张型心肌病时有明确的心肌病家族史,但如果对扩张型心肌病患者一级亲属进行心电图及超声心动图筛查,则发现家族性扩张型心肌病的比例会升高到35%~65%[15]。家族性扩张型心肌病临床表现与其他扩张型心肌病患儿没有明显区别。
目前为止,已发现超过20个基因与扩张型心肌病有关,其中90%家族性扩张型心肌病的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X染色体连锁遗传约占5%~10%,其他遗传方式如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和线粒体遗传也有少量报道[16]。研究表明,不伴随传导障碍的致病基因通常定位于1q32(肌钙蛋白 T)、2q31(肌联蛋白)、2q35(结蛋白)、4q12(β-肌糖蛋白)、5q33(δ-肌糖蛋白)、9q13-22、10q21-23、14q11(β-肌球蛋白重链)、15q2(α-原肌球蛋白)、15q14(肌动蛋白)。而伴随传导障碍的绝大多数定位于1q21的核纤层蛋白(lamin A/C)[17]。肌动蛋白、α-原肌球蛋白和结蛋白基因突变常引起心肌细胞收缩力量的传递异常;β肌球蛋白重链和肌钙蛋白T基因突变会导致肌小节产力功能障碍;肌糖蛋白在稳定肌肉纤维膜及信号传导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些编码参与能量代谢反应的酶的基因发生突变,也可以导致细胞能量代谢发生障碍,可影响小儿的生长发育,也可伴发扩张型心肌病。
曾有观点认为家族性扩张型心肌病预后较散发型差;但有文献报道,分别随访69名非家族性心肌病患者及30名家族性心肌病患者5年,结果发现两组患者5年生存率没有显著差异,分别为55%(非家族性心肌病患者)和51%(家族性心肌病患者);而对预后有主要预测价值的指标为左室射血分数<30%[18]。
4 遗传代谢病
遗传代谢病是因维持机体正常代谢所必需的某种酶、运载蛋白、膜或受体等的编码基因发生突变,使其编码的蛋白产物功能发生改变,而出现相应的病理和临床症状的一类疾病。它涉及氨基酸、有机酸、脂肪酸、糖原、糖蛋白、金属等多种物质代谢的异常而致病[19]。大多遗传代谢病为单基因遗传病,少数为线粒体基因遗传病[20]。这类疾病均为多器官受累,大多缺乏根治方法,常导致早夭或终身残疾。
遗传代谢性疾病引起心肌病的主要机制有以下三方面,过量代谢底物在心肌细胞的沉积、心肌细胞产能过程受损及对心肌有毒性作用的代谢产物生成。没有心功能受损临床症状的患者,仍可能存在亚临床心肌病。超过半数患者(约63%)表现为肥厚型心肌病,或肥厚型心肌病合并收缩功能受损。表现为扩张型心肌病的患者在遗传代谢性心肌病患者中仅占约21%,多见于粘多糖贮积症、氧化磷酸化缺陷病、脂肪酸氧化/肉碱代谢缺陷病、和氨基酸/有机酸代谢病[2]。
尽管遗传代谢病引起扩张型心肌病较少,患扩张型心肌病的患儿进行常规筛查遗传代谢病有利于早期发现并治疗原发疾病,同时可辅助评估心脏移植的可行性。
5 预后
儿童扩张型心肌病在儿童心血管疾病中死亡率最高,大多数患儿死于心力衰竭,而猝死较少见(发生率约0.7%~2.4%)[21]。根据文献相关数据,患儿诊断扩张型心肌病后,1年生存率约90%,5年生存率约83%[22];其中心脏移植治疗和左心室辅助装置显著改善患儿的生存率。对于不同病因,患儿未死亡/心脏移植的复合终点率有显著差异。其中心肌炎、遗传代谢病预后较好,其5年未死亡/心脏移植率分别为73%,78%;而特发性扩心病、神经肌肉性疾病和家族性扩心病患儿预后较差(5年未死亡/心脏移植率分别为47%,52%,59%)[3]。
对于儿童扩张型心肌病的预后因素也有较多研究,但仍未能提出有效的危险分层方案。起病时年龄<6岁,射血分数较高和诊断心肌炎提示预后较好[23,24];如果患儿在治疗6个月内左室收缩功能有所恢复,提示预后较好,而收缩功能没有改善则是死亡或心脏移植的预测因素。除了超声心动图的一些测量数据能够预测患儿的预后之外,有研究发现B型脑尿钠肽>300 pg/mL是死亡、心脏移植和心衰住院的强烈预测因素。
[1]Wilkinson JD, Landy DC, Colan SD, et al. The pediatric cardiomyopathy registry and heart failure: key results from the first 15 years. Heart failure Clin, 2010, 6: 401-413.
[2]Hsu DT, Canter CE. Dilated cardiomyopathy and heart failure in children. Heart failure Clin, 2010, 6: 415-432.
[3]Jeffrey A, Towbin AM, Lowe SD, et al. 儿童扩张型心肌病的发病率、病因及预后. 美国医学会杂志中文版, 2007, 26: 217-223.
[4]Williams GD, Hammer GB. Cardiomyopathy in childhood. Curr Opin Anaesthesiol, 2011, 24: 289-300.
[5]Daubeney PE, Nugent AW, Chondros P,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s of childhood dilated cardiomyopathy: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Circulation, 2006, 114: 2671-2678.
[6]Kindel SJ, Miller EM, Gupta R, et al. Pediatric cardiomyopathy:importance of genetic and metabolic evaluation. J Card Fail, 2012, 18:396-403.
[7]Simpson KE, Canter CE. Acute myocarditis in children. Expert Rev Cardiovasc Ther, 2011, 9: 771-783.
[8]姚建, 孙腾, 张慧敏, 等. 类似急性心肌梗死的病毒性心肌炎一例.中国循环杂志, 2013, 28: 68.
[9]Calabrese F, Rigo E, Milanesi O, et al. Molecular diagnosis of myocarditis and dilated cardiomyopathy in children: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and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Diagnostic Molecular Pathyology,2002, 11: 212-221.
[10]Nelson KH, Li T, Afonso L. Diagnostic approach and role of MRI in the assessment of acute myocarditis. Cardiology in Review, 2009, 17: 24-30.[11]Cooper LT Jr. Myocarditis. N Engl J Med , 2009, 360: 1526-1538.
[12]Yajima T, Knowlton KU. Viral myocardit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rus. Circulation, 2009, 119: 2615-2624.
[13]Cohen N, Muntoni F. Multiple pathogenetic mechanisms in X linked dilated cardiomyopathy. Heart, 2004, 90: 835-841.
[14]Diegoli M, Grasso M, Favalli V, et al. Diagnostic work-up and risk stratification in X-linked dilated cardiomyopathies caused by dystrophin defects. J Am Coll Cardiol, 2011, 58: 925-934.
[15]Ku L, Feiger J, Taylor M, et al. Familial Dilated Cardiomyopathy.Circulation , 2003, 108: e118-e121.
[16]于丽平, 史琳影, 朱晓明, 等. 扩张型心肌病蛋白质组学研究. 中国循环杂志, 2013, 38: 47-50.
[17]王虎, 惠汝太. 基因突变与扩张型心肌病.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6, 34: 193-195.
[18]Michels VV, Driscoll DJ, Miller FA, et al. Progression of familial and nonfamilial dilated cardiomyopathy: long term follow up. Heart, 2003, 89:757-761.
[19]Cox GF. Diagnostic approaches to pediatric cardiomyopathy of metabolic genetic etiologi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rapy. Prog Pediatr Cardiol, 2007, 24: 15-25.
[20]庄太凤. 新生儿常见先天遗传代谢病的研究新进展.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 2011, 5: 3588-3590.
[21]Pahl E, Sleeper LA, Canter CE, et al. Incidence of and risk factors for sudden cardiac death in children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a report from the Pediatric Cardiomyopathy Registry. J Am CollCardiol, 2012,59: 607-615.
[22]Tsirka AE, Trinkaus K, Chen SC, et al. Improved outcomes of pediatric dilated cardiomyopathy with utilization of heart transplantation. J Am Coll Cardiol, 2004, 44: 391-397.
[23]Hollander SA, Bernstein D, Yeh J, et al. Outcomes of children following a first hospitalization for dilated cardiomyopathy. Circ Heart Fail , 2012, 5: 437-443.
[24]Alvarez JA, Orav EJ, Wilkinson JD, et al. Competing risks for death and cardiac transplantation in children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results from the pediatric cardiomyopathy registry. Circulation,2011,124: 814-823.
100037 北京市,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心血管病研究所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心力衰竭诊治中心
郭潇 主治医师 博士 主要从事心力衰竭研究 Email:luciaguo0526@163.com 通讯作者:张健 Email:zhangjian62@medmail.com.cn
R54
A
1000-3614(2013)05-0396-03
10.3969/j.issn.1000-3614.2013.05.022
2013-04-18)
(编辑:王宝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