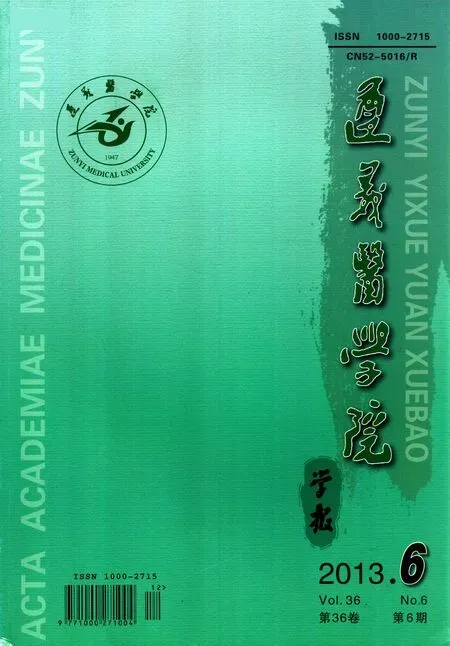肺癌CT灌注成像研究进展
宋之光(综述),李邦国(审校)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影像科,贵州 遵义 563099)
肺癌CT灌注成像研究进展
宋之光(综述),李邦国(审校)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影像科,贵州 遵义 563099)
肺癌;灌注成像;体层摄影技术;X线计算机
肺癌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每年大约有50万人死于肺癌,据2008年卫生部公布的第3次全国居民死亡原因调查结果显示,肺癌已位居中国恶性肿瘤首位。CT是发现肺癌最基本、最常用的检查方法。随着CT成像设备与技术的快速发展,从单层CT发展到多层CT,从单源CT发展到双源CT,以及对各种软件和后处理功能应用的不断完善,不但成像速度加快及图像质量不断提高,CT成像也正从单纯的以大体病理解剖为基础的形态学检查向着反映细胞、分子水平生理生化改变的功能学检查相结合的方面发展,以CT灌注成像(CT perfusion imaging,CTPI)为代表的功能成像技术逐步成为研究热点。现对CT灌注成像的原理及其在肺癌的临床应用价值进行综述。
1 CT灌注成像的原理
1991年Miles等首次提出CT灌注成像的概念[1-2]。CT灌注成像是指通过CT来直观显示活体灌注过程并作出定量分析的方法,即静脉团注对比剂之后,通过CT对感兴趣区域(ROI)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动态CT扫描,得到造影剂通过该组织的时间-密度曲线(time-density curves,T-DC),时间为该曲线的横坐标,注射造影剂后增加的CT值为纵坐标,对比剂在器官、组织内的浓度变化可由该曲线反映,灌注量在组织器官内的变化也间接得到了反映。
根据时间-密度曲线,可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反应组织血流灌注情况的各项参数,如血容量(blood volume,BV)、血流量(blood flow,BF)、表面通透性(permeability surface,PS)、强化峰值(peak enhancement,PE)、峰值时间(time to peak,TTP)、平均通过时间(mean transit time,MTT)等。为获得相应的CT灌注图只需对获得的灌注参数进行图像重组和伪彩染色处理。
CT灌注成像的理论是来源于核医学的放射性示踪剂稀释原理和中心容积定律[3]。CT灌注成像分析主要利用的两种数学模型是去卷积算法和非去卷积算法,在双源CT诞生以前的研究采用的多去卷积法,因为此前的非去卷积法还不够成熟,但去卷积法计算需要较长的采集时间,不适合受呼吸运动影响明显的部位如胸、腹部等,而双源CT采用非去卷积法如最大斜率法和肿瘤灌注模型,无需进行计算静脉曲线,只需要获得输入动脉峰值组织的多种参数如最大斜率、峰值等,与去卷积法相比扫描时间短,更适受呼吸运动影响明显的部位。
2 CT灌注成像在肺癌的研究
2.1 CT灌注成像在肺癌诊断的应用 对于肺内肿块的良、恶性诊断有困难时,可以行CT灌注成像以提供更多信息帮助鉴别诊断。张敏鸣等[4]研究发现恶性结节与活动性炎性结节在血流量、结节-动脉强化值及强化值比等参数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而良性结节以上参数低于恶性及活动性炎性肺结节。在一项肺结节动态增强的多中心研究中,恶性结节的增强明显高于良性结节,增强峰值的差异无显著性[5]。张金娥等[6]研究发现恶性结节灌注参数表面通透性、血容量均高于良性结节。该研究表明在灌注参数中,良性结节与肺癌的BV、MTT 和PS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以BV和PS 值差异最大。以BV≥6 mL/100 g作为恶性结节的阈值,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度分别为87.3%、100.0%、100.0%、65.4%和89.9%。以PS≥30 mL·100 g-1·min-1作为恶性结节的阈值,则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度分别为96.4%、75.0%、87.1%、87.2%和88.6%。
2.2 CT灌注成像评价肺癌血管生成 评价肿瘤血管生成能反映肿瘤生长情况,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子,微血管密度(microvascular density,MVD)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MVD作为评价肿瘤血管生成的“金标准”,可反映肿瘤血管生成活性,代表肿瘤内血管丰富程度。Sharma等[7]认为实体肿瘤MVD最有价值之处为预测其侵袭和转移,并与实体肿瘤的各种预后因素有关,能较好的反映非小细胞肺癌的恶性程度及转移情况。
作为微血管生产主要调节因子的VEGF不仅是肿瘤血管生长和转移的关键因素,也是一种具有肝素结合活性的生长因子。其主要生理功能为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提高血管的通透性,诱导形成新生血管,诱发恶性胸水,促进肿瘤细胞转移等。因此,VEGF是反应肿瘤血管生成的重要分子生物学指标,研究发现其与某些肿瘤的预后有密切关[8],且在肿瘤的增殖、浸润及转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判断肺癌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可根据肺癌组织中VEGF 表达判断疗效及预后。
目前,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VEGF及MVD是定量检测肿瘤血管生成的主要方法。但由于该方法需要获得病理组织,是有创伤性操作过程,阻碍了其在临床工作中的推广应用,而且不能动态观察活体组织的血管生成及其功能状况。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方便、无创、快捷的检测方法来评估肿瘤血管生成,进而评价肿瘤血管生成及其生物学行为。CT灌注成像便是一种无创的新方法,研究表明,MVD、VEGF的表达与多项肺癌的CT灌注成像参数如MTT、PS、BV及BF值等与具有相关性[9-10]。
2.3 CT灌注成像引导穿刺活检 目前,临床上常采用CT引导肺部肿块穿刺活检以确定肿块性质,但有时可能存在穿刺阴性的肺癌。为了减少因选择不当所取材部位造成的漏诊或误诊,可选择在肿块灌注值较高的部位取材以提高穿刺准确性[11],梁昆如等[12]研究表明,进行穿刺活检时选取BV图灌注最丰富、病变最大的位置作为最佳穿刺点,甚至可得到高达100%的成功率。因此,利用CT灌注成像技术引导行肺肿物穿刺活检可提高诊断阳性率。
2.4 CT灌注成像有助于肺癌的分级、分期 肿瘤的恶性度越高,新生血管越不成熟,微血管渗透性越高,即PS值越高。这是利用CT灌注参数PS等对肿瘤进行病理分级、分期、分型的理论基础。在利用CTPI对肿瘤进行分期、分级的研究中PS的重要性得到公认[13]。王小琴等[14]研究发现各型肺癌的BV、BF及MTT值不同。肺肿瘤的CT灌注成像从本质上反映了各种类型肺癌血流特点与肿瘤内部的微血管密度情况[15-16]。
2.5 CT灌注成像在肺癌放射治疗确定靶区的应用 确定靶区及对其进行精确定位是肿瘤放疗中的关键,如果仅以常规CT检查进行靶区勾画,对于病灶部位结构复杂、边界不清的原发灶来说,必将限制靶区定位的准确性。陆忠华等[17]报道,根据CT灌注扫描的参数勾画出的原发病灶范围,与三维治疗计划系统得出的具体数值进行比较,前者范围缩小约19.8%。该研究还表明CT 灌注成像有利于更准确地勾画非小细胞肺癌放疗计划靶区,尤其是肿瘤合并肺不张时,可将不张的肺组织与肿瘤分开。这也使得放疗中在给予肿瘤足够治疗剂量的同时更好的保护了具有正常功能的肺组织,避免增加了不必要的放射性损伤。初金刚等[18]研究表明周围型肺癌在灌注成像后得出的参数结果更能代表肿瘤实际的灌注情况,而且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可重复性,灌注参数图像与常规增强图像相比能更好地反应肺癌的血供情况。
2.6 CT灌注成像在肺癌放、化疗后疗效、预后评价中的应用 传统CT检查对肺癌的放疗、化疗疗效以及随访的评估主要是通过病变大小的变化进行,但是实际上肿瘤的放、化疗可能会对局部的肺组织造成损伤,对局部病变内肿瘤的残留情况的判断显得尤为重要,有时病变大小变化并不明显,此时传统CT检查便很难判断疗效情况。而CT灌注成像可利用肺癌放、化疗前后灌注参数的变化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及预测[19-21]。因此,CT 灌注成像已经越来越广泛地用于评价各种抗肿瘤药物的疗效[22-23]。
3 展望
CT灌注成像作为一种功能成像技术,因能在毛细血管水平定量评价肿瘤的血流灌注信息,成为近年来医学影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通过CT灌注成像技术,对肺癌的诊断、鉴别诊断、疗效评估、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CT灌注成像存在的一些不足:①多种因素影响着CT 灌注取值的准确性,如CT 灌注取值原则的标准化及扫描条件。②通过CT 灌注参数对肿瘤血管生成的评估,其灌注参数与VEGF、MVD关系尚无一致性结论,存在一定的争议。③肿瘤血管生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病理过程,而灌注成像只能近似地反映肿瘤的血管生成,因其仅仅对功能性可灌注的毛细血管敏感。④CT灌注成像X线辐射量较大。
以往对肺癌的CT灌注成像研究,多采用8层、16层或64层等螺旋CT进行扫描。对于多层螺旋CT,无论它的层数是多少,应用范围上一直面临着一些难以逾越的问题,如扫描速度、灌注参数测定准确性、辐射剂量等。而双源CT的出现,翻开了CT成像的新篇章,其具备扫描时间快,时间和空间分辨率高,辐射剂量较低,后处理功能强大,灌注图像质量高,可测定多种灌注指标,灌注参数测量准确等优势[24]。本课题组将充分利用炫速双源CT的优势,根据周围型肺癌的双源CT灌注成像特点与肺癌的MVD、VEGF之间的关系,研究周围型肺癌的肿瘤血管生成特点,有望更为准确地评估周围型肺癌的生物学行为。
[1] Miles K A.Measurement of tissue perfusion by dynamic computed tomography[J].Br J Radiol,1991,64(761):409-412.
[2] Miles K A,Hayball M,Dixion A K.Colour perfusion imaging:a new application of computed[J].Lancet,1991,337(8742):643-645.
[3] Blomley M J,Coulden R,Bufkin C,et al.Contrast bolus dynamic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oild organ perfusion[J].Invest Radiol,1993,28(5):72-77.
[4] 张敏鸣,周华,邹煜.动态增强CT对孤立性肺结节的定量研究[J].中华放射学杂志,2004,38(3):263-267.
[5] Swensen S J,Viggiano R W,Midthun D E,et al.Lung nodules: dual-Kilovolt peak analysis with CT-multicenter study[J].Radiology,2000,214(1):81-85.
[6] 张金娥,梁长弘,赵振军,等.CT肺灌注在肺结节诊断中的应用研究[J].中华放射学杂志,2005,39(10):1041-1045.
[7] Sharma S,Sharma M C,Sarkar C,et al.Morphology of angiogenesis in human cancer: aconceptual overview,histoprgnostic perspective and significance of neoangiogenesis[J].Histopathology,2005,46(5):481-489.
[8] Eichten A,Adler A P,Cooper B,et al.Rapid decrease in tumor perfusion following VEGF blockade predicts longterm tu mor growth inhibition in preclinical tumor models[J].Angiogenesis,2013,16(2):429-441.
[9] 周华,张敏鸣,肖圣祥,等.动态增强CT功能成像评价肺癌肿瘤血管生成的研究[J].中华放射学杂志,2006,40(2):171-175.
[10] Ma S H,Le H B,Jia B H,et al.Peripheral pulmonary nodules: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slice sprial CT perfusion imaging and tumor angiogenesis and VEGF expression[J].BMC Cancer,2008,8(6):186.
[11] Kang L Q,Song Z W,Li Z X,et al.Preliminary study on CT perfusion imaging in guiding biopsy of pulmonary lumps[J].Chin Med J (Engl),2009 ,122(7):807-812.
[12] 梁昆如,康江河,段少银,等.肺内肿物64层CT灌注成像研究[J].临床放射学杂志,2009,28(4):489-493.
[13] 左衍海,施鑫.CT灌注成像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J].医学研究生学报,2009,22(3):324-328.
[14] 王小琴,钱农,武洪林,等.肺癌CT灌注成像与病理分型的对照研究[J].实用放射学杂志,2007,23(12):1623-1626.
[15] García-Figueiras R,Goh V J,Padhani A R,et al.CT perfusion in oncologic imaging: a useful tool[J]?Am J Roentgenol,2013,200(1):8-19.
[16] Spira D,Neumeister H,Spira S M,et al.Assessment of tumor vascularity in lung cancer using volume perfusion CT (VPCT) with histopathologic comparison: a further step toward an individualized tumor characterizatio[J].J Comput Assist Tomogr,2013,7(1):15-21.
[17] 陆忠华,王建华,黄云海,等.CT灌注成像对非小细胞肺癌放疗靶区确定的临床意义[J].实用癌症杂志,2009,24(4):393-395.
[18] 初金刚,黎庶,王强.感兴趣区的划分对周围型肺癌CT灌注成像影响的研究[J].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2010,21(12),878-880.
[19] Curvo-Semedo L,Portilha M A,Ruivo C,et al.Usefulness of perfusion CT to assess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ombined chemo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J].Acad Radiol,2012,19(2):203-213.
[20] Wang J W,Wu N,Matthew D,et al.Tumor response in paticents with advance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perfusion CT evaluation of chemotheraphy and radiation therapy[J].Am J Roentgenol,2009,193(4):1090-1096.
[21] 姚强.CT灌注成像在肿瘤治疗监测与预后评估中的应用[J].医学研究生学报,2010,23(6):647-649.
[22] Bellomi M,Petralia G,Sonzogni A,et al.CT perfusion for the monitoring of neoadjuvant.chemotherapy and radiation theraphy in radiation therapy in rectal carcinoma:initial experience[J].Radiology,2007,442(2):486-493.
[23] Park M,Klotz E,Phys D,et al.Perfusion CT:noninvasive surrogate maker for stratific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response to concurmt chemo-and radiation theraphy[J].Radiology,2009,250(1):110-117.
[24] Nitin P.Computed Tomography in the 21st Century: Current status & future prospects[J].JIMSA ,2013,26(1):35-42.
[收稿2013-07-02;修回2013-09-25]
(编辑:王福军)
贵州省科技厅基金资助项目[NO:黔今科合J字(2012)2361号]。
李邦国,男,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胸部影像学,E-mail:lbg2015@163.com。
R814.42
A
1000-2715(2013)06-06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