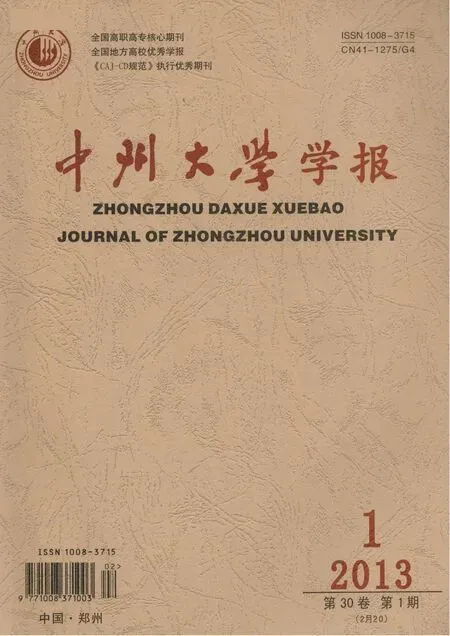个人经验介入文学评论的难度及方式
刘海燕
(中州大学学报编辑部,郑州 450044)
一、在影响的焦虑下,我们忽略了什么
在十几年的文学评论写作之后,近两年我对自己写出的每行字总是心有疑虑,真实吗?准确吗?意义何在?如果它不提供新的意义,于自己是徒劳,于这个文字泛滥的时代是多余,那么还写它干什么?这不是虚无,虽然是一次次的自我否定。这是一个被公共语境渗透而又渴望表达自身处境的评论者,一个把评论写作作为精神事件而非目的和手段的评论者,必然面临的困境。
与创作界相比,文学评论界经历着更大的影响的焦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各种现代文艺思潮、方法被译介过来,在我们接受不同文化营养的同时,也接受了影响的焦虑。多年来,文艺评论界——从文艺美学、古代文学到现当代文学评论界,都在不断呼吁建立自己的理论范式,也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2008年10月由《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浙江省几所高校共同主办的“文学创作问题与文艺学中国式创新”高层论坛,宗旨就是以对“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的共同关切,打通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以便为基本文学观念的“中国式创新”开辟道路。[1]专家们关注的焦点基本是方法论问题,即中国的文艺理论,怎样才能有效应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理论难题?
方法论是必要的,也是可以讨论、达成共识的。但比方法论更难于表述、难以界定的,也是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是评论家的精神世界。一个卓尔不群的评论家,他表达的是未曾表达的经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渊或缘,而不是遵循已有的规则。方法论和技术分析是必要的,但永远是次要的。在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批评家本雅明的笔下,我看到被人评价了千万次的卡夫卡,却像是第一次见到——“理解卡夫卡的作品,除了别的诸多条件外,必须直接地认识到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心里想的是他自己著作的“废墟和劫难场”。“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卡夫卡强调自己失败时的狂热更令人难忘。”[2]
本雅明对卡夫卡如此精当的评价也适用于他自己。这个在臣服于权威和意识形态的团体中,从不会回旋应酬的笨拙之人,一生倒运,处在一个以笔为生的自由作家的位置,还知道自己无法以写作谋生。因为,他发表的东西一点也不多,他不是著述等身的文学史家或学者,而是批评家和散文家,拒绝庸俗和冗长,宁愿用格言隽语写作。这个受其时代影响最小的人,言谈风格显得不合时宜,像是从19世纪漂游至20世纪的,他致力的是在当时的德国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或者说是不被欣赏的东西。他在《书信集》中写道:“我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被视为德国文学的首席批评家。困难是五十年来文学批评在德国已不再视为是严肃的文体。要为自己在文学批评上造就一个位置,意味着将批评作为一种文体重新创造。”他希望在“智慧的史诗性方面已经死灭”的时代找到“艺术”和“理性”的最富成果的存在方式。他曾用十年之功研究波德莱尔,其生命和写作不幸地终止于法西斯肆虐欧洲的日子。在他活着的时候,怎能想到自己死后会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
他的一生很像他的一本被搁浅的书的名字——《论无名的荣誉,论无辉煌的伟大,论无薪俸的尊严》。
他和卡夫卡一样都是在背运中不妥协,不被时代改造的人,并对时代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回应。
凡是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付生活的人,都需要有一只手挡开笼罩在他命运之上的绝望,用另一只手记录下他在废墟中的见闻,因为他所见所闻比别人更多,且不尽相同。
——卡夫卡:1921年10月19日日记
像一个遭船难的人想浮在水面而爬上已经在倾摧的桅杆的顶端。但从那上面他有机会发出信号,唤来搭救。
——本雅明:1931年4月17日致舒勒姆的信[2]
他们的命运和精神气质里有那么多相似的东西,因此,阿伦特说,本雅明无须读卡夫卡的作品就能像卡夫卡那样思考。他们是精神深处的同行者,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同行。因此,本雅明写出了独一无二的卡夫卡,阿伦特写出了独一无二的本雅明。他们的评论文字,是绝伦独创的心智对绝伦独创的心智的理解和阐释。
他们靠单枪匹马的个人的思想魅力,撑起一个叙事的小宇宙,开辟出信念能够自足生长的高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绝不是为理想主义者准备的,但是他们让后来的人们看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如何写作和生活。
这些太超拔的人物,对于今天的我们,只存在于我们的文字中,言说中,而不会在日常行动中被仿效。他们这样一次次被提起时,甚至有些类似我所在的城市开展的学习焦裕禄的活动,耗了不少资源、资金,焦裕禄精神却并没有在人的心中扎根,在日常中被仿效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是两个时空里的事情,其间有太多的差异和现实的不可能。
天才思想家、艺术家都是把性命搭进去的人,都是灵魂的漫游者,他们不分享一个时代共同的喜悦和好处。如只活了39岁的思想家帕斯卡尔,另一位思想家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里这样描述他:“他那忧虑、不安同时又是如此深刻的思想所做的全部努力,目的就在于不让他自己卷进历史的洪流中去。”[3]
今天我们都不愿意这样,我们首先选择的是健康、富裕、妥协地活着,从这个时代得到好处;其次,才是写作和思想。谁会为此而羞愧?当然,也有万一的例外,如逝者、思想者萌萌。
生活和精神气质的差异带来写作的差异。记得多年前我熟悉的一位专业作家就感叹,我们过着和别人一样的生活,所不同的是别人去上班,我们坐在家里写作,怎能写出大作品?!恐怕不仅是外在生活的相似,还有内心的相似吧?各种诱惑和时潮,改变着文人的内心,在一些文学现场,个性、立场、自由气质,这些文人的标志已经非常模糊,代之而来的是权益化规则、等级化秩序、戏谑性说道。
二、在真实处境中言说
还是要回溯一下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语境、文学格局、学术评价体制及利益分配的方式对人文学者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话语方式的影响。
90年代中后期以来,高等院校的相当一部分教师出于科研项目、学科建设、职称评定等的需要,纷纷撰写论文、论著。这些著述戴着正统的学术面具,命名都属于宏大主题,实则貌似神离,基本是知识演绎和学术词语的堆砌。这种学术体制诱导下的功利性写作,为快速获得各种管理和评价机构的通行证,懈怠于思想,忽略个体的经验,谨守学科的分类规范,而进行着知识的批量生产。这些论文、论著以铺天盖地之势,充斥于学术刊物、报纸媒体及文学刊物,败坏着学术及批评的品格。老一代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风范,在知识成果批量生产的时代,迅速地被遮蔽。作为一个高校学报的编辑,我听到过很多作者委屈地抱怨:体制如此,时潮如此,我能奈何?
一旦把罪责归咎于体制,个人就轻松地获得了伦理宽恕,理直气壮地成为技术复制时代的加盟者。一边分享着体制的利禄,一边责难着是体制让我这样做的。实际上,体制并没有强迫你这样做,是你自己的选择,甚至是不择手段的获取。
随着高校在社会生活、学术格局中的优势日益显著,作协系统的很多评论家渐次调入高校,成为特聘教授。主要诱惑是:收入的丰厚,生活的保障,这是物质上的;还有心理需求方面的,在学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成为主渠道,不在学科体制之内,知识生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就会削弱。如果一个人的创造力不再足以支撑他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发出声音,那么,介入团体、找一些文化标签来支撑自己可谓权宜之举。
本来,作为生活中的个人,身份的转变无可厚非,在消费时代,评论家也要生活得更优裕,更主动。问题在于一些很有锐气的评论家也在渐渐地迎合潜规则,被体制内的暗流裹挟着向前走,这裹挟本身也是诱惑,因为它意味着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可以分享利益与成功。《南方都市报》记者与2008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论奖得主耿占春的对话,曾谈到这个问题。
记者:作为一个学院内的批评家,学院化的学术体制对你有束缚吗?
耿:对个人的写作来说,学术体制表现为一种过于功利主义的诱导,不论是学科建设的需要,还是你个人在学科内地位的考虑,都会诱导人去考虑更功利的目的。我自己也不能全然免于这种诱惑,比如你会写一些在学科内说得过去的书和文章,其实这本书也必须为自己发明一个学术研究的面具,必须发明很多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式把自己的感受变成一个理论问题。
我觉得学术领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知识发明权,我们还是跟在西方的后面,别人命名这个知识领域了、这些范畴了,我们才会觉得可以谈,可以做。他们后现代,我们后现代;他们后殖民,我们后殖民,其实知识发明权还是在别人那里,我们还是跟在别人后面。也就是说西方学者的感受与经验可以变成知识,萨义德可以把自己在美国的感受变成东方学或后殖民理论,而我们则好像还不能给自己的经验感受一个命名,给它一个理论化的形态,使它知识化。[4]
其实,这最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前面问题的延伸,或者说两个问题是相互寄生的。全球性的文化语境,公共思潮、术语,知识的规整和权威化形式,更容易获得学术评价体系颁发的通行证;对于看重现世得失的学人,理论的移植与复制自然是更快捷的成功方式。“被学院‘招安’的批评家,或者以学者、教授身份兼任的批评家,都不能不带着这个学术体制的特色。”[5]
在全球性的文化趋同化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合力下,文学评论的独立价值何在?
我想首要的是应该说出我们真实的处境,作家木心说:“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如果你在那合力之中又挣扎着超越其上,内心就总处在撕扯中,撕裂中,疼痛中,你批评的那种东西更深地伤害着你自己,你分享着潜规则下的利益,但并没有心安理得的欢娱,却有无名的羞辱和不安。你对自身充满怀疑——我的言说,我的生活,真实性何在?
很多评论者不愿承受这种隐秘的撕扯,而让自己成为一个顺畅的不省视之人,成为游戏于潜规则中如鱼得水的成功者。
但是,任何时候任何场景下都会有例外,譬如《南方都市报》所提名的那些批评家。2008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委们写给耿占春的授奖辞,也可以看作是对于评论界的寄语:“在知识的面具下,珍惜个体的直觉;在材料的背后,重视思想的呼吸;在谨严的学术语言面前,从不蔑视那些无法归类的困惑和痛苦。”
耿占春先生也讲道写作的动机是为了处理负面经验,处理自己的焦虑、疑惑,甚至受折磨的感受。事实上,通过这种写作,写作者自身不仅能获得某种意义的健康,而且也有助于公共语境中信任感的建立。
经验的简化,大而无当的概念化说教只能让读者调转头去。思想的可能,应该从个人最真实的感受性说起,从个人斑驳陆离的经验说起,个体的心理状况也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也可以说是“光明磊落的隐私”。但是我们习惯于高蹈的语式,习惯于说出不含混的响亮的声音,现在要低声迂回地独语,并不是件易事。波德莱尔曾叹道:“与那些大声疾呼的相反的理由相比,存在的理由是多么虚弱。”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在于“他不只是聆听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而且也聆听那微弱的声音和观念”。
用文化批评、文学批评的方式表达出我们存在的处境,这要一个写作者多年的修炼和心智的明澈、沉潜,方可实现。这里要谈一下评论家艾云。
艾云是一个几乎不受时潮影响的思想者,也没有得过任何大的文学奖项。多年来,艾云一直坚持这么做着——在制度设计的缺欠尚未得到纠正之时,把公共领域中的生活事件引入批评描述和美学分析。
2006年,《花城》杂志推出“艾云专栏”,那些篇目《自我呵护:福柯及其个人自由伦理实践》、《带着不安与歉疚上路:现代性语境中的性态分析》、《谁能以穷人的名义》、《谁能住进最后的宫殿》、《缓慢迈向公民之路》、《寻找失踪者》,明显是艾云式的表述,或者说是艾云式的文体。这些文字和作者本人一样,具有通彻、明媚和上升的气质。
艾云能够给那些含混的边界模糊的经验,输入一种持久不断的沉思和俯瞰的气息。因为经验的基质,艾云的写作带有难得的直接性和生动性,她从万般头绪中扯出的那些问题,都连着我们极敏感的那根神经,无论是个人生活的,还是国家政治伦理的。事实上,经验的整合分序,不是凭善良的愿望便可去做,它要求有整体生活高度、有综合美感者,艾云多年来向着美好聚神的生活为这写作做好了准备,还有就是智性的力量。[6]
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者,得面对生存这一事实,他的可能思想,就在于对自身不断的反省、拷问以及负责,对自己作为一个从此岸到彼岸的泅渡者的复杂人性的清醒认识。如艾云,她的语言因此充满了拷问与挣扎的痕迹,她的思想回到了普通人的生存情状中来,有着斑驳陆离的阴影与光亮。
艾云一再强调:不管是感性还是理性的文字,都应该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之上。她在《理智之年》自序里写道:“没有我们对内与外感知的素朴真实,我们的所讲都会空洞。”艾云的写作始于对个体有限性的追问,沿着个人生存的真实情状而展开,这使艾云的声音一开始就有了可信、可感之处。艾云曾说,如果你是一粒尘土,那么也要成为一粒高贵的尘土。权威或学科代言人的位置与她无关,她只是一个思想着的个人,在普通中高贵,在沉沦中拔擢。艾云的文字以其可信性、心智的贯穿、飞升的力量,既适于学院也适于民间去阅读。
还是有一些这样的思想者、评论家,为写作为文学赢得了感动、声誉和尊严。
三、个人的责任,日常承担
从目前来看,在全球文化趋同化的过程中,西方强势文化带给我们的焦虑性影响一时也消解不了;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的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还有这个时代的消费语境、网络化生活,把文学评论这种需要专业、智慧、耐心和感受力的行当推到了被遗忘的边缘。这几乎就是文学评论的现实状况:在学界,被功利化地利用;在日常生活世界,基本被遗忘。
如果我们一再强调自己被动的处境,强调公共化的潮流对个人经验、个体生活的吞噬,那么,只能增加我们的焦虑感,同时庇护自己对于责任的推卸。这肯定不是有效拯救和承担的方式。
现在我们应该清理一下个人的责任。
2008年冬天,我和朋友一起在书店,翻开《雪莱散文》,为里面的一句话感慨不已:“每个人不仅有权表明他的思想,而且这么做,正是他的义务。”以前只知道雪莱是个诗人,没想到这个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么看重“思想”,把“思想”当成一个人的义务。也就是说,“思想”不是职业,不是哪个单位团体赋予你的任务,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义务。我们很少有人会这么想,更很少有人会这么做。
这和对精神生活的信念有关,像上文所提到的批评家本雅明,就是在绝望之上用思想的光照亮时代暗夜的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为理想主义者准备的。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相对富裕,表达的自由度也相对大多了,但是,为什么精神的力量比较孱弱?最主要的内因恐怕是我们的内心已散乱。
青年评论家中富于才情的代表性人物谢有顺,在与《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对话里,也讲到这一困扰,“在这样纷扰的时代,让自己的心清静下来、坚守信念很难。真正的困扰来自如何把握自己的内心和持守自己的信念。”[7]
当大多数人都在实现种种世俗成功的时候,谁甘愿在世界的边缘孤独地耐心地思想,承受自己的荒凉和“失败”?这是每一天每个人可能要碰到的铁链一般坚硬的逻辑。
这纷扰的现状,散乱的内心,使我们面对文学时很懈怠,缺乏耐心、郑重之情和长期自我训练的专业能力,去发现并说出真正的问题和意义。我们说出的似是而非的话,即便是以个人经验的名义,那个人经验也已是被公共价值标准同化后的个人经验。
我们在评论文学作品之前,也许该审视一下自己作为评论者的内心。在对他人、对大千世界的评论中,也要有自我审视的诚恳在里面。这是评论建立可信度的起点。不是概念化的论文写作,也不是道德优越者的高蹈评判,而是从自我的精神史和时代的隐秘秩序处,开始描述。是耐心地、以更多元的方式描述复杂性和真相,而不是急于评判,如上文所谈到的评论家所致力的方式。
一个评论者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内心太撕扯、太分裂,有效的方法也许是在内心建立起自己的评价尺度,不把写作当成世俗人生的工具和目的,而是当成过程中的事物,当成有限性人生的一个无限之源。还要靠有品质的阅读,养育这孤独的心,让它更稳定,更开阔。
当然,事实远没有这么清晰和简单。我们在不断抵抗诱惑和干扰的过程中思想,如果改写一下卡夫卡的话,描述今天比较优秀的写作者、思想者,大约是这样的:用一只手挡开笼罩在他世俗途中的诱惑,用另一只手记录下他面对纷繁世界时犹豫的所思。
我们也有为数极少的更优秀的思想者,他们一开始就不在诱惑之地,也不在影响的焦虑之中。这类思想者、评论家,在接受西方文化时,他不是技术上的学习和效仿,不是术语和概念的习得,他翻开书页,是想看到精神史上伟大的人物对于世间万物的理解,他获得的是类似空气一样的精神营养。这一切都会成为他思想的资源,而不是遮蔽和阻碍。他在对自身经验、历史、东西方文化和生活现场的打量中,企图找到可以依靠的有普世价值的精神秩序。但是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背靠的青山,而多是流水和沙砾。思到深处,仿佛在迷雾中,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在迷雾中不放弃的人。
还有,就是这类思想者、评论家,他们很重视文体的创造,思想的活力与富于个性、生机的文体本就是一体的。这也是评论的独立价值的一种体现。它不再是附属与寄生的二流文体,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文体。
提及个人责任,并非忽略外部体制的问题。我只是感到,个人的日常承担同样也是必要的。那么,看一下外部需尽的努力,譬如作协系统,应保持和建立更有活力的评价体系,形成与学院相弥补的多元评价机制,让刻板的技术管理和等级化权威化的秩序让位于文学性,无论是文学评论作品还是文学评论现场,都应弘扬真实、自由和思想性的表达;让写作者分享文学的公共价值空间。作协系统也有这种优势,它组织、掌控着文学现场,便于关注文学的当下性;技术时代的量化管理模式还不像束缚学院那样束缚它,这里还有从容做事的空间,有建立丰富性尺度的可能。
其实,这些年,作协做了很多令文学青年感动的工作,如中国作协主办的鲁迅文学院,对于一代代写作者的培养,其个性、多元、高品质的授课方式和非常人文的管理模式,不同于国内的任何一所大学。从那里走出来的学员,总会感慨地说出“终生受益”、“终生难忘”这样的词语。在世俗年代,鲁院给写作者提供了一个共享文学盛典的天堂。
外部良好的精神空间,会激励写作者的深度表达。一个心存广阔感激的写作者,会诚恳地面对每一行字,“起源即目标”(卡尔·克劳斯),对眼前之物辎铢必较的人们,已经败坏不了他的情绪,因为他面对这一行文字时已经面对着未来。
沿着“学院”、“作协”系统来描述,就像其他的分类法一样,难免会对现象本身有所简化。在说任何一种类型时,总会想起不在类型中的这一个、那一个,即使他也具有种种文化符码,但他却是一个自然的个人。如从郑州迁徙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文学教授、文化学者张宁,他有著述,但并不等身,他视为首要的是把人文理念传播给学生,他从大学新生带起,定期给他们做专题讲座及讨论,譬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人文?什么是比较文学?……不是以学术腔讲大道理,而是以具体可感的例证,深入细读作品的方式进入分析,让学生领会人文与社会生活的融会无间。虽然能听进去的学生并非多数,但一个教授、学者尽了自己该尽的努力。这比做了什么“宏大的”人文课题,出了一本又一本大而无当的著作更有意义。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问题很可能是把最基本的东西忽略了,尽管一些高校把教授上课等列入教学管理制度,但人文素质的培养与学术成果的复制比起来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技术时代的学术评价体系很难对此作出估量,也就是说,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与时代风尘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不直接,它更是人文知识分子个人的义务。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现象:有职业耐心和职业理想的教授并不多,急于成功急于富有成效地进入学术评价体系的人却很多。
假如我们能够把人生的节奏、成功的节奏放得缓慢一些,能够回到事物本身,有一些能够扎根的原创性的生活,那么,就会有一些内力抵抗或消解来自各种影响的焦虑。文学教授回到文学教授的位置上,其日常承担首先是把人文理想传播给学生,如果还能创造而不是复制出作品来,那他就不仅是有职业理想而且还是有职业才情的教授了;评论家回到评论家的位置上,诚恳地面对每一行字,如果他还是一个真正懂得悲哀和幻想的人,那他就不仅是有品格的而且还是有品质的评论家了。
[1]汤拥华,王晓华.“文学创作问题与文艺学中国式创新”高层论坛综述[J].文学评论,2009(1).
[2]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3]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M].董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4]耿占春,师彦.我一直生活在沮丧和热情的交替中——耿占春访谈[N].南方都市报,2009-04-12.
[5]王尧.文学批评:在媒体与学院之间[J].人民日报,2008-01-31.
[6]艾云,刘海燕.我为何这样思考——艾云访谈[J].作家,2008(2).
[7]郑廷鑫,谢有顺.一边批评,一边褒奖[J].南方人物周刊,20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