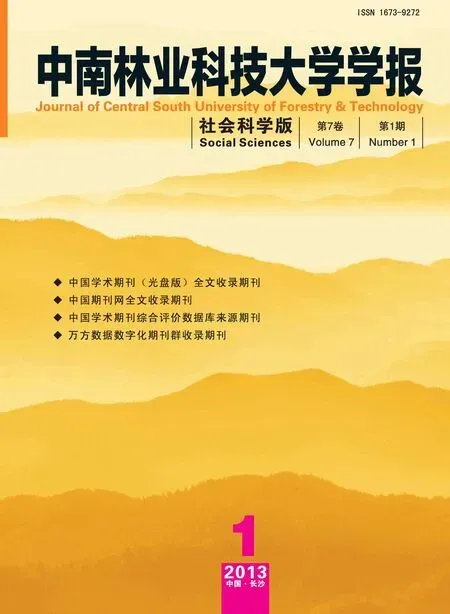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中电影及戏剧、戏曲的结构功能和表意作用
——以《创世纪》与《散戏》为例
陈 然
(福建农林大学 艺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张爱玲小说中电影及戏剧、戏曲的结构功能和表意作用
——以《创世纪》与《散戏》为例
陈 然
(福建农林大学 艺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以张爱玲的两篇小说为例,分析其中传统戏剧、电影、现代戏剧等在文本中的结构功能和表意作用,以此管窥张爱玲的写作行为与写作策略,剖析了她作为现代女作家对于社会文化独到的捕捉、观察、回应与创造。
戏 ;《创世纪》 ;《散戏》
张爱玲这个传奇一开始时就有她自己参与策划、塑造。“传奇”一旦形成,又对她的写作与人生都产生了重大意义。她那充分艺术化和对象化的自我、笔下人物建立自我存在感的渠道,为都市写作注入了新的元素,树立了新的风格。阅读张爱玲的小说,不难发现,“戏”,包括各地戏剧、戏曲、乐曲,话剧等戏剧艺术和电影,常常具有重要的结构功能和表意作用。本文以“戏”的因素为切入角度,对《创世纪》与《散戏》两个具有典型性的文本进行解读,以期窥见张爱玲独具个人色彩的写作策略,以及这种写作方法在现代文学中的开创性。
一、《创世纪》
《创世纪》描绘了三代女性的生活状态。其中,和全少奶奶黯淡麻木的“在场”不同,潆珠和祖母紫微是《创世纪》的重心,张爱玲对这两个角色如何自处,显然有着更多的兴趣。
小说有相当篇幅放在祖母紫微身上。可以推断,一来,紫微的原型是张爱玲祖母的嫡亲妹妹,亦即李鸿章的小女儿,可以增加故事的价值。二来,以紫微代表的“老人经验”与处于“难堪的青春期”中潆珠的视角,前者隐含了张爱玲对于探究和观察家族历史的兴趣,而后者,正是作者自己人生中不能忘怀的困扰。
文本中有大段关于紫微爱看戏的描述。文明戏、话剧,甚至如戏般情节跌宕、回肠荡气的张恨水小说,紫微也每本必看:
“从前有一段时间,春柳社的文明戏正走红,她(紫微)——倒是个戏迷呢,珠光宝气,粉装玉琢的,天天坐在包厢里,招得亲戚里许多人都在背后说头她了。” “她(紫微)喜欢看戏,戏里尽是些悲欢离合,大哭了,自杀了,为父报仇,又是爱上了,一定要娶,一定要嫁……她看着很稀奇,就像人家看那稀奇的背胸相连的孪生子,‘人面蟹’,‘空中飞人’,‘美女遁箱’,吃火,吞刀的表演。”“现在的话剧她也看,可是好的少。”她之所以迷上春柳社的文明戏,是因为里头有不同于传统戏剧的戏码——常常是“新作派”的情感故事。正如她之所以看张恨水的小说,是因为“小说里有恋爱,哭泣,真的人生里是没有的。”“现在这班女孩子,像她家里这几个,就只会一年年长大,歪歪斜斜地长大。怀春,祸害,给她添出许多事来。像书里的恋爱,悲伤,是只有书里才有的呀!”[1]
这里将祖母紫微与大孙女潆珠之间的隔膜,亦即“戏剧的”与“日常的”截然分开。只有戏剧化的情景下怀春才是可欣赏的,在生活里,孙女潆珠的怀春和悲伤,紫微不愿意看也不愿意管。
《创世纪》的结构沿着两条线展开,一是潆珠的恋爱,一是紫微做寿(兼写紫微的回忆)。于潆珠一方,出场时就写到她的寒酸及家境,因为是这样一个老式的家族里几辈人的故事,用了旧戏曲的词来比喻:“潆珠家里的穷,是有背景,有根底的,提起来话长,就像是‘奴有一段情呀,唱拨拉诸公听。’”[1]
到了潆珠自己的故事,涉及到的“戏”就有了不同的内容:
“潆珠她因为有个老同学在戏院里做事,所以有机会看到很多的话剧。”[2]
“她小时候有一张留声机片子......是古琴独奏的《阳关三叠》,嘣呀嘣的,小小一个调子,再三重复,却是牵肠挂肚。”[1]
“我听无线电也是这样,喜欢坐得越近越好,人家总笑我,说我恨不得坐到无线电里头去!”“唱片(《蓝色多瑙河》)的华美里有一点凄凉,像是酒阑人散了。潆珠在电影里见过的,宴会之后,满地板的彩纸条与砸碎的玻璃杯。”[1]
文中还有多处提到潆珠恋爱时与看电影有关的情况。在潆珠这代人的生活,话剧、电影已经成为自我观照的重要渠道,是她们感受自我的途径、行为的驱动力,她们部分地借助戏剧来想象自己、塑造对自我存在的认知,并以此接纳和抵抗新旧交替社会中女性充满挑战的生活。
潆珠的童年生活一度非常优渥,但是家庭陷入窘迫后,她的情绪也随之不为人所看重。因此,早在小时候,怀抱感伤,别意凄楚的《阳关三叠》就被潆珠的心灵捕捉到,成为她后来总感觉“感情荒凉”的源头之一。这种记忆为潆珠后来的人生准备了离别的情绪、非离别不可的意识。《阳关三叠》与《蓝色多瑙河》两首曲子对潆珠来说都昭示着“离别”,潆珠在恋爱中一早感觉到不安与危险,知道这将是需要中止的,但她迟迟舍不得,因这点恋爱是难得的一点生命的温度。“走两步又回来,一步一回头,世上能有几个亲人呢?”接着,张爱玲再用重复来强调了感情的荒凉,“可是,世上能有几个亲人呢?”[1]正是出于潆珠生命中这种顽固的别离感、孤独感,这首与恋人一起听的《蓝色多瑙河》也被她听成另外一首《阳关三叠》。正如“灰姑娘”式成长历程是女性文学中的经典主题,而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更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品。[2]又比如《简爱》中“以女主人公简爱的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坚强,独立,自尊与自信的女性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位值得赞美,歌颂的女教师形象”。[3]从某种角度来说,《创世纪》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双拼”与“对照”意味的文本。张爱玲将她最善于处理的两种经验冶为一炉,两者之间的隔膜,让文本自身在“消解意义”方面取得成功:紫微对于戏剧化故事的接受,与对潆珠感情纷扰的冷淡与漠视恰成对照,潆珠的感情也在自己的想象中退了场。曾创造人的老人,并没有在后辈身上感到生的延续感和喜悦,“被创造”的后辈则不只是身体上离开了创造者,更与之无法沟通、无法相互安慰。《阳关三叠》的两次出现,恰恰体现了这种隔膜、漠然、和意义的隐匿:这首曲子第一次出现,是潆珠童年时对感情稀缺、离别难免的最初体会。末一次出现,是在小说将近尾声时,祖母紫微听到有人在弹《阳关三叠》。虽然紫微一生经历许多别离,她对这个曲子却并无特别的感触:“楼下的一架旧的小风琴,不知哪个用一只手指弹着。《阳关三叠》的调子,一个字一个字试着,不大像。”思绪从回忆中飘回来,“楼下的风琴忽然又弹起来,“阳关三叠”,还是那一句。是哪个小孩子——一直坐在那里么?”[1]《阳关三叠》这首曲子的意义在此被抽空了,紫微喜爱的戏里没有潆珠的故事,她在戏中看到的情,移不到真实的生活里去。
二、《散戏》
《散戏》是一则浅明清丽的小品。“散戏”既交待了场景、时间和情节,也是南宫嫱自比的状况。全篇弥漫着散戏后的失落感——生命的节奏由紧锣密鼓变为寂静,人的精神状态由紧张、兴奋转为倦怠,夸张点说,正是“勋华之后,降为舆台”。戏演完之后,南宫嫱由舞台回到街上,讲过价后包里的钱总算够得上回家的黄包车费,她回忆过往,和丈夫结婚前也曾是“献身剧运的热情的青年”,也曾爱得热烈、轰烈——“心酸的,永恒的手势!至今还没一个剧作者写过这样好的戏。”[1]然而借感情戏大大膨胀、感动过自己的自我,随着感情戏高潮退去也渐渐模糊,模糊到她自己都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的面目,她想,她可能像帮工阿姨想的那样——不过是一个奇怪些的主母。这一切都根源于“她在台下是没有戏给人看了”。[1]生活还在延续,但南宫嫱已经感受到灵性生命正沉向枯寂。
不妨将这篇小说视为对《伤逝》一个遥远的致敬:《伤逝》写的是年轻的、激动的爱情发生之后,在日常物质和意义的贫瘠中,两个灵魂如何不再激动。有趣的是,《伤逝》通过男子的声口,讲述子涓如何不复可爱,变成了一个面黄肌瘦、抑郁多怨言的小妇人。男主人公并不曾想到子涓对他感情是否有改变。而《散戏》补足了《伤逝》的另一面,以女子的独白说出生活堕入平白之后女性内心的空落。南宫嫱就是一个能够温饱的子涓,她已经意识到自我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失去了华采,这正是对待自我和生活的反思的土壤——子涓没有“逃出”家庭的条件,但当城市里女性就业机会大为增加,谁敢说她不会背离爱已死去的婚姻,主动离开身边这个责任心、包容心和能力都不够的丈夫?《伤逝》之后有《散戏》,两者合成了日后日常的男女情感、婚姻的宿命之一种。令紫微无限新奇的“爱上了,一定要娶,一定要嫁”的延续很可能就是如此。
张爱玲一向乐于在文本里表现她智力与幽默的超越感。南宫嫱在台上陶醉于她成为“女先知”的慷慨壮美,张爱玲接着就说“她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有开口......不论她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哑剧。”[1]以叙述者的身份取消了南宫嫱语言的意义,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南宫嫱的自我认知——南宫嫱虽然对舞台下自己的模糊面目有所怀疑,但自认为是舞台上相当漂亮的演员。当这一点被强势的叙述人否定,就等于把南宫嫱唯一剩下的“意义”取消了。张爱玲同时写道,“中国的戏剧传统里,锣鼓向来是打得太响,往往淹没了主角的大段唱词,但到底不失为热闹。”[1]这照应了前述南宫嫱实际上总是在演“古装哑剧”一说——人生的热闹里热闹通常是仪式与器具的热闹,“人”的声音并不突出,这样,又更加深了南宫嫱这一身上的吊诡意味——新式女性在旧式戏剧文化中得到的并不是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只是给予了南宫嫱一个自我安慰的姿势。
需要指出的是,张爱玲常通过戏剧元素,让笔下人物得以通过“自我的对象化”来进行感知、行动,这正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生活状态——社会的发展,给处于不同年龄段、家庭背景、人生阶段和自我状态的女性带来了更为复杂的环境。她的小说,比同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更加显著地昭示着,新时代对女性的考验才刚刚拉开大幕。《倾城之恋》里有这样的片段:“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流苏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她对着镜子这一表演,那胡琴听上去便不是胡琴,而是笙箫琴瑟奏着幽沉的庙堂舞曲。她向左走了几步,又向右走了几步,她走一步路彷佛是合着失了传的古代音乐的节拍。她忽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那音乐便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继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干了。”[1]借由一首曲子完成的心理转换,成为扭转人物行为的前奏。类似这样的手法,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绝不鲜见,正如卡在新旧伦理、文化和社会生活转型期里的女性形象在张氏的作品中屡屡出现。
同时,这种“对象化”的方式,也可以看作生活模仿艺术、生活艺术化的表现——而生活的艺术化,正是现代文明的体征之一。文明发达的必然后果就是人身上沉淀的文化因素和成规越来越深厚,成为人们重要的经验来源,亦成为重要的感受、思考与表达的方式。这正是为什么张爱玲说“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1]的原因。就这点而已,无论男女,现代人都难逃新的社会文化风潮的包裹。在《年轻的时候》里有这样的句子——“绍兴姑娘唱的是:‘越思越想啦懊呃悔啊啊!’稳妥的拍子。汝良突然省悟了:绍兴戏听众的世界是一个稳妥的世界―-不稳的是他自己。”[8]《封锁》更是把一个封闭的时空,演绎成了一个活脱脱的舞台。男女两方的入戏与抽离,与米兰昆德拉的《搭车游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张爱玲在男女、家庭等题材中,借“小”故事和日常生活,讲出了时代深层次的大变化。这种超出同代作家的敏感、观察力与表达力,使她成为现代文化和都市生活不可替代的发言人。
[1] 张爱玲.张爱玲全集 [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18-219,96-98,167,98,7.
[2] 黄艳梅.“灰姑娘”式成长历程——谈从《曼斯菲尔德庄园》到《简·爱》成长主题的延续[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50-53.
[3] 史小平.论《简爱》中女权主义反抗意识[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06-109.
Structure function and expressive function of fi lm and theatre, opera in Eileen Chang’s Novels ——In “Genesis” and “performance” as an example
CHEN Ran
(Art academy of th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Fujian, China)
Using “Ultima” and “After the Show” as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film, and modern dram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building text structure and being ideographic in Eileen Chang’s novel . In this way, Eileen Chang’s writing strategies can be captured. Meanwhile, the paper try to analyze the way Eileen Chang observe, response and create the culture of Chinese modern society as a female writer.
drama; Ultima; After the Show
H059
A
1673-9272(2013)01-0115-03
2012-08-20
陈 然(1981-),女,山东烟台人,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本文编校:杨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