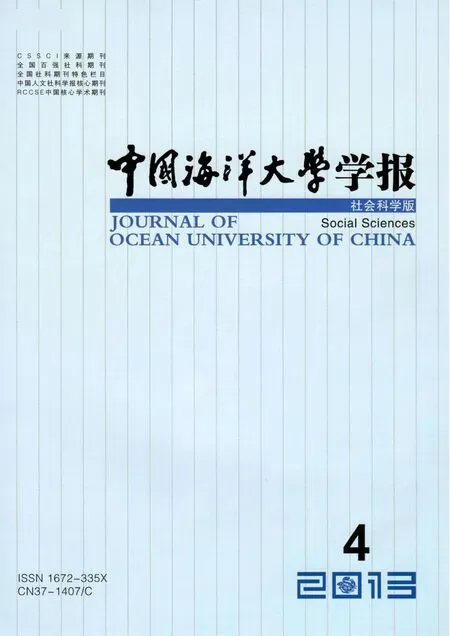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未遂*
董桂武
(青岛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未遂*
董桂武
(青岛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金融票证的载体形式出现了纸质、实物形式和电子形式。不同的金融票证伪造行为模式存在差异,信用卡的伪造包括形式伪造和内容伪造,非信用卡的其他金融票证的伪造仅包括内容伪造。根据实质解释和客观解释的观点,只有纸质或实物形式才是金融票证的有效载体。伪造金融票证罪系结果犯,其犯罪既遂的标准系伪造金融票证行为完成且伪造的纸质或实物金融票证形成。
伪造金融票证罪;未遂;刑法解释;行为犯;结果犯
我国刑法第177条规定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其行为对象包括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或者附随单据、文件、信用卡等。该规定延续了我国1979年刑法第123条的规定的伪造有价证券罪,这一罪名当时包含的对象仅包括支票、股票和其他邮件证券,随着金融业务领域的发展,金融票证不断增多,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确定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其伪造对象扩展至1997年刑法第177条所涵盖的范围,1997年刑法修订对该罪名的法定刑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增加了相应的单位犯罪。该条在规制犯罪对象和犯罪主体上,经过刑事立法的修正已经完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未遂认定出现了新的疑难问题。*相对于伪造金融金融票证罪,变造金融票证罪的未遂并不复杂,因此,本文主要讨论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未遂。
一、问题提出:未遂认定之疑难
我国通说对于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一般通过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的分类进行认定,[1](P147-149)伪造金融票证罪被看作行为犯。[2](P549)但是,即使认定伪造金融票证罪为行为犯,*笔者认为认定伪造金融票证罪为行为犯,值得商榷,下文将详细论证。科技发展到金融票证文本可以纸质形式和电子形式两种载体同时呈现,如何认定伪造金融票证犯罪行为实施完毕,却仍存在着疑问。
例如,在张某等伪造金融票证案(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2)崂刑初字第247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张某于2012年3月,代表珠海某公司与天津某司签订货值8亿元的油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珠海某公司先要将其公司的银行汇票扫描以电子邮件的形式传给某公司,以证明有资金能力。被告人张某于2012年3月23日,在中信银行秦岭路营业网点开设了珠海某公司账户,并索取了空白的银行电汇凭证,指使被告人齐某伪造银行电汇凭证。当日,被告人齐某私刻中信银行青岛秦岭路支行办讫章,又指使被告人黄某在空白的中信银行电汇凭证上填写收款、付款信息(金额为人民币5亿元),加盖假办讫章,之后,黄某把加盖假办讫章的电汇凭证、带有银行工作人员“孙某”的个人名章的银行凭证扫描,把该两份电子形式的金融票证发给了被告人李某,被告人李某通过photoshop软件将银行凭证上“孙某”的个人名章合成到电汇凭证上,又通过QQ邮箱发给被告人黄某。被告人齐某把该同时具备银行办讫章和个人名章的电子电汇凭证发给了张某,张某又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天津某公司刘某。
伪造电汇凭证,一般需要经过两个步骤:一是填写电汇凭证;二是加盖银行办讫章和银行工作人员个人名章。该案中,伪造的犯罪对象为汇款凭证中的电汇凭证,被告人经过了三个步骤完成了电汇凭证的伪造:一是黄某在纸质电汇凭证上填写收款、付款内容,二是黄某在填写收款、付款内容完毕的纸质电汇凭证上加盖假的银行办讫章(即纸质电汇凭证缺少银行工作人员个人名章),三李某在仅有银行办讫章的电汇凭证扫描件(电子形式电汇凭证)上通过电子合成的方式加上了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名章。通过上述三个步骤,被告人实现了电子电汇凭证同时具备汇款内容、银行办讫章、银行工作人员个人名章的目的。
与被告人行为相联系的两个问题是:一是作为行为犯的伪造金融票证罪,行为实行到何种程度已经既遂?二是,与问题一相联系,金融票证是否同时包括电子金融票证和纸质金融票证两种载体?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被告人的罪与非罪、犯罪既遂与未遂。其情况如下:(1)如果认为伪造电汇凭证的实行行为仅仅是实施加盖伪造印章的行为,但不以同时加盖所有章(银行办讫章、银行工作人员办讫章)的行为为行为完成,且其形式只能是纸质形式,那么,被告人张某、齐某、黄某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的既遂,李某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2)如果认为伪造电汇凭证的实行行为仅仅是实施加盖伪造印章的行为,但不以同时加盖所有章(银行办讫章、银行工作人员办讫章)的行为为行为完成,且其形式包括电子形式,被告人张某、齐某、黄某、李某均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的既遂。(3)如果认为伪造电汇凭证的实行行为以同时加盖所有章(银行办讫章、银行工作人员办讫章)的行为才系行为完成,且其形式只能是纸质形式,那么,被告人张某、齐某、黄某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的未遂,李某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4)如果认为伪造电汇凭证的实行行为以同时加盖所有章(银行办讫章、银行工作人员办讫章)的行为才系行为完成,且其形式包括电子形式,被告人张某、齐某、黄某、李某均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的既遂。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2)崂刑初字第247号刑事判决书》的内容来看,其明显采用了第四种认定方式,一方面认为伪造电汇凭证的行为需要同时加盖银行办讫章和银行工作人员个人名章,另一方面认为伪造的电汇凭证的载体形式不仅包括纸质形式也包括电子形式,被告人先后完成在纸质电汇凭证上加盖银行办讫章、在电子电汇凭证上合成银行工作人员个人名章是一系列伪造行为,因此,被告人张某、齐某、黄某、李某均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的既遂。但是,这种认定从金融票整的载体形式、既遂的标准均存在疑问。笔者将从伪造金融票证的行为模式、要素解释、认定标准等方面对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未遂进行论述。
二、行为模式:对象不同的差异
伪造金融票证罪包括四种行为对象:(1)汇票、本票、支票;(2)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3)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4)信用卡。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不同的行为对象在伪造的行为模式、间接法益侵害的危险程度均存在差异。
(一)行为对象不同,行为模式存在差异
伪造是指对刑法特别保护的对象进行仿制或造假的行为,[3]根据伪造指向的对象不同,伪造可以分为形式伪造与内容伪造。形式伪造,是对金融票证外观形式的非法仿造,也可以称作非法仿制。内容伪造,是对金融票证的内容的非法填写,也可以称作非法填制。[3]通常来说,伪造犯罪一般会包括形式伪造和内容伪造,也即先伪造形式,然后再伪造内容。但是,因伪造行为对象的不同,伪造犯罪并不必然同时须完成形式伪造和内容伪造:(1)有的有价证券是内容与形式的同一,如货币,伪造了货币的形式也就伪造了货币的内容,因此,伪造货币仅形式伪造就可以成立犯罪。(2)有的有价证券形式和内容是分离,形式为空格形式,如果使用需要填写并加盖有效证章才能有效使用,如汇款凭证,在各个银行我们都可以随便获得合法印制的汇款凭证,这种没有具体内容的空白凭证就是金融票证的形式,而要完成伪造该汇款凭证,不但要填写相关收款、汇款内容,还要加盖银行办讫章和银行工作人员名章,因此,伪造汇款凭证需要对内容进行伪造,即完成加盖虚假的银行办讫章和银行工作人员名章。
问题是,伪造金融票证四种行为对象是否均包括了形式伪造和内容伪造?就伪造票据的行为我国一直存在形式伪造、内容伪造和形式伪造且内容伪造的争论,[3]笔者认为,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伪造只能是内容的伪造,而对信用卡的伪造则包括了形式伪造和内容伪造。这主要是基于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或侵害法益的危险的法益保护原则。伪造金融票证罪侵害的法益是国家金融票证的管理秩序。一方面,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等的形式伪造显然对我国金融票证的管理秩序的法益侵害性不大,应该不认为是犯罪;另一方面,由于信用卡犯罪的潜在危险,制作空白的信用卡显然具有较大法益侵害性,应该受到刑法的规制。因此,2010年5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29条规定,(1)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或者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或者伪造、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总面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数量在十张以上的;(2)伪造信用卡一张以上,或者伪造空白信用卡十张以上的。
鉴于伪造金融票证罪因行为对象的不同而行为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在认定金融票证罪行为的着手时也因之而不同:(1)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伪造行为的着手点为内容伪造行为的实施,需要明确的是该内容伪造行为不是内容的填写,而是指有效印章的加盖行为。如汇款凭证,在一张合法汇款凭证上任意填写收款、汇款内容并不会构成犯罪,只有在完成填写收款、汇款内容的汇款凭证上加盖伪造的银行收讫章和银行工作人员个人名章的行为才是犯罪行为,也即填写收款、汇款内容是伪造金融票证的预备行为。(2)信用卡的伪造行为既包括了形式伪造,也包括了内容伪造,只要开始伪造信用卡的形式,即可构成伪造信用卡的着手。
(二)行为对象不同,间接法益侵害不同
一般来说,金融票证的伪造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没有实际存在的金融票证,凭空制造出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金额金融凭证,可称为“假的假金融票证”;二是根据实际存在的金融票证,复制了一个实际上真实存在的金融票证,可称为“假的真金融票证”。此两种情况,因其均侵害了国家对金融票证管理的正常秩序,均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其对国家金融票证管理秩序的侵害是相同的。但是,这两种方式间接侵害法益的危险程度却存在不同:(1)伪造“假的真金融票证”,如银行存单,可能让银行存单显示的票据金额存在着被间接侵害的风险,汇票、本票、支票、信用证、信用卡均存在此种可能,但是,例外的是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伪造“假的真金融票证”此两种凭证不可能使票据权利存在现实危险。(2)伪造“假的假金融票证”,此种情况,存在票据权利间接被侵害的只有信用卡,其他的票据权利均无现实间接危险侵害的可能。这也是2010年5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29条规定分两种情况确立立案标准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第1项从金额和数量上对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或者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或者伪造、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立案标准进行了规定,但这并不能表明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法益侵害性大小由金额决定,因为伪造“假的真金融票证”和伪造“假的假金融票证”的间接法益侵害危险性存在巨大差别,且汇款凭证对票据权利不存在现实的间接侵害危险,因此,立案标准和量刑标准应有所不同,量刑标准应因行为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以体现罪刑均衡原则。
三、要素解释:形式解释或实质解释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构成要件要素的内容会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如传播淫秽物品罪中的“淫秽物品”载体的变化。我国1979年刑法第170条规定的淫秽物品仅是淫书和淫画。随着录音、录像等设备的发展,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播放淫秽录像、影片、电视片、幻灯片等犯罪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将淫秽物品扩展到了淫秽录像、影片、电视片、幻灯片。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淫秽物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中,淫书、淫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为淫秽物品,即“诲淫性的音、像、书、画等制品”。199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淫秽物品为“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同时也对淫秽物品做了排除性规定,即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和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我国1997年刑法在此基础进行了补充修改,基本上坚持此观点。至此,我国淫秽物品都是附着在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等有形载体之上。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本来附着在有形载体之上的淫秽内容全部可附着在电子信息这种无形载体之上,电子淫秽物品借助网络传播速度和广度取得了比纸媒时代无与伦比的迅捷和扩大。因此,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第367条中的“其他淫秽物品”进行了扩大解释,认为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视频文件、音频文件、电子刊物、图片、文章、短信息等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电子信息和声讯台语音信息等都是淫秽物品。至此,我国的淫秽物品的载体已经包括了有形载体和无形载体,淫秽物品的内容一步一步扩大。但问题是,在目前刑事立法的条件下,伪造金融票证的“证”的载体形式可否包括电子形式?这有赖于对“金融票证载体”这一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
我国刑法学界目前对刑法解释存在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之争。形式解释是指以刑法可能语义作为解释的必要限度,即使牺牲处罚的必要性也要保障国民基于预测可能性进行行动自由的原则,以追求罪刑法定的形式理性。[4]此观点认为,刑法第263条规定的冒充军警抢劫中的“冒充”只能是以假充真,该项内容不可能包括真军警抢劫的行为。对于刑法第275条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认为应该从形式上解释“毁坏”的含义,从而坚持“物质毁损说”,*“物质毁损说”认为,根据有形的作用,即通过使用有形的力量,物理地损坏或者破坏该物的全部或者部分,损害该物的效用。参见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而排斥“效用减损说”。*“效用减损说”认为,所有损害文书。财物的效用行为,都是毁损。参见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该观点认为,如果仅具有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行为内容的含义已经超出了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对该行为就不能通过扩大解释使该行为入罪。
实质解释认为,以明确法条的保护法益为前提,在刑法用语的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内确定构成要件的内容,同时将字面上符合构成要件、实质上不具有可罚性的行为排除于构成要件之外,且当某种行为不处于刑法用语的核心含义之内,但具有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时,应当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将刑法用语作扩大解释。[5]该观点认为,刑法第247条暴力取证罪的行为构成为“暴力逼取证人证言”,其行为对象为证人,虽然刑事法上的证人不包括被害人,但是,可以通过解释把“被害人陈述”解释为证人证言,从而达到以刑罚规制暴力逼取被害人陈述的行为。
笔者认为,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差别并没有其主张的那样迥然不同。两者均赞成的客观解释可以说是两派观点弥合的衔接之处。客观解释与主观解释相对,客观解释论认为,“法律解释并不是去寻找立法原意,甚至未必有立法原意,解释法律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某个法律用语的可能语意范围内,可以把一些新情况通过解释包含进去,通过法律解释可以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6](P35)主观解释认为,“解释法律要去寻找法律的立法原意,即立法者的所思所想,如果立法者在立法时没有想到就不能包括”。[6](P35)形式解释论者和实质解释论者均赞成客观解释,其认为组织男性向男性卖淫的行为均构成组织卖淫罪。卖淫行为在1979年刑法确立之时,是指女性向男性卖淫,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接受了现实中存在男性向女性卖淫的事实,规定了组织他人卖淫,包括组织男性向女性卖淫和组织女性向男性卖淫,但是,此处的卖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间的卖淫则存在疑问。2003年的李宁组织男性向男性卖淫案,则要求对此问题进行明确的回答,如刑法第358条包括同性卖淫,则李宁构成组织卖淫罪,否则就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形式解释论者和实质解释论者均认为刑法第358条的卖淫包括了同性卖淫,也即认为卖淫包括了同性之间的卖淫和异性之间的卖淫,同性之间卖淫是卖淫可能具有的含义。从对“卖淫”含义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如果刑法用语的可能语义的理解不存在歧义的情况下,同是坚持客观解释的形式解释论者和实质解释论者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不同的是,当刑法用语的可能具有的含义不包括可罚性的行为时,形式解释论者和实质解释论者会出现争议。如上述的冒充军警抢劫,实质解释论认为冒充为假冒和充当,因此,冒充军警抢劫的主体就包括了假军警和真军警。[7] (P864)这种解释已经远远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上述暴力取证罪的取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笔者认为,形式解释论者和实质解释论者争议的焦点为刑法用语可能的边界问题,以及确定边界的准则。也可以说,形式解释论者和实质解释论者的争议在于处理文理解释和目的解释的关系上。形式解释论者认为,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本身就是刑法解释的准则,即坚持文理解释高于目的解释;而实质解释论者认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除了语义解释本身,还应根据法条所保护的法益,考虑行为所具有的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即目的解释指导、决定着文理解释。虽然实质解释论者认为文理解释对刑法解释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实质解释论者往往突破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以实现目的解释。笔者赞成实质解释论的以法条所保护的法益为指导对构成要件进行的解释方法,但是反对因行为所具有的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歪曲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也即文理解释以目的解释为指导,但是目的解释也应受文理解释的限制。如刑法第263条的冒充、刑法第247条的证人等均是以歪曲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方式来对刑法用语进行解释,显然不适当的。但是,刑法第385条的卖淫包括同性卖淫,刑法第329条抢夺国家档案的行为中,把抢劫行为认定为抢夺,符合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合理的。
因此,笔者认为,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应采取实质解释和客观解释。解释过程中,文理解释和目的解释均具有决定性的地位。[7] (P40)目的解释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一方面可以把虽然通过文理解释而符合构成要件、但危害不大的行为排除在构成要件内容之外,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具有处罚必要性和处罚合理性的行为通过文理解释使之涵括于构成要件之内;文理解释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为,无论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多大,只要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该行为就不能被解释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换句话说,目的解释通过法益保护的目的,既可以扩大文理解释的内容,也可以限制文理解释的内容;文理解释通过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限制因目的解释不断扩大构成要件的内容。对刑法第177条金融票证罪的金融票证的载体形式:(1)该条的金融票证载体并没有明示该金融票证的载体是纸质形式还是电子形式,因此,其用语的可能具有的含义包括了电子形式。(2)刑法第177条金融票证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金融票证的管理秩序,电子形式的金融票证能否侵害金融票证的管理秩序是决定金融票证的载体是否包括电子形式的重要依据。伪造货币罪中的货币必须是真实的货币,而不可能是电子货币,因为电子货币不可能危害国家货币管理秩序,同理,伪造电子形式的金融票证也不能破坏国家的金融票证管理秩序,因此,电子形式的金融票证并不是刑法第177条金融票证的载体。(3)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伪造金融票证的行为应该排除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构成要件之外,也即“尽管刑法典第177条对本罪的成立未作任何情节的限制,但根据刑法典第13条‘但书’的规定,对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行为,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宜作为犯罪处理。”[1](P406)通过电子形式伪造金融票证的行为,因其是不值得处罚的行为,该行为不属于刑法第177条规定的伪造金融票证的行为,也即电子形式的金融票证不属于刑法第177条金融票证的有效载体。因此,笔者认为,虽然从文理解释上,金融票证的载体可以包括电子形式,但是,通过目的解释,排除了不具有可罚性的金融票证的电子形式,也即伪造金融票证具有可罚性和合理的载体形式只能为纸质形式。
四、认定标准:行为犯或结果犯
我国通说对犯罪既遂的标准通过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和举动犯的划分来进行判断。结果犯是以法定结果的发生与否作为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别标志的犯罪,行为犯是以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危险犯是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发生的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的标志的犯罪。举动犯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完成和完全符合构成要件。[1](P147-149)伪造金融票证罪未遂的认定,首先在于伪造金融犯罪类别归属。
我国学者一般把伪造金融票证罪作为行为犯,[2](P549)[8][9]认为伪造金融票证犯罪既遂的成立,只要行为人实施完毕伪造金融票证的行为即可,不要求具体的犯罪结果产生,但同时又认为“只要行为人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与真票证的规格、形式以及绝对必需记载事项十分接近,足以使一般人误以为真”构成既遂,[8]而“如果由于伪造、变造手段很低或者设备缺乏、技术落后、材料短缺。资金不足等原因,而使金融票证不能达到足以让人误以为真的程度;或者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的行为没有实施完毕,而由于行为人一直意外的原因被迫停下来,即为本罪的未遂状态。”[9]根据上述行为犯的既遂理论,伪造金融票证行为的既遂在于伪造行为的完成,以及所制作的金融票证具有较高仿真性。因此,(1)伪造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既遂系指所有印章的加盖完成的行为;(2)伪造信用卡行为的既遂是指信用卡的制作的完成,包括空白信用卡和有内容的信用卡的完成。
笔者对伪造金融票证罪系行为持怀疑态度,虽然刑法第177条规定的伪造金融票证行为并无情节的限制,但这并不代表伪造金融票证的行为就是行为犯。*显然,伪造金融票证罪与危险犯、举动犯无涉。伪造金融票证罪属于结果犯还是行为犯,主要依据为伪造金融票凭证行为既遂是否需要伪造金融金融票证结果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坚持伪造金融票证行为是行为犯的学者也认为,伪造金融票证行为的完成会伴随着具有较高仿真性金融金融票证的出现。伪造金融票证罪的行为完成应以出现让人信以为真的实物金融票证为标志,如果一个伪造金融票证的行为没有出现实物金融票证,就不会有伪造金融票证罪成立的余地。据此,笔者认为,伪造金融票证罪应属于结果犯,伪造金融票证罪不但要求完成伪造行为,还要求出现以假乱真的金融票证,没有完成伪造行为或所伪造的金融票证就不能以假乱真,那么该伪造金融票证的行为构成未遂。
五、结论
伪造金融票证罪系结果犯,其既遂标志是伪造金融票证行为的完成和以假乱真的金融票证的出现。根据文理解释和目的解释,以实质解释的观点,伪造金融票证罪中金融票证的载体形式只能是纸质实物的形式,电子形式的金融票证不能成为金融票证的载体形式。因此,(1)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伪造行为的既遂为印章的加盖行为的完成和实物的金融票证的出现。(2)信用卡的伪造行为是指伪造信用卡的行为的完成和伪造信用卡的出现。与此相对,伪造金融票证罪未遂的标志则是伪造金融票证行为已经着手,但伪造行为未完成或者伪造的实物金融票证不能以假乱真。
据上述结论,张某等人的伪造金融票证行为已经着手,但是由于没有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名章等意志以外的原因,其纸质形式的汇款凭证仅加盖了银行的收讫章,其伪造行为并没有完成,伪造的电汇凭证也因缺少银行工作人员名章而不完备,且该电汇凭证在内容上存在以下明显错误:(1)收款人所在地与收款地不符;(2)收款地明显错误,事实上不存在山东省北京市;(3)附加信息为空,导致该笔汇款不能实现,此汇款凭证不能以假乱真。因此,张某、齐某、黄某的行为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未遂,李某无罪。但是,一审、二审判决均认定张某、齐某、黄某、黄某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既遂,判处张某、齐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黄某、李某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其判罚不可谓不重,但是,我们在遗憾畸重的刑罚裁量的时候,不得不面对我们因理解和适用刑法规范的不同而带来的严重后果:本无罪的人被判有罪,本罪轻的人被判重罪。
[1]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 黎宏.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 刘宪权.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疑难问题刑法解析[J].法学,2008,(2):138-145.
[4] 陈兴良.形式解释的再宣示[J].中国法学,2010,(4):27-48.
[5] 张明楷.实质解释的再提倡[J].中国法学,2010,(4):49-69.
[6] 陈兴良.口授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 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8] 曾月英.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刍[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2):36-40.
[9] 黄明儒.伪造、变造金融票证行为分析[J].华东刑事司法评论,2002,(2):127-139.
AttemptedCrimeofForgingFinancialInstruments
Dong Guiwu
(College of Law,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s, there appear three form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cluding paper, card and electronic. Forgery of different financial instruments presents different patterns. For example, credit cards can be counterfeited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 while other instruments which are non-credit cards can only be forged by altering their contents. According to material and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instruments only in the form of paper or cards can be conceived as being valid. Forging financial instruments is appraised as one of consequential offenses. Only completing the forgery and meanwhile making fictitious instruments in form of paper or card can be referred as an accomplished crime.
crime of forging financial instruments; unattempted crime;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behavioral offense; consequential offense
2012-08-04
董桂武(1978- ),男,山东胶南人,青岛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D924.11
A
1672-335X(2013)04-0100-06
责任编辑:周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