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说什么?
◎ 宣晓伟
一本由法国贵族托克威尔在150年前左右(1856年)写的原本是专业人士阅读的学术著作、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居然目前在国内坊间大热,到了洛阳纸贵、一书难求的地步。30多年前(1978年),也写过一本《思考法国大革命》的法国学者傅勒在谈到《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有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旧制度大革命》这本书“引用的人多,读它的人少;涉猎的人多,读懂的人少”(第26页)。傅勒的话颇有先见之明,也很符合现在国内学人纷纷发表相关读书文章的盛况。然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能满足各类人士的需要,大家可以纷纷从它那里获取话语资源、来浇自己块垒。正如谚语有云,一千个人看《哈姆雷特》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有人宣称只有他才是真正读懂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而其他人(尤其是与其意见不同的人)不过是涉猎,不免是一种狂妄和臆想。“真理越辩越明”,涉猎的人多了,读懂的人自然也会多。
对于托克维尔及《旧制度与大革命》,不少研究者有着极高的评价,有人认为“托克维尔不是一位哲学家,也不是一位法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集所有这几者于一身,甚至还要多一些”,“托克维尔走的是一个综合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的社会思想路线”。但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也纷纷指出《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疏漏之处,例如法国贵族的地位和作用、农民的境遇、旧制度末年的财政状况等等。事实上,前述的那位傅勒先生在自己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对于托克维尔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有许多直言不讳的批评。例如,他认为托克维尔将法国贵族的传统统治,描述为“领主和村社共同体之间一阙值得信赖的田园诗,…全然没有按历史方法来分析”(《思考法国大革命》,第210页)。托克维尔对“经济问题方面”的论述“始终流于肤浅和空泛”(同上,第217页),而且书中所“描绘的[法国]整个农民生活场景”,表明托克维尔“对农村经济的技术条件一无所知”。傅勒甚至批评托克维尔对“18世纪以前数百年的史料所知甚少,显然还是个追随前辈的学步者,仅凭自己的直觉和预设假定来重组前人的材料”(同上,第209页)。傅勒对于托克维尔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批评,也许带有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细节的吹毛求疵之嫌,但很明显托克维尔并不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学问家,而更多是从现实问题出发的研究者,“集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甚至还要多一些”的评价不免是对托克维尔的过誉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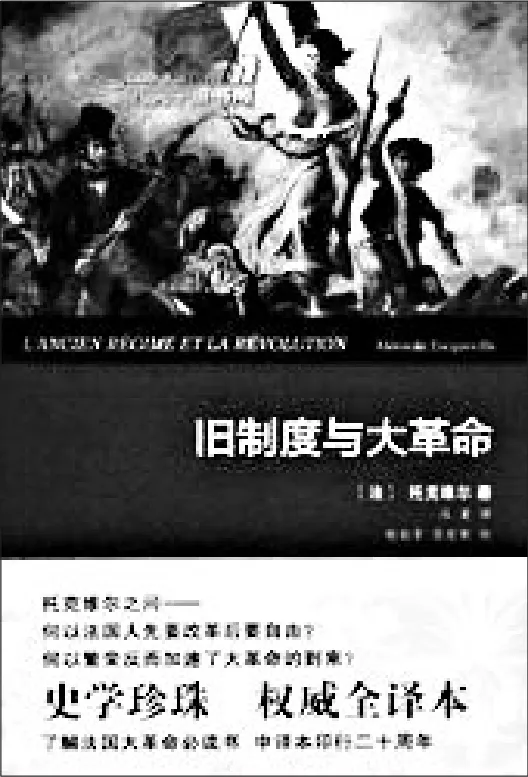
那么,托克维尔究竟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了什么,表达了何种思想,使得这位对其批评有加的傅勒也不得不赞赏托尔维尔的天才(同上,第23页),也使得150年后的我们仍可以借着其智慧的光芒来探究自己的问题?显然,这绝不仅仅是多为时下津津乐道的书中诸如“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15页)此类的名言警句。实际上,托克维尔本人的话最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当我出生之时,贵族制已经死亡了,但是民主制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能引导我既不盲目地倾向前者,也不会倾向后者。…我是如此彻底地置身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均衡状态中,因此我的自然本能让我不会轻易为这两种制度所吸引”。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正如他所言,是传统社会逐渐瓦解,但现代社会尚未成形的时代,是“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逐渐向着“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大转型的时代。而托克维尔的真正高明之处,是他彻底地置身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态度和眼光。他跳出了“维护传统社会的保守主义”和“颂扬现代社会的激进主义”之间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争论,既认识到几百年来欧洲社会“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必所至,天意使然”,伟大的民主革命已经不可抗拒;又预见到民主制度下对于平等的极度追求将有可能反而会使人们丧失自由、陷入被专制所奴役的境地。他一边不赞同传统社会中贫富差距悬殊的“不平等”的自由,另一边又担心现代社会可能会造成的“不自由”的平等。他既看到了以平等、民主、国家权力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预见到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即所谓的现代性)可能导致的种种问题。尽管在当时,现代社会并未成形,相应的问题也并未显现,托克维尔更多是站在传统的角度,对即将到来的现代社会可能产生的弊端做出了一些预判。然而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他对现代社会所预言的根本弊病(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人暴政”、现代政府权力扩张所产生的“柔性专制主义”等),表现出了惊人的准确性和预见性,由此也被誉为是“未来学的奠基人”。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到底说了什么。在书的前言中,托克维尔开门见山地针对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己的两大追问,一是“为什么大革命会如此突然地发生在法国而不在他处(当时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且旧君主制又如此彻底而迅速地垮台?”二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要打破旧的君主专制,与过去传统一刀两断,从而建立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新制度,最终却迎来了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为专制的政府?”(同上,第32、33页)。现在我们看到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实际上只是托克维尔打算撰写的第一部,重点论述的是第一个问题,即大革命产生原因和大革命性质的分析,主要针对革命发生(1789年)前的情况展开讨论。他原本打算在第二部著作里重点分析革命后法国社会的演变并推测它的未来,从而回答第二个问题。但如同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所说“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写出了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于世。我能否有精力完成它?谁能说得准呢?个人的命运较之民族的民运更为晦暗叵测”(同上,第33页)。托克维尔在此又一次展现了他那精准的预见性,事实也正如此,两年多后他因病而逝,未尽的书稿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叹惜和遗憾。
然而如果我们细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会发现托克维尔事实上已经在书中间接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他在讨论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时,给出的答案已经预示了为什么革命后的法国反而会迎来一个更专制的国家,这里的核心就在于法国“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在托克维尔那里,中央集权制既是导致法国发生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革命后法国会回到更为强大且更为专制政府的根本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理解托克维尔这一重要判断,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大革命发生前欧洲(包括法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状况。简要言之,欧洲传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等级君主制为特点的分权化多元社会。这个分权化既体现在君主对所属诸侯、诸侯对从属他的小诸侯和骑士相互之间有着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君主和“自主的”贵族阶级分享统治权;也体现在世俗政治权威之外,基督教会自成一体,既垄断了信仰的问题,又负责教育和学术的传承,同时与王权相互依靠和斗争,通过领地、什一税等制度安排内嵌到现实政治权力中,成为另一政治权威;还体现在鉴于罗马法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使得欧洲社会的统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离;又体现在欧洲的许多城市秉持了古希腊罗马城邦自治的精神和传统,通过赎买的方式而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控制而成为城市居民的自治共同体。凡此种种,这样一个分权化的多元社会,有其缺点,也有其优点。它等级分明、贫富悬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但各阶层之间又能够各安天命、各守本分、各司其职。这种统治方式下的国家(或君主)常常是软弱无力的,但社会却不乏自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普通民众常常食不果腹,但社会总体仍是富有弹性和稳定的。由此,托克维尔曾感叹“当王权在贵族阶级的支持下平安无事地统治欧洲各国时,人们在不幸之中还享到一些我们这一代人恐怕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幸福”。他也断言欧洲传统封建社会“虽有不平等和苦难,但人们的心灵并未堕落”,“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可能有其稳定性和强大性,尤其可能有其光荣之处”(《论美国的民主》,10页)。
然而,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伴随着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伴随着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欧洲传统的封建统治逐渐土崩瓦解,到处陷于崩溃,而身份平等驱动下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然势不可挡。托克维尔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论述法国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总体上就是围绕着法国如何从“传统的分权化封建社会”一步步变为“一元化的中央集权制社会”来加以展开的。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宗教作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受到削弱和摈弃。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改造社会,使人类新生”成为了大革命中法国人的新信仰,国家主义的思想逐渐兴起。文人成为首要政治家,“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的文学政治占据了主导。其次,贵族被褫夺了地方上的统治权,政府官员(总督、总督代理等)取代贵族进行地方上的管理,贵族成为只享有免税权的第一居民,贵族阶层堕落为只牢牢抓住经济特权不放,再也无力承担起应有的政治重任而被边缘化,原有贵族统治下的地方自治遂告终结。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渐渐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距巴黎最远的农村教区要想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房顶,也必须获得来自巴黎的御前会议的裁决(《旧制度与大革命》,第92页)。再次,王权通过御前会议、设立特别法庭的方法来影响和操控司法体系,“凡是涉及公共利益或因解释政府法令引起的争讼,均属于特别法庭的管辖范围,普通法庭只能宣判涉及私人利益的案子”,“任何政府官员,未经事先批准,不得由普通法庭起诉”。政府不断介入司法的天然领域,从而保护各级的政府官员,“不仅涉及要员,而且涉及芝麻小官,只要与政府有一丝一缕的关系便可以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同上,第97页)。第四,国王通过卖官鬻爵(在各城市向某些居民出售永久统治他人的权利)的方式逐渐限制了城市的自由。法国各城市的政府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而要改变这一弊病,只有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同上,第87页)。中央政府逐渐控制了城市的一切事物,无论巨细,所有事务都须征询政府主管(总督)的意见,甚至包括公众喜庆活动中下令点燃灯火。与此同时,巴黎在中央集权制下吸取全国的精华,迅速极度膨胀,成为法国本身。而其他地方省份则自治权力不断消失,难有活力,萎靡不振。
大革命前,以国王为核心的御前会议已领导着国家的几乎一切事物,一个大臣(总监)具体操办各种事项,各省由一个官员(总督)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等王权逐渐将传统社会中分散在贵族、教会、法庭、城市、行会等等各种各样的权力都收归到中央,一个庞然大物般的中央集权制便显露身姿、屹然而立。与这个巨兽般中央集权所对应,传统社会则渐渐演变成一个人人一盘散沙、原子化的社会。“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性、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变得彼此最为相似,然而这些如此相似的人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而这样的感情很快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同上,第35页)。
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前业已形成的法国中央集权制度,既是专制的又是软弱的。表面上整个社会权力的根本来源只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发布各种各样的命令,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命令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然而在现实中,再精明强干的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做到洞悉一切、指导一切。中央政府的规则和命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常常走样、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旧制度原形毕露;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这就是它的特点”(同上,第108页)。与此同时,这个中央集权制度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将触角伸向社会任何领域,能够调动一切资源,政府力量不断增强,道路交通、公共服务、慈善公益等政府事业大力推进。正是有了非常强大但又实行开明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中央政府的推动,在大革命之前,事实上法兰西开始富裕和全面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当中央集权制度拆除传统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自治团队和组织、完全收缴了他们的权力后,便需要独自面对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整个社会治理在实现了一元化集权的同时,也逐渐失去弹性和慢慢僵化。社会中的任何抱怨、任何动荡都会最终指向中央政府,引起中央政府的恐慌。中央集权惧怕社会中任何自治团体的建立,也惧怕任何与其分权的行为。“这个政府是如此地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同上,第150页)。于是,这样一个既专制又软弱、既强大又脆弱的中央集权体制,就像用沙子堆成的巨大金字塔,看起来庞然巍峨、不可一世,但真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轰然倒塌。这就是大革命会在法国突然爆发,而旧君主体制却一下子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而如果法国人民依旧没有认识到中央集权制的教训和危害,反而试图通过大革命的方式来重新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人间乌托邦,那么他们必然会再次拥抱中央集权制度,最终则只能迎来一个更强大和更专制的政府,这也正是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所试图告诉我们的关于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的真正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要片面地理解为托克维尔就是要谴责法国的“中央集权制”,认为“一切都是中央集权制的错”,又过于简单化了托克维尔那复杂、微妙而又深刻的思想。如前所述,托克维尔的真正高明之处是他即认识到了现代社会来临那不可阻挡的种种趋势和变化又预计了这种变化和趋势可能产生的问题。类似于对民主政治的态度,托克维尔同样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中央集权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不对“中央集权制”一味进行谴责。他指出在一个身份日趋平等的社会,“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不是不仅越来越中央集权,而且越来越管小事情和管得越来越严。各国的政府越来越比以前更深入到私人活动领域,越来越直接控制个人的行动而且是控制微不足道的行动”(《论美国的民主》,第857页)。他说:“我无意谴责这种中央集权,而只是指出这个事实”(同上,第854页)。事实上,托克维尔甚至声称“至于我个人,我决不能设想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会生存下去,尤其是会繁荣富强”。他盛赞“英国政府集权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点,国家就像一个单独的人在行动,它可以随意把广大的群众鼓动起来,将自己的全部权力集结和投放在它想指向的任何地方”。与英国相对比,由于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内“几个各自为政的部分总是有权利或机会去拒绝同全国最高当局的代表合作,甚至在事关全体公民的利益时也是如此,…因为没有政府集权,德意志帝国从来不能集中全国的力量,从而一向没有使它的力量产生可能取得的好处”。(同上,第97页)。
一面是中央集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大势所趋;一面是中央集权将可能带来如前所述的种种严重问题,又不能听之任之,不可不防。托克维尔又是如何来思考并解决上述难题的呢?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再次展现了他伟大的智慧和洞察力。他将中央政府的集权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集权(governmental centralization),一种是行政集权 (administrative centralization),前者是“诸如全国性法律的制定、本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与全国各地都有厉害关系”等事情的领导权的集中。后者是“诸如地方建设事业、国内某一地区所特有”事情的领导权的集中。托克维尔认为第一种中央集权是有益的,是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所必需的。而第二种中央集权是有害的,是必须制止的。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时认识到,美国的地方是高度自治的,各个地区的本地事务(不涉及全国和其他州的利益)几乎完全由当地居民说了算;与此同时美国的联邦政府又是强大有力的,在事关全国性的事务上有着压倒性的领导权,正是有了强大的联邦政府才把美国整合成一个真正繁荣富强的国家。托克维尔对于两种中央集权的区分,真正在理论和现实的层面有助于破解关于“中央集权制”的悖论。
如同本文开头所述,阅读经典、品味历史的理由之一是为了满足我们自身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托克维尔在其论著中对于“中央集权制”的讨论无疑会给我国中央-地方关系如何进一步调整带来启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我们打破了计划体制下一体化的格局,中央逐渐向地方分权让利,激励地方发展。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更是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地方的财政权利。各个地区你追我赶、互相竞争成为了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然而目前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远未到位,在现有的中央地方关系的格局下,一方面无论大小事务、几乎事事都要中央部门决策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中央集权过度,地方分权严重不足,跑步(部)进京、跑步(部)前(钱)进的现象越演越烈;另一方面在各种事务具体执行上中央极度依赖地方,中央部门的执行能力非常有限,在一些全国性、跨地区事务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仍很普遍,各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屡禁不止,从这个角度来看则又是中央分权过度、集权严重不足。由此,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中央地方关系,成为了推进改革的核心内容,而“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也成为十八大报告中的重要改革举措。
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想建立起合理的中央地方关系,就不能在已有的中央地方逻辑框架下打转转,而是必须充分意识到区分上述两种中央集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加以探索和落实,真正建立起贴合中国现实又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和规律的中央-地方关系,这也许正是我们在150年后重温托克维尔的经典著作和智慧时所获得的真正启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