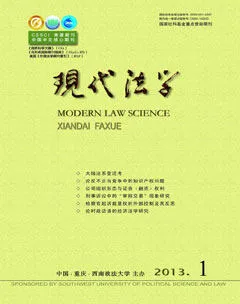开放的事实
摘要:在西方,尽管自中世纪以来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根本上是一个裁量的问题,但直到现实主义法学的勃兴,这种认识方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然而,迄今为止,包括现实主义法学在内的各种理论似乎都没有从逻辑上对事实的自由裁量本质展开系统的分析、证成。艾柯的“开放的作品”理论为这项任务的完成提供了足够的启示:之所以事实具有自由裁量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彻底的开放的作品。对这一结论的证成,除了有利于澄清理论上的相关争议外,也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进一步完善的支点。
关键词:诉讼;事实;确定性;开放的;自由裁量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从《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订空间说起
大概自上世纪初欧美现实主义法学的滥觞以来,司法过程中的事实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比得到重视更重要的也许是,从此人们对司法过程中的事实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一个根本且系统的转向:在此之前,尽管有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司法过程中的事实之可争辩性,并且这种可争辩性甚至也往往被一些立法或实践所反映,但人们更多的时候却以追求清楚、确定事实基础上的公正为司法之圭臬;而在此之后,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根本上是一个主观认定、也即discretio-n的过程。所谓,“事实上,司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diseretion)是每一个法律体系都内在(inherent)具有的因素”。
应该说,如上转变在欧美已经基本完成,但国内却似乎呈现出明显更慢的节拍。以最近(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例,其中的大量具体规定似乎仍然或明显或隐性地表明,至少立法者对司法过程中事实的预期或者说期望是“清楚、确定”,相应的典型条文如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又如第48条“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再如第168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在这些条文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事实作了“准确”、“属实”、“清楚”、“确实”、“充分”之类的限定(类似的条文至少还有第53、172、195诸条)。对司法过程中事实属性的此种强调,还可见于公开发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2012年3月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这个文件中,第一大部分的第1条就特别明确“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均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为准确适用这一标准,建议进一步明确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与这种具体规定所体现出来的对“清楚、准确”之事实的追求相比,也许整个立法所贯彻的追求“清楚、准确”事实的精神主旨才更能体现我国在如上转变过程中的更慢节拍:尽管该法案在第233条明确规定,“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但与此同时却又在第241、242、243、244、245等条规定了“再审程序”,其中第242条对启动再审的实质条件作了这样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仔细分析这五个条件的前两项,就会发现其根本的立法精神似乎只能是:存在唯一的案情或案件事实,并且通过司法可以进而也应当追求到这种事实,故凡与这种追求相悖的法律结论,都不可取、都可以也应当被再一次审理。可以说,从已经公布的立法材料来看,对于如上两项规定,除了这种解释外,似乎无法给出其他合乎逻辑的说明。如果这种推断是准确的,那么,整个刑事诉讼法最能反映如上“清楚、准确”之事实要求的大概正是此种再审规定及其中的精神主旨。
在这里,先不说“清楚、准确”的事实标准其实从根本上与最近一次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新添加的事实认定之“排除合理怀疑”(第53条)标准相悖:排除合理怀疑根本上是一个法官内心确信的discretion,而“清楚、准确”却是一种相对外在、客观的标准;不说“清楚、准确”的事实标准与新添加的整个证据排除规则之间存在逻辑的相悖:证据排除往往依据的是合法律性标准,而“清楚、准确”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标准,而毋宁说主要是一种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标准;也不说“清楚、准确”的事实标准将从根本上消解刑事审判结论的终局性:按照这种事实标准,实际上任何刑事审判结论都可能被提起再审,进而动摇刑事司法系统的权威性。我们想追问的仅仅是这样一个问题:所谓“清楚、准确”的事实,如果从道德上、理想目标上看是可欲的,在司法的实际过程中,它是否可能?
可以说,如果通过剖析能够证明所谓“清楚、确定”本就是司法过程中从逻辑上讲不可能实现的事实标准,那么,这种剖析将不仅仅表明经过此次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事实认定方面还有进一步修订空间;而且还将表明目前存在的“清楚、准确”标准与新引进的“排除合理怀疑”以及证据排除规则、刑事司法的终局性之间的悖谬,并不意味着后三者有什么“错”,而恰恰是前者需要修订;进而表明至少作为最近一次修订所重点引进的“排除合理怀疑”以及证据排除规则确实具有合理性、必要性。
一、现实主义法学的相关贡献及局限——以弗兰克为例
弗兰克(Jerome Frank)本人曾就美国现实主义法学(legal realism)的整体状况作了这样的说明,“事实上,没有所谓的现实主义法学流派的存在……因为我们的研究进路其实并不相同。……也许我们唯一共通的地方是如下一个消极方面:对传统法律理论有所怀疑,以及对当前因法院利益而导致的司法改革热情有所怀疑。当然,尽管我们其实并无什么积极的相通之处,但大体说来,所谓现实主义法学可以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阵营:第一个阵营以卢埃林为代表,主要针对的是规则的确定性问题,可称为‘规则怀疑主义’”,“……第二个阵营可称为‘事实怀疑主义’,此一阵营当然也怀疑纸面规则的确定性,与此同时他们还对那些由下级法院呈交给更高级法院并影响该更高级法院决定的事实有特别的兴趣”。
应该说弗兰克的“自供”有一定道理,但却也多少忽略了所谓现实主义阵营所具有的如下积极方面的共同点:他们都排斥法学的形而上学研究(如纯粹的概念、逻辑研究),强调以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态度研究法律实践中的各种经验。换言之,与动辄关注法律或法律的世界“应当是什么(what it ought to be)”的学者不同的是,现实主义法学者们强调的是法律或法律的世界“实际上是什么(what it is)”。
另外,严格说来,欧洲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法学(Scandinavian Realism)与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多少还是存在侧重点上的不同:前者更多地关注整个法律世界的构造以及法理学的一般问题,而后者则重点研究法律实施、尤其是司法实践过程中的法律、事实问题。也正是欧美现实主义法学存在的这种差别,关联着本文的主题,我们决定仅仅选取美国现实主义法学中“事实怀疑主义”者弗兰克的理论作为研究对象。
在弗兰克看来,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并不具有像传统法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具有确定性。他以证人证言为例,对确定性事实之所以不可得,作了如下三重分析、说明:第一,证人不是机械的记录机器,因而在事件发生时,他(或她)对过去事件的观察就已经发生了错误。即便证人的观察本身也许是可靠的,但第二,证人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当然,就算证人记忆也没有出现偏差,他也仍然有可能第三,在出庭作证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作出有偏差的陈述。
基于对事实的如上分析以及相关的其他研究(如所谓司法过程中的恋父情节、又如司法官个人人格因素等),弗兰克相信,司法官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充斥着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甚至可以说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根本就是“猜测”:证据正如谜面,据以得出裁判结论的事实则如谜底,这一谜底系司法官根据谜面猜测而来。弗兰克进而断言,“不管正式的法律规则是多么的准确和明晰,不管这些正式的规则背后存在着什么能够发现的一致性,由于判决所依赖的事实令人捉摸不定,因此在绝大多数还没有提起或审理的诉讼案件中,现在要预测将来的判决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在将来也通常是不可能的。所以,事实怀疑主义者认为,极大地提高法律的确定性的企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徒劳的,而且认为这种企图尽管是要强化司法公正,但事实上可能导致不公正”。申言之,在弗兰克看来,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根本上不具有确定性,因为它从根本上取决于司法官的自由裁量。
乍看上去,一如规则怀疑主义看上去消解了法律的确定性进而消解了法治的可能性一样,事实怀疑主义的如上论调实际上也等于消解了司法的确定性进而消解了法治的可能性。这对于以法治为志业的法律人(包括法学者和法律职业人)多少有点釜底抽薪式的骇人听闻——可以说,迄今为止的许多反对、否弃现实主义法学的论调,几乎多少都建立在这种“恐惧”上。然而,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对弗兰克的如上分析、论断作中立的考察,也许得出的结论可能恰恰是:他确实道出了司法过程、乃至整个法治实践中事实问题的真相。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完善事实认定标准或证据规则,归根结底,哪些证据可以采信、多少个证据就足以认定某种事实等问题还是取决于法官的依法主观认定或者说法律之下的自由裁量。申言之,也许从经验上讲,尽管在有些情形下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正好与社会学或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重合,但这种重合——不管概率有多大——不过是一种偶然,从逻辑上讲,由于它们具有根本不同的面向及标准,因而也根本不是、也不应当是一回事:这就正如“美女”与“三八红旗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两者毕竟是依据不同标准而得出的不同人群,因而根本上也不是一回事。
当然,这并不是说弗兰克等人的论断全然有理。事实上,几乎从一开始它就始终面临着如下问题:就算在疑难案件中案件事实可能可以争辩,在简单案件(如我国诉讼程序中的所谓“简易案件”)中案件事实也具有可争辩性吗?更进一步讲,弗兰克等人从诉讼、也许尤其是疑难案件诉讼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经验、现象,是否足以证成司法、乃至整个法律世界的事实不具有确定性?哈耶克(F.Hayek)就曾明确指出,“法律确定性的程度不能够根据这些案件的结果加以评断,而必须根据那些并不导致诉讼的争议来判断,这是因为从符合法律的角度来观察,其结果实际上是确定的。正是这些决不会诉诸于法院的纠纷,而不是那些诉之于法院的案件,才是评估法律确定性的尺度”。虽然哈耶克针对的是现实主义法学者关于法律确定性之命题,但应该说,哈耶克此论几乎可以同样“适用”于现实主义法学者关于事实确定性的怀疑命题。
也许是弗兰克等人不屑回应,或者是因为这种回应——从逻辑上证明事实的不确定性是必然的——从根本上违反了他们的经验主义式的学术旨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无力作出这种回应。总之,弗兰克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迄今并没有对如上质疑作出有力的回应。因此可以说,尽管弗兰克等人第一次系统地打开了事实的不确定性这一魔盒,进而使得人们可以第一次直面相关的问题并为解决或缓解相关问题开创了新的局面;但从根本上讲,他们又确实没有能够证立事实的不确定性这一命题,而毋宁说仅仅通过直觉敏锐地观察、把握并归纳出了这一命题。
另外,仅从措辞的角度看,弗兰克等人所谓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certainty or uncertainty)似乎也有一定问题。这种问题可以从如下分析中得到显现:至少对于那些已经得到了执行的司法结论而言,它们本身具有充分的确定性,否则也就无法判断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执行;相对应地,从逻辑上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据以得出这一确定性结论的小前提(事实)也是确定的,因为根据三段论,从不确定的前提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考虑到所有案件最终必定会得出一个交付执行的结论,因此,怎么能断言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根本不具有确定性呢?
二、开放性:艾柯的分析及启示
诚如前述,弗兰克等人的贡献在于,几乎凭一己之力使人们对于事实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一个转向;而其局限则在于,他们仅仅通过对诉讼、也许尤其是疑难案件的诉讼作一种经验主义的观察并进而通过归纳得出了事实的不确定性结论,但却没能或至少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一经验性命题进行更为系统的说明以及更有逻辑的证成;另外,从常识上看,所谓司法过程中的事实不具有“确定性”似乎至少具有措辞上的某种不足。
基于此,本文提出“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具有开放性本质”这一命题。很显然,在这一命题中,“开放性”显然是最需要进行界定、说明的关键词。
“开放性”或者说“开放的”(open)是意大利文艺评论家艾柯(Umberto Eco)首次系统提出并予以阐述的概念。艾柯在对古典文艺作品和当代文艺作品进行对比研究时发现,“一首古典音乐作品,巴赫的赋格、《阿伊达》或者《青春之祭》都是这样一种声音的组合:作曲家以确定的、封闭的形式来组织这一组合,然后献给听众,或者将这种组合用通常的符号标示出来,以引导演奏者用作曲家设想的方式再现作品;而这些新的作品则是没有封闭的、确定的信息,不是以单一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的,而是一种有多种可能的组织方式,使演奏者有可能自己去主动发挥。因此,这些作品不是已经完成的作品,不是要求在一定方向之内使之再生、在一定方向之内加以理解的作品,而是一种‘开放的’作品,是演奏者在对它进行美学欣赏的同时去完成的作品”。
艾柯进而对这种作品的开放性作了这样的解释:(一)“开放的”作品因为是在运动之中,所以其特点是呼吁同作者一起创作作品;(二)从更广的范围来说存在这样一些作品,这些作品从外表上看已经完成,但这些作品对其内部关系的不断演变仍然是“开放的”,欣赏者在理解其全部刺激时必须去发现,必须去选择这些演变;(三)每一件艺术品,尽管是根据明确或不明确的必要的理论创作的,但实质上说仍然是对一系列潜在的阅读“开放的”,每一次阅读都使作品按照一种前景、一种口味、一种个人的演绎再生一次。
那么,为什么对文艺作品的欣赏、把握会具有这种开放性?艾柯对此作出的解释是,一部艺术作品不是一只昆虫,它同历史中的世界的关系不是次要的或者偶然的,而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被解读的过程中往往也会由于欣赏者基于不同历史背景而形成的“前景”、“口味”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艾柯的这种解释虽无多少创意,但却也颇有道理:说它没有创意,是因为它实际上不过是将哲学解释学中的一个基本结论“有解释,解释就会有不同”具体化到文艺领域而已;说它颇有道理,则因为哲学解释学早已经通过“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或fusion of horizons)理论对这一命题作出了雄辩有力的证明——按照哲学解释学,任何解释从根本上都是解释者以自己的前见反映解释对象的过程,而任何解释者的前见又总是被一定的历史情境所局限故而实际上总是一种特定、有限的视域;另一方面,任何解释对象又总是其作者依据其特定视域而给出。因此,从根本上讲,“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一个读者一定要固执己见并完全不顾及作品文本本身的规定性,并坚决宣称自己的解释不过是有所不同而已,岂非容易陷入那些立基于哲学解释学“有解释,解释就会有不同”结论的绝对的相对主义泥淖?艾柯并不认为对开放作品的解释本身就是或应当是无限的,更不意味着人们无法比较对开放作品的各种解释之间的优劣程度。艾柯特意区分了对作品的“利用”(use)和“诠释”(interpretation):利用意味着不以对作品的欣赏本身为目的,如为了寻找灵感而欣赏作品;而诠释则以对作品本身的欣赏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必定需要给予作品文本以及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充分尊重。换言之,真正的对作品的欣赏、把握、解释,具有其特定的内在规定性,这种规定性首先表现为作品的背景。而在更早的一部作品《诠释的限度》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艾柯指出,“文本(泛指各种作品,引者注)是人类将世界转变为容易驾驭之形式的渠道,尽管它具有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却受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的规定。这意味着,尽管也许我们无法判定对文本的不同解释何者更好,但至少我们可以对何种解释更坏作出明确判断”。那么,主体间性的最后标准又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艾柯实际上给出了对作品进行诠释的另一重限制。根据艾柯,这种限制来自于作品文本本身。具体说来,即“对一个文本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文本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不能,则应舍弃。就此而言,文本的内在连贯性控制着,否则便无法控制读者的诠释活动”。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这种作品似乎更为常见?艾柯用一种看上去肯定的语气给出了这样的肯定解释,“也许可以肯定地认为,这种对确定的、确实的必然性的逃避,这种含糊和不确定的倾向,正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危机状况;或者恰好相反:这些理论同今天的科学相一致,表现了人们对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和认知模式采取开放态度的积极能力,表现了人们有效地努力推进自己的选择余地和自己的新境界的进程的积极能力”。申言之,之所以现代社会开放性作品更为常见,这是因为现代性社会的精神实质正是开放性、或更具有开放性。
另外,艾柯还特别提到了作品的“开放性”与“确定性”并不相悖。他援引另一位学者的话对此作了这样的揭示,尽管作品本身具有开放性,但“所有的演绎都是确定的,因为对于演绎者来说,每一次演绎就是演绎作品本身,演绎同时又是临时的,因为每一个演绎者都知道,他必须始终要进一步深化他的演绎。从演绎是确定的这一意义上说,不同的演绎同时也是并行不悖的,因为每一种演绎都不能把别的演绎包括在内,不能否定别的演绎”。
总之,在艾柯那儿,“开放性”或者说“开放的”意味着:第一,尽管作品在作者那儿已经具有了完整的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对于不同的读者而言,会因立场、口味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开放性——在并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开放的作品呼吁读者的共同参与和完成;第二,这种开放性并不意味着诠释的无限性,毋宁说它是一种有限的开放性;第三,尽管有时无法判定哪一种解释更好,因为可能存在多种具有同等“好”的解释,但却可以对哪一种解释是坏的作出判定;另外,第四,由于每一种诠释本身是确定的,因此,开放的作品并不意味着解释结论的开放性或不确定性。
三、事实是一种彻底的“开放的作品”
尽管艾柯第一次创造性地用“开放的”来指称的对象仅仅是文艺作品,但在笔者看来,也许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同样是一种典型的“开放的作品”;并且,其还是一种远比一般文艺作品更具开放性属性、因而也是更加彻底的“开放的作品”。
首先,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具有艾柯所谓的“开放的作品”如上诸个基本层面:一方面,作为已经发生的“作品”,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呼吁作者(当事人)以外的人一起完成作品——所谓“认定”事实或核实事实就是这种完成过程;司法过程中的事实看上去已经发生,因而看上去已经“完成”,但实际上作为事实构成部分的各个片断、证据之内在关联、组合却完全可能在不同的人那儿得到不同的认识——否则也就不会出现事实认定过程中的种种质疑、争辩及观点的冲突;也因此,对同一个事实的每一次认定,其实都是一次重新的演绎。另一方面,对于同一案件可能确实存在几种几乎具有同等“好”之程度的事实认定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事实认定的结论具有无限多种可能,并且对于何种事实认定结论是“坏”的也比较容易得出一致结论。这也正与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谈及司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问题时所作的如下论断之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自由裁量,正如面包罔(doughnut)中的那个空,如果没有外面的一圈面包(原则)划出界限,它本身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所谓自由裁量并不是可以无视某些权威标准而任意的裁量”。再一方面,事实的开放性本身并不意味着结论的不确定性——几乎任何裁判结论最后都是确定的,因而相应的、作为小前提的事实基础也一定是确定的。
而司法过程中的事实之所以更具有开放性,则因为其次,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明显更强的开放性属性:
第一,作为事实构成基础的证据取决于所有诉讼参加人员之择取,而事实本身又取决于诉讼参加人员依据证据而展开的想象、回构。对于一般的文艺作品而言,真正严肃的欣赏者当然可能因其前见或者说视域的不同而欣赏到不同的美,但应该说对所有欣赏者而言,待欣赏的艺术作品本身已经基本确定,并且欣赏者也不应断章取义地仅仅拿其中的某些部分来说事儿,也正因如此,尽管文艺作品具有开放性,但它毕竟具有至少相对明确的限度。但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却似乎是一种具有无限开放可能的“作品”,因为作为该作品构成基础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欣赏者(如法官)的收集、认定、择取,而作品(事实)本身又从根本上取决于欣赏者依据这些证据的想象、或者用弗兰克的话讲的“猜测”:在收集原始证明材料的过程中,证据当然必定有所遗漏;在认定证据的过程中,这些证明材料也当然要经过一定的筛选,至少不具有合法律性的证明材料将被摒弃;究竟多少个怎样的证据才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致于充分到可以依据这些证据认定某种事实是一个只有依赖欣赏者主观能动的问题;最后,在通过这些证据回构案件事实的过程中,欣赏者必定需要揉入比一般文艺作品的欣赏者更大、更多的主观能动性,方有可能根据有限的证据猜测出可以最终作为案件结论小前提的法律事实。申言之,如果说一般的文艺作品在欣赏者进行欣赏之前已经由单一且确定的作者基本给定故而其开放性仅仅体现在欣赏过程中的话,那么,司法过程中的事实这一作品则在欣赏者之前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完成”,因为它的欣赏者(以法官为核心的所有诉讼参加人员)本身就是它作者的有机组成部分——案件当事人或行为人不过给出了作为案件结论小前提之法律事实的一部分也许是最重要的“原材料”,它的完成最后取决于司法官根据法律和证据等其他原材料所作出的回构、推断及认定。简言之,司法过程中的事实之所以具有更为彻底的开放性属性,是因为它的原材料以及“作者”甚至都是开放的。
换个角度说,第二,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并不是赤裸的生活事实本身,而是所谓的“法律事实”,因而它从根本上不可能为原始作者(当事人或行为人)独立完成,而必定需要司法过程中其他诉讼参加人员的参与方能最后完成。尽管当前学界对何谓法律事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可以如下一种相对得到更多认同的界定为基础,“法律事实是由法律规范所框定的,而又经过法律职业群体(法官起着最终决定性作用)证明的‘客观’事实。这其中的法律规范反映了立法者对什么是法律事实的框架性认识,而法律职业群体证明的则是客观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意义”。因此,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其实是一种为诉讼参加人员赋予了特定法律意义的事实。不难想见,由于案件事实不会“依法发生”,因此事实的这种法律意义并非事实的原始作者(当事人)一开始就独立且充分设定好的,而必得经过司法过程经过事实的读者(以法官为核心的所有诉讼参加人员)的接续、加工方能生成。这意味着,即便一个案件证据的收集、认定以及根据这些证据所回构出的“赤裸案情”本身可能由于物证技术的高度发达或案件本身的过于澄明而无法产生争议的话,那么,也绝不意味着作为司法结论之小前提的“事实”本身就不具有可争辩性:无论物证技术多么发达,无论案件本身多么澄明,并且因而无论作为生活事实意义上的案情本身多么没有争议,对这些事实的法律意义的赋予也仍然是可以争辩的。换言之,事实的法律意义也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从这个角度看,与一般文艺作品的意义的开放不同的是,读者所诠释出来的意义并不认为是作品本身的构成部分,也就是说,读者是否诠释出某种意义并不影响作品本身的独立存在,也不影响作品本身的完整性;而司法过程中诠释出来的“法律意义”却是事实本身的有效构成部分,因为生活事实本身根本无法成为审判结论的小前提。这实际上意味着,不仅仅作为案件结论小前提的事实之赤裸案情是多个作者共同完成的,也许更重要且更明显的是,由于事实的法律意义不由行为人给定,而这种意义又恰恰是作为案件小前提之事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部分是“赤裸案情”),因此,司法过程中的事实之作者就注定是开放的。
紧密关联着这一点以及前文第一点,第三,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在如下意义上也并不由它的原始作者完成,甚至也不仅仅由诉讼参加人员完成,因为它还必须仰赖立法者的参与、或至少是间接参与才能真正地完成。如前述,作为裁判结论大前提的事实是一种依法认定的、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事实。这一事实本身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司法过程中任何事实的最终生成,立法者都通过立法之法进行了包括方向上、性质抑或量上、度上的全面参与。可以说,没有立法(者)的参与,同样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作为裁判结论小前提的事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成弗兰克的如下看似绝对的判断。他说,在司法过程中,“对任何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只有那些涉及如何认定事实的法律才是决定性的。因为除非法院认定了某种事实,否则就算它是存在的(in existence)也不具有任何法律意义”。以上分析表明,司法过程中事实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它总是面向立法之法保持着开放性:它内在地要求诠释者(诉讼参加人员)必须结合原始作者在“创作”作品时可能根本没有考虑的立法之法进行最后的完成。很显然,除了极少数情形外,一个完整的文艺作品都不可能具有这种必须仰赖自身以外的作品之参与方能完成的属性。
最后,司法过程中事实的开放性,根本上为诉讼逻辑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诉讼根本上是一种对抗性活动,这种对抗不仅仅发生在原告(或检控官)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间——所谓“诉讼是一场战斗(fight或fighting)”,其实也同样发生在原告与法官、被告与法官之间:尽管最终的事实认定权力属于法官,但在整个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实际上的主导者却可能是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可以肯定,这三方的预设立场具有根本上的不同:原告与被告是对立意义上的不同;而原告一被告与司法官则是根本追求上的不同,前者以追求自身合法合理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而后者则以通过纠纷的解决维续法律的权威以及法治的运转为圭臬。可以说,正是这种立场的根本不同,使得各种诉讼参加人员也许作为一个普通人时也可能倾向于对案件事实作出同一的认定,但其特定的诉讼参加人员之身份却使得他(或它)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必定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这与一般文艺作品的欣赏者之相互关系有所不同:对于一般文艺作品的欣赏者而言,尽管也可能具有不同的立场,并且也可能以欣赏到同一作品不同的美而为更高境界,但这种“不同的立场”或“不同的美”毕竟不是相关欣赏的内在要求(command),而案件事实的认定者从不同立场进行事实的认定却是诉讼活动的内在规定性使然。从这个角度说,一般文艺作品的开放性更多的是一种欣赏逻辑之自然结果,因而它充其量可能也仅仅是“允许”或最多是“鼓励”欣赏者赏析出“不同的美”;相对应地,司法过程中事实所呈现出来的开放性则除了同样必定具有如上“自然结果”之属性外,还是认定者应然且积极追求的目的,否则所谓诉讼各造的对抗意味或诉讼本身的“战斗”属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诉讼逻辑的内在规定性对事实的开放性之影响还体现在它有时候杜绝事实的读者(如法官)成为标准读者和善意读者。在这里,“标准读者”(model reader)是一个源自艾柯的术语,即那些通过考察作品背景并遵循作品连贯性等途径而实际上揣摩到作品本身结构、意图的读者;而“善意读者”则是笔者顺着艾柯思路创设的一个术语,指的是那些有意愿去揣摩作品本身结构、意图的读者。如果说从整体上看,在一般文艺作品的欣赏者那儿毕竟还存在如前所述的作品本身之连贯性以及背景的限制,因而存在所谓“标准读者”或“善意读者”的话,那么,对于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有时候则会因为法律的硬性规定而取消欣赏者(如法官)成为标准读者或善意读者的可能:譬如,在刑事诉讼中,尽管对赤裸裸的案情(brute fact)本身当然存在标准读者所应“读”到的样子,因为从根本上讲赤裸的案情事实本身当然存在唯一的答案,但当诉讼期限届满而检控方又不能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时,法官就只能从法律上认定一个可能他(或她)内心并不一定认同的某种“事实”;又譬如在所有诉讼活动中,一个事实材料明明与案情具有关联性但却因为获得的过程非法或其他原因而导致不具有合法律性,进而也就不能作为认定当前案件事实的依据,这当然也会导致事实的读者无法或至少更难成为标准读者或善意读者。可以说,正是法律在程序、技术上的一些设置——这些设置本身往往基于权力制约、及时性原则等——使得在司法官从赤裸的案情事实到法律事实的“欣赏”过程中不得不接受有时候他(或她)自己内心都未必接受的另外的结论;相对应地,在一般文艺作品的欣赏过程中,则没有这额外的结论负担。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法律的规定使得事实的解读结论呈现出比一般文艺作品更大的多样性。
总而言之,如果说一般的文艺作品在作者那儿毕竟已经完成,因而欣赏者对它的参与仅仅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进而其开放性仅仅体现在欣赏过程中的话,那么,司法过程中的事实这一作品则在它的原初作者(行为人)那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完成,甚至也还没有给出作品的所有原材料,这意味着在欣赏者进行欣赏之前,事实并没有完全确定且完整的存在。换言之,它内在地需要欣赏者的参与方能得到最后的完成、生成。也正因如此,相对一般文艺作品而言,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开放的作品”。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问题时曾有这样一段分析、说明:“对事实构成作出判断,是以经验的情况、对行为所作的证言和类似的直观材料为依据的,或者更以另一些事实为依据,从这些事实就可以推断有关行为,并大体上确定其行为之真伪。这里所应达到的是确信,而不是更高意义的真理。……这里的这种确信乃是主观信念、良心,而问题是在于这种确信在法院中应采取什么形式”。
笔者以为,黑格尔的这一论断深刻且清晰地揭示出了事实认定的discretion本性,并呼应着本文“事实是一种开放性作品”这一结论。这实际上意味着,司法过程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准确”、“属实”、“清楚”、“确实”、“充分”之类的“事实”,有的只是当前的诉讼参加人员(以法官为主)根据当前社会背景、法律、案情及其具体语境所续造出来的、因而也仅仅在当前具体语境下具有最大可接受性的“法律事实”。简言之,在司法过程中,至少对事实的认定无所谓“准确”、“正确”,有的只是何者更“好”、甚至仅仅是更不“坏”。据此,并结合前文的考察、分析和论证,笔者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建议是:删除各种反映、贯穿“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应当清楚、准确”之精神的条文,进一步丰满证据排除规则和明确“排除合理怀疑”规则;与此同时,完善诉讼程序(尤其是其中的论辩、质证程序)以及去除立法精神与此一结论相左的审判监督程序,并要求法官——至少当面对其他诉讼参加人员的质疑时——对其结论作出充分或必要的说理、论证。在这里,为何要特别强调法官的说理、论证的必要性?这主要是因为从逻辑上讲,“事实的开放性”结论意味着从根本上讲,不存在哪一种关于事实的结论是唯一可取的,但法官又必须择取某种事实结论、并且只有法官择取的才是最终有法律效力的,因此,说理、论证既是法官的内在义务(法院本来就应该是说理的地方),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法官任意的限制。另外,尚有必要明确的是,就事实问题而言,司法官的说理论证至少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揭示、展现自己结论的“好”,二是揭示、批驳其他(如原告方)结论的“坏”。相对而言,其他诉讼参加人员则可能只需要展现己方结论或观点的“好”就行,而可以不必一定要指出他者结论的“坏”。
当然,坦率地承认司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本质可能在道德上确实并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引起大众舆论的非议,并且也多少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事实问题上立法精神的根本转变,但既然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承认证据排除规则并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规则),为什么不勇敢地走到底?事实上,欧洲早在中世纪末期废除神判方式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明确司法的自由裁量本质并推行相关做法:专治英国法律史的普拉科尼特(Theodore F.T.Plucknett)曾提及1219年的一个司法令状,这个令状的内容是,“既然罗马教廷已经禁止相关神判方式,国王(也)希望他的巡回法院法官们在处理抢劫、谋杀、纵火以及相类似罪行时,不再使用水判或火判的神判方式。……如果遇到相关疑难情况,请诉诸你自己的判断(diecretion),……按照你的良心自由心证(discretion and con-science)就好”。而在法国,据说自中世纪到今日就一直奉行这样的做法:“在刑事法庭退出之前,它的审判长会作出这样一条指示(教诲),现在还用粗体显示在商议庭最显眼的地方:‘法律并不责问法官以何种方式使自己信服,也不要求法官特别地依照某种规则去判断证据的圆满和充分;她只要求法官在寂静和冥想中自我询问,并从良心中寻找答案,即指控被告的证据和被告自我辩解的方式,在理性的基础上,给法官带来何种印象。法律只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却包含了所有的法官应尽到的责任:你内心深处是否真正地确信(inner convic-tion)?’”
责任编辑:龙大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