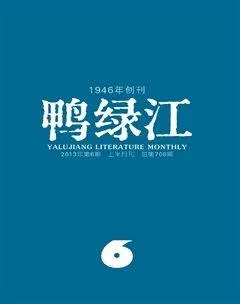横泾河边
林 宕,本名徐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在《上海文学》《小说界》《花城》等刊发表诗歌及小说,小说曾被《作品与争鸣》《小说月报》转载,后停止创作十多年。2007年起重新开始小说创作,作品多次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并于2010年荣获第九届上海文学奖。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上海某报社。
一
许红弟说:“我现在是白天没鸟事,晚上鸟没事。”
一旁的胖子发出了几声嘎嘎嘎的笑,雄鹅样的。
“找点鸟事还不容易?”胖子收住笑,说。他还把目光移到正静坐在他身体左侧的杨木初的脸上,好像要杨木初作出肯定的回答。
杨木初就慌慌地点头。其实,杨木初是一直盼望着这个不知名的胖子早点从许红弟这里离开的,因为他在,许红弟已经把杨木初冷在一边好长时间了。许红弟是晓得杨木初来他办公室里的意图的,冷杨木初或许也无关胖子,是许红弟必然要表示出的一种姿态。杨木初晓得自己不应该久坐这里,可真要叫他离开,轻易放弃要许红弟办的事,他也心有不甘——这就好比在他家的竹园里,明明往上跳一跳,是可以摘到藏在竹叶里的一窝鸟蛋的,可由于没有往上用力一跳,最后就失去了那窝鸟蛋。杨木初今天是想跳一跳的,所以,他就僵硬着上身,一直在沙发上等待着,等待着胖子的离去。
胖子又让目光落在许红弟脸上:“兄弟在今天晚上就给你安排点鸟事吧?”
这下轮到许红弟笑了,他的笑也像鹅的叫声,看来,笑声一般是会相互感染的,一般是要鹅一样相互追逐的。
“要安排,老早有人给我安排了,轮得到你?”
许红弟说着瞥一眼杨木初,似乎是杨木初的在场,让他有些话不便说出口。就像刚才胖子的那道目光,许红弟的这一瞥,又一次让杨木初感觉到了自己在这里的价值,也坚定了他要继续坐下去的决心。可这时候,许红弟却挥挥手,说:“不谈这个,谈别的吧。”
胖子说,怎么能不谈?男人不谈这个,还能谈什么?我看就今天晚上,我和你一道到“花中花”夜总会去白相相。许红弟摇头,我一向不去那种地方的。胖子的脸上露着神秘兮兮的笑意,一向不去,今晚破例,大哥,我看定了,就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白相。许红弟还是摇头,还是说,我从不去那种地方。胖子的眼睛里就露出狐疑的神色,你不去那种地方,赚那么多钱做啥?
胖子和许红弟的这一番对话竟然让杨木初上身的僵硬感消失了,一旦感到自己的筋络活络了,杨木初也挺想插上一两句话。
片刻后,杨木初捉住了一个机会,终于插上了一句: “晚上就到我竹园里白相吧,来白相几把。”
胖子不太懂杨木初的话,许红弟却晓得杨木初是要他们到他的竹园里去赌上几把。许红弟就笑了。
“老杨,你不晓得我是不赌的?”
对上话了,杨木初很高兴,并觉得自己要许红弟办的事情今天或许真能办成。
“不嫖不赌的,我看你的工厂还是关掉算了。”胖子说,“我看是你让自己‘白天没鸟事,晚上鸟没事’的。”
胖子的话让杨木初想起了村里人一道c4974176e395f1d7858598af74e7b648嚼白话时有人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讲究养生的中年人问一位老中医,我平时注意养生,基本做到烟酒不沾、女色不贪,能活到八十岁吗?老中医说,你烟酒不沾、女色不贪,要活那么长干什么?
杨木初想笑,却忍住了,嘴里蹦了一句让他自己也感到满意的话:“许总虽然不嫖不赌,可他开厂是为了让乡里乡亲的人都有口饭吃啊。”
马屁是拍对了,许红弟脸上露出笑。
“老杨把我拔高了,拔高了。”许红弟谦虚地向杨木初摆摆手,可脸上的笑分明含着对杨木初赞许的意思。杨木初觉得照这么谈下去,要许红弟办成那事的把握是越来越大了。
许红弟像是刚刚醒悟过来似的,给胖子介绍杨木初:“老杨是编结专业户,也是我这里的竹艺品供应户。”
许红弟的厂是一家编织厂,用水洼地里长出的蔺草和竹园里产的蔑片编织各种工艺品,都出口。厂里除了常年雇佣着几十名编织工人外,乡里乡外有人编织了工艺品,只要质量合格,许红弟的厂也通吃,不但通吃,有时遇到日本那里催货催得紧,他还把活儿发包给乡里乡外的那些业余编结手。这些年,杨木初也隔三差五地接到许红弟发包来的活儿,所以,严格地说,许红弟是他杨木初的半个“衣食父母”。
轮到要介绍那胖子了,许红弟竟卖了个关子,要杨木初猜猜看胖子是干啥的。看许红弟脸上的表情,好像胖子从事的是一个什么神奇的职业。杨木初猜不出,望着许红弟脸上的表情,说:“开火箭的?”
杨木初对自己的回答很满意,果然,胖子和许红弟都笑起来,杨木初让自己也发出了几声干笑。当自己的干笑与另外两股笑声交织在一起时,杨木初知道自己差不多已和面前的两个男人平起平坐了,他差不多可以向许红弟提出自己的要求了,这要求差不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了。
其实,胖子是干什么的,杨木初一点也不上心,他只想着自己的事能不能办成,他只想着要与许红弟签下个长期的供货协议。他家的竹园被列入了动迁范围,这一纸长期的供货协议就是钱。以前,许红弟要求一些编织专业户签约时,杨木初不上心,现在碰到了动迁这档事,他才悔不当初了。
许红弟还是继续介绍胖子的出处,原来这胖子是许红弟新结识的外镇人,虽然不是开火箭的,可做着的活计和开火箭一样让本地人觉得陌生而神秘:拍电影。可到底是他拍人家还是人家拍他,许红弟一时没有说。杨木初怎么看也不觉得胖子像个电影明星,可明星是他杨木初能轻易看出来的吗?不过,杨木初很快就知道了,胖子其实只是个掮客,在本地的好几个景点和几个北方来的影像制片人之间忙活。
许红弟说:“现在,新行当真是多,也行行出状元。我们这里竟然也出了个拍电影的。沈开,真有你的。”
胖子叫沈开。杨木初把目光移到了许红弟的脸上,感觉是时候了,是到他该把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抖落出来的时候了。
“许总,辰光不早了,”杨木初心里虽然有点急,可还是把话讲得很慢,“我们不要开火箭了,也不要拍电影了。”
许红弟再一次被杨木初的语气逗乐了,觉得老杨这个平时看上去有点唯唯诺诺的男人,一旦给了他脸,还是蛮有意思的。
“那你说说看,我们要干什么?”
杨木初说:“把我那件摸得着见得着的事办了吧。”
许红弟脸上的笑收起了,他想,看来真不能给老杨脸。许红弟说,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许红弟的意思是,既然杨木初家的竹园已经被列入了动迁的规划区,那么,他许红弟再与杨木初签订供货协议就是违规行为了,而如果照杨木初的意思,把签约的具体日期往前挪,挪到动迁消息传出前,那更是一种欺诈行为了。这样做的话,许红弟还想在商场上和社会上混吗?
然后,他话锋一转,回答了杨木初提出的一个疑问:“说最近我与几个蔺草种植户倒签协议,是别人在瞎嚼舌头!”
墙上的挂钟“当”地响了一下,沈开从靠背椅上跳起来,说吃饭了吃饭了。
杨木初也站起来,说:“我请你们吃饭去。”
见许红弟和沈开不接嘴,杨木初又说了一遍。他是真心实意地向他们发出邀请的。虽然许红弟又一次拒绝了他,可他还是想再努力一把,照他的理解,要谈成事也就那两种场合,办公室里和酒桌上,可办公室里有了外人,事就难谈了,就只能到酒桌上了,而事实上在酒桌上把事情谈成的把握也确实比办公室里更大些。
“让你请客?想得出。”许红弟说。
杨木初理解错了许红弟的话,有点急切地说:“我们怎么就不能坐在一起喝酒?你不肯帮我办事,我们就一定是对手了?”
即使真是对手,也可以坐在一道喝酒呀。杨木初告诉许红弟,镇动迁办的乔小刚和上访户张桂根真是对手呢,可一方面是对手,一方面却又常常一道到他那个竹园里来,是客客气气的、输了也不红眼的赌友呢。
许红弟看住杨木初:“老杨,你很有意思啊!”
然后,许红弟又说,今天很不巧,他和沈开有事要马上到市区,改天一定由他做东,请老杨吃饭。
二
玻璃顶响起雨滴声时,杨木初开始为离开他十几米远的另一个玻璃顶棚子里的人下面条。
液化气钢瓶里喷出的火蓝莹莹的,舔着锅底。雨是噼里啪啦地落起来了,盖去了不远处的洗牌声和喧闹声。已经成惯例了,每到下午三点左右,杨木初就要为那些玩牌九的人弄点心,有时是下馄饨和面条,有时是下本地人做的眉毛饺,也有的时候是弄半锅子蛋炒饭。本来,这种烧烧炒炒的生活该是女人做的,可杨木初的老婆过世得早,女儿傻娟又夹在这些赌友中不愿出来,杨木初就自己为打牌的人弄点心了。如果夜里还有场子,杨木初仍要在晚上九点左右为客人们弄点心(比起在每个场子结束后赢家留在桌面上的台费,点心和茶水的开销是微不足道的)。
面条很快下好了,用一把长柄笊篱把滑溜溜的面条下到好几只放着葱油的瓷碗里后,杨木初的目光有点茫然地朝玻璃顶棚子的外面望去,无数白亮亮的雨线穿织在竹林里,青翠的竹叶发出簌簌的声音,像是相互间的絮语,而一些枯死的竹叶不时地从高高的竹枝上脱离,像一些被打湿了翅膀的蝴蝶,悠悠地坠落到地上。
从杨木初待着的这个棚屋到十几米外的另一个棚屋,是一条倾斜的青砖小道,小道的上方,竹枝竹叶相互缠绕,像是一个天然的廊篷。杨木初就沿着这条青砖小道,用一个木托盘分三次把面条端了过去。
打牌的人都儿女吃上了父母端上的东西似的,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而又理所当然的神色。众人稀里哗啦地把空碗扔到地上的一只篾篓里,又纷纷走到桌子边。
“老杨,棚顶上的玻璃灯怎么不亮了?”张桂根在桌子边转过脸来。
因为下雨,竹林里的能见度就低。那玻璃灯早该开了的,可这灯几天前就罢工了,几天来天气一直晴好,不要开灯的,杨木初也就懒得去管它了。
杨木初要众人先不忙玩牌,然后站到了桌子上。原来是小问题,灯泡里的钨丝断了,他摘下了灯泡,跳下桌子,向众人挥挥手,示意他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只有这个手势,让人觉得杨木初不像是这批人的服务员,倒像个将军了,向他的士兵发出了进攻的号令。
杨木初看一眼站在乔小刚身后的女儿傻娟,想叫她到竹林南面的家里去拿个新灯泡,可一直站在乔小刚身后看牌的女儿一口回绝了他,说不能离开,离开了,乔小刚的手气就要坏。众人笑起来,说要不离开就永远不要离开,跟小刚跟到底。
傻娟已快二十岁了,可村里人一直认为,傻娟和常人比,脑袋瓜是不灵光的。对村里人的一些不恰当言论,杨木初是愤怒的,可没有一个人当着他的面说,他的愤怒就不好发作。他一直认为傻娟是不笨的,只是读不出书而已。他的两个女儿都读不出书,早早从学堂里回了家。既然不能指望她们书包翻身,杨木初只好让自己多动脑筋、多伤筋骨,为她们的今后多让自家累些、苦些。
他顺着一条铺着碎石的弯道向老屋走去。当他跨进家门时,十三岁的小女儿珍珍在门角落里蹿出,身体贴上了他。村里人都说珍珍比她姐姐傻娟还傻。杨木初却认为珍珍比她姐姐还要聪明,只要他外出,她就一个人候在门角落里,等,等他回来。其实,傻娟原来也不叫傻娟的,叫秀娟,是村上人觉得她脑子不太灵清,才为她改了名的,也不知是哪一个先开始叫出“傻娟”这个称谓的,反正村里人后来都这么叫了,叫得杨木初也默认了秀娟就是傻娟这个事实。
杨木初用粗粝的手掌摸摸珍珍的头顶,就往自己的房间里走,珍珍像一条小狗一样紧紧跟过来。杨木初家是一幢七路头瓦屋,中间一个客堂,东西是两个次间,一间是两个女儿的房间,一间是他的房间。此外,瓦屋的两端还各有一个厢房,一间堆放杂物,一间是杨木初编织竹艺品的作坊。
在房间里拿了一只新灯泡,返身跨出家门时,杨木初摆摆手,珍珍就很听话地缩回到了门角落里。
屋外,雨已经停了。杨木初重新走进了竹园里,竹园里布满着竹叶的清香和泥腥气,这清香和泥腥气是杨木初闻惯了的,也是他喜欢的。有一阵子,他身上也散发着这种气味,带着这种气味,他去找“新莲盛”编织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许红弟,许红弟好几次远远闻到了这种气味,就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躲开了。
还没有走近竹园里那个众人聚赌的场子,杨木初就察觉到了异样,那场子里的人在喧哗、在起哄。他们碰到了什么高兴事?杨木初紧走了上去。
这群人原来在寻傻娟的开心。“傻娟你还需要跟庄吗?不要的,你只要在乔小刚的脸上亲一口,老子就给你一百元”——河南人张桂根的这句话是由别人转到杨木初耳朵里的,当手里拿着一只新灯泡的杨木初刚看到傻娟佝偻着腰在亲乔小刚的左脸颊时,还有点犯糊涂。他看到乔小刚微微侧转着脸面,脸面上是一副迎合、迷醉的神色。
杨木初急忙拨开身边的几个人,去拉傻娟。
旁边有人开口,说出了河南人张桂根的那句话。这是不能怪张桂根的,在横泾村,开男女玩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甚至有人会当着你的面开你老婆的玩笑,能这样开玩笑,只能说明那人与你是心无芥蒂的,关系融洽的。确实如此,当着你的面,那人能与你老婆做什么呢,开开玩笑而已,明人做的不是暗事。而反过来,做暗事的人恰恰是不敢讲明话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横泾村人是喜欢那些能当着你的面开你老婆玩笑的人的,说明这人是一切做在明处的,你对这人尽管放心好了,绝不会背着你做暗事。
既然这样,杨木初能对河南人张桂根和乔小刚发火吗?不能,也不会。可杨木初还是对傻娟的赚钱方式表示了反对。他看到傻娟的左手中已经捏上了几张百元的钞票,就一下子夺了过来,递还给张桂根。
众人起哄,说,老杨,是你自己要还的啊,不是他张桂根要回来的啊。好像杨木初立刻要反悔似的。
“是我还的,”杨木初说,“老杨家不赚这钱。”
张桂根说:“啧啧,赚钱还要讲究什么,像我,只要来钱,管它什么路数。”他又问坐在对面的乔小刚,“对吧?”
乔小刚点点头,脸上带着笑:“你差不多已经涉黑了。”
张桂根也不动气,只是嘀咕一声,黑不黑也不是你说了算。张桂根从河南来这里快五年了,先是在本地一家企业里打工,后来开始在河南人之间做“娘舅”,就是只要河南人之间有什么过节,都由他张桂根出面解决。再后来,横泾村所有外来人员间的纠纷,几乎都需要张桂根出面来定夺,当然,他也不是光杆司令,他手下也有一批人。直到如今,张桂根已经在帮本地人打理事情了,例如,本地有人在厂里遇工伤了,由他手下的人冒充本地人的家人,躺厂门口,坐厂长室。甚至本地人需要上访,也会找到他,于是他会带着一帮外来人员,坐到镇政府门口。
哗哗哗——有人重新开始洗起牌。
“拿牌吧,待着做啥?阿是也想叫傻娟亲一口?”经营着一个废品收购点的金贵冲他对过的人说。
众人笑起来,傻娟也笑。傻娟笑的时候,是很好看的。
三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夜的岚气弥漫在了横泾河的两岸。空中仿佛有无数只凉爽的手指,在抚摸着在横泾河两岸乘凉的人的肌肤。
横泾河是横泾村人的母亲河,一到夜里,横泾村人就到河边的柳丛中、石凳旁嚼白话、趁风凉。整条河弯弯曲曲的,以前村里曾来过一位不明来处的勘探人员,说如果把这条河画出来,河上的喜雨桥和塘湾桥不是并行的,是相对的,就是喜雨桥的一个桥堍与塘湾桥的另一个桥堍是对应的,可以用一根直线连起来。可想而知,横泾河弯曲得是那么厉害。可是,为什么这河在横泾人的印象中始终是东西向的呢?横泾人弄不清这是为什么,就像弄不清河南人张桂根和镇动迁办的乔小刚第一天还在为动迁的事闹,第二天却相约着去打牌;就像弄不清楚“新莲盛”编织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许红弟为什么平时那么扣克工人的工钿,却又时时会提着钞票到区民政局去捐款,到庙里烧香。
横泾河上其实不止喜雨桥和塘湾桥这两座桥,还有大概四五座桥,其中最大的横泾桥是一座三孔石拱桥。桥的两个桥堍那里还各建有一个毛竹搭的凉亭。每到夏天,毛竹凉亭里、横泾桥的三个桥孔里躺着或坐着乘凉的人最多,有的人甚至整夜躺在那里。其实,横泾村已经有不少人家装了空调,即使不装,也几乎家家有电扇了,可横泾村人还是喜欢在夜里拿一条草席出来,睡到河边柳树下或桥孔里。这从很早以前沿袭下来的习惯,横泾村人为什么一直没有丢掉呢?这同样是一个叫人弄不明白的问题。
现在,沈开跟着杨木初穿行在横泾河的河边,脸上一层新奇、兴奋的表情被薄薄的月光照亮着,横泾河散发出的一股水汽扑鼻而来,水汽里带着一股清淡的东洋草的香气。沈开翕动着鼻翼说:“横泾河很好闻。”
在他们几步路开外,一个有着孕妇一样大肚子的壮汉在一条麻石板上翻了个身,一把由棕叶做成的蒲扇从他裸露着的大肚子上落下来。杨木初记得那麻石板曾是一块野田里的无名墓碑,一般人不太愿意睡。壮汉不但睡了,而且身下还没有铺草席。以前,横经村人睡石板、石条不铺草席,睡久了,好多人就得了僵直性风湿病,走路直不起腰了。起先,得僵直性风湿病的人还以为是长期的农活造成的,横泾村的好几任赤脚医生也不曾识出病因,终于有一位赤脚医生识出了,这样,村民们睡石板条时开始铺草席、竹席了。当然,也有人不信那医生话的,就依旧直接往石头上躺了,就像眼前的这壮汉。
壮汉躺在了一棵青枫树下,树根处的一蓬草丛里传出了纺织娘的叫声,这纤细的叫声和汉子粗重的呼噜声交织在一起。杨木初想上前一步认认这胖子是谁,发觉沈开已经钻进了前面的柳树丛里,连忙跟了上去。
快到横泾桥时,杨木初在一棵老柳树下看到了一个影影绰绰的景象,一个人躺在一条石凳上,就在这人的左下侧还有一条低一些的石凳,同样躺着一个人,下面的人把一条裸露着的胳膊搁在了上面那人的胸脯上,上面那人的左腿则垂下来,搭在了下面那人的大腿上。一男一女。面对这种景象,杨木初已经见怪不怪了。在横泾河边趁风凉的人中,这样的情况还少吗?两个原本离得很开的男女,会越来越近,到后半夜甚至会睡到一张草席上,当然,他们往往不是夫妻。
“快点。”沈开在前面催杨木初,他快到横泾桥南桥堍边的那个毛竹凉亭边了。
沈开是在给杨木初打电话时,才萌发了要到横泾河边来看看的想法。他是在许红弟办公室打来的,打到了杨木初隔壁的耿老四家。许老板要请你吃夜饭啊,上次讲过的。沈开在电话里大声嚷嚷。沈开还说,许老板还有别的事找他。杨木初就说,我夜饭吃了啊,我下昼四点钟就吃了,只有你们有钱人,夜饭吃得晚,越有钱越晚。可杨木初很快醒悟过来,心扑扑扑地跳起来,许老板还有事找他?莫非他愿意跟我签约了?我来我来,杨木初忙说,我正想到横泾河边去呢,现在不去了。沈开问,听人讲横泾村的男人们都喜欢夜里睡到横泾河边去,是不是因为半夜里有美人鱼要爬上岸来?说着,沈开哈哈大笑起来。可是,夜饭还是没有吃成,许红弟突然有事了,说夜饭就改天。沈开就重新打来电话,他让老杨今天夜里仍旧到横泾河边去,还说,他也想来,来看看,说不定这河边的景致能成为很好的外景,用不着花钱布置的外景。
绕过一根爬满了茑萝的石柱,杨木初跟上沈开。
“下礼拜就叫人来拍。”沈开有点兴奋,“说不准在河边真能拍到原生态的男女野合图呢。”
一幅河边乡景图继续在沈开和杨木初的面前展开,在他们身体左前侧的凉棚里,有人影影影绰绰的,闹猛的声音却清晰地传出来。平常里,杨木初也常会进去轧轧闹猛的,也晓得,到了半夜,这团在一道的作人鸟兽散时,总会有一两个人悄悄地尾随着离去,沿着横泾河走,看着哪个桥孔里没有人,就先后钻进去。当然,他们是一男一女。就在这时候,杨木初突然心里扑扑跳起来。他惊醒过来,刚才那老柳树下躺着的女子怪不得看上去眼熟,原来是傻娟。那么,躺在她高一级石条上的是乔小刚了。对,是乔小刚。
杨木初停止了前进的脚步,沈开却在说:“我们上桥去。”
凉棚上方的横泾桥上也站着一些人,他们依在桥栏上,手中烟头一闪一闪的。杨木初记得如果从两里远的庞泾桥上望过来,这些烟头就仿佛是星星落到了横泾桥上。
“你先上吧,我往回走走。”杨木初说。
沈开攥住了杨木初的手,脸上露着笑:“看到什么了?”
“那就上桥吧。”杨木初只得说。
在桥阶上,杨木初绊了一下,掼倒了。可他很快站起来。
“操那娘。”杨木初讲了一句脏话,他是仰着脸对着繁星闪烁的夜空说的,可他看到的是乔小刚那张有点尖削的面孔。
沈开在桥顶上站住,看着从他的身下一直朝东延伸开去的黑黝黝的横泾河面,说:“明天晚上吧,许老板要与你谈谈那事呢。”
杨木初屏息等着沈开往下说,可沈开闭上了嘴。杨木初终于问,许老板要与我谈啥事?沈开回答他,明天一起吃晚饭时他自然会晓得的。
沈开重新迈开了步子,向河的北岸逐级下桥。见杨木初紧紧跟着他,就转脸说:“你回吧,我也要回了。”
沈开沿着河的北岸朝西走。只要朝西走上两百米开外的样子,就是大马路,沈开的那辆破旧的桑塔纳车子就停在大马路上。
杨木初立刻转身,几乎是跳下了桥。他很快来到了老柳树下,可看到的是空空的一高一低两条石凳。
操那娘,看到我后溜了。杨木初表情怔怔的,摸一把脸上的汗。他有点颓丧地往家里走。可真要再一次碰上傻娟和乔小刚,他又能怎么样呢?他早就察觉到傻娟的心思了,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看着她像一只小斑鸠,朝竹园里张在竹梢上的网兜里钻。看来,村里人讲得其实没有错,她傻,她是傻斑鸠,要朝竹园里张在竹梢上的网兜里钻。
踏进家门,杨木初见东面的次间里有晕黄的光线投射到客堂里,他迅速地走了进去。傻娟依靠在木床的床头,在看一本已经被她翻烂了的琼瑶书。身旁,放在梨木梳妆台面上的电扇吹出的风,不时掀起傻娟额头的一缕头发。
“你怎么从河边回来了?”杨木初问得有点气急。
“我怎么在河边了?”傻娟脸上露出的迷惑神色和一个聪明人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傻娟在某些方面就是个聪明人,比如,她用蔑片编竹篮、竹篓以及竹塔、竹猪、竹马等竹器工艺品时,好多同年龄的女孩是不能跟她比的,可她还是被村里人说是脑子里缺一根筋。几年前,她告诉别人,说隔壁耿老四的女人钻到她父亲的被窝里了。被杨木初打了一巴掌后,她立刻晓得这是不能说的,所以,杨木初觉得傻娟是聪明的。
“你不是躺在河边的石条上?乔小刚也在一边?”
傻娟扔掉了手中的书,身子腾地从床上直起来。
“他在河边?”
杨木初连忙按住了傻娟的肩头,“他已经回家了。”看来,是他认错人了。杨木初摇摇头,觉得自己的眼神是越来越不行了,可眼神不行,他的脑袋瓜还行。
“你不能再与乔小刚交往了,”杨木初说,“乔小刚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傻娟脸上露出使劲想的神态,“我们都是横泾人。”
“对,可是横泾人跟横泾人是不同的。”杨木初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要讲不同,就是他是男的,我是女的。”
这真是一句聪明话,杨木初凝神看着傻娟,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不过一瞬后,他还是叹口气,又开口:“男人之间区别更大了,乔小刚家有铜钿,他人又是那么花。家里有铜钿,人又老实的,有这样好的运道能让你碰上吗?”
傻娟认真听着,她又想从床上起来,杨木初再一次按住了他。
“是该给你说个相配的人了,托托人看。”
“不,我要让乔小刚讨我做娘子。”傻娟尖叫起来。
四
二楼的乔小刚把脑袋探出玻璃窗,朝楼下喊:“张桂根,今朝你打算坐几个钟头?”
看来,这一阵乔小刚也是闲着。香花桥镇动迁办是与市政所合在一幢楼里办公的。底楼正中央进门处的不锈钢大门紧紧关着,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进出了。这道大门近阶段整天关着,楼里办公的人都有一张磁卡,往门把处的一个金属片上一贴,这门就开了。这么做,显然是为了防止那些闹事的人进楼妨碍公务。可张桂根对人说,真要进去,这两层小楼,架一把梯子就攻进来了,这钢门顶个鸟用?张桂根还说,他们的闹事其实也是文明的闹事,是摆理讲谱的闹事,不是瞎胡闹。
楼房前的场地上,张桂根带领的一帮外地人坐在一棵白果树下。和以前去坐镇政府门口一样,张桂根不会与那帮外地人一样,自始自终地坐在场地上的,他往往会在半中走开。也与去坐镇政府门口一样,那帮外地人中混杂着几个本地人,碰到要进楼谈判了,那几个主事的本地人就进去谈。而碰到突发事件,如楼里的人叫了镇联防队或镇派出所的人来了,那几个本地人会悄悄地退到白果树的后面,甚至会顺着白果树后面的一条煤屑路匆匆地打道回府,留下那些外地人继续在楼房前做着对抗政府和公家人的样子。
乔小刚也是横泾村人,可他凭着他父亲是镇动迁办主任的身份,竟然也到动迁办替公家办事了。这一次,几乎小半条村子的地皮要被两家港资企业征用,照说,动迁办里有两个人是横泾村的,何况连动迁办主任都是横泾人,好多横泾人就认为在动迁上肯定会得到格外的照顾,其实不然,几户连老屋也要被动迁掉的人家,置换给他们的房子还没有落实,只发了点要他们到外面租房用的过渡费,就要拆他们的房子了。他们当然不情愿,去动迁办、镇里吵了、闹了,都没有用。后来,村民们感到这事恐怕要打个持久战,就干脆找了张桂根,谈定了价钿,由他组织了一支也算庞大的外地人队伍,时不时地到动迁办和镇政府门口去静坐和站上一阵。今天,就是听说区里有一位领导要来镇动迁办来检查工作,那支外地人队伍又被再次指派着过来的。
张桂根从地上站起来,蹬踏了一下已经麻木了的腿脚,又从人丛中走了出来,走到了耀眼的阳光下,扬脸朝楼上喊:“区领导到底什么时候来呢?”
“不知道,讲好下昼两点来的,可现在已经是三点了,还没有来。”乔小刚的脑袋搁在窗框的外面。
“领导应该是很守时的呀,怎么拉了一个小时。”
“领导常常会被别的事拖住。”这一点,吃公家饭的人往往有发言权。
现在,有两位村民夹在外地人中,村上人是轮着参与到这种事当中的。专门负责人员调配的小学退休教师朱炳根今天上午也是叫了杨木初的,杨木初说先要去区中心城办事,办好事后再来。可是,他显然把自家搞得与区领导一样了,到现在还没有到。两位小名分别叫木根与瓜头的村民就对杨木初有了意见,在外地人中间骂杨木初赤佬,说今天散了后就去找他,让他“出点血”。“出点血”的意思并不是真要伤他身体,是要他请客吃喝。
想不到杨木初后来到了,“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样子很急。他跨进了坐在白果树周围的人堆里,想到木根和瓜头身边来。由于步子迈得快,不小心踩到了一个人的脚背上。那天真不巧,因为要到区中心城去,杨木初把脚上的那双布鞋换了,换上了风凉皮鞋。杨木初还有往自己的皮鞋鞋跟上钉铁片的习惯,就是他右脚皮鞋跟上的铁片把那个人的脚背踩破了。
那个人从地上站了起来,一把揪住了杨木初的衣领。其实,到这时候,杨木初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踩到别人了,他认为那人刚才口中唤出的一记痛楚的叫唤声是跟自己无关的,所以,他脸上露出茫然的神色。
“你眼睛长天上了?”那人叫一声,杨木初衬衣上的几粒纽扣掉落下来,也终于明白是自己踩着别人了。
杨木初想道歉,可突然感到嘴里的舌头又麻又大,转不过弯来。年轻人已经拽着杨木初的胳膊了,要把杨木初往人堆外拖。这时候,有几个人从地上站起来,沉闷已久的脸上露出了活泛的表情。
“干一架。”有人嚷起来。
杨木初觉得年轻人的面孔还是有点熟悉的,却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在哪里做的。他舔舔自己的嘴唇,想问,旁边又有人开口了:“李子,把这老头掼地上。”
哦,原来他是村东头那家废品收购站的李子,杨木初见过的。杨木初记得有一次去卖过铜皮,李子还差点儿按铁皮的价格付给杨木初钞票。
李子右手的虎口叉住了杨木初的喉咙。杨木初的喉咙口呻唤一声,两人就扭成了一团。这时候,坐地上的人大部分已经站起来。木根和瓜头拨开人丛,冲过来。
“操那娘,还没有和楼里的人干起来,自家人倒干起来了!”木根说。
其实,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这支上访的队伍还没有走近镇政府门口,由于口角,两位外地人从你一句我一句地相互指责发展到了拳脚相向。
“李子,你狗娘养的看我不把你赶出横泾村。”瓜头也嚷了一声。
外地人看到本地人在帮本地人,也开始起哄起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围住了木根和瓜头。其实,木根和瓜头也只是想动动嘴唇皮,唬退了那李子。现在,看到外地人都逼近了,就立刻噤了声。他们突然想起自己原来对杨木初的迟到也是有意见的,现在干吗要为了他而给自己惹什么麻烦呢?
这时候,李子也停止了所有动作,因为杨木初已经真的被他掼在了地上。李子虽然停止了动作,有一个人却要他再一次做出动作,是张桂根,张桂根对李子说:“把他搀起来。听到没有?”
张桂根的话虽然很轻,可场地上的人都听见了,就连他们面前那幢两层楼里的好多人也听见了。那些人为了看好笑,都把脑袋探出了窗口。
“听到没有?”张桂根又对李子这么说了一声。
“不要搀的。”杨木初快速地就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自己屁股上的灰尘,“我的筋骨好着呢,能一下子掼得坏?”
楼上,有一个人发话了:“不识抬举的东西,木初叔是让着你呢。”
他站在高处,目光远远地投射在李子身上。别人在说李子了,张桂根就反过来帮李子了,他把脸转向楼上:
“关你什么事呢?你少说几句吧。”
张桂根的语气虽是不温不火的,楼上那人却不吱声了,他的脸也隐去了,这时候,乔小刚的脑袋却在楼上露了出来了。张桂根立刻向他扬了扬手。
“嘴干了,扔几瓶矿泉水下来吧。”张桂根往上说。
乔小刚往楼下扔下了几瓶矿泉水,张桂根伛偻下腰捡,刚重新直起腰,乔小刚又在楼上发话了:“刚接电话,区领导不来了呢。”
木根和瓜头的目光里露出狐疑的神色,张桂根侧着脸望着他们:
“要不今天就先撤了吧?”
“撤吧!”见木根和瓜头点头,张桂根转身朝人群挥了挥手。
五
在依着老环城河的一家饭店里,许红弟先坐了,沈开和杨木初就跟着在临窗的一只方桌边坐下。杨木初转脸,看看窗外在微微漾动的碧绿河水,说:“你们请我吃饭,我老杨档次上去了啊。”
饭店前面是一条窄窄的青石铺设的小街。昨天,杨木初在滚烫的青石小街上走过时,曾向这家饭店的门楣上挂着的木匾额看了一眼,终于没有走进匾额上写着“漕溪人家”店名的这家饭店,只是到一个点心摊上买了三个刚出笼的馒头吃。小街两边除了一些饭店和小吃店外,砖木结构的民房里还遗留着一些隐性职业者。杨木初昨天就是去小街东首找一名瞎子算命先生,让他给傻娟掐算婚姻。掐算的结果,傻娟最好是在年内让人做媒,嫁出去。
饭店里客人不多,服务小姐把菜谱递上,许红弟朝沈开努努嘴,沈开就接了菜谱点起菜来。
窗外,有橹声传来,船上一位小女孩的手臂也伸进窗里,她手举着一束粉白色的花。
“阿要买花?”
许红弟朝她摆摆手。
橹声远去,一串水百哥的叫声又逼进窗里。
许红弟请杨木初到饭店来,真有事了,不过不是杨木初盼着的那件好事,签那份长期的供货协议。当他用商量的口吻向杨木初说出这次请他吃饭的目的后,杨木初感到很吃惊。
原来,许红弟有个快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家的亲阿弟,是个瘫子,常年躺床上的,听说脑子也不大灵光。许红弟想给他说个娘子,问杨木初能不能争取把傻娟说给他?
一口酒像火一样停在杨木初的喉咙口,一瞬后,这酒又像火一样滚进了他的肚子里。
“你怎么啦,老杨?”沈开说,“鲠鱼骨头了?”
“老杨哪是鲠鱼骨头了,他是不同意这亲事呢。”许红弟说。
“嗳!你不要搞错。”沈开觉得有必要提醒杨木初,“徐家是什么人家,嫁过去,就好比老鼠跌在白米囤里。”
哪有这么巧的,他昨天刚刚问过瞎子算命先生,今天真有人来给傻娟提亲说媒了,可要把傻娟说给怎样一个男人啊。杨木初觉得自己的肚内依旧在烫。他嗫嚅道:“这不是让我家傻娟去做保姆吗?”
许红弟把筷子往桌上一搁,哈哈笑起来。
“我家里常年有保姆的,一个还是专门伺候我阿弟的呢。”他把脸凑近杨木初,并放低了声音,“我告诉你,他虽然瘫了,可还能做那种事呢。”
可你却不能做,你到现在还没有小人,你们许家怕断后,所以你想到了要给你弟弟娶老婆——对许红弟的事,杨木初多少还是晓得一点的。那天,沈开在许红弟办公室里提议要给许红弟安排“鸟事”时,杨木初真想给沈开抖落一下许红弟的事,可他终于还是不敢。
杨木初觉得喉咙口痒痒的,有一种想吐的感觉,他强压下了这感觉。他想站起来。反正已经吃不进什么了,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呢?可他想是这么想,却一时还是没有站起来,毕竟,许红弟也算是他的衣食父母,许红弟再怎么样,他表面上还是要忍一忍的。
“我阿弟真还能做那种事的。”许红弟又凑近了说。
“傻娟已经在处对象了呢。”杨木初嗫嚅道,“在和乔小刚处。”
许红弟像是一下子没有听懂杨木初的话,凝神片刻,才用突然醒悟过来的口吻说:“为你的竹园,你是想尽了一切办法。”他沉吟了一下,又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吻说,“不过,我也是一个为达到目的想尽一切办法的人。”
许红弟哈哈笑起来。杨木初的目光从许红弟脸上躲闪开去,他凝神片刻,终于站起来,说:“我要回了。”
“走好吧,老杨。祝你的竹园卖个好价钿。”许红弟说。
杨木初走到家门口时,珍珍从门角落里跳出来。杨木初抚摸一下她的脑袋,然后指指屋内,示意她回去。珍珍很懂事地退回到了门槛内。
杨木初没有进家门,拐了个弯,顺着家门口西侧那条滑腻腻的砖道,来到了他家那片大竹林里。一股夹带着竹叶青涩气息的凉气弥漫在了整个竹园里,有馄饨鸟的叫声在杨木初的头顶上不时响起,杨木初抬脸,在竹枝间看到了一对在追逐、跳跃的馄饨鸟,它们的翅膀拍打在了青翠的竹叶上,激起了一片爱情的声音。
杨木初跨进了正在发出一片嘈杂声的玻璃棚子里,在玩着牌九的人群中拽出傻娟。
“跟我走。”他说。
傻娟却犟着,身体往乔小刚那里蹭。杨木初拧了傻娟一下,傻娟叫唤了一声。
“怎么啦怎么啦?”有人冲杨木初嚷。杨木初认出是村东头废品收购站的老板金福。只有金福这么问杨木初,其余的人仍专注于牌九,甚至是乔小刚。看到乔小刚,杨木初就知道今天是双休日。上班辰光,乔小刚这种吃公家饭的人是不来这里的,只有休息了,他才来。他休息了,这里的人也就不把他当公家人看待。
杨木初拽着傻娟的胳膊往竹林外走。到了村道上后,傻娟已经乖乖地跟在他后面了。
“去哪儿呢?”傻娟朝杨木初的后背嘀咕了这么一句,杨木初没有吱声。迈进了媒婆黄琴家的门槛,傻娟还不晓得她阿爸带她来做啥。
“也用不着把闺女也带来啊。”黄琴说。
“我也只是把她从竹园里拉开。”杨木初看一眼立在他左侧的傻娟,“啥人晓得她一直跟在我后面。”
杨木初在一只高背椅子上坐下,说:“成了,十八只蹄子总归给的,放心。”
黄琴转着眼珠,像是在大脑里为傻娟搜罗着适合的人选。
“给我说小刚。”傻娟已经明白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黄琴的眼珠停止了转动,看住傻娟,“扑哧”一声笑了:“傻娟不傻嘛。要你家的竹园值价钿,是要攀这样的亲。”
黄琴收住了笑,“可这事就像动迁办的人来动这里的房子和竹园一样难,难是难,不过动迁办要办的事最后有办不成的吗?”黄琴又笑起来,“我要办的事最终也能成的!这蹄子我是吃定了!”
“你听她的话!”杨木初急了,“你做媒总也要看个门当户对吧?”
黄琴又“扑哧”一声笑了:“你爷俩到底要我听谁的?”
“我已经是小刚的人了。”傻娟说。
杨木初粗粝的大手可笑地要去封傻娟的嘴,在接近傻娟的嘴巴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徒劳而可笑的举动,手就顺势而下抓住了傻娟的胳膊。
“走。”杨木初说。
父女俩跨出了媒婆黄琴家的门口。
六
珍珍双手把着木门的边沿,不断转动门轴,“吱吱扭扭”的声音持续不断地响着,像是在为杨木初翻飞着的双手作着伴奏。杨木初抬头看一眼珍珍,记起有一年珍珍到她姑姑家住了半年,门臼里竟然长出了青苔。
几根纠缠在一起的篾条在杨木初的双手间舞蹈,这篾条散发着一股带着苦艾气息的清香。若干年后,当杨木初家和横泾村里大部分村民一道被动迁到一个农民新村后,他只要远远看到由篾条编织而成的殡品,鼻腔里就会袭上一股清香气息,这气息让他有一种被抽断了根脉、悬浮在半空的感觉。
现在,在杨木初的双手之间,这股气息浮动着、弥漫着,他的双手也像鼻子一样呼吸着这气息,这气息让他的双手有着使不完的力道。那些舞蹈着的篾条在相互纠缠中终于永远联结在了一起,要么变成一只只变形的竹金刚,要么变成一只只胖猪状的储蓄罐,他把这些篾条编成的什物放在了身边的一只椭圆形的竹匾里。
他的身后,粉皮斑驳的后墙上挂着三幅装着细木框的黑白照片,是杨木初的父亲、母亲和老婆的遗像。三张遗像竟然都是全身照,大概他们临死前都没有来得及去拍摄半身照吧。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冬天的装束,父亲头上戴着一顶黑线帽,和此刻的杨木初一样,腰里束着一条褶子作裙,这种褶子作裙某种程度上就是篾匠的标志;母亲头上戴着月蓝布作底的青莲包头,身上束着绣着春桃图案的腰兜;老婆头上没戴什么,耸着一个馒头发髻,身上短衫薄裤。
杨木初的父亲也是篾匠,不过他一生编织的是饭篾箩、篮子、竹匾等日常用品,所以,遗像上的他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杨木初,看着杨木初编织着一些他不理解的竹艺品。
“珍珍。”杨木初的手停止了动作。
珍珍不再摇门,走到了杨木初的身边,像一只乖巧的小猫一样依在了杨木初的腿边,脸上的神气也是小猫式的,有一种柔顺,也有一份期待。
“要快点把你姐姐嫁出去。”
和小猫一样,珍珍没有听懂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显然要比刚才唤她的那声“珍珍”复杂多了。可即便听不懂,珍珍脸上的那份柔顺和期待依旧没有消去。
“哪能再让她待在家里。”杨木初还想说什么,却发觉几个人站在了他家的门槛前。是镇动迁办的人,以前也来过,杨木初记得为首的中年人叫黄玉龙,说是动迁办的一个副主任,年龄介于乔小刚与他阿爸之间。
杨木初从凳上站起来,拍拍褶子作裙上的屑物,要来人坐。黄玉龙在墙边的一条柏木长凳上坐下,说:“老杨,我们要你确认一下你家竹园里的竹子棵数。”
一位短发女子把一张有着格子纹的纸头递到杨木初的面前。
“你的竹园里总共有385棵竹子,签一下字吧。”短发女子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白皮肤圆面孔,讲话时00f2cbe0ca0ae0d488405c691a0793b62594ae040e6ff9ca5bf7f6bf8998c76b声音细细的,这种类型的女子常常会出现在一种对抗性场面中的,某种程度上发挥着软化矛盾的作用。
杨木初起先真想把纸头撕了的,就是这女子,让杨木初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与此同时,他在心里嘀咕:上次你们就来竹园数了,就要我在纸头上确认了,上次你们告诉我的竹子数目是355棵,过了几天怎么多了30棵?就算多给我竹子,我也不会在这张纸头上落字。
一直静静站在一边的珍珍突然用手指着短发女子衣裳上的花,说:“好看。”
短发女人的眼里涌上了一种异样的神色,她把目光从珍珍身上移到杨木初的脸上:“签了吧,你何苦呢。”似还有隐言要讲,停了片刻,果然又讲:“傻娟再怎样,每根竹子的价钿也是不能变了的,上面早定了的。”
杨木初突然低吼一声:“傻娟嫁给谁,你们管不着。这竹园里的竹子,你们一根也不能动。”
连杨木初自己也感到奇怪,他的这声低吼却不是对着短发女子,而是对着黄玉龙发出的。
“我是不会在这纸头上落字的,你们走吧。”杨木初从地上捡起篾条,重新编织起来。
珍珍扯住短发女子的衣角,说:“不要走不要走,我不让你们走。”
可是,黄玉龙的屁股还是从柏木长凳上浮了起来,脸上也终于露出笑意:“老杨,到最后,签与不签其实是一样的。”
跨出门槛时,黄玉龙还向杨木初友好地挥了挥手,短发女子则抚了抚珍珍的头顶,又摸了摸珍珍的脸颊。
珍珍依着门框,看着一行人在场角上的一棵白果树边转了个弯,然后走进了由两垛灰墙组成的一条夹弄里。一只灰猫从夹弄里窜出,在弄口猛地驻足,一瞬后,又迅速窜上南面的那垛灰色墙头。
傻娟回家时已是傍晚时分。
“你下昼在哪里?”杨木初问她,语气是轻柔的。
“我在找小刚。”
杨木初朝屋门外瞥一眼,见珍珍一人在夹弄口玩耍,就跟着傻娟进了她的房间。他反手把房间的木门关上了。
“你真是小刚的人了?”杨木初问。
“真是他的人了。”傻娟说。
杨木初就要傻娟在床上躺下,傻娟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不明白她父亲要她躺床上干什么,不过片刻后,她还是听话地躺到了床上,像一个等待医生检查的病人一样。
杨木初在床沿边佝偻下来,手探到傻娟腰际,撩起傻娟的粉红色薄衫。当杨木初瘦骨嶙峋的右手挨上傻娟凉滑的肚皮时,傻娟格格格地笑起来。
“做啥?”被弄痒了的傻娟举起双手,开始推挡杨木初的右手。
“不要动。”杨木初低喝一声。
杨木初的手在傻娟肚皮上摸了一圈,感觉到她的肚皮瘪瘪的,像是盛着半袋水的一只热水袋,里面的水已经凉了,所以,杨木初的手感觉到的是一片凉意。当这只热水袋里发出一串“咕噜咕噜”的气泡似的声响时,杨木初的手像是受了惊吓,往回一缩,撤离了傻娟的肚皮。
杨木初没法判断里面到底有没有孩子。同时醒悟到,如果这孩子现在还只有弹子这么大时,他是没法摸出的。他有点沮丧,感觉像是盼着傻娟肚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并且这孩子已经大得足以隔肚摸出。
虽然杨木初的手已经撤离了傻娟的肚皮,可傻娟仍旧摊手摊脚地躺着,仿佛等着杨木初再次触摸他。他看着傻娟有点无耻的样子,心里的沮丧转为了恼火。
“起来起来。”他喝道。
傻娟要直起腰来时,杨木初突然又按住了她的肩头,轻声问:“小刚是什么时候与你做那事的?”
傻娟脸上露出茫然的神情,黑黑的眼珠子转动一下。
“他家的猫死了。”她说。
杨木初偏起右腿,让半个身子搁到傻娟的身上,他的另外半个身体在往傻娟身上移的同时,开口:“像这样,乔小刚压过你的身体吗?像这样地压?”
傻娟在下面点头,又很快摇头。杨木初望望傻娟的脸,觉得还是不放心,用手拨拉傻娟裤子的松紧带,往下拨拉。
“还这样,把你的裤子往下剥掉吗?”杨木初说。
傻娟摇头,又很快点头。杨木初突然觉得自己的血在涌动,他的身体差点儿整个地瘫软到傻娟的身上,可他猛地一用力,差不多从傻娟的身上跌落到了床前的踏板上。
七
沈开说有一个影视组要拍竹园里的一场戏。租用一下杨木初家的竹园,给500元,问杨木初干不干。
竹园里的牌九场子散去时,赢家只留下100元的场子费,现在却给500元,这笔账傻子也会算。杨木初答应了。
沈开说,是拍一场男女戏,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竹园里相互追逐,女的追啊追啊,最后却不见了那男的,就在女的失望之时,镜头切到了当天的一轮圆月上。沈开告诉杨木初,顺利的话,半天工夫不到就可以搞定的,竹园里的牌九场子可以接着开。
杨木初问:“演戏的人要不要?”
“演员早定了的,你演那个男主角的爸也不合适。”
“我哪能演,我是想让傻娟演那女的。”
沈开露出了爱莫能助的表情。他虽是专程为这事赶到杨木初家的,可他还没有见到傻娟,见到的话,说不准也会动让傻娟演戏的念头的,说不准会去极力劝说导演更换女主角的。
下午就开演了。开演前,还下了一场大雨,雨后,竹园里有无数的蜻蜓在飞,蜻蜓们时而绕着竹竿飞,时而贴着竹园湿漉漉的地面飞。杨木初听见了蜻蜓振翅的声音,甚至还听见了好多蜻蜓在空中交尾时发出的声音。开演前,杨木初还不解地问沈开:“天上的月亮呢?不是最后要拍天上月亮的吗?”
沈开摆摆手:“主要是拍女的追那男的。那月亮会到电脑里整出来。”
一帮人闹哄哄的,扛着摄影机的男人扎着个辫子,而一个面清目秀的姑娘却剪着个小平头,就在开拍前,一个胖子却拿上一个秀发飘飘的假发套给小平头姑娘套上。这姑娘原来就是女主角,要在竹园里追一个男的。
横泾村的人几乎都想来看热闹,大部分人被摄制组雇来的几个壮汉挡在竹园外,只有来得早的少数几个像漏网的鱼一样尾随着摄制组的人在竹园里窜动。沈开想让人把这几个人也给清出竹园,可留着一部恩格斯一样胡须的导演却摆摆手,说就让他们跟着吧。
正式开拍后,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在竹园里追逐,步子轻盈得就像蜻蜓。男的还没有跑出女的视野,傻娟闯进了镜头。傻娟原来也是一条漏网的鱼。她既像是误闯进了镜头,也像是要追那男的,像是要与假发女子展开同台竞争。
导演向摄影师挥手:“停!停!”
杨木初一下子冲到傻娟身边,他扬起了手,想给她一个耳刮子,可想想为了500元钱,给她一个耳刮子也不值的,就只是把她往回拽。
“你以为那男的是小刚?”杨木初说。
想不到这句话比耳刮子还厉害,这句话刚从杨木初的嘴中跑出,就像是撞痛傻娟了,傻娟一下子坐到地上,先是茫然四顾一下,然后哭起来。
从身后几个村民的窃窃私语中,导演知道老杨家这个长得不比假发女演员差的女儿脑子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最终把骂人的话咽进了肚子里,要老杨把傻娟领回家去,也终于对那些漏网之鱼一样尾随在后的村民下了逐客令。
杨木初从地上拽起了傻娟,转身时,他的额头撞上了一根粗大的毛竹竿,他心里就有点毒,抓着傻娟手臂的右手用上了力,本来已经停止哭泣的傻娟又发出了哭声。
杨木初把哭哭啼啼的傻娟牵回了家。
夜里,杨木初在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从没有拉上窗帘的木格子窗子里投进来,像一层霜似的敷在床板和光着膀子的杨木初身上。
其实,沈开应该带着摄制组再来一次,来拍竹园上空的真月亮。杨木初想象着此刻的月亮该像一张圆圆的发亮的大饼,这大饼样的月亮总比从电脑里整出的月亮好吧。说实在的,他也想不明白怎么从电脑里捣鼓出月亮。既然能捣鼓,他们不来就不来吧,好像他老杨拿了沈开500元钱后,贪心不足,想再拿一次似的。
北面墙角落里的虫鸣声断了,可一阵嘈杂声却从外面传来。杨木初凝神,嘈杂声像是从瓦屋北面的竹园里传来的。差不多半夜了,牌九的夜场也散了,会有什么声音呢?杨木初正嘀咕,有人影在木格子窗前晃动,继而有人“砰砰砰”地敲响了他家的木门。
“杨木初杨木初,你家的竹园着火啦。”
杨木初从床板上惊跳起来,窜到了客堂,见客堂的门已经开了,村上的几个人已经站在了客堂里。他们怎么进来了?门闩难道没有闩上?顾不得这些了,杨木初往屋外冲,进了屋的几个人也跟出来,有人说:“不要急不要急,已经被扑灭了。你去看看。”
杨木初放慢了脚步。
“你去看看到底怎么起的火。”有人又说,口气里还有一层没有说透的内容。
杨木初心里犯起疑惑,边琢磨着那人话里没有说透的那层意思,边绕到了自己家的屋后。空气中飘来了一股焦臭味,杨木初翕动一下鼻子,带紧了步子。
在竹园东南角的一片丛生竹边围着一帮人,焦臭味显然就是从那里传出的。杨木初家的竹园里就东南角上种植着五六片丛生竹,竹园里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株一株的散生竹。虽然散生竹不容易点燃,可一旦竹园里随便哪一处起火,由于散生竹的顶部基本是连在一起的,整个竹园就有灭顶之灾。
那帮人看到了杨木初后,散开了一条缝隙。那帮人中有不少是妇女,一名因参加过扑火而使自己的头发散乱开来了的妇女拉住杨木初的衣角:“你女儿又发痴了呢。”
在一丛一半已经被烧黑了的竹子下,傻娟坐着,丛竹的阴影笼罩在了她的脸上,使她的脸看上去也像一小块烧黑了的东西。
“拉她也不肯起来。”又有一名妇女说。
“走。”杨木初一拉就把傻娟从地上拉了起来。
八
“你们谁敢动这里的一根竹子,我这老命就不要了。”杨木初朝卡车上跳下来的人喊,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镐,样子很吓人,那帮人停住了脚步。
杨木初家的竹园只有南面的一个进口,别的地方都扎紧着荆树篱笆。其实,只要用一把砍刀就可以在篱笆上砍出一个豁口的,可既然有了一个进口,大家就不由自主地往那个进口处走了。
动迁办副主任黄玉龙带着这帮前来砍竹的人,他说,虽然他们这是文明动迁、人性化动迁,可不管杨木初接受不接受动迁办给出的竹子赔偿价,他们都会先把竹园里的竹子砍下来,让许红弟的工艺品厂收购去,而这收购费是给杨木初的,是杨木初在得到动迁办给出的竹子赔偿款后额外得到的。
可杨木初不认这话,我不要你们动迁办给的赔款,也不要许红弟那个工艺品厂的收购费,可以吧?他还看到从两辆卡车上跳下来的人竟然大部分是河南人张桂根手下的,心头的火更大了。一会儿替村里人去闹事,一会儿又反过来找村里人麻烦,两头吃啊。他定定神,在人群里没有发现张桂根,却发现了跟他闹过不高兴的废品收购站的李子。
“你们都给我滚。”杨木初大声说。
杨木初现在底气很足,因为本村的一些男女老少也来到了他的身边。他没有招呼,他们却来了,可见,一旦发生啥事,村上人还是能抱成团的。村里人认为,动迁办开始动杨木初家的竹园了,那么离动别人家竹园的日子也不远了。
对峙的局面一旦形成,时间仿佛如凝固的胶水一样,化不开,流不起来了。后来,大家都在心里等,等中午的时候快到来,中午的时候一到,大家就可以回去吃饭,就可以与动迁办支使来的人一道离开这里了。
阳光通过竹园入口处那棵苦楝树的枝叶,斑斑驳驳地洒落到地面上。卡车上下来的大部分人都站在了树下,阳光的斑点也像蝴蝶一样在他们的身上跳动。有几个人想在树底下坐下来,可是被黄玉龙制止住了。
“又不是要你们在镇政府门口静坐。”黄玉龙说。
这批人是黄玉龙叫来的,黄玉龙找到张桂根时,张桂根起先有点犯难,说这些人一直是帮村里人干事的,现在怎么能去挖村里人的墙脚呢?黄玉龙说,怎么是挖墙脚呢?是帮杨木初家砍竹子,砍下的竹子仍是杨木初的,卖给许红弟的工艺品厂后,钱是给杨木初的,而弟兄们砍竹子当天的人工钿却由动迁办来支付,这不是在帮杨木初又是什么?
叫外地人去砍竹,动迁办主任乔建中起先也是不同意的。他认为这些外地人有奶便是娘的,怎么能叫他们砍竹?黄玉龙反驳,正因为他们有奶便是娘,所以,只要给他们奶喝,他们就会干得更卖力。何况要在附近找一批愿意砍竹的人,一时也是难找的。黄玉龙嘴皮子的一阵翻动,终于让乔建中和张桂根打消了疑虑。
干等在树下,时间真的凝滞的胶水似的,流不起来了,苦楝树上突然响起的一声蝉鸣也显得十分悠长。树下的一个人像是猛地被这声蝉鸣从昏睡中弄醒了似的,问黄玉龙:“到底让我们砍不砍了?不砍的话,一上午的工钿会付我们吗?”
黄玉龙看一眼站在竹园入口处的村民,喉骨“咕噜”转动了一下,说:“没有砍竹子,怎么能算你们工钿?我们也要按株给你们结算工钿的。”
废品收购站的李子当下就叫起来:“操哪,当我们什么啊?”
刚才问黄玉龙的那个人也高声嚷:“走走走,我们撤。”
有人不愿意撤:“那我们刚才耗在这里算是白耗了?我们走的话,不是被人当猴耍了?”
大家都觉得这句话讲得对,如果现在就走的话,真是把他们当猴子耍了。可不走,万一这黄玉龙最后真是一毛不拔,那不是又要在这里多耗一段辰光吗?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胖子看上去是个好脾气的人,他朝离他大约有六七步远的杨木初开口:“老阿哥,我真不明白,有一大笔赔款,卖了竹子的钱又归你,还要那个烂竹园干啥?”
“是啊,还要这烂竹园干什么?”有人附和,“里面的牌九场子也不会让你设长的,老派就要来冲的。”他们叫派出所的人为老派,不知是为了表示敬畏还是为了表示轻视。
怎么是那帮外来人员开始做杨木初的思想工作了呢?黄玉龙觉得好笑,也觉得自己是失职了,他清清嗓子,示意别人不要开口了。
“老杨啊,”黄玉龙挤着一对小眼睛,像是在思考着要说些什么,“他们讲得对。再讲,听说许红弟想把自己的厂卖掉了,真卖掉了,这厂还收不收竹制工艺品还是个疑问呢。”
黄玉龙讲得很温和的,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这句比所有外来人员讲得要温和得多的话,倒像是一下子惹恼了杨木初,大家听到杨木初的喉头发出一记怪异的叫声,朝苦楝树下冲过来,手臂抡圆了手中的镐,嘴里那怪异的叫声像是冲锋号角似地继续响着。
对于被叫来砍竹的那些外来人员来说,最让他们难受的其实是没有事情可做,而一场冲突往往正是他们在内心所期盼的。他们千里迢迢地从偏远省份赶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享受清闲的,他们是来找事的,这事可以说是能挣钱的各种生活,也可以是能点燃他们热血的一场冲突。现在,他们在苦楝树下左腾右突地躲闪着杨木初手中的长镐,个个显得那么生龙活虎。一个人的大腿像是被杨木初的长镐终于击上了,他发出一记既像是痛楚又像是兴奋的叫声,紧随着这叫声,杨木初握着镐柄的双手也终于被人捏住了,那把长镐迅速变成了外来人员的战利品,杨木初本人也被摁到了地上。就在这个时候,刚才一直站立在竹园入口处的本村的男女老少冲了过来,他们的喉咙口也发出了杨木初冲到树下时发出的那种啸叫。
看到事态扩大了,黄玉龙吼叫起来:“都给我站住!”
他觉得这时候手中如果有一把枪的话,他肯定会朝着树底下开的,而绝不会像电影里放的那样往天上开。
“都给我住手!”黄玉龙觉得自己的身体像要腾空而起,结果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么到人群中央的,他在人群中央边挥舞着手臂边继续吼叫着,“你们这群猪猡,都寻死啊。”
黄玉龙的脸上和胸膛各挨了一拳后,冲突的双方也终于住手了。外来人员中响起了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走吧,算我们倒霉。”
横泾村的那帮人则依旧衣冠不整地站在树下,他们的脚像是和身边的那棵树一样,在地上生根了。脸上挂了彩的黄玉龙弯下腰,想把躺在地上的杨木初搀起来,想不到杨木初甩开了黄玉龙的手,女人似的说:“别碰我!”
他躺地上的身体也像是生了根。不过,当苦楝树上已经停了好一阵的蝉鸣又突然响起时,杨木初被唤醒了似的从地上爬起来。他旁若无人地拍拍自己身上的尘土,然后朝自己家的竹园走去。
村上人的脚也在地上动起来,当他们往前迈动几步后,杨木初猛然转身,再一次女人似的说:“别跟我。”
黄玉龙这时发觉老杨脸上的神态和他的两个女儿,特别是小女儿珍珍像极了。他想,杨木初脑子坏了。村上人帮他赶走了那帮外地人,他却一点也不感激,倒像是村上人也得罪了他。
村上人站住了。他们是为了他才与外来人员发生冲突的,现在杨木初既然一点也没有感激的意思,反而好像对他们有意见了,他们就觉得很无趣。
很快,苦楝树下就空荡荡了。
不多会儿后,杨木初家竹园的上空有几缕浓烟升起。有几个刚才从苦楝树下撤离的村民看到了那袅娜着升起的烟尘,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傻娟又去了她家竹园东南角的那片丛生竹下了?他们想立刻跑去看看,可很快耳边再一次响起了杨木初那声“别跟我”的话。
他们觉得要不是杨木初傻了,就是他们自己傻了,自己在苦楝树下被人傻瓜似的耍了一回。现在如果再往杨家竹园那里跑,他们就是想当第二回傻瓜。
这一天真是奇怪,即使没有到过苦楝树下的村民,竟然也没有一个再到杨家竹园那里去。而那天夜里,虽然夜已经很深,却居然还有好多村民跑到了杨家竹园去,把一丛竹子上的火给扑了。
九
许红弟把杨木初接到北大街上的“漕溪人家”饭店里,两人居然又坐在了上趟坐过的那只临窗方桌旁,只是这一次没有沈开在场。
“老杨,你没有变傻。”许红弟边招呼服务员边说。
“可横泾村一半以上的人说我傻了呢,把自己家的竹园都烧了。”
“真傻了倒是桩好事,”许红弟俯过脸来,“我也想傻啊。前天夜里,我想把我的厂一把火烧了。”
杨木初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不过,这神色很快消去,他把脸转到窗外,漕港河清澈的河水在微风中轻轻漾动,有水鸟在水面上闪电般地掠过。
当许红弟问他要喝什么酒时,他才把脸从窗外转回来。
“绍兴特加饭有没有?”杨木初问。
服务员回答说没有,杨木初就要服务员随便拿一瓶什么黄酒来,又开口:“怎么又想到要请我吃饭了?我皮厚,怎么跟来了,其实是承受不起的。”
“哪里话。”
“到底做啥又要请我吃饭?”
“做啥?我也不晓得。”想了想,许红弟又开口,“就是有一次,突然想把你请过来,让你也把我的厂烧了,因为你傻了嘛。有些事只能叫傻子办。”
“你讲这话,你才真傻了呢。”杨木初瞪大了眼睛。
“我没有傻,傻的话,自己烧了。”
“你日子这么好过,却要烧掉自己的厂,你不是傻子,谁是傻子?你是被钱撑傻了。”
许红弟哈哈笑起来。这时候,酒和冷菜都来了。两人就吃喝起来。
“就为那次突然想把你请来放火这个念头,今天才接你来喝酒的。”许红弟说。
“许总,那你还要不要我放火了?”杨木初问得很认真,脸上那种认真的神色差不多又要让许红弟觉得他是真傻了。
许红弟又与杨木初碰了一杯,说:“都说你傻了,我看不像。”
沉思一下,再一次开口:“其实做傻子也蛮好。”说罢,就独自猛灌了几口。
听说最近许红弟的工厂碰到一些麻烦,到底是什么麻烦,杨木初也不愿去打听。见许红弟那么灌自己,就劝他少喝。
“老杨,我、我不能做那事的,你知道吗?”许红弟有点醉意了,讲话时舌头显得僵硬。
“知道,你说过,你白天没有鸟事,晚上鸟没事。”
许红弟刚想讲什么,想不到杨木初又开口了:“我没儿没女的,整那么大一个厂干什么?”
许红弟打了个酒嗝,盯住了杨木初:“老杨,你其实不会傻的,你家不会出第三个傻子的。”
窗外,有橹声传来,两人都动了动头颈,看到船上小女孩的玉臂伸进窗里,她手中是粉白色的花束。
“阿要买花?”
许红弟拿过身边空座位上的皮包,拉开拉链。
“拿去。”许红弟说。
小女孩看着许红弟手上好几张钞票,眼睛里露出不相信眼前景象的神色,手伸了一下,又缩回去。
“拿去!”许红弟直起了身子,把钞票扔进了鸭头小船的舱里。
粉白色的花束也没有给,鸭头小船就慌忙地调转了头,偷了什么东西似的快速往西划去。
杨木初伸颈,看到小船的后面形成了一条蛇一样的水波,向西逶迤而去。
杨木初嗫嚅着说:“你的厂再有麻烦,你也比杨家有更多钞票。”
“对,所以,你家不需要有啥钞票,你还守着那个竹园做啥呢?”许红弟歇口气,手往空中一劈,“不需要!傻娟以后一定会过上最好的生活!”
杨木初又一次往船窗外望去,小船刚刚留下的蛇一样的波纹已经不见了,整个河面平滑如镜,反射着晃眼的光亮。
责任编辑 晓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