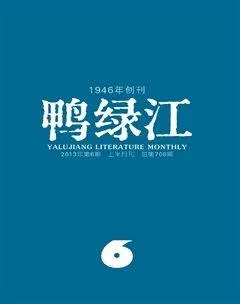河洛文化与阎连科小说创作
吴 燕,1986年生,大连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在《大连大学学报》《文化学刊》公开发表两篇学术文章,参与完成两项省级科研项目。
张祖立,大连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持完成多项省社科基金项目,主编教材一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大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阎连科说过:“地域就是作家的世界,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出生地……对他的影响非常重要。”[1]“河洛文化”对河南作家阎连科有着深刻影响:一方面,河洛的地理情状、生活习惯、风俗信仰、历史经验等都为作家所熟知,成为构成其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要素,经过与作家心智的感应融合生成为一种文化意识,成为作家认识自我和世界的一个基点;另一方面,源于特定地域文化精神影响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体验必然外化在作家的文本中,形成独特的艺术气质。
从自然地理方面讲,“河洛”主要指在黄河和洛河所形成的夹角范围内,以洛阳为中心的广阔区域。文化意义上的河洛地区称为“河洛文化圈”,其精神范畴远远超出地理概念的范围。有人认为, “河洛文化圈应该涵盖河南省全部,东与齐鲁文化圈相衔接,西与秦晋文化圈相衔接,南与楚文化圈相衔接,北与燕赵文化圈相衔接”。[2]
河洛文化是含英咀华的文化。儒学创基于河洛,周公营建洛邑,在洛阳“制礼作乐”,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礼乐文化。孔子正是经过中原的游历,建立了儒家学说。道学产生于河洛,家居河洛的老子创作的《道德经》被奉为道家经典。佛教始传于河洛,东汉永平年间明帝派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被认为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开端。永平十一年,明帝敕令于洛阳修建白马寺,白马寺因此被尊为佛教的“释源”和“祖庭”。谶纬神学形成于河洛,董仲舒“天人感应,必有征兆”说首开谶纬之风后,光武帝刘秀进一步发扬,谶纬之学在东汉之初就传遍全国。理学渊源于河洛,理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均为洛阳人,二程之理学又被称为“伊洛理学”或“洛学”。含英咀华、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对阎连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打上了河洛文化的烙印。
一、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
阎连科坚持以故乡“耙耧山脉”为地域背景,深情描绘着这里的“土地文化”,其作品充满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一)耙耧山脉
自然景观作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一种外在、形象的组成部分,最能直接表现出地域文化的特点,同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丹纳论及希腊民族艺术时说到:“在民族的事业上和历史上反映出来的,仍旧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3]阎连科介绍过:“我的家乡就在秦岭余脉的最末端,属伏牛山系,那里有一条山岭叫耙耧山,在我的‘瑶沟系列’中,‘耙耧’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名词已经不断地出现,写《寻找土地》时,已经是有意识地以这一地域背景作为写作对象了…… ‘耙耧山脉’已经成为了一个明确的写作方向。”[4] “耙耧山脉”既贫穷落后,又原始封闭。《情感狱》中的瑶沟、《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受活》中的受活庄、《耙耧天歌》中的尤家村,均坐落与世隔绝的耙耧山深处。这是一片被世人遗忘的土地,现代文明也姗姗来迟,三姓村多少年来没有接到过到公社开会的通知,国家成立了那么久,村人仍是按老辈习惯把医院称为“教火院”。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在精神上也失去了探寻外部世界的兴趣,在他们看来,“世界”只是“耙耧山脉”。 “耙耧山脉”成为作品的重要标识。
(二) 河洛风俗
风俗从本质上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定区域内的人们在长期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并代代传承的群体文化心理的表现和行为方式。作为群体文化的标志,它“层积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也有群体的伦理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5]
生产生活风俗。河洛地区农耕文化烙印鲜明,突出的表现就是重视农历历法和二十四节气。《年月日》中的先爷最需要的就是一本万年历,因为没有万年历就不知道玉蜀黍到底啥时候成熟了。河洛人婚嫁、建房、动土用农历推算吉日。《斗鸡》中,“我姥爷”和汪家小女儿行婚事之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来对方的生辰八字测凶吉。河洛是小麦、玉米的主产区,人们的饮食以面食为主。阎连科作品中的人们最常吃的就是饼、馍,最爱吃的就是“蒜汁捞面”。除了吃食品种, “饭场吃饭”是一个典型习俗,庄子里有几个固定的饭场,饭间,人们陆续来到饭场,端菜拿馍,三五一堆,边吃边谈。《受活》等描述了 “东家短,西家长,端起碗,撵饭场”场面。
人生礼仪。河洛人有重礼、崇礼的习俗风尚。作品中首先体现在对婚礼、婚俗的繁复描写上。婚礼多依“六礼”而办,每个环节写得很细致。丧葬礼俗也别有意味。河洛人顺生重死,甚至把死后看得比生前还重,“棺材”在河洛葬俗中被置以特殊的地位,“活有房,死有棺,死人没有棺就如活人没有房”是村人们的普遍观点。河洛人不仅关心到死后的房屋住所,连死后的婚姻之事也一并考虑。“冥婚”俗称“结阴亲”,在河洛地区非常流行,其婚礼仪式几乎和生人一样。在《寻找土地》《丁庄梦》等作品中,人们都表现出对“冥婚”的巨大热情。
信仰习俗。河洛先民“由于知识和经验的局限,对自然界所发生的现象不能解释,于是形成对‘天’的敬畏,进而发展为对日、月、风、雨、雷、电、山、川、湖、海、奇禽、异兽的敬畏,再进而乃至巨树、怪石和各种器物也都成了神灵之物”。[6]《情感狱》中的九爷把老皂角树的树根看作灾难的根源,《两程故里》中的村人对古柏的声音忌讳莫深,《黑乌鸦》中人们把乌鸦当作灾难的预兆,其他的如“药碗摔碎”预兆人命没几天,儿童歌谣暗示蝗灾来临,水缸裂口预示主人死亡,等等。人们相信万事万物的神力,小心地趋避着,也以毒咒和符咒来传达自己的心思。《丁庄梦》里“谁家恨了谁家了,就在他家门前深埋一个桃木或是柳木的棒,把木棒的一头削尖儿,写上想让他死的人名”。这种愚昧与乡情、迷信与纯朴融合在一起的民间信仰,正是河洛人某种精神状态的写照,作家对此有着深刻而矛盾的感受:“从所有普遍流传下来的风俗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农民的‘躲避’、‘乞求’和‘保佑’的苦苦哀求。”“今天的农村……将在很长很长永远一样的历史长河中更集中更神秘地浸泡在风俗的染缸里发酵,久而久之地被一种不知不觉的桎梏所捆束。”[7]
游艺习俗。农民的生活充满辛劳和苦难,但会承袭着坚强乐观的生活态度,阎连科理解这种态度,谙熟农民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这突出表现在他对民间曲调的运用和民间庙会的描写上。“冬天日出地上暖/两口儿在地上晒清闲/男人给媳妇剪了手指甲/媳妇给男人掏着耳朵眼/村东有一户大财主/有金有银住着瓦楼和雪片/可财主一天把媳妇打八遍/我问你谁家的日子苦呀,谁家日子甜?”[8] 类似小调经常穿插文中,“庙会”描写也是如此。《受活》描绘了“受活庆”这一每年麦后欢庆丰收的盛大仪式。
(三)方言俚语
方言是语言地域性的变体,能折射地域的历史文化内涵,表达地域特有的自然状况和民俗风情。在《日光流年》《耙耧天歌》《受活》等作品中,阎连科大量穿插豫西的方言俚语,增添了“耙耧世界”的地域色彩。他笔下的人们把白白错过叫“白枉枉”,把受不了叫“不消受”,把中心、中央叫“当间”。这些“土得掉渣”的方言俚语,生动地展示了受活人的生活情致。而在“受活”“儒妮子”“圆全人”“热雪”“死冷”等方言词语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豫西地域所特有的苦难和凝重。河南是豫剧之乡,豫剧的语言、唱腔、表现手法都给作家带来了无形的创作影响。《丁庄梦》的语言就有豫剧“一唱三叹”的感觉,“一想到让我爹在全庄人面前磕个头后去死掉,爷爷惊了一下。惊了一下。惊了一下,我爷也就往庄里走去了。就往我们家走去了。真的走去了。”[9]在《日光流年》的开篇第一句“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豫剧形容一个人倒地死掉就是突然的一声锣响,“嘭”的一声,演员就倒在地上了。
阎连科对方言俚语的发掘、运用很自觉:“我就是要强调方言在中文中的作用,如果萧红的小说、沈从文的小说没有大量的方言的运用,他们的小说魅力就会消弱很多。”[10]
二、丰厚的河洛文化精神
作家曾经谈到家乡文化资源对其创作的影响:“从小生活在理学大师的庙宇之下,你会不断地道听途说。知道它的大概,时间久了,形成了一种文化浸淫,肯定也是一种情感的压抑。”[11]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影响着作家文化视野,使他的作品凝聚和表现出丰富深刻的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当代作家中,阎连科格外“迷恋”苦难,执著地关注苦难深重的乡土大地,将苦难作为一生书写的“核心”,始终以“令人疼痛和战栗”的笔触反映底层农民的生存绝境及其承受的各种苦难,展示了取向鲜明的写作姿态和立场。
作家故乡土壤贫瘠,自然灾害多发。历史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引发的兵家之争又不断地加剧这种苦难。如何生存、生活成为人们最紧迫、最关注的问题。产生于河洛的《易经》被看作是中国人道主义的源头,西周初年,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民生”思想,至春秋战国时形成社会思潮,并成为后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基点”。《诗经》中反映河洛地域生活的《王风》《周南》等就散发人文光彩。此后,贾谊、曹操、曹植等河洛诗人的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感慨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命运。“安史之乱”后,以杜甫和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们发出了关心民生的最强音。这种关注民本民生的精神传统是河洛文人身上最耀眼的光芒,必然照射着在苦难的河洛大地生长、对苦难有着刻骨铭心记忆的阎连科的心灵,影响着他形成坚定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写作立场。他的作品中,可怜的人们总是不断遭遇天灾人祸,在巨大的灾祸面前往往显得那么渺小和无助。阎连科对“人”的关注更体现在他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思考上。《丁庄梦》中,夏玲玲和丁亮的结合虽有悖于伦理,但无悖于人性,他们凄绝的爱情感动了善良的村民,村民给予他们最大的宽容和理解。面对艾滋病这个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作者的悲悯意识和人道主义的情怀充溢其中,这种对生活热爱、对生命尊重的创作使作家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超越。
(二)坚忍自强的“天行健”精神
因为看到了绝境中爆发的生命力量,阎连科创作注重表达对生命韧性的崇高感。他笔下的耙耧山人,面对命运抛来的生死困境,没有屈服认同,以一种极端酷烈的方式与命运做殊死的抗争。他竭力寻找揭示来自多灾多难的大地民间的生生不息抗击命运的潜力和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坚韧奋进是河洛文化精神内核,诞生在河洛大地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都充满了行天之健的文化品格,“盘古开天辟地”“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无不体现河洛先民的创世精神。作家塑造的主要人物中,除了路六命不堪生活的重负选择自杀外,其他的都是在绝望中抗争命运的英雄。《日光流年》从死写到生的“索源体”结构展现的就是人类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在阎连科的世界里,尤四婆取骨献髓,拯儿救女;先爷与天抗衡,以身喂苗;司马笑笑与蝗虫恶战,自杀伺鸦;蓝百岁深翻土地,牺牲女儿;司马蓝拼命治水,劳累致死。他们都是集勇气、智慧与献身精神于一身的英雄,这种气概与河洛大地上坚韧自强的“天行健”精神一脉相承。
(三)王都文化下的“权力情结”
洛阳自古为“王者之里”,历史上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定都,这使它逐渐生成一种特有的“王都文化”形态。阎连科曾揭示过:“我从小就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中原农村的人们都生活在权力的阴影之下,在中原你根本找不到像沈从文的湘西那样的世外桃源。……这样的环境,自然就形成了普遍对权力的敬畏和恐惧。”[12]村长这类的“掌权者”是作家笔下集中描写的典型代表,他们有的可以为所欲为,霸占民妻,决定村民婚姻,甚至决定村中残娃的生死。老实的村民经常深陷权力的梦魇之中,“朝廷三爷”主宰下的寨子沟少女、寡妇媳妇,《三棒棰》中戴了八年绿帽子的石根子,《天宫图》中为村长与自己妻子偷情放哨的路六命……在权力的桎梏下,我们看到凌辱中的扭曲惶恐,同时也看到民间对权力的膜拜与向往。《情感狱》中的连科、《坚硬如水》中的高爱军、《金莲,你好!》中武老二、《日光流年》中的司马蓝,为了争夺权力都作出了种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行为。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大队公章竟然成为了权力的象征而被人们疯狂争夺。《耙耧山脉》的大队公章和记录返销粮的账本成为作品叙述的焦点。《丁庄梦》中的老村长丢了公章一直死不瞑目,直到“我爷”拿一个假公章给他看才闭上了双眼。这种夸张、喜剧性、隐喻性的写作显示了作家内心的透彻感悟。与其他作家书写权力不同,阎连科注重从底层的生存苦难实际境遇出发看待人们的这种心理和行为,并不直接地从现代启蒙的角度进行简单的批判,他把对权力逼仄人性的痛恨、对底层者遭遇权力后无助不幸的怜悯、对民众麻木糊涂的哀楚混合一起,在更多的理解中,彰显了人道主义的情怀。
(四)“理学名区”里的“伦理叙事”
河洛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理学名区”。阎连科家几里远之外就是二程的故里,当作家“拿起笔,游荡于‘耙耧山脉’之间时,寺庙才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仿佛看到寺庙的象征意义和无形的力量,看到了人们对‘程寺’的敬畏和对‘程寺’精神的继承”。[13]这种潜意识的文化浸染,使阎连科的小说世界呈现出浓厚的理学文化色彩。作品中的父母与子女关系,充溢着“孝亲情怀“的人伦风情和“父为子纲”的理学脉络。《情感狱》中,家中虽困苦不堪,但家人在咀嚼苦难的同时也处处感受着家庭的亲情与温暖。除了“父慈子孝”的人伦温情,作品中着墨最多的还是“父为子纲”的伦理思想。《日光流年》中,司马蓝的父亲司马笑笑临终向其嘱托“要把这个村长要回司马家”,父亲的志愿和教诲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当发现母亲与人偷情时,他毫不犹豫地把母亲逼跪在父亲的坟头边。家庭伦理关系的另一重要维度便是夫妻关系,“三从四德”“夫为妻纲”“夫妇有别”等伦理规范在“理学名区”的河洛表现尤甚。阎连科坦承“河南作家普遍对女性的漠视”。“骨子里,女性在河南作家的作品中永远是他者,是属从。除了周大新对女性有些温柔情怀外,别的更多的还是传统文化观念在作品中的潜意识。是不自觉的。”“我在写作中只知道女人是人,而没有意识到女人是女性。”[14]《黄金洞》中的老大媳妇得知老大和桃儿的奸情时,只微微抱怨一句,就被老大“啪的一下在她的脸上打了一耳光”。《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男人们奉行的是“就是把媳妇打死也行”地观点。这也种导致了女性对婚姻家庭的集体无意识。《日光流年》中杜竹翠的一席告白道出了河洛女人们的心甘情愿,“你要是娶了我,我会像磨道里的驴一样侍奉你一辈子”。在这里,女人的所有作用就是对丈夫的侍奉、对公婆的孝敬,她无权干涉男人的外遇甚至甘心等待被另一个女人取代。
面对在现代都市文明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的乡土人伦,阎连科有着自己“理学名区”般的思考。作家在现代人遭遇精神危机、新的精神构建尚未完成情境下,对慢慢消逝的故土文化会有着本能的关注,尤其是当他真切感受到这种文化对自己的曾经滋养,就更容易对身边的文化传统产生认同,而难于进行迅捷的现代反思。这是时代的无奈,也是作家的局限。
(五)老庄世界下的“避世思想”
“耙耧世界”呈现了一个自然、自足、与世隔绝的诗性空间。《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受活》中的受活庄、《风雅颂》中的“诗经古城”,都是座落在耙耧山脉的褶皱里的“化外之地”。《受活》中,作家展示了“宛若天堂”的“至德之世”。受活庄地处深山,水足土肥,人们过着一种散淡无束、殷实富足的天堂日子。阎连科作品还经常闪现出老庄“道法自然”“天地有大美”的自然情怀。无论是“藤、葛、蔓”还是“松、柏、竹”的人名取意还是“花嫂坡”絮言中那到处是花红和柳绿、到处是草木和芳香的迷人风光,都令人顿生庄子“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15]的陶醉情怀。“小国寡民”“至德之世”是建立在崇尚自然、反对外界干涉和自我欲念的基础之上。小说《受活》正是展示了一个宛如天堂的“化外之地”在进入现代人类文明的过程中所遭受到的瓦解。入社之后,受活庄人“天堂般”的日子消失了,相继遭遇了“铁灾”“大劫年”“黑灾”“红罪”,那盖着“红艳艳”公章的要粮条子变成对受活庄人赤裸裸的掠夺与抢劫,县长柳鹰雀更是在个人政治野心的鼓动之下,将受活人推入到了万劫不复的地狱。柳鹰雀野心勃勃,留给他的是自己撞向车轮的惨烈以及幡然不及的悔悟。而受活庄的那些残人们,在经历了外面世界的种种诱惑之后,心灵还能保持与世无争的平和吗?日子已经如平静的池水被突然搅碎般变得面目全非,而那天堂般的“散日子”注定成为不再复现的梦。
阎连科不断地表现着他对“外面世界”的探究,思考村人与“外面世界”的关系:三姓村的人付出惨痛代价从“外面世界”引来了灵隐渠的水,却是臭的;先爷最终放弃迁徙到“外面世界”,决定固守旧土;受活庄里的天堂日子因为“外面世界”的介入一去不复返了。作家试图从两千年前的老乡“老庄”那里找到思考的答案,这种追溯有着鲜明的“复古”意识。阎连科描写的“避世思想”似乎与前面提到的“权力情结”有些矛盾。但这往往是现代人的生存实际,也是当下的真实语境。
三、河洛文化与阎连科作品的艺术特质
河洛文化影响了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体验,经过自己的个人体验和滤化后,必然使作家文本的表现形式、创作风格和艺术技巧,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面貌。
(一)神秘诡异的文章气韵
河洛文化是以“河图洛书”和《易》为起源的文化,“河图洛书”表达了远古先人们的神灵崇拜、祖宗崇拜、物象崇拜以及生命崇拜的信仰,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神圣与神秘色彩。在“河图洛书”神秘思想的暗示和影响下,这方地域的人们格外注重尊神、敬神,好祭祀,多用巫吏。之后,佛教、谶纬神学相继在这片土地上产生影响,“业报轮回”“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潜化为河洛人的潜意识。洛阳为王者之里,北邙山水深土厚的地质构造和背山面河的地理特点使之成为皇陵的首选之地。自古的河洛文人们面对这一片茫茫,无不发出人生莫测的感慨。河洛之地孕育着的种种神秘精神与诡异元素使自古以来的河洛文人不免受其熏染,呈现出奇崛诡异、夸张荒诞的美学特色。李贺的诗充满着离奇想象和荒诞诡异的氛围,被誉“诗鬼”。李商隐的《无题》化用神怪典故,复杂奇异。唐代还出现大量的以描写灵异、鬼怪、神佛的“神怪传奇”。 阴阳相通,人鬼共存,现实梦魇交织,虚假难辨、亦幻亦真,河洛之地充满了诡异神秘。
很多研究者谈到域外文学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作家的影响,但作家非常注重河洛神秘主义文化因子的作用,他说“我的小说,充满着无数的民间语言和民间传说,民间的神秘感都在小说中有体现,而且人家都会说阎连科的小说充满着不可思议的神秘,那是因为在我的生活中遇到的神秘的事情特别多”。[16]阎连科作品中,千年的古柏常常与古庙和陵墓相伴而生,祖传三代的老屋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情感狱》中叙述八十二岁的九爷在隆冬的夜里挥刀砍树,带有神秘诡异的气息,而九爷在树根砍断之前倒了下去,也验证了梦中的谶语。《耙耧山脉》里,死去村长的阴魂整夜坐在村边坟头滔滔不绝地讲话;《黄金洞》里,已吞金而死的爹指挥二憨背着自己的尸体,摆脱女人桃的追赶;《耙耧天歌》里,尤石头的阴魂长期陪伴尤四婆,看见三女婿拉走了家里所有的粮食,还会哀哀地哭。《受活》开篇就以“天热了,下雪了,时光有病了”为题,呈现了“酷夏里下雪”的骇人听闻的气候,文中蒙上神秘荒诞的色彩。阎连科以对河洛神秘文化因子的超常感悟力和把握度,挖掘出了民间久违的神秘、奇诡和荒诞,在此基础上“构筑起的是一个更为成熟的艺术形态:一种以现实经验为根基的充满河南乡土味的‘超现实小说’”。[17]
(二)厚重悲凉的创作风格
《日光流年》前言写到:“谨以此献给我赖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的人类、世界和土地的遗言。”作家沉浸在自己的“苦难”世界中,他的文本里充斥了极端的生死、极端的苦难抗争,呈现出残酷、冷硬或者是荒寒的美学追求。
河洛大地多发的苦难促生了此地文学厚重、悲凉的底色。建安年间,河洛文人学士目睹社会动荡和人间苦难,形成慷慨悲凉的创作风格,构建了“建安风骨”。唐“安史之乱”使诗人们饱受干戈离乱、民不聊生之苦,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怆情怀。抱着以为“劳苦人”写作为宗旨的胸怀,阎连科所表达的正是与其血肉相连的那片苦难土地的内心,他说“你是农民,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永远背负着土地与农民的沉重。你的心灵是由土地构成的,是由泥土和草木建造的。这种沉重是无法摆脱的。”[18]
《丁庄梦》开篇写到:“庄里的静,浓烈的静,绝了声息。丁庄活着,和死了一样。”一种由苦难衍生的悲凉感浸入其中。《年月中》中,一个孤独的老人、一条看不见东西的盲狗、一株随时可能死去的玉蜀黍、一片荒无人烟的干旱原野,在如此荒凉的背景中,当我们发现玉蜀黍的根须“都如藤条一样,丝丝连连”“穿过先爷身上的腐肉,扎进了先爷白花花的头骨、肋骨、腿骨和手骨上”时,顿生一股凄惨悲凉的感觉。《日光流年》中,残疾的孩娃必须扔到深山活活饿死,濒死的老村长以自己身体作为乌鸦苟延残喘的食物。这样的情节让人触目惊心。阎连科以惨烈的、酷厉的、极端的方式描述了河洛大地的故事,文本中充斥了对“劳苦人”悲剧命运的深厚同情和无能无力的痛苦心境。
(三)灵活多变的艺术形式
费正清说过,“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传统,即‘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和‘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传统’。‘小传统’表现为较先进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大传统’则以‘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的价值观念’缓慢前行。”[19]河洛自然属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传统”范围之列,因地跨黄河、淮河、丹江三大流域,境内伊、洛、汝、颍等河穿流而过,河洛长期是全国的交通中心。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洛阳更是一跃成为全国交流最便利的地区之一。水陆交通之利大大促进了商业活动的交流,打破了“大传统”的封闭性,外面世界的融通新潮、勇于创新的“小传统”融入其中。诸多文化交汇、碰撞,使河洛文化更具包容、凝聚的胸怀,也增强了河洛人对外来文化艺术的认同感、理解力以及自身的创新力。
阎连科一直寻求写作上的创新和超越。他说过:“新的小说生命元素,才是作品和作家的生命力”“没有新的小说生命元素,你的小说就只能死亡”“一部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差异性”“当你在这个地方已经成熟之后,你必须要离开它,必须脱离它,否则,你就会落进陷阱里面。成熟最终意味着衰败,你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创作道路”。[20] 他的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在语言上,作家追求读者不能一开始就轻易辨出是他的小说。因此,他避免用《日光流年》的语言去写《坚硬如水》,不愿重复“瑶沟人的梦”那样的叙述风格。写《情感狱》,他的语言是质朴的细腻的,有种不动声色的温情在流动;到了《年月日》《日光流年》,他开始注重语言的陌生化审美,在文本中经常加入奇怪、荒诞式的描摹式语言,比喻、通感等修辞手法比比皆是,语言风格是艰涩、凝重和诗意的;《坚硬如水》几乎是革命语言的颠狂,革命对联、语录歌、样板戏、政治演讲、政治豪言充斥其中,呈现一种汪洋、泛滥的语言姿态;《受活》全部用河南方言写作,甚至需要不断地注解才能使人看懂。一路走来,阎连科的语言风格可谓一变再变,不断激起人们的惊奇感。在文体上,阎连科是一位“文体自觉”的作家。作家曾经谈到,“创作上的困难不是故事的问题;故事总有写不完的故事;最怕的是你找不到一个新的方式去表达它。”[21]他不断地进行着文体方面的大胆尝试,于是我们看到了《年月日》中的“寓言体”,《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看到了《受活》中正文和絮言的相互补充,《丁庄梦》中梦境与现实交织一起的叙述,看到了《坚硬如水》的“革命叙述”,《风雅颂》的“诗经叙事”。正是这种开放的写作姿态,使得阎连科的小说能够取精去糟,博采众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世界。
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使得中国作家可能无意中忽略本土的文化和文学经验,在创作中迷失自我。优秀的作家善于在滋养自己的故土中寻找自信和灵感,构建自己的精神高地和艺术世界。莫言做到了这一点,阎连科也做到了这一点。
注释:
[1] 阎连科、姚晓雷:《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二期。
[2] 朱绍侯:《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文史知识》1994年第三期。
[3]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第255-2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4]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4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5] 韩养民、韩小晶:《中国风俗文化导论》第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6] 杨海中:《图说河洛文化》第352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7] 阎连科:《褐色桎梏》第4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8] 阎连科:《受活》第35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
[9] 阎连科:《丁庄梦》第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
[10] 陶澜:《阎连科:方言是种挑战姿态》,《北京青年报》2004年第四期。
[11]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31、6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12] 石一龙:《我的小说是我个人的良知——阎连科访谈》,《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三期。
[13] 郜元宝:《论阎连科的“世界”》,《 文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
[14]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1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15]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1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16] 韩维志:《庄子》第60页,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17] 韩维志:《庄子》第126页,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18] 程光炜:《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我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五期。
[19] 秦方奇:《地域人文传统与伏牛山文化圈新文学作家群的建构(上篇)》,《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六期。
[20]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第21、47-4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21] 阎连科、姚晓雷:《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