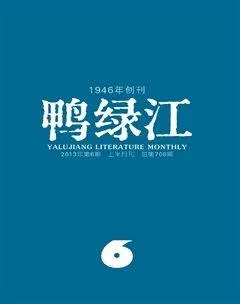莱山之夜(之一)
张炜,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单行本多部。主要作品有《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七卷)和《万松浦记》(二十卷)、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刺猬歌》《你在高原》(十卷)等。作品分别被两岸三地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你在高原》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这是一场无始无终的奔波。莱山之夜,山雾笼罩,疲惫不堪,却常常无法入眠。林涛阵阵,不断听到小鸟的叫声一荡一荡远逝。再次打开笔记,注视这幽深的莱山夜色,这所见所闻所思……
西边颗粒不收
随着往西,一路上的流浪汉突然多起来。他们可能都是从东边的打工地返回的,想赶在这个秋天回来忙庄稼,可想不到迎接他们的是根本用不着收获的一片光地。他们踏入自己的土地时,一个个惊得半张着嘴巴,不知是干渴,是绝望,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他们一路饥渴难耐,由于一直赶长路,像西部的人一样,头上捆一条又脏又臭的手巾,两手被日头烤得像锅底一样黑,衣袖短短的,两只大手突兀地垂着。它们好像急着要找点事情做,却又无从下手。在这一伙人中,只有我一个逆向而行,一直往西,都有点吃惊。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汉子擦肩而过,走开几步又转过脸来。我以为遇到了熟人,一抬头正见他向我跺脚,说:“伙计,到哪里去?西边颗粒不收哩!”
我点点头,感谢他的提醒。
他拍着叭叭的脚步走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那么高的个子,身上的行李卷却只有一个枕头那么大。我不知他是怎么过夜的。当然,每个流浪汉都有自己过生活的方法,有些绝招甚至秘不示人。比如说在野地里过夜,有人靠点火,有人靠钻草垛子——我还遇到一个古怪的家伙,他竟然在夜晚往自己身上埋一层又细又干的沙子。那沙子白天被太阳烤了一天,热烘烘的。用这个办法来取暖的人我以前从未遇到。
我远看着这个汉子的身影,有些犹豫是否还要继续往西。我这时有点后悔的是,应该在朋友家里多耽搁些日子才好……
我在旅途上把他们全都想了一遍,有时恨不得即刻就奔到他们身边。我渴望见到一双双熟悉的眼睛,向他们倾诉,也听他们叙说。久违了,我的朋友。我们共同经历了,走过了,喘息之后,该是从头长话的时候。一些谣传、一些可怕的误解,所有这一切都等待我们去澄清。当然,这非常重要。想到这些,我差不多一刻也不能等待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脚步踌躇,为什么还要无望地徘徊。
后来,我终于停住了脚步。
我好好端量了一下前方。我想由此向北,然后再向东……
见了两样东西红眼
我在离村子稍远的地方支起了帐篷。
这儿不仅要远离村庄,而且还要远离田间小路;最好在沟边渠畔,要有一丛灌木遮挡,我才能安顿下来……就在类似的地方一连过了两夜,太太平平,没什么打扰。我点起篝火做野餐的时候,尽可能在灌木的另一面,因为这样村里人就看不到火光了。尽管如此,第三天夜里我刚刚熬好稀粥端起碗,就听到灌木丛里发出了啪啦啪啦的响声。刚开始还以为是个野物,没有在意,后来竟然借着微弱的火光看到了什么:那是紫穗槐棵子里探出的一个头颅——那个人头发不长,眼睛特大,脸上乌脏。我吓得差一点儿把碗扔掉,随即大喊了一声:“你是谁?”
那个人浑身一抖,沉默了片刻,然后索性钻出来。
这人穿着老式黑布衣服,头发留得很短,可是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女人!因为她的胸部无论怎样紧紧束起,还是高高耸着;尽管她脸上抹脏了,可是大大的眼睛还是十分妩媚。她一开口说话,那就更让人确信无疑是个女的了。她大约只有二十左右岁,一双手满是茧子,但巴掌很小。她直直地看着我,像是发呆,一声不吭。
“你要干什么?”
她摇摇头,取一个怪姿坐着:一只腿跪着,一只腿盘在地上。这样静了一刻,她说:“我在树丛子那边听到这儿有响动,又闻到了米饭香味。俺知道这边开伙了。”
“开伙”一说是当地人才有的,意思是做饭兴炊。
“俺妈两天没吃热食了,我想给她讨碗粥。”
她说着从衣服里边摸出了一个小小的搪瓷缸。我毫不犹豫把粥分出了一半。她千谢万谢,一转身钻进了树丛子——这让我知道,原来在树丛的另一面早就宿着两个人。
我胡乱吃了饭,忐忑不安地钻到了帐篷里。但我没法睡去,有点担心。春夜凉得很,低低的雾气里有一种不好的气味。这个夜晚浊气压得很低,我知道这是远处那些工厂飘来的烟尘和蒸气。大约是夜间七八点钟的样子,要睡觉还太早。我点起小桅灯,不敢把篝火拨得太亮。我想读点什么,也只能这样打发这个夜晚了。可是我刚刚打开一本书,就发觉树丛里面噼哩啪啦响。不用说又是她们了。
刚才来过的那个姑娘扶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手脚看起来还灵便,只是疲惫瘦弱得很。她坐在篝火旁向我道谢,问我是从哪来的。还没等我回答,老太太就说:“我让女娃儿来一趟,女娃儿不敢,说这边有个黑胡子黢黢的男人。我告诉她,天底下哪有这么多坏人,壮起胆子去吧……你是个好人。”
“大娘可别这么轻信哪,只一碗粥就能证明我是好人吗?”
老太太拍拍膝盖:“俺娘俩游荡惯了,什么人俺还看不出?那些坏人,别说一碗粥,一粒米也不白给呀,他们就知道想方设法捉弄人。哎呀,今夜里多好的一堆火啊……”
她说着往火堆跟前凑了凑,伸出手贪婪地烤着。在火光下我才看清,这个老太太戴了一顶崭新的黑色丝绒帽,帽子上钉了一块绿色琉璃。她见我的目光落在帽子上,就说:“这是俺闺女前些天在集市上买的。俺说你妈老皮老肉了还戴这么新的帽子?我让她戴,她嫌老气。我娃儿忒孝顺!”
当她弄明白我是从哪来的时候,就说:“俺娘俩就是到城里去的呀,走了半个月也没走到车站。”
原来她们是要去东部城市的那个火车站。我问她为什么不乘汽车。
“就为了一路上做点活计,正好也挣足了坐车的钱。”
老太太说她们那个村子在城里做“服务员”的女娃可多呢,她也想把女儿送去做“服务员”,自己身边无依无靠,想来想去就和女儿一道走了。“听人说城里老太太做的活儿也多着呢,洗衣服,给人家扫地擦桌子……”
原来她就住在芦青河西岸的一个村里,老伴早死了,她一个人拉扯着这个女儿过日子。自从起了进城的念,她们就不再安生了,终于选一个日子过了河,不紧不慢地往东挪蹭了。先是在南边那些富庶村子做活儿,受了一次骗就赶紧拔腿赶路,一路上受的苦楚没有数……她叹息道:“如今的人哪,除了钱什么也不认了,别看都是土里刨食的人,也能老乡骗老乡。”
我没有作声。一路上全是这些故事。不管你想不想听,老太太还是盯着向上蹿去的火苗高一声低一声讲起来。她大概讲出来心里会轻松一些。这使我明白了路途上那些流浪人为什么乐于把自己悲凄的故事讲给生人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抛开心事,卸去心头的沉重。
“你猜俺为什么在路上耽搁这么长?那会儿俺在一个村的磨房打工,来送粮食的两个司机认识了俺这娃儿,就天天甜言蜜语,说要给她找个好差事。他们去的地方多,都是开汽车的人嘛,经多见广。俺的娃儿活该就信了他们。有一天娃儿叫一声‘妈’就走了,说安顿下来就回来接妈。结果哩,一去十天八天不回。有一天夜里俺正睡着,外面有人拍打窗子,那个急呀,那是娃儿啊!啊呀娃儿可回来了……”
老太太说到这儿,旁边的女孩眼圈红了,叫了一声妈,想阻止她往下说。
“孩儿也不用不好意思,我要数叨数叨给这位好心的大哥听听,让他知道咱这地方是人少鬼多,大白天里你受了多少冤枉。他大哥不知道,这孩子一回来可把我吓了一跳:娃儿脸上有血,头发揪得东一缕西一缕,肩膀上还有牙咬的印子。孩子哭啊哭啊,哭了半宿才敢告诉我,说妈呀,孩儿再也不离开妈了,孩儿这一路上九死一生啊……你猜怎么?那两个歹毒的东西原来是外省人,他们千里迢迢来送粮食,回去想捎个女人走哩,走到半路上把俺孩儿按在车上好一顿欺负。俺孩儿从小在妈心上揣着,见了男娃眼不抬,哪受过这个,说不活了不活了,抬头就往车上撞。最后他们就把俺孩儿绑起来,用一根绳牵着,像耍猴似的牵到了外省,五千块钱卖给了一个瞎子,硬拜下天地。俺孩儿宁死不从。瞎子又叫了本家人,硬是推着按着捆进了洞房,接着人不离身绳不离腿。还亏了俺孩儿年纪小身子轻灵,跳了窗户马不停蹄地跑了这些天,算是一口气跑回来……打那以后我就让她把头发剪短,装个男人模样。她老哥啊,你说这世道怎么了?如今这人哪,只见了两样东西红眼:一是钱,二是女人。谁能欺负人、谁心狠胆大,谁就能过上好日子……”
老太太说着抽泣起来,抹起了鼻子。旁边的女娃先是一声连一声阻止妈妈,伸手扯她的衣襟,再后来就一声不吭垂下了眼睫。
老太太说:“俺要积起盘缠,早就去城里了。俺那儿半个村子都走空了,人家早进城了。”
听着老太太满怀希望的絮叨,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女娃紧紧抱住母亲的一只胳膊,不停地叫:“妈妈……”她的声音里充满羞涩和悲凉。
地母在疼
我在这个夜晚紧挨着茅屋宿下。一夜不知多少次被惊醒。我听到地下的隆隆炮声,是这不停的轰击使大地抖动……一想到这会儿正有人在地下挖掘,心里就发疼。
绝大部分采掘工都是从这个平原的农家子弟中招募的,他们戴上矿工帽、提上矿灯走入地下,然后就开始了没白没黑的挖掘。地下巷道曲折漫长,足够他们挖上一生。那是一座地下村庄,它使他们忘记了地上的村庄,忘记了祖祖辈辈生存的热土。可怜的孩子,他们从地上出生了,如今却要像鼹鼠一样钻到地下,用两只前爪把它一点点掏空。平原才是他们的母亲,这会儿他们一割断了脐带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儿,开始动手毁坏生身之母。母亲白发苍苍,牙齿脱落,脸上的皱纹数也数不清;可是她的儿子还要在母亲脸上再划上一道深痕。母亲眼花耳聋,听不到这轰轰炮声,也无力管教欺爹欺娘的儿子。
他们挖呀挖呀,先折下母亲的肋骨,再掏出她的心肺……就是这些不孝的儿孙把母亲折腾得气息奄奄;母亲的眼睛干枯混浊,可是最后一刻还散发出慈祥的光,寻找她的每一个孩子,望向他们。她知道孩儿们无论做多少孽、跑多么远,最后还要扑到她的怀里来吮吸和乞求,在她的怀中长眠。一个遍体鳞伤的母亲仍然要宽容自己的孩子,用自己的乳汁去哺育他们,满足他们永不餍足的饥渴。这就是母亲。比起慈母,她的儿女总是令人失望。当母亲富足的时候,他们就拥过来争抢,剧烈吵闹,尖利的指甲把母亲的衣服都撕破了,把母亲的皮肤都划伤了。可是当母亲贫穷的时候,他们就远远躲开,四散奔逃,再不回来看上一眼。没有多少儿子真正怜惜母亲。
对于母亲,我不知道犯了多少难以饶恕的罪过。我只要活着,就会记住这一点。
地下的炮声响个不停,从黄昏响到黎明。人要在这儿安睡可真难啊。我不知道这一带的人是怎么安睡的,大概这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地下的炮声太令人恐惧了,它似乎就在脚下炸响。我的确感到了整个大地都在抖动,那是地母在疼、在抽搐。
我想,那个设计和规划开发这个矿区的人——此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魔头,因为谁都不难明白,用这种方法掘出了地底的一点东西,赔上的却是整个的海滩平原!在丧心病狂的轰击和挖掘下,一片平坦如坻宛若绘画一般美丽的原野变得坑坑洼洼,脏水漫流,荒芜遍地;更可怕的是地下水脉被切断,地下水逐渐消失,连最深最旺的甘泉都在干枯或变臭。只有昏头昏脑或垂死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在这儿度过了一个夜晚,接着又是一个白天。当第二天黄昏来临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走出去,向西遥望。
太阳落下,原野一片模糊,凄凉的■乌又叫起来。我回到了帐篷里。大概因为太疲乏了,这一次很快就睡着了。睡梦中仍然能够听到轰轰隆隆的地下炮声。
褪火
走在这条街上,我被一个少女的笑脸给吸引了。当我的目光转向她时,她却突然地、出乎意料地、明明白白地对我做了一个猥亵的手势。同行的朋友也看到了,喝了一声“无耻”!少女听到了,脸上是无比得意的神情。我扯一下他,小声说:“千万不要惹她们,这些可怜的孩子……”朋友走开了一段路还愤愤不平地回头去看,而那个小姐还在朝这边招手,嘴里叫着:“多好的小伙儿,帅小伙儿呀,该给自己褪火了……”
朋友不再敢回头,一直走开了很远才问:“‘褪火’是什么意思?”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心里也正为这句挑逗纳闷呢。“褪火”一般是中医给害了热病、口舌生疮的病人治疗时说的,它的直接意思当然是十分明白的。可是这里小姐显然另有所指,这就有些晦涩了。我在心里慢慢揣摩:时代对人的强烈锻造期也许真的过去了,淬火期也过去了,剩下的日子也就是“褪火”了。这个时期会是短暂的,然而却是十分折磨人的。不同的是这个时代也会遇上一些不同的人,其中有的会成为不驯顺者,有的是奇怪的对手。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我的这位朋友了,他肯定是少数几个能够经受巨大折磨的、不会屈服的人,因为他身上更多的是旺火,经历了反复无情的锻造过程,这个过程从父辈就开始了。这种钢火的确是很难在一朝一夕被褪掉的。
哲学家
哲学家来农场时,要求把老婆孩子一块儿带上,因为他已经下了决心,只想远离战战兢兢的城市,在边远之地了此一生。谁知有关方面不仅不让他带老婆孩子,连书籍也不让带,还说那里就是一所大学校,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哲学家被分派的活儿是拉地排车,实在拉不动,他们又让他去修剪树木,可又偏偏不给他梯子。这样他就得学着爬树,好不容易爬到树顶,有人就在下边不停地踹树,树一摇,他就从树上掉下来。幸亏树下都是沙子,他摔得嗷嗷叫,监工的人就拍手大笑。
半年之后,妻子孩子来探视他了。
孩子已经高中毕业,在一个工厂里当钳工。他们来探亲,哲学家按规定要求农场给一个单间,他要和妻子住在一块儿。场里让他们住到一个破草棚子里。
哲学家和他爱人一起住的三五天里,有个络腮胡子和另一个背枪的民兵在屋角挖了个小洞,从那个小洞往里观望。哲学家的爱人一出门他们就尾随着,说一些下流话。她本来要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后来实在住不下去,就领着孩子回城了……人走后,哲学家给气蒙了,一天到晚低着头不说一句话。他的嘴巴歪得厉害,头颅不停地颤抖。大家都知道哲学家病得不轻。那个络腮胡子说:“还是俗话说得好呀:色是刮骨钢刀,酒是穿肠毒药……”
大约又过了半个多月,哲学家就躺倒了。这一回大家都知道事情严重了,就一刻不再耽搁,通知了他的家人。
还好,家人赶来了,并且来得及与他做最后的道别。
俊男
今天的农场里只剩下这个老人了。夜里睡不着,他对我说起了“俊男”的故事。
“什么时候都有利落人儿、俊人儿。比如他吧,喜欢打扮,平时注意仪表,最苦最累的秋天,他从地里一回来就把自己弄得整整齐齐,把头发梳好。后来他头上是一处处秃斑,脸上有了疤。从那以后无论天多热他都要戴一顶帽子,那些管理人员冷不防就要给他摘下来。
“因为这里灌溉用的地下管道常常淤塞,淤了就得掏,他给毁在这上边……那一年他才四十岁,人长得年轻,高高瘦瘦,胡子黑旺。他的身体比谁都好。地下管道被一些淤泥乱草堵塞了,没有别的工具,只能让人钻进去。这些管道比人的身子粗不了多少,脏臭不用说了,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先要把竖向的石槽清理好,然后再横着钻进去,一点一点往外挖那些淤塞物:一个人趴在里面,外面的人在石槽口上用筐子提……俊男在里边,只干了二十多分钟,就憋得脸色发紫出来换气。里边氧气严重不足,气味刺鼻。他赤身裸体,只穿一个小短裤,脸上被划破了,血水混着臭泥往下淌……
“大家都对监工的说,这样施工实在太危险了,还是把土路刨开吧,把那些管子整好再埋上。监工说:‘危险?你们的命就那么金贵呀?’他们命令必须在两天之内把管子通开。俊男壮实,像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样有生气,差不多是他一个人在下边挖,挖一会儿上来喘一口气,再下去……大约挖到一半的时候,下边就没声了。平常他隔一会儿就敲一下管子,那是告诉别人自己平安无事。我举一个火把下去了,火苗儿眼看越来越细。我往里摸,发现这管道太细,有尖尖的东西刺着后背。不知费了多少劲儿才爬过隘口,看到俊男伏在那儿。我拽他的脚,他不动。我把身上的绳子拴在他两只脚上,一点一点往外拖。好不容易把人弄出来,阳光下一看,老天,他全身发紫,脸是青黑的,只剩下一丝气了。赶紧做人工呼吸,折腾半天才活过来……他的脑壳上、头发上,到处都是血……
“我们找人给他上了药。可是几天后他身上好多地方还是化脓了,怎么也愈合不了。最可怕的是头发下边起了一片水泡,水泡一破就化脓……几个月后头上的脓包算是好了,可是结疤处再也长不出头发了。妻子是一个中学教师,两人关系一直很好,但他回城后,妻子还是离开了他。
“谁听了都会埋怨他的妻子,不过亲眼见过也就不会了,因为俊男的模样实在太吓人了……妻子的背弃对他打击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是独身一人。我到城里看过他,他告诉我:妻子离开两年后,有人给他介绍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见面时戴着帽子,就这样订下了婚事。他忙着筹备结婚,可就在婚期到来的前几天,那个女人不知怎么打听到了一些事,再次见面冷不防就给他摘了帽子。她也离开了。
“俊男从那以后就发誓不再结婚了,要一个人过完这一辈子。尽管妻子离开了,他还是怀念她。有一回他跑到已经再婚的妻子家里,恳求她回家,不巧被那个男人碰到了,对方一把操起了刀子……”
这家伙
顺着这个城市又熟悉又陌生的街道往前,会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感觉。当年我初出茅芦,曾对这儿怀着多么大的热情和向往。那时候我把它想象得无一不好,简直是一个没有半点疤痕的、水光溜滑的纯情少女,再不就是一个深奥无比的博学老人。反正它既让人迷恋,又让人信赖,可以激发出一个人无限的想象力、对生活的无边热忱……当年这儿的风气远不像现在这样开化放浪,我那个初中同学第一次跨进这座城市,竟玩得如痴如迷,最后离开时却这样评价:这儿虽然美女如云,但并不适合搞男女关系。
这家伙走到哪里都能发现一些奇怪的、别具一格的事情。比如说他到省会徘徊了几天,接着就胡言乱语,说那个地方的女人“乳房分外下垂”;翻过一本旧画报,看过几场怀旧的电影,就感叹说:所有的女人当中,还是“女八路”最可爱。他这后一句话到底是赞扬还是包含了其他,就不得而知了。有一次他把类似的话在一位老妈妈跟前讲了,老妈妈拿着菜刀恶狠狠地朝他比画了一下。原来老人年轻时是一位老游击队员,曾经击毙过三个鬼子。我对他有时会产生说不出的厌恶,可有时又觉得他像一个极具观赏性的、张牙舞爪而又怪模怪样的动物,隔一段时间总想瞧上一眼。那时他一天到晚想象着到欧洲或北美去过一段日子,千方百计寻找出国的机会,在前些年出国还是颇为麻烦的一桩事时,他就千方百计打钱的主意。他认为钱这个东西是无所不能的——这算让他说对了,他把一笔钱交给了一个旅游公司,于是到欧洲尽兴转了一圈,高兴得手舞足蹈。现在鬼头鬼脑的人要搞点钱是很容易的,那些散布在广阔荒原上的暴发户们,常常是目不识丁,昏头昏脑,对外部世界糊里糊涂,很容易就被他这一类骗子搞走了钱。被骗后还笑嘻嘻的,与骗子成为莫逆之交。暴发户们对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既斜眼相向,又奉迎巴结,二者之间相互利用,如果勾搭成奸,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就能做成一两件骇人听闻的坏事。
他从外国回来之后,有好长时间蓄着长发。他头发又疏又长,看起来真像是一个游魂饿鬼。他还使人想到北伐时期那些剪了辫子的革命党,想起了半男半女的阴阳人。他的那双斗鸡眼好像被西餐给弄得更厉害了,一直盯着你时,让你无论如何还是忍不住要笑。他说:“嘿,人家那才叫人呢,对客人礼遇有加,思维也奇特。你知道天才兰波吗?你知道我去的地方他也到过吗?妈的绝顶的天才!二十郎当岁,留下的诗篇竟然千古不朽。那才是个旷世奇才。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另一个小秘密:他和我一样,也经商十年……”
他很神秘地朝我耸着鼻子,接下去就是眯着眼睛朗诵兰波的诗:“雪白的奥菲莉娅苑如一朵圣洁的百合花/漂流在人的繁盛如梦的平静而阴郁的波涛上/漂漂悠悠地渐渐远去/安眠中裹着长长的轻纱……/微微颤抖的柳丝扑在她的肩头/泪如雨下/芦苇向她耽于沉思的面容频频鞠躬/被碰响的睡莲纷纷在她的四周叹息……”
“妈呀……”他睁开眼睛大叫一声,呼喊着:“不可抵抗的力量啊!你听到了吗?这是兰波的诗!他在说‘温柔而狂热的爱情’,天哪,妈呀,怎么办呢?我无望而悲伤,我盯着兰波那聪明绝顶的眸子,我要紧步他的脚印前行……”
他在我面前疯狂地走来走去,捶胸顿足。这时候我才多少觉得他有点可爱。是的,兰波的诗。可是,可是我怎么评价眼前这个疯癫的、总是以天才自居的斗鸡眼呢?他是我的初中同学,在学校里,他那些奇怪的故事可真不少呢。后来我听说,他还不足二十岁时就设法把三十多岁的女班主任搞到了手。这种荒谬而无耻的勇气到底来自哪里,让我一辈子都搞不明白。我们十几年没有见面,当他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生活的那座城市里时,已经成了一个蹩脚诗人了。他竟然一见面就冷着脸,挥舞着拳头对我说:“怎么样?我要办到的事情无一失手……”
他呼喊着,我不知他的狂呼是指写诗,还是指当年女班主任的事……
这家伙刚刚从国外回来时,有一段时间常常突发大声地呼叫:“走啊!走啊!怎么能待在这样一个鬼地方?出国去啊!瞧这里连棵草也不生,连个像样的花也开不出来。为什么还赖在这里不走?为什么?”他都有点火了,盯着我的眼睛,伸出的两根手指像一对铁钩子一样。
“赖在”两个字让我极其反感,为什么是“赖在”呢?我想这片泥土上面长的花呀草呀树木呀活动的人群呀,一切一切都与我不可分离,这里可是我的出生地。我怎么能算“赖在”这儿呢?这是什么鬼话?
“糟透了!糟透了!”他喊着,“一切都给搞坏了,一切都乱七八糟了……”在他嘈杂的呼喊中,我想他说出的倒有几分不错;问题是这儿正是因为有了他这一类人,才变得更加不可救药、更脏更乱也更腻歪了;这儿脏兮兮的样子起码是与他们有份,再不就与他们的父辈有份。我听说他爸可算一个权倾乡里的人物。那个人并不可爱,虽说没干多少坏事,可也没干多少好事;至于他,则有好几次差点成为强奸犯。这样的人、这样的出身,已经早就失去了谴责的权利。你们正深深地亏欠,从上一代起就欠下了这片土地很多很多,所以绝不能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你还得偿还呢!至于我,走开的理由倒比你多得多了,可是我反而没有走,反而没有那么轻松……我伸着手指盘算了一下,计算从我熟悉的朋友当中、我知道的人当中,走掉的有多少、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走掉。结果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当中还真的有那么几个像样的人物。有痛苦者,有旅行者,有沉思默想的精灵。但这样的优秀人物在数量上而言,还是微乎其微。这之中占极大比例的,倒是一些“女二百五”、对当官的老子深感绝望的财迷、满口仁义道德的不负责任者、强奸犯、逃避徒刑的人、毫无希望的人、平庸的傻冒、一无所知却又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第一批系领带的人……是这些人先自走开了,离开了,并且发誓般地说道:从迈出国门的那一天起,他们才算过上了真正的人的生活。
我就是想熬下去
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曾有意无意地、不可避免地接触了大量可爱的同胞。他们有的很好地安顿了自己,有的则患了深深的思乡病,走入了另一种绝望。也有人在咧着嘴傻笑。那些“女二百五”怎么也忍不住自己的口水,盯着外国的摩天大楼,一双空洞的眼睛充满了欲望。她们慌里慌张不知所措地眼睛转过来,盯住我,好像在问:这一下明白了吧?不明白。
从那儿回来,我常常陷入一些老派人物所常常有过的麻烦。关于道德方面的忧虑。我在想公民责任之类,想放弃、出走,这种种行为的道德依据是什么?我这里当然不是从什么情感角度讲的,我是在讲某一种原则。我不得不一次次在那些死脑筋没法转弯、经常打结的一个字眼上徘徊,它就是:责任。我想我们仍然要讲讲责任吧!我当时就忍不住对一再挑衅的某人吐出了这两个字。我的意思是:我最终还是无法放弃,无法割爱,无法忽视自身的一份责任。我对事物,就是对脚下踏的这一块土地,仍然还有一种难分难舍的“情感”。对方呀的一声跳起,像踩着了地雷。他愣怔怔地端量我,还围着我转了一圈,然后伸出一个手指,离我的鼻尖只有一公分距离……他大概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了,最后吐一声:“好吧,那你命里就该着和这堆破烂一块儿熬。我可不熬了,我受够了!”
“你讲对了,我就想熬下去,想试试韧性,看谁熬得赢。”
这不是气话,这真的是我内心里所具有的一股倔劲儿,而且真的无法改变。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就是想熬下去。”
“哼哼……”他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饱受凌辱之地
那是东部最大的一座城市,地处海滨,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一段特殊的历史:她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落在欧洲人之手,据史书上说这个时期她正“饱受凌辱”。不过欧洲人至少给这儿留下了一大批优美的欧式建筑,这在后来倒构成了一座城市骄傲的资本。今天这儿看上去似乎一切不错,红顶别墅楼在海边山坡幢幢矗立,草皮油绿;在市区内曲曲折折的街巷上,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生锈的铜牌,原来是某一处名人故居。这座城市里还有一份默默无闻的纯艺术刊物,一家出版分社和两三所大学。许多著名人物在这儿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我很早以前就从教科书上了解了这些,但直到二十多岁才踏上这座城市的边缘。
那一次我简直是怀着朝圣的心情走来的。我至今记得那长长的水泥铺成的环海路和一幢又一幢尖顶别墅,记得草坪和公园,公园中洁白的大理石雕塑。我还记得在公园里有一群聚会的人,他们在拉小提琴,吹萨克斯管……这儿还有一家著名的酒厂,因此这儿后来被誉为东方最著名的“葡萄酒城”
——据说从规模上看,可以与之一比的也只有欧洲了。欧洲几个大的葡萄酒酿造公司都与此地有密切的业务联系,交流频繁,相互之间来往不断。
这里在任何时候都要领风气之先,今天更是证实了人们当年的一个预言:这里将出现北方的第一批艾滋病患者和同性恋群落。外国有的这里总是最先拥有,哪怕是从肤浅的模仿开始也好,谁都得承认,只有这儿的模仿才“蛮像那么回事儿”。据说有一天早晨,有一个小伙子用蛋清调起来的什么颜色把头发抹弄了一下,然后走上街头,结果让大清早起来散步的市民大吃一惊:天哪,这只有在外国画报和电影上才见过,瞧大红色的头发直直地向上竖着,真像毛发直立的食人饿鬼。这不过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警察后来过来干涉,最后把他扭送到家里去——他的父亲是当地驻军的守备区首长,气得两手颤抖,当即唤来勤务兵将儿子绑起,谁来求饶都没用。那一次首长可算好好揍了儿子一顿,儿子闹着要割腕之类……这个故事在那段时间简直是家喻户晓。
责任编辑 郝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