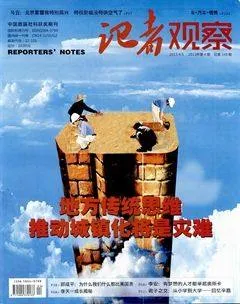太原战役历险记
2013年4月24日,是太原解放64周年纪念日。望着窗外耸立的高楼,听着孩子们的欢笑嬉闹,我的思绪又回到了64年前父亲的故事之中,耳畔依稀响起轰隆的炮声。
1948年10月初,为配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当时在平遥县文教科任科员的父亲,被抽调出来,带领民工队支援太原战役。同时被抽调的还有雷子玉(当时任平遥县秘书)、高志义(当时任平遥县民政科科长)、田锡仁(当时也在平遥县政府工作),由他们4人组织500余名民工组成支前民工队。雷子玉同志任营长,高志义同志任教导员,田锡仁任连长,父亲任指导员。当时父亲年仅19岁,第一次背上了驳壳枪,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行动,很是神气,也不免有些紧张。
10月21日下午六时许,支前民工队全体在平遥火车站集结,乘火车向太原战场开进。当时,榆次刚刚解放,是战斗的第一线。车到榆次站,离敌人已经很近了。为防止敌人火炮的袭击,火车不许鸣笛,列车徐徐进入榆次车站,几百名民工悄然下车。在夜幕中,支前民工队到达指定地点一一榆次北关村,就地露营。第二天黎明,民工队整顿了连排班建制之后,开往住地榆次北王明村,支前工作正式开始了。支前民工队的第一次任务是送白面,之后送弹药、送器材、送给养等等。总之,前线需要什么,他们就送什么。
11月6日这天,支前民工队给坚守在太原东山阵地上的战士们送给养,完成任务返回北王明村,当队伍走到鸣李村附近时,天空出现两架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的小型战斗机,从榆次向太原方向飞去,大家谁也没有理睬它。两三分钟后,飞机调头向民工队俯冲下来,由于一开始谁也没有在意,这一下几百号人慌了手脚。几个带队的指挥员赶紧让大家卧倒隐蔽,父亲也顺势在一个枯井旁边爬下。敌机俯冲到最低点时,机头前的机关枪“哒……”扫了一梭子弹。然后,飞机仰头向高空飞起,机尾的机关枪又是一梭子。两架飞机此起彼伏,轮番扫射,子弹在人群中溅起一串串土花。打了十几分钟,两架飞机才扬长而去。父亲连忙清点人数,除了在鸣李车站打伤了一头骡子和打着一些干草之外,几百人无一伤亡。这是父亲在太原战役中第一次遇险。之后父亲还拣了几个机枪子弹壳,比一般的子弹壳大许多,火药味很呛鼻子。
第二次遇险是在1949年初,农历腊月二十。八纵队某部九团解放了北营东侧的一个村庄。晚上六点左右把敌人打退,当时正下着小雪,为坚守阵地战士们爬在雪地里,非常艰苦。平遥县武装部部长兼平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王茂同志命令父亲带领支前民工队“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前线阵地上的困难”。父亲接到命令后,率民工队连夜为前线战士送草廉。为防止意外,他们只能走小路。地形不熟,天色一片漆黑,又不准使用手电筒和火把,行进非常缓慢。正当他们焦急万分的时候,遇到了当地的一个农民。农民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撤腿就跑。父亲只好派人把他抓回来,农民跪在地上求饶,大家向他讲明道理,要求他带路并向他讲清楚“把我们带到指定地点,就放你走,如果带错了路就枪毙了你!”那人满口答应,领着民工队窜沟爬坎,很快到达了指定地点,把草廉子送到了每个战士手中。在返回住地时,带路的农民稀里糊涂也走错了路,明晃晃的探照灯照过来时,父亲才发现眼前的铁丝网后边就是敌人的阵地。敌人立即用机关枪向民工队扫射,民工这下子乱了营,胆小的人到处乱钻,父亲命令大家原地卧倒隐藏。敌人乱打了一气,没有回音,也就不再打了。这样,父亲他们才悄悄地把民工又带了出来,安全返回。这次任务完成的又快又好,虽然出了点差儿,但无一人伤亡。总指挥王茂同志把几个带队干部叫到一起,吃了一顿简简单单的饭,就算给大家庆功了。王茂同志操着浓重的平遥口音对父亲说:“你的名字叫崔钟秀,软绵绵的,我看给你重起个名字吧。”父亲问他该起个什么名字,他说:“叫崔秀山吧;山,永远也塌不了。”王茂同志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人物,是战斗英雄;后来由于受伤双腿截肢,解放后在太行仪表厂作领导工作。从那以后,父亲就一直使用王茂同志给他起的这个名字。
1949年的春节,父亲是在太原东山的孟家井村渡过的。年饭是小米饭红萝卜菜,大家吃的津津有味。到了晚上,父亲和几个战友爬在山坡上看太原市的灯光,闪闪烁烁很是迷人。春节过后不几天,支前民工队接到了往前线送木料的命令,500多人每人扛一根木料向指定地点进发,连长田锡仁在前进带队,父亲在后边“压阵”。到了前沿阵地之后,大家就顺着挖好的交通壕走。离敌人很近,民工们都比较紧张,走的很快,但也有个别人体力差一点,落在后边,父亲就只好拔出手枪在后边催。因为一是前方急需木材,二是这样多的人一旦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在父亲的催促下,大家跟上了队,可父亲自己却和两个扛木料的民工掉了队。交通壕大大小小支支叉叉,他们三人走岔了路。当他们三人爬到山坡上时,才发现离双塔寺很近,并到了我们部队的前沿阵地。当即就被敌人发现了,炮弹一个接一个打来,三人不知所措,爬在地上不敢动。就在这时,几个守阵地的我军战士不由分说把他们连拉带拽拖到战壕里,一个年龄稍大的同志怒气冲冲地喊道“你们不要命了!你们是那一部分的?”看到父亲背着手枪,态度才缓和了一点。父亲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连忙说,这已经是前沿阵地了,对面就是敌人,非常危险,并让他们赶紧走。父亲和两位民工这才放下木料,顺着战士们所指的方向,去寻找大部队。这是第三次遇险。
第四次遇险是1949年3月的一个上午,支前民工队接到了送门板的命令,大家扛着调来的门板,沿着箭花湾的一条河沟向前线开进。在沟口遇到了我们的部队,部队首长命令支前民工队停止前进,因为前面的开阔地区被敌人的炮火封锁。民工队的目的地是前线,但部队首长考虑到几百名民工的安全,在沟口就接受了他们的门板,并开了收据,父亲便带着民工返回。在返回的路上,不知是什么原因,敌人的炮火向民工队袭来,大家迅速隐藏。炮火停后,大家整队出发,刚走不远,一排炮弹又打了过来。在前线的几个月里,父亲经历了无数次的炮击,渐渐地学会了根据炮弹飞来的鸣叫声判断爆炸点的远近。比如说,炮弹来的声音要象口哨那样,就说明比较远,一般没什么问题。如果声音有撕裂的感觉,就说明离自己很近,必须卧倒。这一排炮弹非同小可,空气象被撒开似的,爆炸的震波震的贴在地上的胸口直擅。父亲正准备爬起来时,就听到一声撕裂的鸣叫,接着就是“扑嗤”一声。父亲深知这枚炮弹一定离他非常近,爬在地上一动不动。过了一阵子,没有动静,父亲偷偷地向那边看了一眼。天哪,离他四五米远的沙地上,扎着一颗亮锃锃的迫击炮弹。因为父亲经常送弹药,这家伙他见过,半截弹头插在沙土里,后杆和尾翼露在外面,发着阴森森的光。父亲这次真的吓出了一身冷汗。慢慢爬起来,压根也没敢去再去碰它一下。多亏这枚炮弹是个哑弹,否则父亲恐怕不会在这里回忆这一切了,而我也就更不知道在哪儿了。
每每回忆到这里,父亲总会喃喃地自言自语:当年我们都是不到20岁的大娃娃。新婚燕尔,匆匆相别,我在前线送支前物资,你妈妈在后方组织支前物资。相互之间,或许曾擦肩而过,却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现在,我们也只能告诉青年人:孩子们,珍惜吧!这日子来得可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