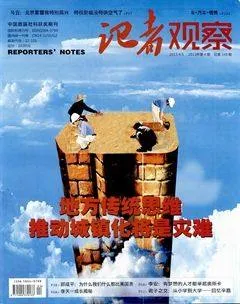李铁:地方传统思维推动城镇化将是灾难
两会热议中国城镇化前景,各方献策,有展望,有忧虑。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宁中央提出的城镇化战略是否被误读?究竟又应如何解读?农民进城无法享受公共福利,户籍制度改革该从何处破局?未来的城镇开发中又该如何保护农民利益?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为读者详解被误读的中国城镇化。
Q:记者
A:李铁
城镇化不能再强化大城市对资源的占有
Q: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界定一个概念,城镇化跟城市化是一回事吗,中国目前究竟需要哪个?
A: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问题,很多人对这事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叫城镇化,国外叫城市化,很多人提出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叫城市化。中国和国外不一样,我们现在有7.1亿城镇人口,可是我们只有658个城市,这658个城市都是高等级的,县级市、地级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还有接近两万个镇,平均人口一万多,这一万多的镇区人口在国外也就是城市,像巴西、美国、德国,三四千人口就可以设市。我们设市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这些城市都管着这些镇,大城市管着小城市。如果我们提出城市化,如果在中国这种国情下,很多市长会动用自己的权力把自己的城市做大。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大量资源都在城市里,因为它等级最高。如果你提城市化,它就更冠冕堂皇地说城市化是发展城市,只能发展这658个城市。提出城镇化两个概念,第一中国叫镇,实际上这两万个镇也是城市,所以我们叫城镇化,不能在城市发展基础上忽视镇的发展;第二在中国国情下,镇代表着一部分农村人口就地就近的转移,这是很重要的过程,过去叫乡镇企业,大量的工业企业都集中在这里,就地就近转移,也是我们重要的目标,我们既需要城市人口流向大中城市,同时也希望就地就近消纳一部分人口。城镇化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
Q:曾经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乡镇企业家”这样的说法,但是好像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所有的农村人口出去打工,都向北上广深这些大的城市尤其是向沿海城市涌,乡镇企业家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陌生了,是什么情况使城市对于资源过度集中地占有呢?
A:我们想是84年城镇体制改革,我们提出县改市,地改市。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体制就是通过县管市,地管市,是把乡镇资源拿到市里来,我们从95年开始进行改革试点政策,在全国抓了一批镇,试图通过合理的分配地、县、市、镇,这种行政关系,给镇一级更大的活力,80年代中国整个经济增长靠县以下,我们叫十分天下,县以下占70%,广东、浙江、福建、山东70%靠乡镇企业,那么乡镇企业不光创造了产值,还创造了税收,税收按道理应该给镇里的,可是我们通过包干、承包这种体制,把大量的资源全部拿到上一级政府。拿到上级政府以后,就意味着上级政府可以通过我得到的财政收入来搞我自己的地方,我也可以通过扩大我的权力来发展县级市、地级市,使县级市、地级市发展快,但是乡镇地级资源通过一系列政策把发展活力给丧失了。
政府要逐步取消农民进城所有制度障碍
Q:如今我们重提城镇化概念,尤其是强调了镇这个层级,是要再度扭转在资源分配上过度集中的趋势吗?
A:我们不要局限在镇的概念上,更重要是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问题。对城镇化的理解确实有特别大的反差,企业家理解成投资机会,政府理解为更多的项目开展或者怎么样把城镇做大,城市搞好,学者对城镇化的了解觉得这里有更多的研究内容。但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提出城镇化自始至终就一件事情,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在中国,有一个和西方国家最大的区别,很多人说推进城镇化,是不是政府强力推进?不是。中国有户籍制度,有土地制度,是把人束缚在原来的制度内,我们政府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不是把农村向城镇引进,是在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关系,逐步取消所有的制度障碍,允许农民向城镇迁移过程中,有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比如现在我们讲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是他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什么措施来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我们要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进行农民工深化的一系列改革,使他们充分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这不是推的过程。你想想大量的农民在城里,既得不到社保,也得不到保障房,买房各方面都受到种种限制,是不合理的。所以推进城镇化的概念核心意义是什么?就是把门槛打破!
改革户籍制度让流动人口享有市民福利
Q:说到户籍制度,现在不光是一个政策安排的问题,在户籍制度下的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也有非常强烈的博弈,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在纷纷讨论的京沪籍高考家长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可以看成不同群体之间博弈的典型样本。
A:你提了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们来理解城镇化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么多年,我们中国的整个户籍制度实际上把所有的公共福利限制在一个行政区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人住在城里,谁有更多的话语权,谁有更多的决策权,谁是弱势群体。肯定在城市里,特别在大城市,在最重要的城市里居住的人都是有话语权的人,既有媒体人,也有专家,也有学者,也有企业官员。他们是城市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话语权决定政策主导权。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我们提出无数次城镇化政策,可是一直难以落实,就是农民进城,几亿农民工是没有话语权的。我特别注意到在媒体,在各种大的媒体,我们的决策和研究的讨论过程中,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弱势群体,你提的大家仅仅是同情的方式,我们要关怀,要同情,但是没有人希望他们和我们站在一个空间去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这里最核心的要点就是你必须要切割我的利益才能给了他,因为城市财政是既定的,如果我给了既有的居民,这种增长会带来我原有的居民这种经营阶层的增长,既定的福利,可是我再给新增的人口一大块,那一定会动了这块蛋糕,那就会使我原有的利益增长幅度下降,或者是总体水平下降,高考就是这样。北京高考高于外地,低于外省一百多分,因为北京所有城市居民适龄的子女都可以享受到北京高考政策,甚至达到100%入学率,可是北京有800万外来人口,如果他们要把他们子女全部迁移到北京,增加了将近40%的人口系数,这个人口系数加上子女教育,等于原有的高考入学率至少下降20%。那有一部分户籍居民要承担这次改革的利益损失,当然他反对了。高考最关键是孩子命运前途的问题,这个反对,京沪两地都是非常强烈的,这就是利益的考量和利益的平衡。
Q:打破门槛究竟怎么实施,尤其遇到既得利益阻力的时候。
A:一方面要通过一个操作过程的具体的设计,同时要考虑到承受能力,更重要也符合长远发展方向。我们认为户籍改革不是一次性简单的,一次两亿全转掉。比如现在北京有800万人口,至少20是迁徙几十年,我相信新浪20%、30%甚至更多的人没有北京户口,这都是我们白领、精英还有很多企业家,还有饭店营业者,饭店包工头,还有小企业家,他们在城里住很多年,都是我们邻居,我们同事,他们为什么不能有户口,所以对这批人,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居住条件,我们可以一次性解决户口,放开就完了。他们已经是市民,为什么不能享受公共服务?
比如说就业尚不稳定,今天在东边打工,明天在西边打工,今天在这个城市打工,明天在那个城市打工,这种人可以他们的情况,逐步完善公共服务,使他们公共服务逐步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实行均等化了,我们户籍改革利益就没了,但是这是长期的过程,因为实际人口太大了。800多万一下子转户口,财政肯定解决不了,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一批可不可以,可是到现在一批都不解决。
户籍改革至少开个头,现在在全国各地近来户籍改革的时候,各地都办居住证,非常苛刻严格的条件就是积分,那么这种改革没任何意义。把过去的年龄一笔勾销,现在开始逐步计算,达到劳动模范,达到某种学历,就业年龄多长等等,最后才能办,比国外的绿卡还难,这都是不合理的政策。其实就是解决就业年限,十几年,举家迁徙,一批解决一批,大部分白领不是农民工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不仅仅有两亿多农民工,还有七千万城镇人口,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他们有话语权,所以他们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对社会是利好,是一次更好的改革开放难得的历史释放的机会。
Q:这背后不同地方政府也存在着利益博弈,中间要中央下一盘很大的棋,不同的政府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沿海发达城市更多的是人口的输入省,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城市他们是人口的输出省,让沿海的城市更多拿出他们财政收入解决收入这部分的人口利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怎么协调呢?
A:重庆全改了,沿海地区确实存在着问题,像广东2400万外来人口,都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这要改起来就麻烦了。东莞840万人口,本地户籍人口180万,有660万外来人口,全改压力很大。番禺区外来人口将近一半以上,这种情况要改,地方财政承受能力不够。我们想象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行户改的,有些人还希望回家居住,有些希望在中部地区生活成本较低的时候进行居住。第二还要解决财政转移支付的问题,我们在广东调研的时候就涉及到具体问题,比如东莞77%外来民工在民办子弟学校上学,27%的在公办学校,我们去民办学校以后,他们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政府不能拿出钱补助民办学校,政府老师为什么不到这里就业、来教学,为什么不能给这些孩子不解决义务教育?地方政府讲了,我的教育每年上交中央了。我们财政贡献比较多的省份,已经通过转移支付,我们税收交了中央以后,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给了输出省,涉及到中央是不是3b8e3b0b6b348cb3798d351e4a516f88要重新调整一下,因为你输出省的人都到这里来打工了,就白拿了义务教育经费,那是不是重新调整一下。
这里就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分摊机制,中央、省、市、县以及包括企业各都要分摊一部分,这个可能是未来改革想去计算到底怎么来解决这么大批农民工未来的市民化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们的户改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将来可能性的财政产业支付重新调整,这个是要进行深入研究的,但是前提是得要做。
宅基地确权流转是城镇化改革难点
Q:农民工在进行市民化的时候,怎么去处理他们家乡现有的那块土地,能不能在他进入城市之后,在他取得市民化的身份之后,成为他的财产的来源呢?
A:首先这个土地不应该是前置性条件,中央在这个问题很清楚,在户改政策上已经明确了农民进了城以后,地不交。这是2011年中央文件,县级市以下的农民进城地不交,意味着土地不是先决条件,意味着农民可以保有自己的土地,然后可以自由迁徙。第二怎么进行相应的土地制度改革,来解决土地的流转,宅基地流转的问题。
Q:很多人在假设说,如果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他家乡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可以某种程度上成为他自己的一种资产或者资源的话,可以帮他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您觉得家乡的那块土地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A: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土地物权,但是我觉得这个提法还不够。对于农民宅基地和承包地,这两块土地怎么进一步界定,我们现在叫集体土地所有,这里的改革动作比较大,在公有制前提下,使用权是不是可以流转。现在农地流转已经基本开始了,现在大量农民流转,在制度上没有太多的限制。至少在使用权上。可是在宅基地问题上还没有进行突破。我们看宅基地大概两块,第一块近郊区农民和远郊区农民,近郊区农民土地升值欲很高,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转户,因为转户土地所带来的利益不见了。在远郊区农民的土地没有价值,到河北,山区,土地给他,也卖不了多少钱,很多人进了城,包括现在已经成为大学生,分配到城里,在家里有一块地卖不出去,这里怎么变革,需要统筹研究的。但是我想有一个,我们至少可以认定,这个选择权在他自己,而不是通过政府来怎么做,我第一制度上是不是允许你流转,无论是宅基地还是承包地。第二流转的收益归谁,第三是不是在尊重你自愿的前提下流转还是我强迫你流转,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很多矛盾就可以解决。现在不是,流转是看重你的地,给你补偿。这块因为我们有关的流转政策没有进行颁布,所以现在都属于一种补偿低价征地来进行。农村集体土地是公有,但是和城镇用地没有平等的,原因在哪里,当你进行城镇开发的时候,必须把农村集体土地征有国有才能开发,恰恰征用过程中,是不平等的交换,这种不平等的交换意味着政府有权利来干预,甚至来强迫你进行土地的使用转化过程。这个是我们现在导致城乡矛盾,拆迁矛盾频发的很重要的原因。
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大概有几个过程。第一要进一步探讨城乡用地不可以同权,第二农民承包地或者宅基地有确定的使用权,第三流转之后,如何流转,政府如何进行干预或者通过税收等等方式,怎么通过法律和各种制度上进一步完善,恐怕是未来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目前看还没有解决,现在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提高征地的补偿标准,可以按市场价,还有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界定存在很大的争议。什么是公益性用地,比如危旧房改造是不是公益性用地?很多人不同意危旧房改造属于公益性用地,但是政府认为危旧房改造是改善整个小区的居住生活。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去讨论,进一步去研究,来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政策,这个事情我想已经为时不远了。
地方传统思维模式推动城镇化会是个灾难
Q:我们当谈到城镇化的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意味着一系列的一轮建设,在您刚才的论述当中,我们听出来是围绕着以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改造的问题。
A:最后这30年,我们看到的城镇化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城市建得越来越漂亮,城乡反差越来越大,使农民进城门槛越来越高,最后形成的结果是我们在排斥农民进城,这种环境,特别高档的城市建设的标准,使农民已经没有办法进城了,这是我们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面临三亿,四亿,现在是52.6%,六七亿人口,到了60%,8亿人口,70%是9亿多人口,这么多人口进城了,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居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总结国际上城市化规律和中国不一样,国际城市化规律是和贫民窟相伴随的过程,我们中国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在广东2400万农民,在北京居住800万外来人口,绝大部分都是城乡结合部,绝大部分住在乡镇村,住在出租屋,住在基础设施特别差的地方,它不是大面积贫民窟,但是小面积的,它也是相对城市,城中村,藏污纳垢的地方,事实上它就是这些低收入农民相对集中的地方,包括城市里的地下室。在这个过程中,理解城镇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对城里人来讲,对决策者、媒体人来讲,他们想的是如何锦上添花,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堵车,如何解决雾霾,如何解决我们的道路美化、亮化、绿化、生态问题,可是对农民,他们要求就两条,我有没有就业,稳定的就业,我的居住条件怎么改善,我基本的公共服务怎么满足,这就是对城镇化理解的不同导致的偏差。
Q:在您看来,城镇化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打破在政策上的障碍,使农民更好地以自由的姿态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如果一旦完成这样的步骤,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A: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可以计算的过程,现在两亿多农民工,如果我们想把他们长期消费行为转到城里,必须解决他们城市里稳定的、有尊严的一种市民生活。那就是说我们在城里可以享受公共服务,我可以把我的家乡,把我的孩子迁到这里来,我可以把长期消费行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对现在的城里人也只不过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村人,就是我的父辈也可能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是经过两代人转入市民,经过这么长时间转入市里,为什么他们不能。如果他们能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房子盖到北京,盖到上海,或者盖到中等城市或者中小城市或者在这里买房,两亿多,三亿、四亿农民进城以后,即使解决租房和买房的问题,会不会带动房地产需求?一定。如果他们买了房子,意味着是不是我们的住房相关的支撑品的工业幅度,消费会大幅度的增加呢?他们孩子要在城里接受教育,他们要在城里享受医疗,会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增长,也会带动工业支撑品的增长,这种消费需求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他们进城了,几亿农民进城了,集中改善城里基础设施,来解决整个居住生活条件的供给的问题,是不是也是一笔巨大的投入。这种投入他会带来我们整个国家内需的增长,这是显而易见的。
Q:正如您所说,大家谈到城镇化的时候,真的有诸多的误解,尤其是刚才所说的很多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可能把城镇化理解成新一轮的大量的投资、建设的过程,甚至也有学者说,城镇化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下一轮强劲的引擎,可以保证中国未来更长时间的高速的增长的状态。但是也有批评的声音,其实那将带来重复的无效的投资,尤其是运动式的建设可能会是灾难,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A:这里可能就存在着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地方的认识,是传统习惯性的认识,他就想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对学者来讲,城镇化就是文明水平的提高,就是锦上添花的过程,当然了,结果和我们想象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制度问题,如果我们还遵循地方的传统思维模式来推动城镇化,当然是一个灾难。前几天去了河北一个县城,县城就8.9万的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十一二万,可是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工业区30平方公里,居住区40平方公里,如此大的浪费,形成如此的城市环境,怎么可能让农民进来呢?
Q:有人住吗?
A:有人住,十几万人,十几万人,用了70平方公里,我们现在建设部规定,我们城市应该的理想化的人均占地标准是100平米,他是600多平米,这种资源耗费是巨大的。
Q:可能就是空城?
A:不是空城,基础设施压力非常大,严重浪费。按照现有的地方官员或者一些学者来理解的城市化,他可能就会走向这个方向,包括现在看到很多中等城市都是这么一个结构,这么一个格局,我们有很多省会城市,中等城市都在这么建设城市。当然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但是他并不了解中央提出这个政策,新型城镇化有两个基本要点,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转变。所谓数量型增长,关键是农民市民化这个过程要完成,进城不光就业,要定居,要解决公共服务。第二从粗放型成长向集约型转变,意味着城市发展模式,要从原来的摊大饼式形象化政绩化的工作,转向来解决老百姓生活的问题,解决人口密集提高,解决资源浪费的问题,这两个是中央提出城镇化很重要的观点。
经济学家不了解中央政策,看到了这些现实,认为所谓城镇化可能就是城市建设,真正中央提出这个东西从没有讲过城市化就是城市建设。讲到城市健康发展,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农民工稳步的市民化进程,包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生态城市,低碳城市。这是中央提出来的。
Q:可是在中国有很多情况都是这样,中央提出政策的动机总是好的,到了地方执行的层面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歪曲和误解。
A:我们现在提出要改革,要提出推进城镇化措施一系列的改革,恐怕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要解决怎么从中央到地方的贯彻落实,当然政策还没有颁布,在研究过程之中,但是它的核心内容和思想不会发生变化的,毕竟我们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是矛盾积累,城市发展出现了扭曲的过程,这些扭曲的过程需要未来政府在未来政策中需要来调整,需要改革,来扭转的。
Q:您可以想见到的去扭转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官员对于城镇化的理解。和这种建设驱动的措施有哪些?
A:那么这些措施有这么几条,可能是大家都想得到的,第一个怎么样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因为我刚才讲过的所有这些是核心的,农民工市民化。
Q:我可能没有问清楚啊,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改变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的官员在城镇化问题上的态度,让他们以更多的动力来做跟人相关的一系列工作,而遏制他们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一部分的动力?
A:首先一件事情,政策要点要清晰,指向要明确。
Q:但是可能利益不一样。
A:这个需要一系列的工作,毕竟我们过去很少对城镇化问题进行正面的阐述,大家也不知道城镇化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过去我们假定政绩观,制度设计可能迫使他向这个方向去做了,比如短期政治,短期行为,几年大拆大建,最后为这个事升官了,如果中央态度很明确了,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目标,有一系列跟进的主政策,用什么样的官,解决什么样城市发展途径模式。当然我想一定会矫正,根本的矫正是不可能的,但是矫正的目标一旦确定之后,一定会发挥作用的。比如这次八条宣布,廉政八条,春节期间就没人大吃大喝,问题要落实。
Q:比较有效的一个可能就是靠改变政绩考核的办法。
摘自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