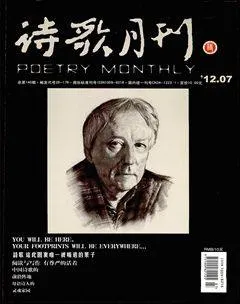中国新诗“第三浪潮”中的“女性身份”重建
诸如大家所论,这次现象的命名主要是以“网络博客”这种诗歌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及“女性”为依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两个要素始终放在一个必要充分的位置,让这两个要素来行使它们的选择自主性,让概念来自行指认适用者。而绝不能因为诗歌的传播方式经历了心灵、口头、物体、纸张、网络这几种方式和路径,就作出了“心灵时代的女性诗歌”、“口头时代的女性诗歌”、“石刻时代的女性诗歌”、“纸张时代的女性诗歌”、“网络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等等类似的以科学性、物质性为主导的概念判断,而打算适用于所有、全部和集体。诗歌命名,毕竟是一种精神创造领域内的艺术产物。尽管它有时候是以物质性依据为主来完成的,但其内部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性,物质性有时正是昭示了精神性,这种物、神的有效转换,就建立在对概念的界定上,建立在对它的适用范围和所指的不断缩小和收拢上(比如“鸳鸯蝴蝶派”),而不在于使用时空的无限放大。概念和命名的有限性,才是它的生命力和合理性所在。以上的名单列举,显然是与这一原则背道而驰的。
那么,谁才是这次现象命名必然的主体所指?纵观这些年的历程,我想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公开报刊发表时期,2.民刊发表和圈子游走时期,3.以上两种方式和网络论坛结合时期,4.纯粹的网络博客上升为必然主要的载体的时期。这四个时期,应对着不同的诗歌现象,也对应着不同的诗人群体,其中也包括女诗人。其中,第一个时期是“朦胧诗”之前,第二个时期是“第三代”,第三个时期则主要是“70后”、“80后”、“中间代”,第四个时期,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评论家们这次所谈到的“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或“新红颜写作”。关于网络媒介与诗歌的关系,在2009年10月的一篇题为《网络传播革命带来“诗场”巨变》的短文中,我曾说过:“新世纪中国诗歌10年中具有革命性的行动不是诗学观念的变革,而应该是传播方式的革新。互联网的出现,和历史上历次诗歌的传播载体的出现一样,对中国诗歌在近十年的影响可谓深远……诗歌的网络传播在这十年中大概经历了五个阶段:早期的bbs时期(1999年以前)、大量的论坛时期(2000年—2004年)、综合网站时期(2005年—2006年)、网站专栏时期(2006年—2007年)和现在的博客时期(2005年至今),而为近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显耀贡献的是论坛时期和博客时期。”而“博客时期”的一部分,是网络与诗歌的结合,发展成熟到一种“博客”环境时,引起了学术的介入和关注。这样看来,这次命名的所指群体,必然只能是以这一时期的女诗人为主,而不是要尽可能地囊前括后。这次“现象”的命名与提出的时间和动因,也刚好是与博客和诗歌的关系逐渐成熟趋于稳定的进程默契相关的。作为一个专指名词,它不是指之前的那些女诗人,更不会是之后的那些女诗人,在其产生前提和结果上,它指的都应该是“这一部分”,而不是全体。这就需要研究者准确地把“这一部分”从混淆的“全体”中剥离、凸显出来。所以考证以上评论家的那个漫长的名单,我们会发现,“这一部分”,肯定不是翟永明等以“民刊发表和圈子游走”为路径引起关注和认可的女诗人,也不可能是在安琪、路也、阿毛、娜夜等以“公开报刊发表”为路径引起关注和认可的女诗人(路也直到今天也没有在论坛上贴过一首诗歌,甚至是一个没有博客的女诗人),不是巫昂、尹丽川、宇向、扶桑、吕约等在“70后”诗歌运动中以“民刊发表和圈子游走和网络论坛相结合”为路径的于2000至2001年间引起关注和认可的第一轮70后女诗人,也不可能是李小洛、苏浅、叶丽隽(风事)、唐果等在“70后”诗歌运动中以“公开报刊发表和网络论坛相结合”为路径的2003至2004年间引起关注和认可的第二轮“70后”女诗人,不是白玛这样的十来岁就在《他们》和《诗刊》上大量发表作品,直到现在也一直游离于现场之外迪金森式的女诗人,作为“群体”的主体,也不可能是零落香、蓝冰丫头、原筱菲、高璨等这些正在切入写作现场“90后”女诗人。“这一部分”,实乃指的是一部分有着先期的网络论坛经历,但直到博客出现并与诗歌的关系逐渐成熟之后,才引起大家集中关注的“70后”女诗人和为数不多的几个“80后”女诗人。她们参与网络的时间大多在2005年以后,在2007年之后慢慢进入个人写作的集中时期,而在2009年之后渐渐成为一种集体现象。所以说,作为一个能赋予历史意义和研究可能的专指性诗学命名,不论是“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的说辞,还是“新红颜写作”的提法,其所指主体实质上就是在一个整体的“70后”诗歌运动中,在“第三轮”出场的“70后”女诗人。在这一点上,这次命名,和早些年的“中间代”命名,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其实是对一代人在写作和人数上一次局部补充。
毋庸置疑,被按照“事实”界定之后的“新红颜写作” 或“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或者干脆往明白了说“在第三轮引起反响和关注的70后女诗人”和她们的作品,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早在2007年,作为一个读者和关注者,我就开始在我建立的一个“汉诗博客年选”(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hanshibokenianxuan)上,大量收集和选载她们的诗作。她们不但是在稍后几年再一次补充了“70后”女性诗歌和“70后”诗歌运动,而且也呈现出了自身的独特的美学气象、思想现象以及关于诗歌艺术本身的认识和结论。笼统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相对于之前的女性诗歌写作,她们重新恢复和张扬了鲜明的女性和母性身份,2.重新认识了精神的古典、传统和永恒,并针对自身,发出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呼唤,3.搁置了“立场”、“路线”等写作内部的问题,写作更加自由,4.自觉褪除了“社会身份”和“地理身份”的影响,将笔触直接指向了个体内心中最为纯粹的诗意生活,5.进入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创造,显示了高超的语言能力,6.人数众多(起码也有10万人以上,已经写得比较优秀的也要有100人之多),作品量大(每天至少有10万首上传博客),已经成为当下女性诗歌创作生产的主要群体。
霍俊明在《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中论述:“可以肯定地说,面对着当下女性诗人在博客上的无比丰富甚至繁杂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女性诗歌的写作视阈已经相当宽远,面对她们更具内力也更为繁复、精深、个性的诗歌,当年的诗歌关键词,如镜子、身体、黑色意识、房间、手指、一个人的战争、自白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研究者予以调整和重新审视,这些词语已经不能完全准确概括当下的个人博客时代,女性诗歌新的质素和征候。虽然面对当下的女性博客诗歌写作,我们仍然难以避开身体叙事和欲望诗学。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下的个人博客语境下,更多的女性诗人关于身体的诗歌叙事,显然并没有像当年的伊蕾、翟永明和后来的尹丽川和巫昂那样强烈、集中地带有雅罗米尔的气息,而是将身体更多地还原为个体生存权利,身体、灵魂和那些卑微的事物一样,只是诗人面对世界、面对自我的一个言说的手段而已。”这两段话,起码道出了在“第三轮”出场的这些“70后”女诗人作品中的两个关键点,即现代性在社会现实中的不断深入,让她们重新意识到了自身性别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在经过了前一阵子的拒认、模糊之后,她们不是宿命而是勇敢地再一次亮出了自己的“子宫”和“乳房”这些不再以器官示人而是以象征和寓意昭告的足以告诉别人我是女人的显要特性。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女性的爱、女性的情怀、女性的情调、女性的眼光、女性的脾气、自恋、自审、躁动与娇气,有一部分也从而上升到了一种母性的高度。与前两轮的“70后”女诗人甚至是更早一些的女诗人作品中的“去女性”、“中性化”相比,这种转变的原因我想还有两个隐蔽的原因,一是她们与之前的那些女诗人相比,她们都没有与诗歌有关的复杂直接的生活经历,她们与诗歌发生关系,大多是通过网络,这种缺乏真实的“圈子游走”和“民刊集会”的简单的“诗歌生活”,减少了她们要被男性诗人同化,要作为一个“女知识分子”。在诗歌作品中针对历史、时代、民族、世界等公共话题发言的可能和欲望,但同时却保存、培养了她们自身的女性意识;虽然眼下其中有一些女诗人已经开始“游走”,但这只是近来的事情,是在她们写下大量的前期作品之后。二是家庭生活和年龄的原因。与那些第一轮出道的“70后”少女、第二轮出道的“70后”少妇相比,这一轮出线的大多数“70后”女诗人写出成熟作品时,都已是三十多岁年近中年,她们的身体已不像早期的那些“70后”女诗人在当年的饱涨、充水,而是相反,渐渐出现了缩水和女性资源的物质退化,在这样的一个临界点上,与前面的她们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女知识分子”并极力行使“知识分子”的权利和责任一样,她们已不可能再主动地去“挥霍身体”,写那些“挥霍身体”的诗,恰恰相反,她们已经在此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人,一个唯一而不可更替的物质特性或精神寄予之所,正在变得大不如从前,她们已经真实客观地接受并认识到了“女性”这一称呼的价值和意义,她们只有通过对于女性情感和精神的张扬才能弥补这种“渐渐地消失”。她们的这种心理结果,其实也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集体成长的一个结果。
与此同时,在这一年龄段,她们的家庭生活也处于一个关系较为稳定的状态,而不是早期那些“70后”女诗人在青春中所面临的漂泊、游移和关于物质的焦虑,这也让她们以女性的身份开始不断渴求一种时代共享、历史共享的超验的女性“幸福感”,并以此来认识和塑造一个“红颜”的自我,而不再像她们之前的那些“70后”女诗人一样因为并依靠一种时代、历史的焦虑感来写诗,她们的作品开始尽可能地立足于“女性”而单纯地表达一个女性视角上的情感和灵魂诉求。与之前的那些要通过表达自我来认识历史、时代、集体的女诗人相比,她们认识历史、身世、时代,是为了认识和安慰自我的女性身份。正如虞朵(横行胭脂)在她的一首题为《玛蒂尔德》的诗歌中所言:“真的,下辈子别嫁穷丈夫 / 哪怕自个过一辈子 / 打死也别嫁穷丈夫 / 在结婚之前 / 记得翻翻他的口袋 / 亲爱的玛蒂尔德 / 我见不得女人受苦 / 流出钻石一样宝贵的眼泪”。这个莫泊桑精心制造的故事,由于出发点和审美原则变得不一样,当被再一次使用时,其意义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在另一首诗里,徐颖将“女性”推向“母性”时,则淋漓尽致地亮明了这一部分女诗人对于她们女性身份的毫不回避、坚决执行和无限放大:“我要生一个孩子 / 叫他格瓦拉 / 我要让他的父亲事先熟悉草药 / 熟悉暴力、不公和救赎 / 要以爱情的名义 / 是复活,而不是纪念地 / 为我种下格瓦拉”。而这些“新的”“70后”女诗人之所以要在她们的作品中,重新恢复和张扬她们鲜明的女性和母性身份,另一个关键原因,就是霍俊明所表述的那种诗歌自身的艺术流变。不论这些女诗人们,是否在主观上认识到了一种写作“规避”的必要,是否对于前期的女性诗歌尤其是和她们同代的女诗人的创作有一个高度的理性判断,她们都会因为对一些前期女诗人作品的熟悉,而在写作的潜意识里,实现尽可能的避让,而另辟蹊径。这是她们作为创作主体的本能反应。而另一方面,诗歌艺术的发展也在不断地要求自身针对于那些早些时候的“女知识分子”和“祛女性化”写作发生再一次的变化。这两个诗歌本身因素的潜因,直接导致了她们走向了“复本、复古”之路,集体重新回到了“女性”这一出发点上。而时代,也当然给这次“复本归位”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有利的条件。
这些“第三轮”出场的“70后”女诗人是自动远离了“女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中性化”身份的变异的,那么,她们的写作,离开、抛弃了这些男性化的公共话题,将会到哪里去?这关系到“何为现代性之下的中国当下女性”的思考,关系到她们对自身的认识。考证她们大量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基本是在精神要求上的走向了古典,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上接近了传统,在审美上看重了美的永恒的一面,并由此而发出了对古老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呼唤。而这些女诗人之所以这样选择,有诗歌的艺术性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她们的精神危机和身份危机所指示。这种选择,恰恰证实了她们一旦回归到“女性”,时代的精神供给和审美输出所带给她们的心灵落差,从而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时代已经无法提供一个“原本”意味上的女性的精神所需。她们之所以痴迷于古典和传统,其实是对于时代的精神供给的反驳,她们只能去集体建造一个虚拟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完成一个“原本”女性的各种情感、精神活动。所以说,她们回归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时间追溯中的古典和传统,而是一个虚拟的集中了所有可能的一种精神乌托邦。在这其中,她们的生育是虚拟的:“生一个孩子就叫格瓦拉”(徐颖);她们的“幸福感”是虚拟的:“我和敌人共同种完庄稼 / 然后趁空闲打仗 / 凭战争结果来瓜分果实”(虞朵:《幸福》)。她们的英雄主义是虚拟的:“春夜,草木发情。/ 天朝上国,我记得是有星星的 / 有颗星星,打碎我房间的一扇玻璃 / 之后我披了白袍,提起刀,飞身而出”(金铃子:《星期二》)。在这些女诗人的诗里,她们之所以有时候又化身成一种男性化的影子,实在是因为她们的女性意识已经万分强烈,她们需要制造一个英雄的、理想的、古典的、具有永恒之美的影子来对应、满足这种强烈。李清荷近年来写下的系列长诗:《写给项羽的11封情书》、《遗失在大唐的咏叹》、《一个人的长恨歌》、《太平公主》、《武则天》、《上官婉儿》、《小乔的战争》等。在这一点上,这些女诗人似乎和先期的那些女诗人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先前的那些女诗人是虚拟了自身,而她们则是虚拟了他人,而且她们没有直接对问题说话,而是以一种转身,把问题当做了制造乌托邦的推动机。所以,也就是霍俊明所说的:“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使记忆的火光、生命的悲欣、时间的无常、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现代人在城市化背景下的无根的漂泊,都在暗夜般的背景中透出白雪般的冷冷反光。”
由于这部分女诗人的写作是直接奔向“诗意”,而非“诗歌的”,也由于在她们之前的那些女诗人已经在诗歌写作的艺术性上做了大量的探索,为她们积累了丰富的可鉴经验,而她们也从未参加过任何的诗歌社团、圈子,这些第三轮出场的“70后”女诗人,一出场就不大讲究被先前的一些女诗人极为看重的“立场”、“路线”等写作内部的问题,而是随心所欲,率性而为,甚至不讲章法,在创造那个自我的“女性世界”和解决其间的诸种问题上,实现了与诗歌最自由的结合。她们不仅自觉地褪除了“社会身份”和“地理身份”的影响,还依照这种关系的自由,进入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创造,显示了高超的语言能力,从而借助语言将笔触直接指向了个体内心深处,那些最为纯粹饱含心灵审美的诗意生活。 “阅读博客上的女性诗歌,我们会发现起码有半数以上的女性诗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气味的青春期的偏执性,而且是以包容、省察的姿态,重新打开了女性诗歌崭新的审美视阈和情感空间,在经验、语言和技艺的多重维度上,扩展了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的空间视阈”(霍俊明:《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这部分“70后”女诗人在几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并最终作为一种集体现象。她们把诗歌作为了重建女性内心世界和永恒性审美的一种方式和路径,也因此赋予了诗歌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巨大自由,正如她们自己所言:“阿拉说起木槽,没有什么含义 / 就像阿拉说水盆、枯井、高架桥 / 说起它,先别提到耶稣降生 / 好好感受粗糙美。也许将再也看不到 / 这东西如今是少了(余小蛮:《木槽》)。她们甚至把诗歌写成了自由不羁的“说说胡话”:“多久了 / 金属氧化,木头生出蘑菇 / 糜烂时代 / 你有完整的器官和自己叫劲儿”(粉灰:《说说胡话》)。甚至是关于“北极”的一场“白日梦”:“我无数次在温带地区 / 想象美丽的北极光 / 那光里确实有一只珍贵的北极熊 // 大口大口吃雪 / 全身长满雪白的皮毛 / 因为眼睛黑而亮”(张洱洱:《我的北极熊》)。而读梅林的作品,首先看到就是灵魂的高贵和尊严,已经寻找不到在另外一些诗人那里所强调的“社会、地理身份”:“如果不能在夜里写下一首完整的诗 / 就写一个完整的句子 / 如果不能写下一个完整的句子 / 就写一个完整的动词”(梅林:《如果不能在夜里写下一首完整的诗》)。更难以让人相信的是,在她们之间,竟然也诞生了《隐身人的小剧场》这样的综合、囊括众多诗歌实验的长篇诗剧。这部巨制的作者田暖几乎为她们的“女性实验”,提供了任何的戏剧可能。这些“70后”女诗人以原生、蓬勃的创作激情和干净、纤细的诗歌能力,源源不断地向她们的博客世界输送了大量的新作品。在作品中,她们处处强调了情感至上、灵魂公平和精神自由,并把时代的变化自觉地融入了自身的转变,以一种女性精神复原的方式,与网络博客一起,深刻地呈现了她们的美学趣味、诗学观念和艺术魅力,以一种网络的野地生长方式,再一次验证了中国诗歌传统中那个真理:诗在野。近年来,也正是她们在第一、二轮的“70后”女诗人进入集体“休渔期”后,延续、丰富并提升了“70后”女性诗歌的版图。
但正如评论家所说的,正是由于精神和网络的双重自由,在与这一部分“70后”女诗人有关的各种现象中也出现了一些与诗歌写作无关的“偏移”:“在女性诗歌的博客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女诗人的精彩纷呈甚至是诱人的工作照、生活照和闺房照……以及更为吸引受众的写真照,甚至不无性感、暴露的图片随心所欲且更新频率极高地贴在个人的博客上”(霍俊明:《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很多女诗人依赖于靠勤奋(频繁更新博客)与高见面率(不断贴最新照片)获得声誉。这种图文互动的发表方式,似乎更适合于博客时代的大众阅读。”(刘波:《网络时代的多元审美》)。这些陈述无疑是事实。虽然我个人把这种现象视作是这些“70后”女诗人中的部分和个别行为,是伴随着诗歌写作和“女性”复原的一种辅助性行为,是副产品,也难免要联想到诗人的品性。而比此类现象更为有害的是“博客游走”,或者称为是对观众和读者的主动“招徕”。这种有别于以往的“空间游走”的网络游走,得益于网络技术,它让诗人们的“游走”既省钱又快速,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过去的诗人在几年间才能完成的事情,进而引来大量的观众,这是一种交流的方式,但同时也显示了作者的某种心态,而这种心态必然会影响到诗人的创作。还是在2009年10月的那篇《网络传播革命带来“诗场”巨变》的短文中,我曾说到网络传播方式的出现,对中国诗歌最大的影响是让一个异化多年的中国诗歌创作、呈现、传播现场转向平常……《诗刊》等主要刊物的“场所性”和权威性被大大削弱,并被新诗人们质疑,以早期的游走、民刊以及学团、同仁为号召力、凝聚力的诗歌“群体”和“流派(实际上是圈子)”现象已渐渐退出,更多的新诗人以“个人”出现于博客现场。这是中国诗歌参与这次“网络革命”所获得的最大“利益”,所产生的效应和影响是最大也是最积极和最深远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媒介的出现,应该是中国诗歌界能源、资源和权力的再分配,也是最民主的一次分配。核心是以读者和论者构成的评价体制的变更……这已慢慢改写中国诗歌史的形成和制造机制,让考察的主要精力只针对“个人”和“作品”这一最为科学、最为真实、最为必要的诗歌理论活动即将成为可能……互联网,看起来是一项科学技术,但实质上它和诗歌一样,是人和人之间,一种具有未来意义的关系。可见,诗人和诗歌都最终放弃了“论坛”而选择了“博客”,还是因为它的安静和个人性,而不是热闹和群体。“博客”,可能最终还是为那些像萨福和迪金森那样安静于外的女诗人准备的,它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让诗人们能在自己的一处安静地写作,在写出忠于自己的内心的诗篇并得以保存之后,被路过的读者读到。而眼下,这部分“70后”女诗人中的一部分人俨然已误解、滥用了“科学与技术”的这个美好赠予。
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诗启蒙称作“第一个时期”,朦胧诗、第三代、70后、中间代的探索、拓展是“第二个时期”,那么,由网络所引起的诗歌体制的改变以及由于博客所带来的发表传播方式的改变,正和更大的历史、时代因素一起引发中国新诗的“第三浪潮”,作为一个开始,她们到底能为这“第三浪潮”贡献什么,也是后话。而我最后想说的是,这种现象,不仅是诗歌的,也是小说的,也是散文和其他文学门类的,而这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