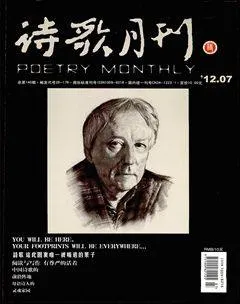诗歌的理想读者在哪里?
不存在不需要读者的诗歌,诗歌需要找到它的理想读者。我在二十六年前,也就是1986年,命名了自己的盲目主义,但是从未着急阐释这一盲目主义的具体内涵。我于1993年去国,至今也有十九年,对诗歌的理想读者早就另有主张,耐心多于盼望。
诗歌的理想读者在哪里?在我看来,不要幻想读者先于诗人存在。读者是诗人创造出来的,正如诗人本身是时间创造的作品一样。 这是一场路遥知马力的长期角逐,坚持不懈的对立决斗。但决斗的结果不是如一般想象的那样,你死我活,而是各退一步,彼此重新打量,相互尊重,欣赏。正如或多或少根据我个人的经历而定义的异性爱情那样,男人欣赏女人全方位的美丽智慧,女人欣赏男人全方位的魅力才华。
我所写作的是人的诗歌,是自由跨越的诗歌。我的理想读者并不一定受限于汉语本身的听众。这是因为,虽然我的起源和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从我有限的个体生命中衍生的与天下世人同呼吸共患难的梦幻则无穷无尽,不可能不超越溢出语言的人为边界。正因为如此, 不可画地为牢,限定某种自说自话、好似自尊其实狭隘的当代汉语诗歌。什么是当代汉语诗歌?那种有能力重新定义乃至打破语言和存在界限、重新创造其读者以及地平线的诗歌就是,那种能够直取人心的诗歌就是。
我是一个有着永恒时差的诗人,因为自青年时期开始便不断跨越边界,所以对自身的过去和未来都充满了好奇和错位感。今天在这里接受柔刚诗歌奖,我把这视为率性不羁的浪子终于开始回头,曾经博大深厚的母语也终于开始拥抱承认浪子的贡献的一个停顿时刻,一个简单但意味深长的时刻。当代汉语诗歌需要不断地增强自我更新造血的能力,更多地接纳这种不尽在言中的点点滴滴的微妙成熟,这种太阳底下谦逊的信心十足。对世间万事并不全知,更不全能,然而从容不迫。万物俱备,何惧之有?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盲目主义者视而不见那存在于广大时空中背景各异的读者的质询眼光,仅仅是友好地微微一笑,表示欣赏的时刻。
谢谢大家!
2012年5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