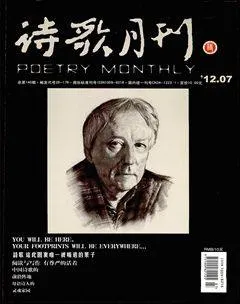童话的消逝与找寻(诗评)
1980年代兴起的新生代诗歌正在努力逃离着政治牢笼的束缚,开始寻找人的“存在”,转向对主体意识的关注,即,关注现代人的心灵困境:对于生活意义的困顿,对于他人感情的冷漠,对于自我价值的迷茫,对于原有价值判断的质疑……他们多选取平凡人生活中散落的点滴来展现平凡个体,这种对于生活细节的关注和淡淡哀愁的情感格调,再加上非线性形态的意象组合形式,使得新生代诗歌越来越成为一种脱离政治生活的小众化文学品读。但事实上,这种新的诗歌形态并非完全去除了政治因素,他们只是把大的社会政治化藏在单个主体的生活思索当中。诗歌正在由“男性化”的指点江山,针砭社会职责的正统价值观向温婉细腻,关注个人生存发展困境的“女性化”视角转变。女性作家此时登上时代舞台是相当自然和谐的,她们的突出表现也让长久寂寞的诗坛刮目相看,夏春花的诗歌无疑是体现这些的一个非常好的例证。
一、童话世界的消逝
以孩子的眼光来看,世界永远是童话: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生动鲜活的,母亲与孩子之间永远是温暖的,爱人间的喃喃细语是永远都听不厌的美妙音符……夏春花从不曾撇下这种童贞,她心中的生活应当像是被紧攥在手中的糖果——处处都是甜的。基于这种想象,她设计出多重的童话意象,充满在长长短短的诗行中,让每一次语言的应用都飘洒着蜜糖的红色芳香和纯真的蓝色海浪。“可以用木耳代替耳朵去听电话吗/如果小气泡变成了大气球会怎样/为什么不生个红色妹妹代替蓝色超人/问题之多,并不影响生活之美好”(《狐之疑》)。好像童话的王国永远不会被繁琐的问题打败。
但现实的强大破坏性让童话王国摇摇欲坠。诗人也毕竟早已不是无知的孩童,作为细腻的女人和敏锐的诗人,这种贪恋纯洁之心不是让她无忧的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而是让她对丑极度的敏感:自然在日渐枯萎,母子间有着永远无法跨越的代沟,爱人间永远存在不能解开的绯闻……诗人知道所谓的童话只不过是自己在梦中的一厢情愿罢了。梦醒之后压力和冲突一直都在,个体心中的苦与痛也一刻都不得减轻:在途中/她吃下六颗糖果:/“瞧,生活是甜的。”/它可以医治深入人心的苦,与痛/这只是暂时的/在船底,/在车上,/在山中/巨石如鹰,/盘旋在头顶/他们一刻不曾放松紧握的拳头(《梦游症患者》)。但她是多么想重建起那个童话的国度,她同样也相信只要那个美的国度重新建立就能医治现代人的焦虑:“它也握有甜美的糖果/转身离去时,有那么一瞬间/她想剥下糖衣,把所有的甜/一一赠予正在身边的旅人”。(《梦游症患者》)
二、在混沌中的迷失与找寻
但事实是,童话世界坍塌后,没有谁能建造起一个美丽新世界,断壁残垣形成的“荒原”表现在后现代艺术家这里就是解构意义和结构的荒诞。极富代表性的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解构下的意义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与结构对视觉的挑战相辅相成,展现出更大的骇人听闻。
《大风歌》中意义的混沌在短短的八行诗句中非常明显,作者采用象征隐喻法,打破了传统上真实描写和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使抒情角度转移,让象征从表面看上去毫无联系,也无所指,但深层却有无穷的意蕴。超现实的意象,在被认为是不存在的同时又让人感到真实,其秘密就在于这些意象中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打开人们生命的真实记忆中封尘已久的潘多拉之盒的钥匙,强烈的记忆同时喷发而出,形式的凌乱就是必然的。夏春花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利用意象营造出混乱的意义世界场景。这些凌乱甚至是带有点荒诞性的:酒鬼打翻了构成自身世界另一元的酒瓶;奴隶爱上了最为压迫他们的国家……这个世界的事物进入了镜子里面,映照出南北颠倒的两极。再加上完全打破逻辑结构的句义组合以营造跳跃的语言节奏,打破人们原以为正确的价值认同。
外在世界的混乱是由人类自我心灵的迷失造成的,寻找自我是重建家园的必然途径。朦胧诗人找到的“自我”实质上是“人民”的代言,那时人们为了国家的崇高也是充实与快乐的,但那样的自我毕竟太过高大,太过单一,现代人更执著于彰显个性,信守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