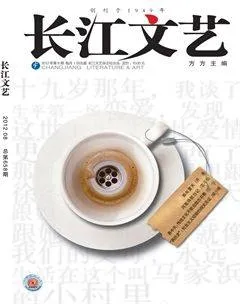镜中蝴蝶缓缓飞
作家王旭烽说她创作小说《南方有嘉木》时,对虚构的主角之一“杭九斋”这个人物形象难以把握。一天,偶尔在报纸上读到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写的一则掌故,她心中豁然开朗。郑逸梅那篇掌故写的是鸳鸯蝴蝶派旗手陈蝶仙,准确地说,是转述了陈定山的一段回忆文字。
“……他有颀长的身材,戴着金丝边近视眼镜,穿熟罗的长衫,常常喜欢加上一件一字襟马甲,手上拿着一把洒金画牡丹的团扇。”(陈定山:《我的父亲天虚我生》)王旭烽说她看到这段文字后,感觉“一位正向新时代转型的旧时代文人,就此在纸上栩栩如生地立了起来,做了我小说中的血肉载体。”王旭烽心中的陈蝶仙“几近半仙,潇洒是不用说的,而且书生不穷酸,开了现代文人下海的先河,挣钱去了,还因为实业救国,成了五四时期的民族工业代表人物”。即便实业之花在天南海北到处开放,陈蝶仙仍没有忘了风花雪月琴棋书画。
本篇将要讲述的人物,就是这个陈蝶仙。
陈蝶仙生前十分喜爱玻璃镜。他曾置一“镜庄”,房屋和长廊上安放各式各样的镜子,一旦有人走进去,从各个侧面投映出不同的影像,似真似幻,扑朔迷离。——那真是个梦幻般的世界!陈蝶仙自喻是庄周梦蝶中的蝴蝶,纵观他的一生,镜中那只蝴蝶仿佛活动起来,在缓缓地飞。
繁华一梦,转眼皆成追忆
1879年7月22日,杭州西湖畔陈氏大家族新添了一名成员。这个人原名寿篙,字昆叔,后改名栩,号蝶仙,别署惜红生、天虚我生、太常仙蝶、超然、国货之隐者、樱川三郎、大桥式羽等。他的叔父是位官员,父亲陈福元,字月湖,是江南名医,略通星相占卜,娶妻王氏,无生育,续纳妾戴氏,生四子四女,陈蝶仙在四子中排行老三。
陈蝶仙出生的年代,中国旧式大家族的景观还随处可见。他的叔父有一子二女,加上家族里其他分支的堂姐妹来访及长住,如果算上男女仆佣在内,陈家的常住人口多达六七十人。虽然难和《红楼梦》中的繁华场景媲美,仍不失为华丽之家。陈家家园旧址位于杭州紫阳山麓太庙巷,这里相传是南宋■胄南园的一角,花木茂盛,山石玲珑,尤为名贵的是院子里那株数人合抱的桫椤树,南宋时栽种的一棵小树苗生长至今。树荫数亩,其下为惜红轩,玻璃三面,绿树绕池,轩外为箭道,墙上挂着几张弓……不远处是公子们读书的红楼,彩绘的墙壁上挂了几只鸟笼,鸟儿啾啾叫着,树林深处隐约传来弹古筝的乐声。
陈蝶仙7岁那年,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先是当官的叔父病逝,陈家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撑。祸不单行,父亲陈福元不久也病逝,在中国旧式大家族中,男人是天,现在天塌了,陈家的华丽大厦即将倾覆。7岁的陈蝶仙并不清楚叔父和父亲的死对陈家来说意味着灾难性的打击,他伤心地哭了一会,由两个女佣人伺候着去读书。
嫡母王氏出身于诗书人家,喜欢弹词和明清小品,她常给小蝶仙诵读《西厢记》、《再生缘》片段,加上私塾先生陈颂诗细心引导,陈蝶仙对小说、诗词和音律产生了浓厚兴趣。14岁时,他将习作刊印成册,题名《惜红精舍诗》,年岁稍长,又辑成《一粟园丛书》。据他自撰《天虚我生传》云:“生为月湖公第三子,钱塘优附贡生,两荐不第。而科举废,遂以劳工终其身。”这里说得很明白,他曾先后两次参加科举考试,未被录取,17岁出门远行,先是在海关某专员名下当助手,继而在浙江德清一带做小生意,仰人鼻息,在他人手下讨生活。
甲午海战惨败后的次年,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城发动“公车上书”,呼吁变法。当时陈蝶仙正在杭州,一边做小本生意,XXCb74QyKHDwAUCvQp5F+bEN5KtbD9+k78xqHIQbht4=一边与文友诗词唱和,时有习作《桃花梦传奇》和《潇湘雨弹词》,雏莺新试,啼声嘹亮,已在杭州城小有名气,与何公旦、华痴石并称为“西泠三家”。
西风渐进,旧式书生也不甘落后,有一天,蝶仙与好友何公旦、华痴石聚首商议,准备盘下一家快要关门倒闭的报纸。旧时办报,很多人只是玩票。那时候出版界相当自由,政府既未实行新闻检查,也不必向租界当局呈请登记,说出版就出版,玩腻了,兴头过了,随时可以关门大吉。公子哥逞一时高兴,花上几百块钱,骂骂人,出出风头,登点诗词小品,也是桩有趣的雅事。何况“西泠三家”另有想法,他们选择办报,既是为国家振兴鼓与呼,又可尝试走实业救国之路,议题一拍即合。1895年,新盘下的报纸改名为《大观报》,正式在杭州清和坊创刊,17岁的陈蝶仙担任主编。
然而青春年少的浪漫抒情,经不住几番人生风雨的摧残。《大观报》因发表反对义和团的文章而被禁,他们接手了另一家报纸,又是同样的命运。初涉商海,流年不利,陈蝶仙意兴阑珊,有些心灰意冷。不久他害了一场大病,回紫阳山麓老家疗养。眼前风景依旧,却有物是人非之感慨。
这一年是1998年,时光驶到了20世纪的大门口,陈蝶仙20岁。
此时的陈蝶仙,已经从一名翩翩少年成长为富才学有担当的成熟男子。前一年他已完婚,妻子名叫朱恕,通诗词歌赋,擅理家政,对丈夫也百依百顺,按说是打着灯笼也难寻的贤内助,遗憾的是这桩婚姻由嫡母王氏拍板而定,陈蝶仙先前有两段感情纠缠于心,成为他与朱恕之间难以弥合的小小伤痛——这将在后边的章节中细说。
陈蝶仙养病期间,每天踏着石径在树林中散步:风景如画,片片红枫叶飘落,依依难舍地在空中旋转,仿佛在留恋什么。陈蝶仙被浓浓的怀旧情绪包围着,他想起了昔日繁华的大家族,想起了叔父、父亲病逝后的破败衰相,各房闹分家,变卖财产,签定协议……一幕幕闹哄哄的场景涌现到眼前。
这年秋天,陈蝶仙着手写长篇小说《泪珠缘》,一经在他自办的《大观报》上连载,便轰动了上海文坛。据作者自述:“这部书,是作者二十岁时候,在病中做着消遣的。从头到尾不上一个月工夫,所以里面的情节,也叙不到十年。”夫人朱恕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陈蝶仙写作时蛰居家中,不理一切,像是一尊坐佛。每当写作痛苦至极,陈蝶仙就常以如来佛受难故事来化解,笑曰:“如此则觉我身所受,总不如如来之难忍。”
《泪珠缘》摹仿《红楼梦》,是一位年方20岁的青年作家对文学前辈曹雪芹的致敬之作。好友金振铎作过统计:《红楼梦》中男子232人,女子189人,共计421人,《泪珠缘》乃有523人,“又复时时照眼,绝不冷落,亦大能手。”
范伯群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对《泪珠缘》曾作评价:“穿越了100多年小说史的长河,继承《红楼梦》的人情传统,竖起清末民初言情之纛的是陈蝶仙的长篇小说《泪珠缘》。” 范伯群说《泪珠缘》是陈蝶仙在“养病中的排遣寂寞之笔,当然会在小苦而微甜中温情如水”。又说:“天虚我生深得《红楼》技巧之三昧,也有从容调度大场面、驾驭宏大叙事网络的能力;从突出作品主题而作不同侧面的巧妙设置,直到对故事起承转合的轻松调遣,皆有上好表现;从对几百人物的出场、退场的自然安排,可以看出作家心中具有运筹帷幄的统领腕力。总之,对天虚我生承继《红楼》精华来说,他学的是大家风范和胸襟见识,学的是拥有驾驭全局的大家手笔。”
陈蝶仙写这本书时毕竟还只有20岁,无论是人生体味还是对社会的洞察力,都难以企及曹雪芹那样的高度,他承认自己所写的也不过是“儿女痴情,家常闲话”。十多年后,陈蝶仙续写《泪珠缘》第64回至96回,在《自跋》中坦诚道出了自己的心情:“金圣叹说的好,文字要立时捉住,方是本色。那过去和将来的,又是别样一种文字。我这《泪珠缘》便是当时捉住的文字。倘使现在再做一部《泪珠缘》,不要说字句情节另是不同,便是依样葫芦的画了出来,也只算得别样一种文字。”
小儿女的爱情
说说陈蝶仙完婚前的两次12bcc16f41f2b2b14575ba2d2a3a74f11ab1fd6ff128780e15e2fcf0f2fd62e4爱情萌芽。
第一次是他与苏州表妹顾影怜的爱情。顾影怜生于苏州怡园,是个才女,当时在江南小负诗名。可是她从小父母双亡,成为孤儿,寄宿在杭州紫阳山麓太庙巷的陈家(陈蝶仙嫡母王氏是顾影怜的姨奶奶)。如此飘零的身世,让人怜爱,她也和《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身世十分相似。而太庙巷陈氏大家族里的“宝玉”,正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多情种子陈蝶仙,一双小儿女的爱情,在这个温柔乡里悄然生长。
这是一场注定了没有结局的爱情。至于原因,陈蝶仙妻子朱恕在当时《女子世界》撰写的一则诗话中曾隐约透露过:顾影怜比陈蝶仙大三岁,而族谱辈分上又小一辈。这种关系,在封建大家族中是不可能成为夫妻的。
多愁善感的顾影怜,对陈府中小她三岁又大她一辈的男儿陈蝶仙有着浓郁的好感和依恋。顾影怜的诗集题名为《小桃花馆诗词集》,就是以她在杭州陈家居留时的住处为集名。这个喜爱吟诗弹琴的弱女子,身世与林黛玉相同,结局也与林黛玉相同:因为不能嫁给陈蝶仙,“卒至抑郁而死”(朱恕语)。这场精神上的恋爱,竟是以坟墓划了个圆圆的句号。
在陈蝶仙最初的两部作品《桃花梦》、《泪珠缘》中,顾影怜都化身为婉香出场成为重要女主角。在陈后来的自传体小说《黄金崇》里,顾影怜更是以本名出现,她的诗作迭次被搬入小说中。顺便提一句,陈蝶仙的写作始终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自娱自乐,自得其乐,是他所有写作的初衷。他的妻子朱恕、好友华痴石与何颂花、另一个早期恋爱对象筝楼,都曾以本名或者化名进入到他的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而且这些人往往又是他小说的第一批读者。在《黄金崇》中陈蝶仙不无得意地提到:他的小说每完成一段,妻子朱恕、情人筝楼、好友华痴石与何颂花就争相先睹为快。
另一个恋爱对象筝楼,是陈蝶仙一生的伤心和痛。1886年,陈蝶仙第一次见到筝楼,当时蝶仙8岁,筝楼11岁。筝楼是陈家邻居,来到陈家的家塾里借读,与蝶仙的一个表妹同桌,一段青梅竹马的情缘由此生发。两年后,正当陈蝶仙心中的爱情火焰熊熊燃烧时,筝楼却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陈蝶仙伤心欲绝,整天像掉了魂似的在家园中四处游走,他无数次揣摩筝楼消失的原因,全都找不到答案。直到1894年筝楼重新回到陈府,隔老远两人一眼就看见了对方——那年陈蝶仙16岁,筝楼18岁,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当时的窘境让双方都感到尴尬。他们伫立原地不动,像是木偶戏里的两个角色,一个脸上写满了娇羞,另一个想上前打招呼,然而欲言又止。事后陈蝶仙写了一封信,说通表妹转交给筝楼,两人在后花园中约会,交换了礼物。可是陈蝶仙诧异地发现,眼前彬彬有礼的筝楼和他记忆中活泼开朗的筝楼已经判若两人了,她坚持称陈蝶仙为弟弟,尽可能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什么样的变故使筝楼变得矜持疏远?
之后的几年,陈蝶仙与筝楼一直断断续续保持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他们似曾有爱,却又常常形同陌路人;若说他们没有爱,却又藕断丝连,彼此间互为牵挂。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陈蝶仙与朱恕完婚时,筝楼称病不起,陈蝶仙前去探望,病榻前什么也不敢说,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不久陈蝶仙前往武康求职谋生,筝楼送他上船,此后每次陈蝶仙来来去去,两人都会见面,相伴到杭州各处游玩。这种特殊的暧昧关系最终还是被妻子朱恕察觉到了。这年夏天,朱恕在陈蝶仙的诗稿里发现了筝楼的十几张照片,明白了丈夫心里爱着的人是筝楼。按照当时贤妻的标准做法,她试图说服公婆戴氏,允许陈蝶仙娶筝楼为妾,但是这件事最终还是因筝楼本人不同意而作罢。
仍然是这年夏天,陈蝶仙与筝楼发生了性爱关系。事情是这样的:夏末,陈蝶仙在武康害了一场重病,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筝楼,诉说心中压抑的情感。筝楼收到信后,立刻乘船来找他,劝阻他的自杀妄念。就在武康陈蝶仙寄宿的公寓里,二人鱼水交欢,陈蝶仙旧病复发,筝楼将他接到自己家中养病,一对小儿女的爱情,渐渐的枝繁叶茂了。
在陈蝶仙后来的人生中,筝楼成了除妻子朱恕之外的重要一人。陈蝶仙在杭州开办萃利公司,筝楼卖掉首饰帮他筹款,陈蝶仙创办石印书局,也是用筝楼的钱作为开办经费。陈蝶仙透露这段感情时如是说:“由是女益爱余之诚,情谊尤笃。余欲弃商仍儒,女止:‘不可。’”从陈蝶仙的夫子自道中,明显能看出他与筝楼之间的精神依恋关系。
筝楼为什么突然消失?她的钱是从何而来?她为何终身不嫁人?这一系列问号,陈蝶仙在自传体小说《黄金崇》中作了全面回答。
筝楼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在家里开设赌局,还给有钱人做情妇。筝楼全家突然消失,是因为要躲避一场赌局迷案,逃脱警察局的跟踪。此后不久,筝楼的母亲用酒将女儿灌醉,强迫她与一个有钱人睡觉,筝楼逆来顺受,开始漫长的皮肉生涯。但她傲气十足,藐视客人。她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在一个金钱统治的世界中获得独立。
陈蝶仙有一首诗《自题筝楼聚影图》,咏叹这段刻骨铭心的情缘:“姐弟相呼二十年,情长如此岂无缘?终身有约今重订,孽债冤由两可怜。”
美国学者韩南称《黄金崇》是“一部青年成长小说”,小说从始到末笼罩着人生如梦的幻灭感。韩南说:五四以前,中国文学中写童年生活的极少见,《黄金祟》是个意外,成为犹豫、茫然、痛苦、绝望、迷乱和屈辱的文学的代表,特别是爱情文学的代表。“在《黄金祟》里,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在迅速变幻的时代里成长于一个错综复杂大家庭的青年身上的压力和紧张。在当时的社会里,这个家庭仍然强大,但力量逐渐衰弱,它受到婚姻选择自由等新观念的挑战,同时也受到充满新的独立自主的商业世界的挑战。小说揭示了一个敏感、才华横溢、娇惯而沮丧的男孩,努力将自己的爱情与当时的社会规范相互妥协调和,却极少成功的过程”。
匆匆追赶时代的人
陈定山在《我的父亲天虚我生》中说,1901年前后,陈蝶仙身上已经流露出了他积极追赶新时代的种种迹象。那一年陈蝶仙25岁,在杭州清和坊开设萃利公司,专门辟出惜红轩做了化学室,“其时,在杭州还没有人懂得什么化学,把几何算术也当作一门神话,但是我父亲却能把CHK的原理了解得非常神速。他还变了不少戏法给我们小孩子看,一杯白开水倏忽间变红变绿;一个四寸见方的草亭子里面拴着一条纸牛,到下雨时里面的牛便会自己跑出来;而惜红轩的玻璃,也变了五色的。天井里的凉蓬,装了机括,自会舒展。诸如此类,都是我父亲学了化学和机械之后的新发明”。
读到这些文字,会使人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何塞,当何塞从吉卜赛人那里看到磁铁,便想用磁铁来开采金子;看到放大镜可以聚集太阳光,便试图研制出一种威力无比的新式武器。对新生活的向往鼓荡在胸中,使陈蝶仙成为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一个人物。在清和坊萃利文具公司里,陈蝶仙采购了大批欧洲仪器到中国来试销,如八音盒、西洋镜、手摇留声机、自鸣钟、珐琅钻石表、幻灯机……生意并不像事先预想的那么好,甚至于可称作清淡,次年陈蝶仙又投资办起了一家图书馆,取名为“醒目社”,隐含有文化启蒙的意味,又办了一家石印书局,仍然是与文化有关的实业。
可是陈蝶仙的左冲右突,却遭致了亲戚朋友们的嘲笑,他们说:“蝶仙真成了洋鬼子,尽把这种怪力神的东西搬到我们杭州来。”在给好友王钝根的一封信中陈蝶仙写道:“人生处世,顺逆之境,莫非天命,无可与抗。惟听天由命,署一切荣辱于度外,庶身心渐渐能安,而境遇亦渐渐能顺。否则,如逆风行船,徒费苦力。弟在廿五六岁时,即陷此境,作任何事,无不失败。家人佥谓太公卖灰面。后索性不复营业,冥心息念,随朱芙镜兄,赴遂昌作幕,月入虽微,而身心有所寄托,由是渐渐得人信用,作事亦觉有兴。”
陈蝶仙信中提到的朱芙镜即朱兆蓉,江苏如皋人,工诗词,喜治印,也擅长绘画和弹琴,与陈蝶仙是文友。陈蝶仙在杭州经商失败后,先后在江浙一带的绍兴、靖安、淮安等地当幕僚,有时候也代课教书。1906年底,他曾在上海创立著作林社,主编杂志《著作林》,销售情况也不太理想。眼看已过而立之年,仍然浮萍般四处漂泊。1909年春,朱芙镜援手相助,请他到幕中来当幕客。
其时朱芙镜在浙江遂昌任知县,此地山清水秀,环境幽美,明万历年间,汤显祖被贬至遂昌当过知县,其代表作“临川四梦”与遂昌密不可分,当地一直有许多戏曲爱好者。朱芙镜将陈蝶仙揽入幕中,并不安排具体事情,镇日与当地一帮戏曲爱好者雅聚,赋诗谱曲,研习昆曲唱腔技巧。朱芙镜也是个有趣之人,经常参与其中,悠然自乐。县衙门是理政办案的处所,不宜鼓乐笙箫,就选择了县城东郊的绿玉亭,稍加修葺,为昆曲迷的演艺之地,邀约众人携酒放歌,演唱《牡丹亭》、《紫钗记》、《长生殿》等,与民同乐,大有“鸣琴而治”之古风。
在大时代的潮流中,陈蝶仙暂时被抛到了沙滩一角,静静地等待机会。
沪上文友王钝根
1911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浙江遂昌光复,朱芙镜捧出一颗官印交给革命党,择一处清静地成了佛家弟子。陈蝶仙也出走上海,继续笔墨生涯,同时也为创办家庭工业社做准备。
这年夏天,江苏青浦人王钝根正在上海编创《自由谈》,久已知悉陈蝶仙的文名,书信不断,力邀蝶仙加盟。是年冬天,陈蝶仙来到上海,经王钝根推荐任中华图书馆编辑,创办《女子世界》杂志,12月10日创刊。从杂志的编辑方针看,该刊强调妇女实用知识的传播,开辟有“音乐”、“工艺”、“卫生”、“家庭美术”等栏目,这与陈蝶仙早期办报刊的名士作派有了细微的区别,他的重心已在向实用方面转移。该刊翌年7月停办,共出版6期。
王钝根与陈蝶仙是情投意合的契友,两人都为对方写有小传。王钝根对陈蝶仙的才华极倾慕。陈蝶仙曾撰有《钝根先生传》,收入《栩园游戏文集》,文中极尽幽默调侃之能事,可见二人关系不同一般。
陈蝶仙的小说《玉田恨史》,就是根据王钝根内弟李清澄的真实经历创作的,陈蝶仙在《〈玉田恨史〉传概》中谈了他写作这本书的缘由——
钝根的内弟李昌海,字澄清,江苏青浦县朱家角人。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译著甚丰。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六月十八日夜,因纳凉,得伤寒症,七日而死,年仅二十一岁。同村有个女子名叫黄氏,小李昌海一岁,工书善绣,会弹风琴,经常弹唱李昌海谱写的歌曲。得知李昌海病危的消息,黄氏愿以身替。李昌海死后,黄氏焚衣自投于火,家人及时援救,得以不死。从此朝夕号泣,哀毁无状。家人多次劝说,黄氏不听,口称只求速死。她狠狠地摧残自己,饮冷水,洗冷水浴,寒冬腊月仍穿单衣,脸上战栗无人色。第二年六月,黄氏果然病发,且死于李君的忌日,年二十一岁。
这是一个标准的旧式道德故事,满纸弥漫着男权主义的色彩,在新旧时代的转换之际,陈蝶仙想用这种旧式道德故事来实现灵魂救赎。显然是投错了游医抓错了药。尽管这部小说在表现形式和叙述手法上有其先锋性,全书从头到尾用第一人称写女主角的内心活动,以类似意识流的方法让女主角倾诉种种哀思和悼亡之情,但是在这件貌似现代性的外衣背后,读者看到的依然是封建传统旧道德的鬼怪影子——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作家转型之不易。
王钝根也是鸳鸯蝴蝶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一生参与了十几个报刊的创办,其编辑宗旨是讲趣味,重本真,不喜说教。后来他创办了《礼拜六》,闻名遐迩,杂志出版赘言中他写道:“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续,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天读之。”“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宁闲此日,不亦快哉!”当年上海滩风行一句广告语:“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
辛亥革命后,文艺更是急剧向左转,一顶莫须有的“鸳鸯蝴蝶派”的帽子,压得那些旧派文人喘不过气来,大多数旧派文人噤若寒蝉,听任各种责难、讥讽、谩骂和鞭挞。在鸳鸯蝴蝶派不多的辩护词中,有王钝根率真的声音。
1924年,王钝根从友人处得知,柳亚子在一封书信中有诋毁沪上小说家语,柳亚子说他向来不看此类(鸳鸯蝴蝶派)小说,皆上海一帮文丐所为,不屑于与全无道德之文丐为伍,云云。王钝根说他听到消息后感到诧异,也感到可笑,“亚子号称学者,何其言之蛮不合理如此。余初见新文学家谩骂文言派,辄作一笔抹杀语,以为少年浅躁使然。不图亚子有养之士,才习白话文,便亦轻狂如此。”王钝根说,你们可以提倡白话文,但为什么要提倡骂人?是不是不骂人就不能成为新文学家?柳亚子昔日为南社干事,常与我等所谓文丐者周旋甚欢,自亚子投降新文学阵营后就变了脸,常指责以文章卖钱者为不道德,那么新文学作家领取稿费是不是也不道德?更好笑的是,旧派作家写的白话小说,因为未加标点符号,被谩骂为下流淫秽,而同一篇文章,一经新文学酋长批注,加以新标点,则被推崇为模范,被学校拥为教材。
用左翼文学阵营代表人物郑西谛的话说,他们的时代需要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风雅、吟风啸月的冷血作品,在一片甚嚣尘上的声讨声中,王钝根的声音太微弱,被淹没在口水中。王钝根早年曾参加南社,也喊过激昂的口号,并非一味只沉醉于风花雪月的旧文人,纵观他的一生,更应该算是一个矛盾体,在大时代的漩涡中沉浮,终于还是被巨浪吞没了。办杂志屡遭抨击,且经营也难以持久盈利,后来他设立明记公司、经营铁业,又遭惨败。1933年,王钝根重操旧业,在沪上继续办杂志《自由闲话》、《新上海》,均未获得成功。此后他的兴趣又有转移,热衷于戏曲,尤其是京剧,撰有《聂慧娘弹词》等,建国后的1950年,王钝根在上海病逝。
国货之隐者
陈蝶仙有枚牙章,上面刻着五个篆文:“国货之隐者”。这个名号是一位达官贵人赠与的,陈蝶仙在工商尺牍上常用,且为这个名号自豪。民国年间的政坛,官商常常混杂在一起,办实业也成了做官的捷径之一,陈蝶仙则对此现象不以为然,镌刻了这枚牙章行走于世,也有戒备和自警的意思。
陈蝶仙对办实业的向往由来已久,当年在杭州办文具公司、醒目社、石印书局等,皆可视作牛刀小试。据其子陈定山回忆,在杭州父亲还专门请了个日本人教家人学习化学。在上海办杂志期间,其住宅是沪西门内静修路三乐里,沪上文化人都知道陈家有个家庭工业社,研制成功了无敌牌擦面牙粉。陈蝶仙还在报刊上撰文,提倡国民工业常识,在《自由谈》开辟《常识》专栏,撰写的文章五花八门,如“造胰皂法”“苛性钠制法”“制火柴法”“漂白法”“洋磁制法”“造糖法”“镀金法”“造樟脑法”“摄影制版法”“彩色照相法”“照相石印法”“制酱油法”“普通肥料制造法”“薄荷油制造法”“甘油制造法”“纸纤维制造法”等等。此后又出版《家庭常识》单行本若干册,风行一时。
陈蝶仙最初试制无敌牌牙粉是在1912年,他曾在浙江镇海县任代理知事,其时市场日本货泛滥,国人引以为忧,创办实业者多为棉纱、布匹等类别,而三个铜板一包的牙粉,并没有什么人关注。陈蝶仙即从小处入手,开始他的国货生涯。这一年,好友何公旦在慈溪县任知事,陈蝶仙前往拜访,两人在县衙门后面的文昌阁品酒赋诗。时届初冬,潮落河平,海天如镜,推窗一望,见海滩上白皑皑一片,绵绵数十里,灿如积雪。陈蝶仙用手一指好奇地问:“那是什么?”边上有个小吏答道:“老爷,那是乌贼骨。”
陈蝶仙听后异常兴奋,赶紧回到镇海县,叫来四弟陈蓉轩商议。陈蝶仙的一生中,四弟陈蓉轩始终是他的得力助手,时任镇海警察局长兼罪犯研艺所所长。陈蝶仙说,乌贼骨又名■硝,是天然磨齿的牙粉原料,他建议用罪犯研艺所的名义向上峰打个报告,争取拨款两千元,作为试制牙粉的经费。两人一拍即合,连夜呈文,然后是满怀期待。谁知批文发下的结果大出所料,上峰不仅没有拨款,反而是一顿训斥,说陈蝶仙这个代理县知事颟顸至极,居然想出这等糊涂主意,要用两千元巨款来办渺小的一包纸袋牙粉,云云。陈蝶仙一气之下辞了官,从此寓居上海,专心投入到牙粉事业中。
陈蝶仙一生创办实业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研制无敌牌牙粉,二是改良手工业造纸。陈定山说他父亲“前者是成功的,后者是失败的”。当年的无敌牌牙粉风行全国,四亿国民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在用,成功显而易见。而改良手工业造纸的失败,其原因一言难尽。
陈定山回忆说,父亲陈蝶仙不喜欢机器,办造纸厂的想法是依靠手工。有一次,陈定山赴日本参观了几家大型造纸厂,回国后大发感叹,认为日本人从植树、锯木、造浆,一直到成纸,甚至连带印刷以及装潢成册,都是一体化的机械化作业,规模宏大让人叹服。相比之下,中国的造纸业显得太渺小。陈蝶仙听后微笑,抚着儿子的肩膀说:“你不要灰心,你要知道,现在的世界各国工商实业有的是资本,而我们有的是人力。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手工业的丰富人力,使穷人个个有饭吃,而一定要跟在人家后头,用机器来逼迫自己呢?除了飞机、火车,无法用人力推挽,一切工厂里面的马达,我认为都可以用人力来代替的。”陈蝶仙还说,“我不是不会造机器,只是我们不愿意用机器来压迫我们的工人,使他失业。尤其是我们家庭工业社,二十年来,每一个工人,大都成家生子,他们父母子女都在我家庭工业社做工。我一旦造了机器,拿装粉部分来说吧,一只装粉机的效能,至少可以抵七个人。我们的经常开支固然要省得多,但是我们的六个工人就失业了。”这种思维方式带有浓郁的旧文人痕迹,文人经商的惨淡后来始终像影子似的跟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魂归处,是深爱……
陈蝶仙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他说,人的灵魂是一种至大至刚的人间正气,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他认为人要常持一念,不可极喜,也不可极哀。前事早已化为云烟,不要因得失而沮丧,甚至也不必怀念。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譬如昨日死”,这是一种看透了沧桑世事才会有的人生境界。
芦沟桥事件后,陈蝶仙的家庭工业社迁至上海金神父路410弄,这里是法租界,相对而言安全许多。随着战争逐步升级,尤其是“八·一三”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后,大批难民涌入租界,租界成了拥挤不堪的诺亚方舟。
陈蝶仙电召儿子陈定山来沪,商议工厂西迁事宜。按照陈蝶仙的计划,拟将他们设立在上海、江苏、浙江的所有工厂全部向重庆西迁,可是合伙人李新甫却不同意,李新甫听了迁厂的方案后哈哈一笑:“这是谁的计划?要迁,你们营业部迁,我的厂不迁。”李新甫认为,就算日本人来了,做生意的还是要照常做,与国家胜败存亡无关。当时持有这种想法的实业家不在少数,陈蝶仙说服不了他,只好听任李的意见,留下了半数工厂。
工厂西迁过程中,先搬迁的是上海、江苏两地的工厂,陈家在浙江也有不少企业,父亲陈蝶仙一字未提,唯独对杭州的手工造纸厂恋恋不舍。临别之际,陈蝶仙专门回了杭州一趟,手工造纸厂是陈蝶仙亲自设计的,远远看上去,不像是一座工厂,更像是一所花园,打浆房,漉纸室,都是飞檐挑角的亭榭……陈蝶仙站在山坡上,喃喃说道:“走吧,这次,我是失败了。”说这话时他的眼眶微微有点潮湿。
一路向西撤退,经芜湖、汉口、宜昌、重庆、成都、昆明。按照陈蝶仙的想法,在宜昌、重庆、成都、昆明这几个西部城市一路设立工厂,以实业支持抗战。可是沿途建起来的工厂不断惨遭日寇飞机轰炸,成为废墟。不仅如此,上海方面还传来消息,原合伙人李新甫反目,拒不承认陈蝶仙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更糟糕的是,过了段时间又传来噩耗:留在江南没有撤离的上海总厂、无锡纸厂等企业被日寇飞机炸毁,只剩下一片砖块瓦砾,满目荒凉。面对此情景,陈蝶仙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豁达大度。有段时间他住在成都,每天泡在茶馆里听说书人摆龙门阵,有空了也为朋友写写对联,好像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也绝口不提那些被敌机炸毁的工厂。陈定山在昆明,写信请父亲去处理公务,陈蝶仙回信说:“成都的青豆蒸肉饼子,实在好,等吃满了一百蒸格,我便飞来。”
妻子朱恕留在上海,女儿陈小翠伺候左右,西迁的那些日子,陈蝶仙经常给上海的女儿小翠写信,排遣寂寞,倾诉思念之情。他在信中写道:“我早想造一个桃源乐境,等太平之后,就从蝶庄边的空地入手,左右都有余地可买,实行孟老夫子的五亩之宅,再种些番薯备荒。”又写道,“夜深如难入眠,只要呵出几口浊气,自然会得调息安神,一次睡足八小时。”
1940年3月24日,陈蝶仙在上海病逝。弥留之际,他将儿子小蝶、女儿小翠叫到床头,脸上含一丝微笑说:“我以名士身来,还以名士身去。”又说平生有两桩心愿未了,一是《天虚我生全集》尚未刊行;二是死后必归葬于桃源岭。
陈蝶仙的两桩心愿至今仍是人世间的遗憾。在他死后的那些不正常的年代里,出版《天虚我生全集》无异于是个梦呓,即便今天,时过境迁,陈蝶仙的读者已不复存在,鸳鸯蝴蝶派仍等同于罪孽,要出版全集何其难也。至于他死后必归葬于桃源岭,也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知情者只能摇头叹息。
陈蝶仙是大觉悟者,对生死有达观态度,早在1931年,他就在西湖边选择了一块风景极美之地,为自己和夫人建造了死后的坟墓——生圹。陈蝶仙还为生圹题写了墓联:“未必春秋两祭扫,何妨胜日一登临”。他又请著名书家董皙香行书刻石,题其墓曰“■”。妻子朱恕在墓道两旁栽种了83棵松树,过了几年,树木已长成林,每遇春秋佳日,陈蝶仙臂弯里挂着手仗,带着家人沿着墓道去登高。看着满湖游艇在湖上穿梭如织,心情欣然而又惆怅。
生圹造好后还未来得及立碑,战争爆发,日本人来了。陈蝶仙忙于工厂迁移,一路辗转到了大后方昆明,他依旧念念不忘故乡那座生圹,曾对儿子陈定山说:“琪儿,我昨天梦见桃源岭了。它还是好好的,松树长高了,梅花开得很盛,你的祖父,我的二伯伯,三姑夫母,连你的堂房大姐姐在那里看月亮,他们想来是等着我呢!……我的坟上开着一口池,池上开着一朵白荷,一转眼,它就萎了,我是六月二十四,荷花生日生的,这个梦兆或者就是我的归宿。”陈蝶仙还特地写了一篇《桃源梦》,寄给了远在上海的夫人朱恕和女儿小翠,此文后收录在《栩园遗集》中。
几年后——1944年春天,陈蝶仙的妻子朱恕也去世了。陈定山在《桃源岭十年祭》一文中回忆:母亲的遗言和父亲一样,“我死以后,可以把我们的双柩葬到桃源岭,桃源岭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没有理由默许给日本人。”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上海,陈定山准备运灵柩回杭安葬。谁知道才短短一年时间,人世间已发生了沧桑巨变,管理生圹的钱老伯去世了,墓道两旁的83棵松树被人砍伐成薪,满坡的梅花荡然无存,先前修建完毕的石亭子也被拆毁了。陈定山请人将父母的灵柩运到桃源岭,在生圹里安葬,墓道两旁的松树重新栽种,原来满坡的梅花改栽了竹子,再之后是三年内战,陈定山于解放前夕去了台湾,1950年他写作《桃源岭十年祭》时说道:“我天天梦着桃源岭,看见我的双亲,携手同行,指点湖上山光水色……天涯寒食,在台湾更免不了思乡的病。”
1959年,陈定山收到了妹妹陈小翠从大陆寄来的一封信,其中有段文字与桃源岭祖坟有关,信中写道:“海上一别忽逾十年,梦魂时见,鱼雁鲜传。良以欲言者多,可言者少耳。兹为桃源岭先茔必须迁让,湖上一带坟墓皆已迁尽,无可求免,限期四月迁去南山或石虎公墓。人事难知,沧桑倏忽,妹亦老矣。诚恐阿兄他日归来妹已先化朝露,故特函告俾吾兄吾侄知先茔所在耳。”从这段文字来分析,陈蝶仙夫妇的坟茔似已迁移,如今迁坟的当事人陈小翠也已作古,这座坟墓只怕是再也找不到了。
责任编辑 何子英 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