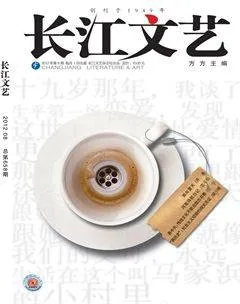易中天 : 传统文化不能当励志书看
范宁,80后,武汉媒体文化记者。来自三湘四水,遍访文化名家,问道、修业、解惑,从文化的视角看世界,乐得其所。
易中天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江湖仍然流传着他的传说。
正如他几年前对我说过的那样,将来可能不会再过多“曝光”——除了此前答应过的“文债”、“稿债”或“讲座债”。现在,年逾花甲的易中天,自然还是有许多的讲座、座谈和活动,自然还是要登上各个地方的文化讲坛,自然还是会出现在央视,被人视为“救视(救市)”的灵魂人物,但他在家中也多了外孙女的牵绊,要开始做一个外公。
现在还在看央视《百家讲坛》节目的观众,还会啧啧称奇地回味起2006年。随着《易中天品三国》的播出,不仅《百家讲坛》收视率攀升,主讲人易中天也炙手可热。五六年时间,从大学教授,到畅销书作者,从电视文化节目主讲人,到博客和微博上的“公知”,易中天并不高调地推进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转型。
这条轨迹看似喧嚣而复杂,其实静谧而简单,那就是一个获得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无论是推广传统文化,还是提升公共意识,在现代传媒的平台上,“易中天”成为了一个注脚,一种方式。
一
走上央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多会被贴上“传统文化”的标签。易中天也不外如此。他与于丹、王立群、钱文忠等一批学者,以大众传媒为平台,掀起了重读传统文化典籍的热潮。
如何解读这种热潮?如何领会传播者在推动其发展时,背后的苦心?还有如何逾越“普及”层面而进入“深读”和“精读”?在文化讲坛节目火爆过后,主讲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几年前易中天已经在思考,毕竟,传统文化解读本成为畅销书,不应成为传统文化热的最后结果,终极目标依然是国学大师们常常提倡的那个——回到典籍,回到经典。
范宁(以下简称“范”):无论是《品三国》,还是《读论语》,在“三国”和“论语”之前,都有一个动词,“品”或者“读”,这是后人在对前人经典咀嚼之后提供的读本,并非经典本身。那么,如何破解这样一个命题——读者究竟是要读一个解读本,还是原作典籍本身?
易中天(以下简称“易”):正如我的《我山之石: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不是讲儒墨道法留下的结论,而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回过头去想一想,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那些思想家,他们当年是怎么想问题的。
我在书中采取了问答的方式,把读者在阅读中可能想到的问题先替他们想到了,然后用辩论的方式讲出来。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把经典变得好读。解读经典有三道工序,首先梳理它,提供所有相关注释;然后把它转换成大家可以接受的话语;第三,融入自己的看法,不做简单翻译。
范:传统文化走上电视荧屏之后,变得生动有趣,这是否意味着传统文化开发出了娱乐的功能?
易:追求传统文化的娱乐化、实用性,恰是传统文化的误区。大众现在容易把传统文化当成励志、培优、成功学的工具。其实诸子百家是什么呢?除了法家提倡实用,其余都是当归、枸杞、六味地黄丸,养生可以,救不了命。
范:您数次登上《百家讲坛》,甚至被称为收视率的“救视主”。从文学名著讲到诸子百家,除了讲故事之外,相信您不仅仅只是为了对名著和经典进行解读,如此劳心劳力,其中深意何在?
易:我们始终扮演的是一个传统文化普及者的角色,做的是普及推广的工作。
比如我讲诸子百家,是因为我渴望寻找到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我发现诸子百家各有自己理论,从不同角度看,它们都是成立的,都是我们的精神遗产。墨家关注社会,强调“平等、互利、博爱”;道家关注人生,强调“真实、自由、宽容”;法家关注国家,强调“以法治国”(韩非子语),追求“公开、公平、公正”;儒家关注文化,强调“仁爱(孔子)、正义(孟子)、自强(荀子)”。我们现在的所谓“国学热”、“传统文化”,不自觉地局限于儒家文化中的孔子思想中,其实中华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等于孔夫子,我想提醒观众和读者,应该取不同学派的精华。
范:央视《百家讲坛》达到最巅峰的时候,有人曾认为,电视将是学习国学的现代化手段之一,但是也有观点认为,电视这一传播手段的特性,对于真正触及国学精髓是不利的。现在回头再来看《百家讲坛》,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它?
易:《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论坛。喜欢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这是这个节目的宗旨所在。这是一个文化传播当仁不让的平台,是以老百姓为对象的学术讲坛,而不是以专家、学界为对象。
《百家讲坛》并不要求主讲人是该专业的顶级专家,达到一定水平就行,但他们必须适合上电视,口音浓重到听不懂、演讲不吸引人缺少表现力,都不适合上电视。所以,主讲人的观点并不见得是学术权威意见,他们重在推动文化传播,明白这一点,不同意见的反弹可能会缓和许多。
我们遇到的沟通不畅,是文化传播在发展和前进中的问题,只能继续摸索着解决,大家应有这个耐心。
范:您所提到的耐心问题,曾经演变成一个比较激烈的事件,那就是阎崇年被掌掴。作为普及推广文化学术的平台,主讲人遭到不同意见者的掌掴,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我认为掌掴这种冲动且不文明的行为,的确会带来负面影响。毕竟学术论争应该在一个理性的范畴,“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易:当时的确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那时通过电视交流学术的经验还很匮乏,大家都没想到它的传播效果能被如此放大。学术研究本应有不同意见,没有反倒不正常;但这种“不同意见”也要分析,有的是学术论争,有的可能只是“抬杠”。
二
除了教授和学者,易中天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微博时代,扮演“公知”角色似乎并不难,困难的,是在线下依然能够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立场,去做出判断并发挥影响。离开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离开虚拟世界提供的匿名保护,“公知”还能不能秉义直言,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
易中天保持了自己的犀利。作为一位教授,一位老师,他尤其关注教育问题,在许多教育问题上,他风趣幽默又毫不留情,比如那一个“要求发论文才能毕业就是逼良为娼”的观点,至今振聋发聩。
范:您有一次到华中师大来演讲,提到硕士研究生必须发多少篇论文才能毕业,指出这种要求无异于“逼良为娼”。当时您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生的热烈回应,他们有强烈的共鸣。
易:我的确非常奇怪,为什么要规定硕士研究生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才能毕业?本应是做研究有了心得,才会写成论文发表,现在为了毕业,为了评职称,研究生、青年教师不得不买版面、找关系发表论文,甚至是抄袭,这简直是荒唐!
全国的学术刊物总共就那么多,教师评职称,要发表论文;完成课题,要发表论文;博士生毕业要发表论文;硕士毕业也要发表论文。且不说学生们能不能写出这么多高质量、高产量的论文,就算写出来了,上哪儿发表去?最后的局面无外乎三种:要么抄袭造假,要么想办法花钱买版面,要么就是走后门,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学术腐败。这种环境就是不折不扣的逼良为娼。
范:由于您的教师身份,对于学生,对于教育总是最关注的。
易:是的。学习谋生,读书谋心,谋生是第一位的,但如果只谋生不谋心就和动物没有区别了。人应该全面、自由地发展,不能把我们的学生教成书呆子,不要把大学变成培养工匠和账房先生的地方。
只有一种办法、一条道路的制度,只会扼杀人才,春秋战国为何会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因为当时读书人有很多出路,“朝秦暮楚”,在秦国不受重用可以去楚国,可以“跳槽”,人才的选择是多元的,而多元才能最终实现和谐。
在懂得如何做学问前,先要明白为什么要做学问,做学问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幸福,把做学问的部分成果转化成人们能接受的内容,传承下去,这才是做学问的真谛。
范:这几年大师逐渐远去,我们如何认识“大师”?
易: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优”不是优秀而是优裕,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习的精力有富余就可以去做官,而不是学习好就做官。现在的人才分很多种,但大师一定是有全面修养的,不仅理工科人才需有人文修养,文科人才也需有自然科学的修养,而唯一的办法是读书,读好书、读适合自己的书。
范:教育离不开读书。现在励志书仍然非常火,不过我记得,您也曾说过对这类作品深恶痛绝?
易:我最反对给孩子培优,以及依靠外在力量进行“励志”。首先,一个人有没有“志”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强迫出来的;其次,一个人感到幸福是一生最重要的,而拥有平常心才是幸福。这不是靠外力强加得来的。美国孩子要成为科学家或者家庭妇女,大家都会鼓励他(她)。不像我们,凡事喜欢一窝蜂,培养出来的都是“人造森林”。所以,我根本就不看什么励志书。
三
1978年,在新疆教高中的易中天,白天执教鞭,晚上复习研究生考试。仅三个月时间,他就成为恢复研招后,武汉大学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用他的话说,考研就是要改变“工资没别人高”的现状。
武汉,由此成为易中天人生中最重要的站点之一。易中天回武汉的次数,恐怕比回家乡长沙的次数还要多。武汉的求学生涯,武汉的恩师好友,武汉的历历人生,他永远都无法忘记。
范:您能成为一位学者,家庭教育在其中有什么影响?
易:很重要。我很感谢我的母亲,家教成功十有八九是因为有位好母亲。同样,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很重要。要为孩子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我提倡自由选择、宽松环境和民主氛围。
范:考研对您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
易:考试是门技术活。那时动荡年代刚刚结束,题目不可能出得太偏太难,只能是加大题量,让你没有时间思考。我当那么久的老师,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三个月之内,我就把所有教材弄得一清二楚,我还以考试教材为蓝本,自编了一套“古代汉语辞典”和“中国文学史大纲”,将知识点分门别类。
现在的学生读书条件太好,没有书可以复印,上课可以录音,实在不行还能从网上下载。可是下载来的书,看十遍不如抄一遍。前人有云,不动笔墨不读书嘛。
范:说说您那时候上课和求学的情景?
易:我上课从不迟到,也从不翘课。好不容易进来读书,谁会这么浪费光阴?当时研究生享有进入书库查书的特权,我拿着图书证冲进武大的图书馆,顿时兴奋得傻了眼:这么多书,从哪看起?
学生是“熏”出来的,也是“训”出来的。当时吴林伯老师教我学《文心雕龙》,讲究“通一经”,即“打通”一本经典典籍,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吴老师先要我用毛笔将《文心雕龙》50篇抄写一遍,然后手把手教我点断古文,最后是作注。《文心雕龙》成为我的“童子功”。
范:2007年,您在上海以拍卖文集的方式为胡老师筹集教育基金,后来又在武大设立了恩师名义的奖学金,足见当年的老师们对您的影响非常深远。
易:我记得有一次,我向胡国瑞报告读书情况,我说我读了《唐诗选》、《宋词选》、《诗经选》,胡老师眯眼一笑说:“原来你读的都是‘选’啊?”他立刻给我开了基本原著,读书要读原著,就这样成为我的习惯。
吴林伯先生是另一位名师,他规定学生每天都要上他家去读书,自己却挤在小桌子上做学问。我的论文草稿出来之后,不光是指导老师看,很多老师也在看。当时学生少,我们研究生像是独生子女,老师待学生比待子女还要好。
范:今天的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非常迷惘。您那时候会有这种窘迫感吗?
易:我当时是带薪求学,一个月有五十多元的工资补贴,学校还发放两到三元的书报费,算下来比大学讲师收入还高,整个中文系数我收入最高,成了“首富”。
我们那个时代不可能有迷茫、郁闷、纠结和焦虑,我们很单纯,从一个痛苦的年代走过来,都觉得赶上了好时代。寝室的大师哥丁忱曾写过一首小诗,“到处浓阴环绕/最宜相亲拥抱/可是我们的学子啊/却投向了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这就是我们那时生活的写照。
范:听说您现在在家里练“孙子兵法”?
易:是的。就是如何带孙子的兵法。其实家里轮不到我管外孙女,有她妈、她外婆在呢。
责任编辑 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