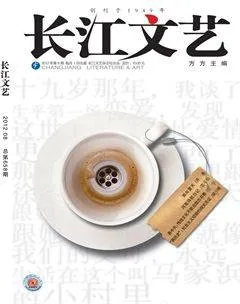那年夏天
马家浜村的清晨从来都跟夜晚一样寂静
这里没有鸡啼,没有鸟鸣,也没有狗吠
有的只是风留在树梢上的声音
还有男人们跑出屋子在墙角旮旯里撒尿的声音
大地在浸透了一夜的露水后
张着嘴尝到的第一口液体
就是马家浜村的男人们泛着泡沫的尿液
然后,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升上天空,成为蓝天下的白云
十九岁那年,我谈了平生第一场恋爱,发现这世上再没有比爱情更美妙的东西了。
那时候,我一心只想跟徐冬梅在一起,白天跟她一起干活,晚上跟她一起睡觉,就像我们的父母,永远生活在这个叫马家浜的小村里。
虽然,我从来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过这个村庄,可它确实存在,就在红旗塘河北岸的田野里,远远望去仿佛老天爷拉下的一坨屎,悄无声息,却又热气腾腾。一百年前,这里只有九十九户人家,到了现在仍不满一百户,但它却有杭嘉湖平原上最大的一艘乌蓬船,如同一头黑色的史前巨兽蹲在田野里,守护着我们的村庄,同时也像在吞咽这个村庄。
我跟徐冬梅的爱情就始于这条田野里的巨船。那里是我们的天堂。无数个白天与黑夜,我们在幽暗的船舱里拥抱、亲嘴,有时也静静地躺在甲板上,微闭眼睛仰望天空,直到一天午后。
徐冬梅的父亲忽然从一排野槿丛中钻出来,就在我推着她的屁股爬上架在船舷上的竹梯时,他在我们身后重重地咳嗽一声。
徐长贵一直等到女儿涨红着脸跑开,才看着远处的地平线,说,你跟我来。
我跟在徐长贵屁股后面到了村委会办公室。这里也是我们村五金胶木厂的厂长室。
他关上门对我说,你要认清形势。
我说,什么形势?
他的眼睛像蚊子一样在我脸上盯了一会,问我信不信,他说,你再敢耍流氓,我就把你吊起来。
这怎么是耍流氓呢?流氓我不是没见过,我家隔壁的马三宝就是。他偷看女人洗澡,偷她们晾在晒场的花裤衩,还在村口的磨坊里摁着公羊给母鸡配种。这样的人才是流氓。但要是徐长贵说我耍流氓,我在马家浜村迟早会成为一名流氓。因为,他从来都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他是我们的村支书,他还是我们村办的五金胶木厂的厂长。想当年,他去公社看了一场电影,回来就让我们在所有的土地里都种上高粱,他要让我们马家浜村成为一片青纱帐,这里就得成为一片青纱帐。他还让我们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扎上白头巾,我们的头上就都扎上了白头巾。因为这是出入马家浜村唯一的通行证,不然我们会变得有家难回。可是,老天爷与土地爷从来都是两位不听人使唤的爷,而且常常还要背着人的性子胡来。那一年,我们全村上下颗粒无收,只有那些疯狂生长的高粱秆子在田野里摇曳,到了秋天还是一片青翠,就像春天永无尽头。
徐长贵不光威胁我,还威胁了我的父母,让他们把儿子管教好,别等到哪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来求他。徐长贵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全家围着桌子正吃晚饭,他背着双手进来了,说大老远就闻到了清炖猪卵子的味道。
徐长贵就是这么一个人。每天到了黄昏就背着双手在村子里转悠,像条狗一样伸着鼻子,嗅到谁家灶间透出的香味,他就往谁家里闯。进了门,笑呵呵的就像回到自己家里,搬开凳子,端起碗筷。用他的话说这就是联系群众,与乡亲们打成一片。还有什么比上饭桌更能深入群众的?徐长贵常常是自问自答,说除了钻进人家的被窝里,那可是要犯错误的。徐长贵就是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吃着我家的猪卵子,教导我父亲——共产党的干部,一不能搞贪污,二不能搞腐化。
我父亲连连点头。他对徐长贵的话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尤其在入党后,就更加坚信了一条真理——走党的路线,首先得听支部书记的话。
乡里突击计划生育那年,徐长贵让我父亲带个头,他二话没说,隔天就把自己给结扎了。回到村里后,他就成了计划生育的义务宣传员,指着自己的小肚子,逢人就说不疼,一点都不疼,就跟刮了把胡子似的。
就因为这句话,我父亲在村里得了个绰号马胡子,但他一点都没在乎。他曾认真地对我妈说,这有什么?你省事了,我也省事,我们的国家更省事。
我妈眼泪汪汪的,一个劲地埋怨他平日里阉的猪太多了,让猪屎进了脑袋。她说,现在你跟头阉猪没什么分别了。
父亲一下就火大了,扯着嗓子说,怎么没分别?怎么没分别了?阉猪得花钱,这是免费的。
我父亲是马家浜村的会计兼兽医,公社没撤掉那会,他还是方圆十几里唯一的赤脚医生。这让他在很多时候都把自己当成了马家浜村的第三把手。可是,他赤脚医生的生涯干到1985年就结束了。
1985年的夏天,我的父亲马胡子捧着那张《人民日报》坐在徐长贵家的堂屋里,反反复复地说,怎么可以取消呢?这往后的,让乡亲们找谁看病去?
当然找你。徐长贵严肃地说,当不成赤脚医生你就不为人民服务了?
我父亲想了想,说,可名不正,言不顺嘛。
徐长贵板起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再也不理他了。在对待我父亲马胡子的态度上,徐长贵跟我们村长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对付那些经常自以为是的人,我们就得拿自己当耍猴的,要一手巴掌,一手糖。
可我父亲从来都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只是认为自己是我们村里最有学问的一个人。这从他给我们兄妹四人取的名字上能看出来——马中林、马中海、马中雪、马中原。那是他对革命样板戏深入研究的结果。说句毫不夸张的话,在整个马家浜村(当初也叫红旗第三生产队)也只有他知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小说《林海雪原》的产物,是《林海雪原》生出来的一个儿子。
结扎之后的马胡子在以后的很多年里都是理直气壮的。他经常会在床上挑着眉毛对我妈说,我都生出一部《林海雪原》来了,难道你还想再来一出《奇袭白虎团》?
但是,在我跟徐冬梅的问题上,他却像变了个人,每次都说我这是瘌蛤蟆想吃天鹅肉。说到尽头,他还让我撒泡尿自己去照照。
我在一天傍晚的饭桌上终于发火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里面嗓门大过我父亲。我瞪着他说,关你什么事?我跟谁相好,碍你什么事了?
父亲看着我,没说话,有些发愣。他的目光一下变得深不可测。夜深人静以后,在我准备出门去跟徐冬梅幽会时,发现他像条狗一样蹲在院门边。父亲抬眼看着我,一口一口地用力抽着嘴里的烟。
父亲蹲在地上说他跟支书合计过了,秋季征兵的时候,把我的名字也报上去。说着,他站起身,把烟屁股扔在地上,狠狠地用脚一碾后,盯着脚尖说,别去招惹人家,我们惹不起。
我说,这个不关你的事。
我是你老子。父亲喊完一嗓子,马上变得心平气和地说,当上兵你就是城里人了,到时候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可我找的绝不只是女人,女人不等于爱情。我在十九岁时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一把拉开院门,一头扎进茫茫的黑夜里。天上星星点点,我的脑袋里只有徐冬梅,只有她那张香喷喷的脸蛋,还有两片软绵绵的嘴唇。除了这些,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
我沿着马三宝家的土坯墙一直往前跑,穿过整个漆黑的马家浜村,一直跑到那条停搁在田野里的巨大木船上。
可是,那天晚上徐冬梅又失约了。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我知道是她父亲把她关在房间里了。徐长贵不仅在她房门上装了把锁,还把她的窗户用木栅栏钉了起来。我还知道,徐冬梅在乡里有个还没见过面的对象,这话是在她枕着我的胳膊看星星时说起的。那人是乡长家的小舅子,是乡政府小汽艇的驾驶员,家里有一幢三层楼的红砖房。但徐冬梅马上在我耳边接着又说她不稀罕红砖房,也不稀罕驾驶员。她说,我一天是你的人,一辈子就是你的人了。
我靠着船舷整整等了一夜。第二天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就看见满天的朝阳下,大地是湿漉漉的,甲板是湿漉漉的,我整个人也是湿漉漉的。
马家浜村的清晨从来都跟夜晚一样寂静,这里没有鸡啼,没有鸟鸣,也没有狗吠,有的只是风留在树梢上的声音,还有男人们跑出屋子在墙角旮旯里撒尿的声音。大地在浸透了一夜的露水后,张着嘴尝到的第一口液体,就是马家浜村的男人们泛着泡沫的尿液。然后,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升上天空,成为蓝天下的白云。
可以说,马家浜村的每一天都是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开始的。
在我初中毕业那年,徐长贵在村里搞起了我们全乡的最后一家村办企业,我就成了马家浜村五金胶木厂的一名热压工,有时候也充当押运员和装卸工,就是把生产的那些电熨斗上的胶木配件装上船,运到斜塘镇上的轮船码头,再由那里通过水路运到县城的中转仓,再运到市里的熨斗厂。
斜塘镇是我十九岁前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也是最繁华的地方。但我知道比斜塘镇更大、更繁华的地方是嘉禾县城,比嘉禾县城更大的地方是秀州市,再远再大的地方,在跟徐冬梅谈恋爱前我从没想到过。我是在第一次亲完徐冬梅那两片潮湿的嘴唇后,莫名其妙地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带你上北京的。
徐冬梅愣愣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在黑暗中比天上的星星更加闪亮。
我说,真的,我一定要带你上北京去。
徐冬梅把一口热烘烘的气息吐在我脸上。她的气息里有一股白米饭刚刚揭锅时的芬芳,每次嗅到它都让我如痴如醉,以至常常无心留意她转瞬暗淡的眼神。
就在那晚失约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吃饭,而是直接去了村里的磨坊。
推开磨坊的后窗就可以看到徐家的院门,但我始终没有见到徐冬梅。我看着徐长贵捧着茶杯从门里出来,踱着方步去了他的村委会兼厂长办公室。我一直等到他老婆提着篮子下地去摘菜后,从窗口跳了出去,像个贼一样闯进徐冬梅的家里。
我脑袋里唯一的念头是她病了,这会正躺在床上发着高烧。
但是,我的心从徐家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发慌。我的恋人并没有在床上,也不在屋里。屋里只有她那几个不懂事的弟弟和妹妹。他们家就这么几间屋子,连猪圈我都闯进去了。
徐冬梅就像一滴露珠在阳光下消失了。
马三宝在磨坊的后窗口冷冷地看着我,忽然说,你去支书家偷东西了。我没理他。从辈分上排,他应该是我的堂叔,但我从来没拿正眼看过他。我的心头竟然有种让人划了条口子的感觉。马三宝却还是冷冷地说,偷人家姑娘的也是贼。
马三宝是唯一见过我跟徐冬梅在巨船里亲热的人。他每天夜里都像个幽灵一样在村里游荡。整个马家浜村的人都相信,发生在黑暗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逃过他的眼睛。
我用乞求的眼神看着他,说,告诉我,她去哪里了?
马三宝想了想,往窗外的草丛里吐了口痰,转身就拉下了窗户板。
两天后,我在五金胶木厂的门口见到徐冬梅时,她穿着一件水红色的的确良衬衫,就像个新娘子似的低着脑袋,跟在她父亲的身后。我用眼睛紧紧地盯着她,可她就是不抬头。
徐长贵瞥着我,说,愣着干什么?干活去!
整个上午,我对着热压机填料,加热,出模;再填料,再加热,再出模。我干得满头是汗;可满脑子惦记的都是在检验室里的徐冬梅。然而,我哪儿都不能去,徐长贵搬了把椅子就坐在他女儿检验室的门口。他竟然坐着喝了一上午的茶,连尿都没撒一泡。
但我还是见到徐冬梅了。几天后的深夜里,徐冬梅忽然爬上巨船,一动不动地站在熟睡的我跟前,站在满天的星光之下。
一连几天,每个晚上我都从家里溜出来,就睡在这艘田野里的巨船上。甲板成了我的床铺,天空就是我的屋顶,盖在我身上的露水让我感到既冰凉又温暖。我坚信,这就是爱情的滋味,它一半是露水,一半是血液在身体里奔流。
当我在徐冬梅的泪水中惊醒时,她已经蹲在我面前。她的眼中泪光闪烁,同时又暗淡无比。就像还在梦中,我伸手抱住她,一直到把舌头伸进她嘴里,在里面搅了很久才发觉这不是梦,这是我日夜等待的时刻,这是我又冷又暖的爱情。
好一会,我吐出一口气,说,你想死我了。
徐冬梅点了点头,说,我也想你。
可当我问到她是怎么出来的,徐冬梅轻轻推开我,坐在一边,什么都不说了。她抬头望着天空。她的眼睛里没了泪光,也没有星光。
过了很久,徐冬梅还是开口了。她说她要嫁给乡长的小舅子了,要住进那幢三楼三底的大房子。她的婚期就是几个月后的建军节。
原来,她失踪的两天是去了乡里,跟她的对象见面谈日子去了。
我的心又被划开了。我说,你一天是我的人,一辈子就是我的人。
徐冬梅忽然笑了,钻进我怀里,把脸紧紧地贴在我胸口。她说,现在还来得及,你带我走。
我说,你想去哪里?
徐冬梅没说话,贴在我胸口又开始落泪了。冰凉的泪水让我热血沸腾。
仲夏之后,阳光更加肆无忌惮地照耀着大地。远远望去,马家浜村就像要在烈日下融化那样,只有村里的老人们坐在树阴底下,如同一条条晾干的咸鱼。马天亮就是这个时候回来的,他用一副茶色的蛤蟆镜遮着大半张脸,但还是难掩眼中的忧伤与疲惫。自从分田到户后,再也没人愿意在红旗塘河上划渡船。他在河对岸候了一天一夜,才等到一条肯渡他过河的渔船,回到家时连话都懒得说,把行李一丢倒头就睡。
马天亮是我们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用徐长贵的话说,他就是一条跳进了龙门的鲤鱼,带着他的户口去了省城的大学。他迟早有一天会永远地离开我们马家浜村,一去不返。可这些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去地里偷瓜,去红旗塘张网捕鱼,我们不管白天与黑夜,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会跑到红旗塘的岸边,把自己脱光了,跳进水里尽情地扑腾。那个时候,我们自由自在,我们没心没肺,我们从来不顾忌这条河里曾经死过那么多的人,我们钻进水里就成了两条没有鳞片的鱼。
不过,现在的马天亮不一样了,他看上去比城里人还要像个城里人。哪怕天热得让人恨不得揭下一层皮来,他都安安静静的,再也不肯光着膀子一头钻进水里面。他的白衬衫就像是他的白皮肤,扣子一直要扣到领子下面,就连晚上睡觉都要穿件汗背心。但更大的变化是在他的眼睛里面,每次坐在红旗塘的堤坝上,望着波光粼粼水面,我都能在他的眼睛深处听到一种声音。
马天亮的父亲就死在这条河里,跟我的祖父、我的大伯,跟我们马家浜村里许许多多的父老乡亲们一样,他们在开挖这条红旗塘时,被冲垮堤坝的水流卷走。那一年,马天亮刚刚出生,而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可我们都听到了一个声音在马家浜村的上空回荡,阴沉而悠远。为了掩盖这个可怕的声音,徐长贵跑进广播间,在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东方红》,但还是难以阻挡恐惧在每个人心中蔓延。
上了年纪的人都说,红旗塘里的每一朵浪花中都藏着一双死人的手,就想伸到岸上来把活人拖下水。
这一天,马天亮坐在红旗塘的堤坝上,自言自语地告诉我,是这条河分隔了这片土地,让一块成了两块,让一个世界成为两个。他闭上太阳镜后面那双忧郁的眼睛,仰着脸说,这里,连吹来的风都跟对岸不一样。
我可顾不上这些风,也顾不上这条河。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只有徐冬梅。我再不带着她离开这个鬼地方,她就会成为别人的老婆。
当我第一个告诉马天亮,我要带着徐冬梅私奔时,他睁开眼睛,就像要望穿秋水那样望着红旗塘的对岸,吟了两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马天亮接着又说,过了这条河,就是一片新天地。
可只要是马家浜村里的人都清楚,过了这条河往前走就是斜塘镇,几乎每个月我都要送货去那里,有时也顺便替我父亲去信用社,把支票兑现后带回厂里发工资。我从来不觉得是红旗塘把一块土地分成了两块。土地永远是土地,上面有沟有壑,有山有水,才会有船有车。
马天亮说,可是你没有钱,没钱的人哪儿都去不了。
但我还是等来了我的私奔。在去斜塘镇送完货之后,我带着从信用社里兑现来的钱回到村里时,天色已黑尽。为这个晚上,我已经足足等待了半个月,也盘算和准备了半个月。我站在送货去斜塘镇的船舱里,用眼睛对岸边的徐冬梅说,等着我,等我回来就带你走。
徐冬梅用一种谁也无法觉察的表情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跟谁都没有道别。我只通知了我的堂兄马劲松,让他帮我弄一条船。我说,什么都不要问,把我们送过红旗塘就行了。
可他还是问了,你们?还有谁?
我说,天亮。
马劲松说,你们不能游过去吗?
我有点不耐烦地说,叫你弄就去弄。
说着,我往他手里塞了五块钱。
马劲松是我堂兄。他父亲也死在红旗塘里后,就几乎就成了我父亲的儿子、我的亲哥,但是他却是我这辈子第一个出卖我的人。
我站在田野里的木船旁,看着马家浜村里的灯火一家家地熄灭,一直等到一片漆黑后,徐冬梅还是没有来。
忽然出现的人是马劲松。
你该等在船里。话一出口,我就有点明白了。
马劲松没吭声,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我时,我已经看到了徐冬梅家的大舅、二舅与她的两个表哥。他们都是马家浜村里的人,都是我们马家这根藤上结出来的果。他们一个个像从地底下钻出来那样,把我围在中间。
一道手电光忽然亮起,照得我睁不开眼睛。
我对马劲松说,你有种。
马劲松还是不说话。
我扭头想走,马上就有人扭住我的胳膊,按得我抬不起头来。
我说,放开我。
支书在等你。马劲松总算开口了,他接着又说,你爸也在等你。
我说,马劲松,我操你妈。
马劲松说,你文明点,她是你婶。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我忽然想哭,想吼,可就是张不开嘴。我看到我的爱情像花朵那样凋零了。
在押着我进村的一路上,这些人都跟我一样,谁也没有出声。我们就像是一群出殡回来的人,悄无声息地走着,快走到马天亮家时,我对马劲松说我要撒尿。
马劲松说,忍忍吧,你不是孩子了。
我说,马劲松,你还想让我尿裤子吗?
马劲松朝扭着我胳膊的人看了一眼,向马天亮家的篱笆墙抬了抬下巴。
可我站在篱笆墙前,就是尿不出来。我扭头看了看照在我身上手电,说,你们照着让我怎么尿?
手电光灭了。
徐冬梅的二舅说,中林哪,你就别磨蹭了。
我没理他,飞快地抽出插在裤腰的那包钱,往篱笆墙里一塞后竟然真的有了尿意。我在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后,就像被押赴刑场的共产党员那样,昂着脑袋通过五金胶木厂的后门,一直被押进堆放货料的库房里。
徐长贵沉着一张青皮脸始终不说话,他只是努了努嘴,让他的两个外甥把我吊在梁上,又让他的一个小舅子把我全身上下搜了一遍后,对他们说,回去吧,都回去睡觉吧。
我始终瞪着我的堂哥马劲松,看着他头也不回地出了库房后,我对徐长贵说,放我下来。
徐长贵找了块破布堵住我的嘴,然后平静地看着我。到临走时,他关了灯,在黑暗中说,要是放在过去,我就把你浸猪笼了。
黑暗中,到处是胶木粉刺鼻的气味,我都能感到它们在闷热的空气中飘浮,一点一点地吸附到我身上,钻透我的衣服,一丝丝地钻进我的皮肤,顺着血液在我身体里流动。我奇痒难忍,可我喊不出来,也动弹不了。我只能像条麻花一样扭着我的身体,直到汗水把我整个人都湿透。我连呼吸的力气都快没了,但我还是想着徐冬梅,想着她滚烫的身体,想着她湿润的嘴唇。我的鼻子又嗅到了她身上的气息,一下子,耳朵里同时也灌满了她的声音。我听到她在我耳边说——我一天是你的人,一辈子就是你的人。
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刚从田野的尽头升起,徐冬梅就冲出她家的院子,做了件震动整个马家浜村的大事。
彻夜未睡的徐冬梅两眼通红,她换上那件水红色的衬衫,对着镜子仔细地扎好辫子后,起身敲了敲了反锁的房门,对她妈说她要洗把脸。
徐母亲自伺候女儿洗漱之后,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粥捧到她手里。徐冬梅一边喝着粥,一边淡淡地问徐长贵,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徐长贵坐在门口喝着早茶。徐长贵喝早茶的时候一般不答理人。但这一次,他破天荒地开口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徐长贵捧着茶缸仰头想了想说,放心吧,拐骗妇女,盗窃公款,三五年里肯定回不来。说完,他看着女儿,又说,你不能再胡闹了。
徐冬梅点了点头,放下碗,对她妈说,妈,我吃不下了。
说完,她抹了抹嘴巴,起身就往屋外去。
徐长贵一愣,看着她说,你去哪儿?
徐冬梅没说话。
屋内的徐母忽然叫起来:你还不拦住她!
可是,谁也拦不住,徐冬梅一转身就跳进了她家院子的那口井里。
本来准备押我去派出所的那条船把徐冬梅送进了镇上的医院。临行前,徐长贵在百忙之中让人找来我父亲马胡子,命令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徐长贵说,我不能让你趁乱回去把儿子放了。
我父亲早已吓得面如土色,一直到发现有血从徐冬梅的裤裆里流出来,他才壮着胆子跟徐长贵商量:我们多置些彩礼怎么样?我父亲马胡子胸有成竹地说,支书,你就说个数嘛,多少都成。
徐长贵看了看站在船头撑篙的外甥,扭头又看了眼船尾掌舵的大舅子,他把目光落在不醒人事的女儿脸上。徐冬梅的脸上嵌满了井底的淤泥。
很久,徐长贵摸着下巴说,等人活过来再说吧。
马胡子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
但我早就被放了,就在全村人都挤在村口看支书家的笑话时,马劲松打开了库房的大门。他让我快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他说,你弄出人命来了。
可更加要我命的是那些钻进皮肤的胶木丝。它们让我整个人又红又肿,痒得恨不得把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揪下来。没等他说完,我狠狠地推了他一把,头也不回地跑出五金胶木厂的后门。我想去马天亮家篱笆墙取回我的钱,但我不能,那里到处站着议论纷纷的乡亲们。我只能沿着僻静之路跑出马家浜村。我气喘吁吁地穿过阳光灿烂的田野与荒地。我在旷野中汗流浃背地奔跑,朝着我心中的方向。我的爱人生死未卜,我就怕我停下来喘口气的工夫,我就永远见不着我的徐冬梅了。
傍晚,当斜塘镇的那个高烟囱在天边出现时,我被地里的农民堵在田头,他们不由分说把我扭到镇上,送进派出所。我眼里布满血丝,我的身上一丝不挂,而且又红又肿,还粘满了泥土与草屑。我就像个伤痕累累的血丝虫病人。但这些朴实的男人与女人,他们把我当成了流氓,也当成了一个疯子。
红旗塘的激流卷走了我的衣服与裤子,就在我把自己脱光跳下去的那一刻,阳光像鱼儿一样在水面跃动,河水还是那样清澈见底。我托着我的衣裤,两脚不停地踩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游得专注而用力,可曾经的传言却在这时忽然应验。无数双手从水底伸出来,成群结队地拉着我、抱着我、摁着我、缠绕我。我几乎能听到每只手都在叫着我的名字,就像那些淹死的亲人们,在拼了命地拉着我往下拽。
我从未感到如此恐惧,拼命地往前划水。一直到肚子贴在对岸的泥滩上,还在拼命地划。
公安给了我一身衣服,穿上后开始审问我。
我忽然想起马三宝说过的一句话: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我用直愣愣的眼神看着眼前的公安,一直到他最后说,原来是个哑巴。
关我的拘留室屋顶上有个天窗,透过上面的玻璃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也可以看到阳光沿墙壁一点一点地移动,一点一点地爬到地上。
马天亮忽然来了斜塘镇,揣着我的那包钱,背着他的行李,戴着那副太阳镜。他站在派出所的一张办公桌前,把他的校徽与学生证一起放在上面,说,这就是我的证明。
那不行。派出所长说,没有单位的证明,谁也不能把人带走。
神经病哪来的单位?马天亮指指地上的行李,说,你看,我这是要送他去精神病院的。
所长拿着学生证又把他对照了一遍后,没再吱声,起身就去拘留室,打开门把我给放了。他看着我们俩,对马天亮说,你爹妈真有本事,生了你们兄弟俩。
马天亮没说话,就像真的领着个精神病人那样牵着我的手,一直把我牵到大街上。我甩开他的手,问他怎么知道我在派出所的。马天亮笑了笑,说这才屁大的一个镇子。说着,他戴上太阳镜,问我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要去医院。
隔着茶色的镜片,马天亮看着我,说,那你还是回派出所吧。
我说,我就是为她来的。
马天亮说,徐长贵不会放过你的。
我毫不犹豫地说,她能为我死,我为什么不能为她去坐牢。
但我最终没有见着徐冬梅。
从县医院到火车站的一路上,是我这辈子走的最长的一条路。
我在斜塘镇的卫生院里没有找到徐冬梅。她被一艘小汽艇连夜送往了县城。当我赶到县医院,替我去见徐冬梅的人是马天亮。他在医院的门口拉住我,说,还是我去给你打个前站吧。
马天亮是个考虑周全的人,但他并没有见着徐冬梅。他撞见的人是徐长贵。
徐长贵站在病房的走廊上,审视着他,说,谁让你大老远赶来的?马天亮说没有谁,他是来医院办点事,正好碰上了。徐长贵叹了口气,说,你大老远赶来,是来看我徐长贵笑话的。
马天亮说,不是的,我不是这样的人。
徐长贵不说话了,蹲下去,背顶着病房的墙朝马天亮摆了摆手。
马天亮是从护士那里得知徐冬梅小产了。由于失血过多,医院从市里调来了血浆。
徐冬梅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后回到马家浜村。她脸色苍白,眼睛看上去更大了,黑得就像个两个深不可测的窟窿。
那年的建军节,她没有嫁给乡长家的小舅子,而是很快投入到另一场恋爱。马劲松每天傍晚都准时在支书家里报到。为了这一天,他已等待了好几年。他对徐冬梅说,我是一片真心。
徐冬梅不说话,只是用她那双深不见底的大眼睛看了眼马劲松。
马劲松又说,真的,我会对你好的。
徐冬梅缓缓垂下头,还是不说话。这回,她看着自己的脚尖。
马家浜村里的每个人都见证了他们俩的爱情,规规矩矩,正大光明,就是徐冬梅的妈有点不甘心。一天夜里,她在被窝里跟男人唠叨:跟老寡妇家的儿子,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
徐长贵闷了好一会,说,那你说怎么办?
徐冬梅的妈叹了口气,隔了好久才说,我就是不甘心。
徐冬梅的婚事重新定在了国庆节,这么快娶她的人是我的堂兄马劲松。
我的父亲马胡子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上连襟家借了一头猪赶到支书家里,笑呵呵地说,这样也好,这样还是一家人。
徐长贵没理他。自从把他的会计撤了后,徐长贵就没拿正眼看过他。
马胡子■脸在一边坐下,掏出烟想敬,一看徐长贵的脸色,就赶紧收回来,往耳朵背后一夹,说劲松是他的亲侄子,自从他老子死后就成了他半个儿子。我父亲马胡子说,支书,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聘礼上头,你尽管开口。
你有钱还是先去堵你儿子捅的那窟窿吧。徐长贵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为了补上那个窟窿,父亲已把家里能卖钱的东西都卖了。他曾在一天午后站在徐长贵的办公桌前都要下跪了,说,只要不坐牢,你把我卖了都成。
徐长贵还是那句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有这工夫你还不如劝你儿子投案自首去。
马胡子都快要哭出来了,说,支书,你让我上哪却找那王八蛋去?
那天晚上,马胡子赶着那头猪回到家里,哭丧着脸对我妈说,我已经不管用了,我现在拿热脸都贴不上人家的冷屁股了。说完,他又对躺在母亲被窝里小儿子说,你也看到了,一颗屎就是这么坏了一锅粥的。
马中原这年十岁。他一边咬着手指甲一边看着沮丧不已的父亲。
但徐长贵却像打了鸡血,就在女儿婚期临近的前夕,他的劲头忽然来了,就因为徐冬梅饭桌上说的一句话。徐冬梅放下筷子,眼睛对着碗里的饭说,还是算了吧,这婚还是不结了。
徐母的眼睛一下直了,瞪着女儿说,帖子都下出去了。徐冬梅不说话,起身拉开堂屋的门,在迎面吹进来的微风中看着院子里的那口井。徐母慌了,赶紧放下碗上前拉住女儿,说,我们这种人家,不能再让人笑话了。
什么笑话不笑话的,徐长贵一拍大腿站起来,对女儿说,这就对了,我这就把婚给你退了去,我倒要看看谁敢笑话我徐长贵!
马家浜村里的人笑话的是我。每个人都以为我会像条野狗一样在世界上游荡,直到老死那天,蜷缩在路边仍然像条无家可归的野狗。但我从没有一天忘记过我的家乡。我每天都会想起它。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与徐冬梅相遇。我时常都想念着,想念那年夏天,想念我那场十九岁的爱情。虽然我至今都没有再回马家浜村。
责任编辑 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