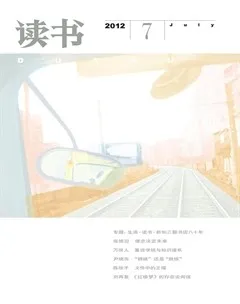“《读书》服务日”忆旧
三联书店八十周年庆,《读书》编辑部的朋友约写文章,因为我是“老作者,老朋友”。这样说,让我觉得责无旁贷。写点什么呢?想到三联书店,就会想到《读书》杂志,想到《读书》,就会想到“《读书》服务日”,想到那些单纯、热情而充实的日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学子,如果有人文、社科方面的兴趣,更不用说其中自认为有思想者,大约案头都备有《读书》,否则,其思想视界和文化趣味就会受到怀疑。这本三十二开的书评月刊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不过,对我来说,《读书》当时提供给人们的,不只是知识、观念和思想,还有人生际遇,成长的机会和可能。
我有幸成为《读书》的作者,自一九八五年始。这件事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因为一些特定原因,当时《读书》的作者,差不多可以被视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而成为《读书》的作者,就意味着成为这个知识群体的一员,意味着开启一个新的社会交往空间。我的许多朋友最初认识就是通过各自发表在《读书》上的文字,而且,也容易因为这种作者身份而引为同道。这种友朋和同道间的交往,因为每月一次的“《读书》服务日”变得更具吸引力。
那时,三联书店还在北京朝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楼内,“《读书》服务日”就在那里举行。除了展新书,服务日并无主题,它更像是一道风景。一间房,若干桌椅,几杯清茶,一群读书人,那就是“《读书》服务日”。去到服务日的,不必是《读书》的作者,甚至不一定是《读书》的读者,但那个日子,那个场合,对喜欢《读书》的人来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去“《读书》服务日”的人,或为谈事,或为交稿,或为见人,或者,没什么具体事,只是到那里坐坐、看看、听听,随便见什么人,总不会一无所获。《读书》当时的编辑们,王焱、吴彬、赵丽雅、贾宝兰、杨丽华,会在那里招呼来者,通过她们介绍,新来者也可以很快结识新人,融入谈话。那时候,编辑同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更接近于朋友和同道,而少职业色彩。记得某个夏日中午,不知什么人提议,一群人跟着赵丽雅,到她在东总布胡同的家里,上上下下地参观,然后在树荫下天上地下地闲聊。又有一次,在服务日上聊到午饭时间,杨丽华便请大家到附近的咸亨酒店,边吃边聊。我记得,那里的菜味道不错。还有一次,也是在服务日,午饭之后,大家意犹未尽,相约要跟一位朋友去他家里参观他的藏书。我与那位朋友初次见面,不知道同去是否唐突,正犹豫间,那位朋友却招呼说,愿意来都来吧,大家都是读书人。于是,一众人等便骑了车,浩浩荡荡地去了。那位朋友家住南锣鼓巷炒豆胡同,他的名字叫赵越胜。后来,我们也成了朋友。经他引荐,我还参加了一个当时颇为活跃的“编委会”,一个有更紧密联系的年轻知识群体。而我发现,那个群体的成员,差不多都是《读书》的作者,而且,“编委会”的出版合作者,就是三联书店。
那是一个心灵尚未腐化的年代,年轻,热情,开放,向上,充满朝气。虽然物质还匮乏,但是精神饱满;思想虽不够深刻,但质朴有力,理想不坠。《读书》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读书》杂志,三联书店,还有她的作者和读者,都是和那个时代一起成长起来的。对今天的人来说,要理解《读书》与其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理解《读书》当时的那种影响力,已经不太容易。因为,那不只是关于一些人和一本杂志或一个出版机构,而是关于一个时代,一个已经逝去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