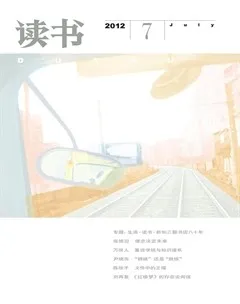读《〈春秋〉与“汉道”》
十年前,陈苏镇先生出版过一部专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最近,书又增订再版,扩充了约二十万字关于东汉的内容,书名也改为《〈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算上旧作,这部书我一共读过三遍。因为本书确是汉代政治史研究领域少有的力作。它作为第一部详实的两汉政治通史,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极具魅力的个人风格,能够为汉代史的研究者提供诸多有益的帮助和启发。不过,到目前为止,这部书(包括其前身)的影响还远没有体现出它所蕴涵的价值。思虑再三,决定不揣冒昧、不避嫌疑,写出自己阅读本书的感想。
首先,梳理一下我理解中本书的结构和线索。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儒学复兴的历史背景。西汉非承秦不能立国,同时又要避免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这是汉初政治面对的主要问题。为了矫正亡秦之弊,汉初在政治指导思想上崇尚清静无为,制度上采取郡国并行、东西异制,注意尊重东方六国故地的社会风俗。这样的政策有助于缓解冲突、休养生息,但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统一帝国的长治久安。因此,到了文景时期,随着东方政策发生变化,文化整合的进程开始加快,黄老之术的弱点暴露出来,儒术遂逐渐兴起并取而代之,成为汉朝的政治指导思想。这一章是全书的引子。
第二章讨论汉儒两种对立的政治学说:一是贾谊和申公及其弟子的“以礼为治”说;一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以德化民”说。全书以政治史为纲,本章却离开政治史的主线而专谈思想,内容看似也比较枯燥,很容易被读者忽略。但这部分恰恰是作者最初着力突破的点,也是理解全书宗旨的关键。在本书的框架中,此处梳理出的两种政治学说,又演化为独尊儒术以后政治指导思想的两个基本倾向。其中,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的“以德化民”说在汉武帝以后长期居于主导,而同《谷梁》、《左氏》学密切相关的“以礼为治”说则扮演配角与之竞争,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补和强固“以德化民”说的薄弱环节。两者的互动,产生了汉代政治文化环环相扣、不断深入的发展史。以我的理解,这就是书名《〈春秋〉与“汉道”》的命义所在,而此后各章对汉代政治文化演进的论述,也都围绕着这条线索展开。
在思想史层面做足铺垫之后,作者重新转回政治史。第三、第四章即是结合《春秋》学的发展和影响,论述汉武帝以降直到王莽时期的政治和政治文化进程。由于申公及其后学的《谷梁》学不合武帝心意,《公羊》家趁势兴起,占据朝廷高位,并使《公羊》学成为政治指导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武帝的内外政策。昭帝时主政的霍光和其后的宣帝,都基本秉承此前的政策,继续着武帝未竟的事业。这一时期,《公羊》学所持的“王道”与朝廷政策中原有的“霸道”结合起来,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法度”。然而,这一法度杂糅不纯,所带来的吏治苛酷等顽疾也日益凸显,无法让儒生满意。于是,从元帝朝开始,兴起了一场要求纯化“汉道”、“任德教,用周政”的改制运动。起初,《谷梁》学曾一度有凌驾《公羊》之势,但最终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春秋左氏》为核心的古文学。因为,西汉后期的今文学家要求重建先王礼制,却说不清先王之礼的具体内容,而古文学在复原古代礼制特别是周礼的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身兼外戚和儒生身份的王莽上台主政,恰好将外戚集团这一改革最大的障碍转化为推动力量。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学家便与王莽合作,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激进的复古改制运动。在上述历史进程中,武、昭、宣三朝是“以德化民”作为主导思想的时代,西汉后期至王莽则是“以礼为治”对“以德化民”的第一回合的挑战和补充。
接下来的第五、第六两章,除其中一节外均为新增的内容。不过,两种政治思想倾向的互动仍然贯穿其中,只是表现得较此前两章隐晦一些。作者首先论述了《公羊》学重新成为东汉政治指导思想的原因和影响,指出东汉的建立客观上并非简单的汉室“中兴”,相反,刘秀之崛起几乎等同于白手起家,故而只得借助谶纬天命,以弥补其权威和号召力的不足。由于与谶纬的密切联系,今文学特别是《公羊》学因缘际会,随之复兴。谶纬称汉家为“尧后”,东汉儒学受其影响,也宣称要以“尧道”治天下,这就意味着将政治重心从王莽式的制礼作乐转向道德教化。然而东汉中后期,随着豪族社会引起的吏治苛刻、政治腐败等问题日益突出,促使人们对今文学下的教化能否成功产生怀疑,古文学遂再度应时而起。东汉的教化突出“义”,经学研究因而也从注重国家之“拨乱反正”转向探讨个人的修身养性。在这一方面,古文学与今文学没有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却在礼仪的细节方面颇具优势。于是,复兴的古文学家通过以“礼”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再次丰富和强固了“以德化民”说最薄弱的环节。是为两种政治思想互动的第二个回合。
对于“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互动的这条线索,对于思想学术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这样密切的关系,不同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者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预设的任务。他通过思想这个新的维度,盘活政治史研究,写成了一部自成体系的两汉史,并且做出了一系列极富个性的精彩论断。在书中,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发展被描绘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同时又呈现出细致绵密、环环相扣的强大历史逻辑。对于两汉史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现代中国史学建立以来,政治史一直没有成为两汉史研究的重心。在这个传统的史学领域中,现代史家在材料上仍只能以《史记》、《汉书》为主,难以超越前人,而在对史料的熟悉和梳理的精细程度上反倒有所不及。因此,近代以来对两汉政治史最详备的论述,仍当推吕思勉的《秦汉史》。吕著胜在对史料的剪裁和重编,在政治史方面的论述则大抵仍不出旧式“史评”的窠臼。真正为汉代政治史开拓新境的作品,是田余庆先生的《说张楚》和《论轮台诏》。两篇文章的选题与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对历史细节极尽精微的复原上,在分析历史问题的深度上,在从现象纷纭中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方面,全面超越了旧史学,堪称现代史学中政治史研究的典范。我相信,《〈春秋〉与“汉道”》的构思、写作,一定深受这两篇文章的启发和影响。
本书展开线索时,利用了田先生的两个重要观点。《说张楚》的结论之一,是“非承秦不能立汉”。本书接受这个观点,并专辟一节,将之阐发为三个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作者指出,这三点构成了汉初政治的基本格局,同时也是汉代统治者为了避免重蹈“亡秦之迹”必须克服的局限。作者进一步认识到,这正是儒术兴起的重要历史背景,从而抓住了儒术反“秦”并且反对“承秦”之“汉制”这一特征,由此打开了理解儒家“拨乱反正”之术的门径。田先生的第二个观点,是《论轮台诏》中提出的汉武帝政策转变问题。在这一点上,本书受其启发但不全盘接受。田先生指出,汉武帝的主要事业在元封以前已经完成。本书在研究《公羊》学对武帝内外政策的影响时,认为武帝心中对自己的事业有一个三十年的时间表,而元封元年的封禅即是计划中的完成标志。这与《论轮台诏》中的观点是有联系的。但接下来,田先生认为武帝通过颁布罪己诏,改弦易辙,转向守文,并且奠定了昭、宣两朝政策的基调;本书则主张,轮台诏并未全面否定此前之功烈,武帝晚年仍希望后人继续完成自己的事业,并将霍光、宣帝之治视为武帝事业的继续。在作者看来,汉朝坚持“霸王道杂之”而不能真正转向“守文”,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儒生下一波攻击以及改制运动的原由。田先生深挖政治史的细节,获得了两个重要的点。而这两个点,在本书中已经被拿来系联在了一条线索之中。
在此,我们遇到了本书与以往政治史研究的一个不同之处。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胡宝国先生语)。他首要关注“点”的问题,只有画出的“点”足够多,才会顺势将之连成“线”,比如,《东晋门阀政治》;当他认为“点”还不够多时,便停止于此,不再去尝试连“线”了,他的西汉史研究就是这样。本书作者则不然,他真正关注的是“线”。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点”连起来成为“线”,如何将历史发展描述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过程。在本书中,作者关注的线是两种政治思想互动下的“汉代的政治变迁”。书中对细节的研究大多紧扣着这条论述主线,或者说是被“线”所牵引而出的。细节研究所得的结论,也都能够服务于这条主线。如果我的猜测不错,作者在搜集和处理这些细节时,心中应该已经有了一条线索,即便当时它还比较模糊。
在史料欠缺的历史时段,画“线”之前往往无法积累足够多的“点”,由“线”带“点”便成为进行较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的原因。由“线”带“点”的方法还造成了本书的一个特点:整体性。书中的一些章节如果拿出来作为单篇论文,或许不能够十分出彩,但将它放回书中,却立刻成为全书论述不可缺少的环节,在整体中彰显出重要的意义,作者在其中的深意也随之一一凸显。因此可以说,本书不是一本论文集,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专著。
本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也是能构成长篇的重要原因,是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作者自己将这个视角称为“政治文化”。在我看来,“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引入中国史学后,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和宽泛,不再限于本义了(我并不是反对这种变化)。如果要更明确地归纳本书的视角,我倾向于将之称为“带着思想史的意识看政治”,或者说“思想史视角下的政治史”。书中所真正关心的对象归根结底是政治史,思想史只是用以理解政治史的一个维度,一种解题模式。因此,对本书的写法,我有一个与作者不同的表述。我认为,本书是以两种政治思想的互动为线索,来解答“政治变迁”这个问题。(也因为如此,从思想史角度来阅读本书的读者,或许要对书中的有些内容感到不解甚至失望了。)当然,如何表述不重要,重要的是:本书利用思想史这一视角或者线索,系联起政治史上散乱的点,使得两汉政治变迁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完整、系统而且逻辑连贯的整体解释。这在汉代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