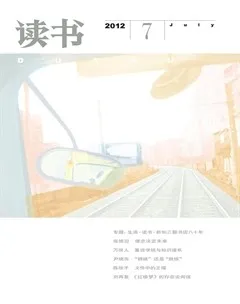我与《读书》
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北大研究生,到北京来读书。大概在一九七九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报刊亭看到《读书》,被她朴素、大方的封面吸引买了一本。读过之后感到与“文革”中读的《学习与批判》和当时的正统刊物完全不一样,有一种清新而活泼的气氛。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是我所敬仰的学者撰写。以后只要看到《读书》就一定要买回来读读。
大约是在一九八○年,《读书》编辑部的王焱到北大来找一些研究生座谈《读书》,并约请大家为《读书》写文章。当时的座谈会就在哲学系研究生的一间宿舍里举行,参加者大约有十来人满满坐了一屋子。参加者都是我们那一届的各系研究生,我记得有钱理群、温儒敏、刘笑敢、张隆溪、胡平等。这些人现在都是“大腕”了,但当年还是默默无闻的学生。当年王焱极为儒雅、谦虚,他介绍了《读书》的宗旨、风格,希望我们支持《读书》,为《读书》写文章。那个会没有瓜子糖果,没有茶水饮料,但开得十分热烈,气氛极好,好久没有参加过这么务实而亲切的会了。
受王焱的鼓励,我也就不知深浅地向《读书》投稿了。先是写一些“品书录”中的小文章,我记得自己介绍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等。这些文章都发表了,给我以很大的鼓舞。当研究生时,厉以宁教授曾以他和罗志如教授合写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为内容开过一门课,并组织我们进行课堂讨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八二年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又认真读了一次。阅读中,感到这本书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有许多新意,于是就想写一个书评。当年的思想界还没有现在如此开放,许多传统的框框还没有被打破,想写的许多想法不敢写出来,但仍想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写一点与传统观点不同的东西。
《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自然是写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讲帝国主义传统的思想框架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本书我上大学时就读过几遍,但读完《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之后,深感《帝国主义论》只是一本政治著作,以帝国主义的垂死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尽管当时我还没想到从根本上否认这个观点,但感到它并非严肃的学术著作,个别观点仍然是可以探讨、发展的。顺着这个思路我写了一篇题为《一本崭新的书》的书评。我所强调的“新”是思想与观点的新。我的书评就想探讨当年许多人思考的“帝国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问题。根据书中的论述,我提出这就在于英国通过各种政策调节使“今天英国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英国经济崩溃的力量是“英国全民族较高的科技文化水平及资产阶级民主意识”,以及“福利政策的作用”。这篇文章于一九八三年发表在《读书》第一期上,以后还被《中国日报》译为英文转载。
在《读书》发表了我第一篇五千多字的书评给我极大鼓励,以后沿着这条路子写这种借书谈自己思想的书评,直到今天。
当时整个学术界对西方的社会科学仍以批判为基调,当年考研究生时我的专业名称就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学习一段以后深感这种做法的荒谬。尽管这是绝对主流,而且当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时高时低,且有一批左得可爱的人拿棍子随时准备打击不同声音,但我深感这个误区不破,学术没法发展。于是就在几经思考之后写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开放》的文章。这篇文章借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的言论来反对一概批判的做法,主张有批判有吸收。表面上是公正兼顾,而且没有违背革命导师的教诲,实际上是要以学习、吸收为主的。这篇文章也发表在《读书》上。我沿着这个思想,又写了不少文章,越写越“赤裸裸”了。我记得有一篇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
九十年代初我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期间深感经济学发展之快,我们之闭塞,回来后写了一篇《重要的还是学习》,在《读书》发表之后受到好评,据说李慎之先生夸奖了这篇文章,直到十多年之后还经常有人告我说他们读这篇文章所受到的冲击。大概也由于这一篇文章和其他文章我在一九九七年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二十八人的名单。我记得这个名单上许多人都经常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由此可见《读书》对自由之追求。
我喜欢《读书》的风格,她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而又包容、宽厚,让作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受约束而写自己爱写的文章,坚持自己对或不对的思想。即使在“八九风波”之后也不改变自己的风格。我在美国时听说有人以《读书》为线索来探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而且写成了博士论文。我没有去查证这一说法,但我相信《读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极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影响力。以后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这段历史时,绝对不能不重视《读书》
从美国回来后,我深感自己的数学基础决定了我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于是决定写通俗类的文章普及经济学知识。所写的许多文章陆续发表于《读书》。以这些文章为主,我的第一本文集《经济学的开放》收入“读书文丛”中,一九九九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读书》不仅为我发文章,而且帮助我写文章。记得当年我曾想写一个“西方经济学系列”,写过几篇而且也发表了几篇之后,王焱告诉我《读书》的风格是轻松、活泼、有趣,要让大家休闲时躺在床上也读得津津有味。回想我写的不少文章还是学究气浓重,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文风,现在看来,努力付出了,进步也是有的,这就要归功于《读书》给我的帮助。
在王焱之后和我联系的是贾宝兰女士。她为人忠厚,工作极为认真,对我们这些作者,既热情帮助,又真心相交,我的所有文章都是她作为责编发表的。以后又认识了编辑部的其他朋友,我深感《读书》编辑部作为一个整体,有思想、有风格,极为认真尽责,其中“五朵金花”早已在读书界和思想界大名鼎鼎。
《读书》不仅发表了大量优秀文章,而且还组织作者的交流活动,无论是专题研讨也好,“读书日”也好,都是读书人交流的好机会,参加这些活动不仅让我认识了更多的人,而且也获得了许多思想,得到了不少启发。这种活动“清茶一杯”,但大家感到极为愉快而有益,每次都空手而来,满载而归。
现在年龄大了,精力不行了,加之外出讲课多,给《读书》写的文章少了,但每期《读书》我都认真看,从中仍然能感受到她当年的那种风格。年轻一代不仅继承了老《读书》的传统,而且把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使《读书》能与时俱进,永领思想界之新潮流。
《读书》是三联书店创办的,她的风格正体现了三联的宗旨,她的成功也是三联对文化贡献的一部分,我与三联的友好关系,《读书》就是最重要的纽带。人要有归属感,要有心中的偶像,要当“粉丝”。我永远是三联和《读书》的“铁杆粉丝”,愿意在三联和《读书》的引导下不断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