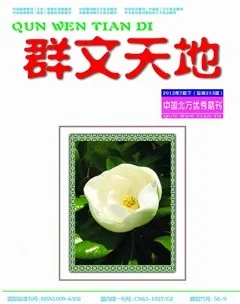多样化和米提斯的力量
《国家的视角》一书是作者对现代大型国家项目失败后的反思,既结合了国家层面的宏观视角,又从城市设计、农业集体化、农业种植的细微经验入手,是一部比较研究的巨作。其中对单一化与多元化、知识帝国主义与米提斯的论述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一种普适性的自然法则是否存在?如何处理高度抽象的科学原理与土生土长的地区实践知识之间的关系?国家对地区的统一规划利弊何在?这都是这本书带给人们的思考。
作者斯特林教授在本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极端现代主义在现实中进行实践的例子。从勒库布西耶对直线式城市布局的偏爱,到巴西利亚城市分区的井井有条,再到坦桑尼亚被整齐规划的农村,我们看到的是多元化被抹杀,所有的独特性的特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统一规划。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巴西利亚市政厅前面的广场在周围建筑的包围下显示出不可侵犯的神圣威严之感,虽然广场是供人们聚会、休闲娱乐的,但是人们在这个广场上并不能感到一点轻松愉悦的气氛,反而被这种权力的至高无上感所同化。同时,被规划好的道路没有往日熙熙攘攘的街角生活,人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来来歇歇脚,喝杯咖啡,与别人聊聊天,也不能找到一间楼下的杂货店在自己忙碌的时候帮忙看管一下公寓的钥匙。农业种植由国家派来的农业部专家进行统一规划,甚至需要将已经建好的农舍进行移动以保证这些建筑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实际上当地的农民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中了解了土地的习性,能够根据土地的特征进行不同的农作物的种植,看似杂乱无章的天地实际上包含了来自实践的智慧。这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米提斯"的概念,即从生活中得出的,但并不是经由正规的科学实验得出的知识,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来自于民间的智慧。
作者在本书中批判的是极端现代主义,这是一种将理性和规则运用到极致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后果是表面的整齐划一和内部的死气沉沉。极端现代主义有着不同的目的,有的是建筑家为了追求极简美学,有的是因为政府需要加强对国家的控制。当然,这些项目也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藏在这种行动的共同点中:他们将一切都简单化了,忽略了独特性,消灭了多元化。独特性是米提斯生长的土壤,当适应于当地独特的生活习惯、劳作习惯被强制性地打破时,统一的标准对于当地来说可能并不适用,甚至会造成负面的结果。例如书中所举关于玉米种植的例子,单一品种玉米的种植使这些玉米染病的情况大大恶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植株间密不透风的位置,导致了病毒会很快在玉米中传播开来,对玉米的收成产生很大的影响。同质化虽然便于管理,也能短时间内提高产出,但是这种忽视当地情况并抹杀了独特性的行为并不能获得长期的收益。
当前的社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飞速向前发展,从近代的泰勒制到今天学者们对麦当劳化的反思,科学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科技为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人们也在思考,机械代替了众多的人类劳作,那些积累下来的生活智慧、因日常活动而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会不会因此而淡化甚至消失。理性化指导着人们向着更方便、更快捷、更程序化的方向前进,然而韦伯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了对理性的反思。韦伯思想中对理性最具有代表性的描述之一就是“理性铁笼”的概念,韦伯认为科层制将人们置于各个层级中,公式化、官僚化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原本作为工具的理性将人们束缚于一个铁笼之中。由此可见理性的力量若使用过度,就很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本书列举的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例,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说,这本书强调了来自于生活的日常智慧的重要性。这些智慧承载了当地居民的父辈记忆,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中包含了当地的人文、历史、气候、地质等一系列事项的记录,也是人们如何适应这里的生活的印证。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极端现代主义对城市、乡村的规划世纪上体现的是国家与地方的断裂,是国家运作思维与地方实践逻辑的冲突。国家通过统一的住房、街道和农业技术打造了一个个十分便于管理的居住点,但是这其中被忽视的是地方独特的运作体系。两者的断裂导致了国家推行的集体化产生了无效率的后果。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正是由于多元的文化、多元的区域、多元的方法,整个世界才显得生机勃勃。如果理性化和现代性被运用到了极致,带来的并不是幸福的敲门声,反而是实践逻辑被打破,混乱即将来临。我们从本书出发,从国家的视角可以转向生活的视角,可以转向世界的视角,也可以转向学科的视角,虽然视角不同,但是本书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保护好米提斯生长的土壤,给时代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