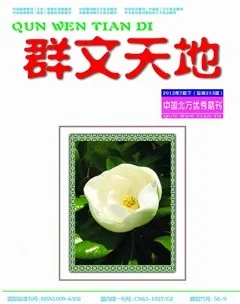政治童谣的发生机制与功能分析
摘要:政治童谣的本质在于其政治针对性和目的性。本文认为,政治童谣之所以能够发生和长期存在,并广泛影响社会政治进程,既与童谣自身的特征——与天命神意紧密关联、童谣传达主体的独特性、童谣创作主体与传达主体的分离——密切相关,同时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滋生土壤。此外,政治童谣由于有强大理性精神和政治军事常识的注入而偏离了它的本来性质,承担其重要的社会功能,既作为传到社会民众诉求的渠道,又演变成为权谋家的政治斗争工具,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政治趋向做出几乎确定无误的判断,从而在历史进程中产生持久而广泛的作用域。
关键词:政治童谣;发生机制;功能分析
童谣者,“儿童歌讴之词”,亦即传唱于儿童之口、不掺杂严格的乐谱规律的歌谣。从总体上看,童谣隶属于民间文学(民间歌谣),是民间文学中一支最绚烂的花朵。童谣的创作与民间歌谣的创作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就开始了。清人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把“儿谣、女谣、小儿谣、婴儿谣”等统归为“童谣”。按照内容划分,童谣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政治类童谣、生活游戏类童谣、益智常识类童谣和传统道德类童谣。本文所关注的是第一种也是占主要地位的政治类童谣,主要探讨的是政治童谣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功能。
一、政治童谣的本质
杨慎在《丹铅总录》卷二十五中云:“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这就说明了童谣与其他歌谣的一种共性,即都是人类籍由语言的自然节奏来强化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等情绪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因而从根源上看,童谣具有纯真性、非理性和非政治涉入性等特征。然而,不论是从传统典籍中,还是在刘秀之兴、董卓之败等史实里,无一例外地均有童谣的预测和参与。历史上利用童谣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和事亦不胜枚举,从褒姒祸周、荧惑之说到更始,童谣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受到政治家和权谋家们如此的青睐呢?政治童谣又是何以可能的呢?按照现代功能主义的观点,一种社会结构或社会事象的存在是由于其在整体中承载着某种特殊的功能。那么政治童谣的功能何在呢?在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政治童谣的概念和本质做出清晰的界定。
政治童谣,顾名思义,是指携带了某种政治意图和指向而以儿童之口传唱的歌谣。这类童谣或褒贬捭阖,或颂扬清官廉吏,或赞扬农民起义领袖,或反映人民的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或揭露统治阶级剥削的残酷,或鞭挞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或揭示吏治的昏聩黑暗,或预示统治阶级的灭亡,等等。但是,仅仅作以上表面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是政治童谣中明确的理性参与特征——政治针对性和目的性,这才是政治童谣的本质所在。亦即,政治童谣在本质上不过是政治家或权谋家们借以实现自己政治企图的工具和手段。
二、政治童谣的发生机制
基于以上对政治童谣的概念与本质的界定,本文认为,政治童谣之所以能够产生并长期存在,并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做出某种预测对社会政治的走向施加影响,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这是由童谣的自身特点决定的。
其一,我国童谣自产生之初就与天命和神意结下了莫大的关联。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杜成宪教授的研究,中国传统童谣之源当追溯于西周末年。《国语·郑语》云:“宣王之时有童谣日:‘繁弧箕服,实亡周国。”征诸典籍,宣王时的这个童谣应是现存最早的童谣。那么这个童谣讲述的是什么事情呢?“繁弧箕服”,指山桑木做的弓和箕草做的箭袋。这短短的两句话是说:那卖桑木弓和箕草箭袋的,就是使周灭亡的人。据说当周宣王听到这首童谣时,即下令捕杀售卖弓箭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逃亡途中适逢宫中小妾所遗之女婴,哀而收之,奔于褒。幽王时,褒人得罪于周,献此女示好,是为褒姒。幽王十分宠爱褒姒,为博红颜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致使诸侯日渐远之。当外敌真正入侵时,烽火却再也招不来救兵,幽王遂被杀于骊山脚下,西周亡。那首童谣就这样离奇地应验了。由此,童谣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异样的面貌,与儿童自身的生活毫无瓜葛,而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致使本来与兴亡大事毫不相干的黄口小儿竟成了诡谲动荡政局的预言家和天命与神意的传达者。
其二,童谣传达主体——儿童的纯真性和“特异性功能”。儿童自古以来,即因为其纯真的本性而广受社会的认可,正所谓“童言无忌”,儿童的话语虽然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不成熟的而予以否决,但是它的本真性确实不容置疑的。至于“特异性功能”也缘起于上述“繁弧箕服,实亡周国”的童谣,它不仅为政治童谣的真实性找到了合法合理的起源和依据,而且也赋予了儿童以广为社会认可的传达天命神意的能力。所以,每当某种政治趋势和社会变迁由诸多儿童之口传达出来的时候,它所能引起的社会共鸣是其他任何主体的叫嚣所不能相比的。这也正是政治童谣能够产生社会作用的基础。
其三,童谣创作主体的多元性与传达主体的单一性特征。童谣的创作主体无非有两种。第一,儿童出于自娱娱人的目的创作出来而后在儿童群体中广为流传。这类童谣是最为纯正的童谣类型,它在创作过程中不含有任何的其他成分介入,纯为儿童自娱自乐之用。而从史籍文献中能够发现的这类童谣数量少之又少,主要包括前文所述的生活游戏类童谣。第二,由时人有意无意为之,后经直接间接的途径在儿童中广为流传开来。这种类型的童谣的纯正度则有大可质疑之处。传统典籍中记载和传留下来的大多都属于这类童谣,前文所述的政治类童谣、益智类童谣和传统道德类童谣多归属于此。它们所以能够传承下来,原因也较为显著,即它们均承载着创作人不同的目的,因而具有看意义性。如前文所述,童谣的传达主体——儿童,具有广为社会认可的纯真性,并被社会赋予了某种“特异性功能”,因而,一旦某种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歌谣由众多儿童之口传达出来的时候,不管这种目的性和针对性对社会大众而言是多么的不可接受或者多么不真实,它也能产生强有力的社会影响和一定的作用域。而童谣创作主体的多元性恰好又为政治家和权谋家们将自己的特定目的注入童谣之中提供了绝好便利,进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故而,童谣创作主体的多元性为政治童谣的长期存在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其次,通过对古代政治童谣的消长规律的认识,我们也能窥见政治童谣发生与延续的端倪。据湖北师范学院舒大清教授的研究认为,“童谣和变乱有最密切关系,矛盾尖锐、大变将起的时候,总是童谣活跃的黄金季节,表明童谣有为人们指引未来政治方向的作用;时代越长,童谣越多,反之则少,是因为时代长,变化就多,因应这种变化的童谣就多,反之则少。”可见,童谣的产生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滋生土壤的。政治童谣的产生同样导源于深刻的社会政治危及。人们往往会在政治急剧混乱、统治极度腐败之时,借助童谣来传达社会呼声、制造变动氛围、引起社会共鸣。
三、政治童谣的社会功能
可以看出,上述政治童谣只不过是一种对具有某些确定性的结果的再称述而已。应该说,历史上的政治童谣,绝大多数是这种以政治常识理性作为基础的预言,那么它们能够正确预见未来政治结果几乎就是必然的了。这样,政治童谣实际上是承担了一种为失范社会的重组充当先锋的功能,即一方面成为社会民众传达特定诉求的渠道,预示“天命”转移和归属;另一方面充当权谋家的政治斗争工具,影响社会历史进程。其中,不论是社会民众的诉求,还是权谋家们的别有用心,理性成分的参与都将赋予童谣某种独特的、以发起社会行动为指向的社会意义,这种社会意义的广泛扩散必将在童谣在作用域内产生应有的效应并最终引发必要的社会重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政治童谣之所以能够发生和长期存在,并广泛影响社会政治进程,既与童谣自身的特征——与天命神意的莫大关联、童谣传达主体的独特性、童谣创作主体与传达主体的分离——密切相关,同时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滋生土壤。同时,政治童谣由于强大理性精神和政治军事常识的注入而偏离了它的本来性质,演变成为传到民众诉求的渠道和权谋家们的政治斗争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政治趋向做出几乎确定无误的判断,从而广泛持久地影响社会历史进程,这即是政治童谣所承担的重要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儿歌之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顾素芝.点点滴滴话童谣[J].安徽文学(评论研究),2008(9).
[3]张梦倩,杜成宪.“荧惑说”与“童子之情”——从童谣的历史变迁透析传统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J].教育学报,2009(6).
[4]舒大清.论中国古代政治童谣的消长规律[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作者简介:徐吉鹏(1992.2-),男,湖北十堰人,本科,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09级社会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