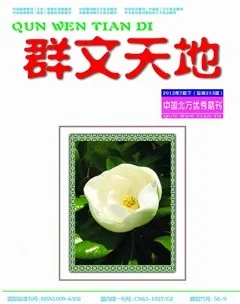唐代妇女地位初探
摘要:现代社会,婚姻自由作为男女平等的一项重要标准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普及,女性也可以自主的掌控婚姻存废。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长期处于夫权父权控制下的妇女,其对于自己的婚姻往往没有选择权,这不仅体现在不能任意选择如意郎君,也表现为无法在婚姻生活不幸的情况下自主解除婚姻。受胡风影响的唐代的文化开放和包容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本为旨在就唐代关于离婚制度上的研究,探索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自由程度。
关键词:唐代;离婚;制度;妇女地位
“离婚”,是指依照法定的手续解除婚姻关系。受传统婚姻观念的制约,在中国古代,离婚与结婚一样同为关系到两个家族的大事,选中一门好的亲事,整个家道都有可能随之振兴,反之亦然,是故婚姻历来受到从上到下的一致重视,因而离婚制度也成为是社会关注的重心。与现代完全不同,中国古代妇女在婚姻方面的发言权是微乎其微的,她们很难对一门父母定下的亲事说不,也很难主动的逃离一段不幸的婚姻。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放的时代,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相对薄弱,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黎民百姓,妇女的再嫁和改嫁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那么,在同样能体现婚姻地位是否平等的离婚方面,唐代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通过对唐代离婚制度的探究,我们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对当时妇女离婚状况进行了解,并希望能依此对当时妇女的地位略窥一二。
一、“出妻”之离
出妻是古代最常见的终止婚姻的形式,也是古代夫权压制在妇女身上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一点在唐代也没有多大的改观,“七出”就是这一现象的制度体现。“七出”原名叫做“七去”或“七弃”,《大戴礼记·本命篇》曰:“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从实质来看,其目的不是为了保障婚姻的持久,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家族利益,在其实际执行当中,也给男子离婚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如北陵虔亭儒家之女慎氏与严灌夫结为姻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年无嗣息,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①;又如“回秀母少贱,妻尝詈媵婢,母闻不乐,回秀即出其妻”②。不管是因为无子的原因,还是家长不对为妻的有不满,都可以成为男子抛弃妻子,与之离婚的理由,更有甚者因妻子年老色衰而想方设法找着借口出妻,可见“七出”之制实为夫权压迫妇女之显著体现。
如果任由这种制度漏洞存在,恐怕唐代也无法号称中国历史上典章制度完备的典范。在“七出”之外,唐代有“三不去”来限制出妻,这种独特的制度设计让人眼前一亮。所谓“三不去”是:“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③。从制度层面上讲,这是对于妇女婚姻的一大有力的保护,防止无限制的出妻行为;然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三不去”的限制作用却是相当的有限。唐代诗人张籍的诗作《离妇》很好的反应了这一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离……昔日初为妇,君当贫贱时……洛阳买大宅,邯郸买侍儿,夫婿乘龙马,出入有光仪”④。这一典型的因无子而出妻,无视“三不出”中“娶时贱后贵”之条的例子,深刻的反应出在当时的民间,“三不出”对于“七出”的限制是很有限的。如果将“七出”作为离婚的必要考虑因素的话,那么“三不出”只能算作选择性考虑条件,是否真将“三不出”纳入决定离婚与否的考虑要素当中,其关键在于男方家庭的主观因素。如此看来,尽管有制度上的“三不出”的保护,倘若夫婿要出妻,唐代妇女除了诉讼一途外还是没有办法抗拒这一命运,而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婚姻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且不说成功的可能性,在甘愿背负风险的同时还需要很大的勇气。
二、“和离”
类似于今天的协议离婚,唐代也有所谓的“和离”。和离是由于双方的感情不睦而导致的离婚,既可以由男方提出,也可以由女方提出。《唐律疏议》中有关“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⑤的规定可以明确告诉我们,“和离”这种情形确实是存在的,且不会带来任何的不良后果。《太平广记》载“(李)逢年妻,中丞郑昉之女也,情志不和,去之”⑥。这里虽然没有写明两人是和离,却点明李逢年去⑦妻是因为“情志不和”,而非其他属于“七出”之列的名义,也不属于下文将要讲到的“义绝”。由于当时不允许没理由而随便出妻,或可以推测两人是和平离婚。
有一个例子,也可以从反面来印证上面的推测。唐宪宗时,户部尚书李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庆之孙,性柔弱,元素为郎官时娶之,甚礼重,及贵,溺情仆妾,遂薄之。且又无子,而前妻之子已长,无良,元素寝疾昏惑,听谮遂出之,给予非厚。”妻族上诉,诏李元素以出妻免官,另给王氏钱物计五千贯。可见唐代官员是不能随意出妻,赔偿女方经济损失事小,丢了乌纱帽事大。考虑到上文提及的李逢年和郑昉皆为中央的高级官员,应同样有类似于此例的考虑,是故在没有“七出”和“义绝”之实的前提下想要离婚,似乎只有“和离”一途可行。
比起“七出”和“义绝”来,“和离”这种离婚形式要平和得多.它尤其顾及到了女方的声誉和地位。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这一离婚形式下,法律将男女双方置于同等的法律地位,双方共同决定婚姻归于消亡,这是对女方权利和地位的一种肯定。女性的解放程度,唐以前诸代似乎无法与唐比拟,然而也不能说唐代女性毫不受封建礼法的制约,因此像这种“和离”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不过,就此时已经出现的小部分和离事件来看,唐代妇女在关于婚姻的存废问题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尽管这种发言权尚无法变成决定权,至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可以加入自己的想法行事,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风尚的进步和对妇女地位的肯定。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强调一次,“和离”这一离婚制度,仅仅是唐代离婚制度体系中的一项.并不具有对抗七出和义绝的效力,当男方行使“七出”权利的时候,“和离”便不可能成立。
三、“义绝”而离
义绝,是我国古代十分具有特色的一种离婚制度,“义绝,谓‘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夫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的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及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⑧。在古人看来,夫妻关系是通过“义”来维持,这种“义”是基于基本的人伦道德向对方家族承担一定的义务,因而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更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是故“义绝”所列范围全为两个家族关系破裂之情形。
“义绝”是由政府判处的离婚,形式类似与如今的诉讼离婚,但不是由存在婚姻关系的双方主动提出,它更像是两方家族之间发生重大纠纷后的衍生产物,因为没有“义绝”行为的产生,就不存在“义绝”离婚的情形,其不能如“七出”一般单独成立。
细看形成“义绝”的几个条件,我们不难发现除“夫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一条外,其余诸项当中,妻方要负的责任明显大于夫方,这点不仅体现在夫家与妻家对于同一义绝构成要件的标准不相同:如夫对妻方亲属有殴、杀行为才构成义绝,而妻对夫方亲属仅有骂、伤行为就构成义绝;又如妻与夫缌麻以上亲属相奸构成义绝,而夫只有在与妻母通奸时才构成义绝。此外,“义绝”只承认妻害夫作为成立义绝的条件,夫害妻则不属于该范围之内,这是明显的不对等责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具有行政规范意味的“义绝”可以作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来判断婚姻结束,也对夫方伤害妻方利益进行了限制,但其充斥着强烈的男权思想,两方的责任负担完全不对等,实质上也是对唐代妇女的一种轻视和压迫。
四、结语
离婚问题作为古代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不是特别常见却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虽然不能完全展现出古代妇女在社会生活当中实际所处的地位,却也将夫权和父权社会下妇女的悲惨境遇真实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总体来说,唐代的妇女和中国古代其他任何时代的妇女一样都免不了落入“在家从父,既嫁从夫”的俗套,尽管制度的保证使得她们在婚姻问题上有了一定的选择权和发言权——如“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⑨,甚至在部分地区出现过“弃夫”的情形——如“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病,到处求医问药。有一白衣妇人,自言医术精湛。卢佩遂具六礼,纳为妻。妇人朝夕供养,妻道严谨。但卢氏母子以为妖异,对其猜疑。妇人遂离家而去,改嫁靖恭李谘议。卢佩悔之莫及”⑩,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男尊女卑的权利地位差距,在民间男子依旧可以不受“七出三不出”的约束对年老色衰、不符心意的妻子弃而不顾,父族也同样可以违背女子的意愿,随意将女儿嫁给选定的人选。
我们现今研究这段历史,如果只是聚焦于古代女子是如何饱受压迫、没有自主权上,希望揭露古代社会礼教的害人一面,痛斥男权对女性的侵害,那么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段历史也将变得没有多少价值。当今社会,男女不平等之情形依旧存在,细看之,多数情况可谓是古代礼教之翻版与革新,为什么我们将礼教害人、男权欺压的一面深刻地揭露出来却还是没有阻止其“死灰复燃”呢?这恐怕不是仅仅用一个封建残余就可以概括回答的问题。
注释:
①《太平广记》卷271《妇人二·慎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136页。
②《新唐书》卷99《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14页。
③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14《户婚律·妻无七出而出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8页。
④《唐张司业诗集》卷七《离妇》。
⑤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14《户婚律·义绝离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8页。
⑥《太平广记》卷242《谬误以往附》,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72页。
⑦《旧唐书》卷132《李澄附李元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58页。
⑧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14《户婚律·妻无七出而出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7页。
⑨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14《户婚律·夫丧守志而强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5页。
⑩贾艳红:《唐代妇女离婚类型浅析》,《济南师专学报》,2002年2期,第64页。
(作者简介:曾 恺(1991-),男,湖南邵东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基地班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