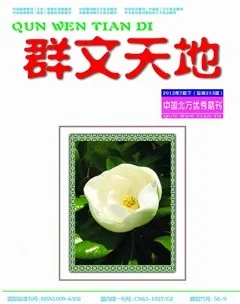论阎连科小说中的语言选择及表意策略
摘要:小说修辞学强调作者写作的意图,即“作者为谁写作”,事实上包含两个问题:“为谁写”和“怎么写”。作为作家的阎连科,豫西方言已成为了其的“终极词汇”。在《日光流年》中,他通过对方言词语的重视与叙述,让小说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让文学回到底层,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呐喊。方言已经成为他自觉表现“底层命运”与“人类困境”的主要语言策略之一。
关键词:《日光流年》;阎连科;方言;表意策略
引言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强调作者写作的意图,即“作者为谁写作”①,事实上包含两个问题:“为谁写”和“怎么写”。每一个作家,既是作者,也是读者,阎连科一直也在强调自己的读者意识:“直到今天,我们敬仰三十年代的文学,敬仰三十年代的作家,除了敬仰他们的作品以外,还敬仰他们对‘劳苦人的命运’的书写。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劳苦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越来越明晰地构成了我写作的核心,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写作的全部内核。”②
在确定“为谁写”的同时,他也开始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即“怎么写”才能达到与读者的有效沟通。在其代表作品《受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中,他通过对于语言结构的发现与选择,达到了对方法的完成,如李陀所说,他并不是为了某些抽象的美学意义而去追求语言的独特性,而是出于表达的需要,努力寻求语言与其社会批判意识的融合。
(1)“命通”与“命堵”
在《日光流年》(1998)的开篇,作者留下一段话:
“谨以此献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③
“遗言”,最通俗的解释为“临终时的话”,对象为活着的人。这里构建出一种写作的“当下”性与“交流”性。而“遗言”作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表述,它带有某种权威性与诚恳性,于是也具有了某种规劝性。同时,“遗言”是介于生与死之间的对话,它必定与命运具有某种强大的关联性,昭示着某种神谕般的启示。而整个文本果然就呈现出一种“生死挣扎”的状态——为了对抗不让“三姓村”人活过四十岁的“喉堵症”,杜桑、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等四任村长带领村民通过种种方式与命运进行抗争,而最终失败。
“喉堵症”是“三姓村”这个在历史记载中不存在、在地图中未曾得到标示的山村所特有的。由最初的黑牙病、关节病最终死于喉堵而来,而且村民的寿限从六十岁慢慢减至五十岁,又减至四十岁,最终到了人人都活不过四十岁的境地。因为“喉堵症”,而产生了一对“三姓村”独有的方言词汇:“命堵”与“命通”。“命堵”一词在文本中是有双重意义的,首先是对命运的看法,认为“喉堵症”导致人寿命的缩短,人处于“命运不通”的堵塞状态,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抽象化;同时,它的来源却是具体的,是对具体历史事件——由村长司马蓝主张的修灵隐渠,引水入村,益命长寿的一种带有地域色彩的概括。“命堵”与“喉堵症”有着相同的具体事件指向,但它加入作者想要传递给读者的带有某种神秘意义的命运观,“命堵”一词在意义指向空间比“喉堵症”范畴扩大了许多,达到了与现代汉语中“命运观”的某种契合,因此取消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隔膜,拉近了叙述者与受述者的距离。
同样的,“命通”从具体的事件指向来看,是对修渠的看法,认为修渠就是通命,渠通了,命就通了。虽然“渠通”与“命通”在文本的具体语境中有着相同的指向性,甚至可以互换。但是进入语言层面之后,两者在概括意义上的指向具有了不同的空间。“命通”从字面上已经离开了具体的事件,成为一个独立的词汇,有了不受事件影响的外延。
我们可以从这一对方言词汇的产生,可以看出语言一旦被抽象成概念,具体的事件意义就慢慢地被取消了,而扩大了理解的空间。如果从“真实”的角度上来讲,事件的“真实”被观念的“真实”已经慢慢取代了,即便是方言,它本身也是具有概括意义的,虽然有“原始性”的特点,但是仍然是一种抽象概念。真正本真性的语言,在方言中也未必能得以实现,但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作者是尽可能地还原某种“真实的生存”困境,它比共同语仍然更具有单一情感指向性。
(2) “合铺”与“分铺”
《日光流年》中以司马蓝、蓝四十、杜竹翠三者在婚姻上的相互制约与纠缠,提到了两个方言词汇:“合铺”与“分铺”,“铺”当然指的就是床铺,男女正当地结合为“合铺”、男女感情破裂分手为“分铺”,把婚姻关系直接定义为肉体关联。这是三姓村人对于婚姻表达看法的两个重要词汇,具有婚姻的原始意味,可以与现代汉语中的“结婚”、“离婚”相对举。
在伦理世界的读者理解中,婚姻首先是一种制度,它是男女两性依据一定社会体制内的法律、伦理和风俗的规定所创建起来的夫妻关系,它是组成家庭的基础和根据,同时,也是家庭成立的标志。这个定义意味着婚姻首先是要得到相关法律的认可,取得某种合法性,才能得以实现。这是一定的社会体制以内为维护秩序的行为,将“合法性”作为婚姻的前提。那么,在“三姓村”——这个取消了时空所在的独特封闭空间,以村长集权为主的体制下,取消了现行社会的法规,“合铺”、“分铺”却是以何物为前提的呢?
作为读者,我们对“合铺”与“分铺”进行观察,最初的“合铺”应该发生在司马蓝与蓝四十之间,无论是以他们青梅竹马的感情基础为前提,还是以蓝四十为全村人的“命通”委身于卢主任的牺牲精神,甚至在司马蓝“喉堵症”发作时,为他筹钱而去做“人肉生意”来看,司马蓝都应该选择与蓝四十合铺。
而杜竹翠出于对“喉堵症”的恐惧决定外嫁,而打破了“村里女不外嫁”的公道时,作为司马蓝的村长,为保持权力,只得妥协,同意与杜竹翠“合铺”。这样,司马蓝为了保持公道,维持乡村秩序的进行,不得不背叛与蓝四十的契约,而使“合铺”体现出某种“合理性”。注意,如果说现代婚姻强调的是“合法性”,那在原始乡间,婚姻强调的却是“合理性”,那被“合铺”抽空的是什么呢?是人类的真实情感。在这个复杂的权力社会中,制约着人的情感因素的,仍然是“法制”或“理性”,而不是“情感”本身。那么,“合铺”与“分铺”传递某种关于婚姻的共同感受,从原始意义上达成了与现代意义的某种契合,而让现代的读者能够扯掉法律的面纱,看清笼罩在婚姻之中的权力制约关系,达到对婚姻制度的某种反思。
(3) “教火院”与“冤皮生意”
三姓村的人称县城里的烧伤医院为“教火院”,作者指明其时间为1892年,为英国传教士所修建,最初是教堂医院,1942年之后,日军进驻河南,改之为战场烧伤医院,专门救治战场上的烧伤士兵,日本投降后撤走,但留下异人填皮术,被称为“教火院”,解放后虽然更名为县医院附设烧伤医院,但当地百姓仍称之为“教火院”。
阎连科对“教火院”进行了历史考证,而在正文中仍然保持着民间的用法,所指向的历史停留在解放前。而与“教火堂”相关的则是三姓村人的“冤皮生意”。
“冤皮生意”指的是三姓村人卖皮子的行话,即在卖皮中遇到冤大头,你要多少钱,对方便给多少钱。冤皮生意是从司马南山开始的,时间指向1945年——这是历史叙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而作者所描述的三姓村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与历史毫无关联,“教火院”的日本院长,在1945年的时候,不能以“城北监狱里的中国犯人”、“公路桥下的民工”为活人皮源了,恰好碰到了司马南山,同意将钱甚至烧伤院、整个县城都给他,换取他的活体人皮。这桩生意,在三姓村人看来,是一次“发财的冤皮生意”,为三姓村的生存获取了极大的资源——到青岛买盐和海带。尽管三个月之后,日本人投降,他们的“冤皮生意”本未获得真正的收获,但他们还是认为值得。
在这里,作者故意将叙事指向一个宏大叙事的时空,但从乡间的日常生活来看待战争的意义。伟大的民族战争对他们的生存而言,完全没有意义。日本人的入侵与失败,并不是他们所想要关注的,他们唯一关注是“如何生存下来”。这种极致化的叙事策略,通过“教火院”与“冤皮生意”,解构了历史的宏大意义,而将日常的生存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受中国现代历史浸染的当下读者,在阅读中必然会产生一种新奇的感受,这种历史与“正史”表现出一种悖反关系,反而在日常叙事中呈现出历史与常人的真实关系。
作者通过具体历史事件中的日常叙事,所有传递的,是真实的、与常人相关的历史感受,而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民族国家”的“反侵略战争”历史。作者通过这种叙事,进行回望的,不仅仅是某种乡村苦难,某种历史情境,更是一种真实的人类生存感悟。而在这种感悟下面,若是再去回望“启蒙”、“救亡”等事件——全部由三姓村人的“冤皮生意”转化为无意义的知识分子“独语”,那么人类唯一的意义是什么呢?作者指向生存, 指向人类在生与死之间的挣扎。司马南山“一次发财的冤皮生意”与“日本人投降”并举,作者利用反讽,对历史进行了虚构中的解构。架空“启蒙”,走出“启蒙”,否定“启蒙”,将文学对于人类的思考还原为人类生存的目的——仍然是生存,“活着”得以成为纯粹的“活着”。
自1980年代始,语言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渐渐成为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王安忆就自己的创作经验及阅读经验,对1980年以来在“寻根文学”中对方言、俗语的借用进行分析,认为这是一次“试图从大众语言中寻找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学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④在梁鸿看来,“方言写作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试图改变‘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底层世界的代言方式,试图从叙事者与被叙事者之间寻找新的关系存在。”⑤事实上,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共同语对等级秩序的划分,导致语言分级,方言对特殊“此在”的叙事作用被屏蔽,《故乡》中闰土一声“老爷”,将乡土空间与知识分子构建的文化空间完全隔裂成两个世界,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话的可能性。
要想使“对话”从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语言本身,回到共同的思维方式中。于是,当代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方言”当作“回家”的手段,通过对方言词语的重视与叙述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
当然,对于方言是否能被委以“回归”的重任?看法总是两极的,比如于坚认为“普通话把汉语的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⑥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农民之子,豫西方言已成为了阎连科的“终极词汇”。尽管他所接受的文学素养已经将他的某些内在进行了转化,但是在表达情感时,不自觉地加入了方言因素,在他早期的创作“瑶沟系列”中已经出现了“喜兴”、“地场”、“讨个家业”等方言词汇,对于这种不自觉的广度运用,他个人认为,在当时“完全是一种非自然状态,懵头懵脑,仰仗的是生活的经验和感觉,而不是文学修养与写作技巧。”而到《日光流年》,方言已经成为他自觉表现“底层命运”与“人类困境”的主要语言策略之一。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1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1jytp063。
注释:
①[美]W·C·布斯: 小说修辞学,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10).
②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南方文坛 [J],2004(02).
③阎连科:《阎连科文集(日光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09).
④王安忆: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上海文学 [J],1990(03).
⑤梁鸿: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论阎连科小说语言兼谈一种写作精神,扬子江评论 [J],2007(06).
⑥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诗探索, 1998(01).
(作者简介:鲁红霞(1978.11- ),女,湖北天门人,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学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