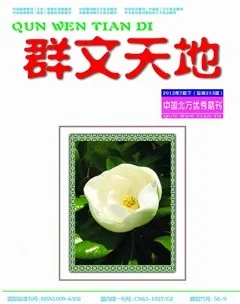拍拍你的后脑勺
杨德昌导演的电影《一一》是一部关于后脑勺的电影,从一开始就是。
在片头,一家人合影时,站在洋洋身后的几个女孩调皮地用手拍他的后脑勺,洋洋几番回头,却无法判断谁是“作案人”。这一特写貌似一个小插曲,其实却为洋洋后来得出“我们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这一结论,以及他为解开困惑而拿起照相机去拍别人的后脑勺这一行为埋下了伏笔。
在《一一》中,人物众多,围绕NJ一家展开,没有绝对的主角,是一部群像式的电影,但片中每一个角色的故事都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洋洋,他鲜活了一部电影。因为他的相机正是导演的镜头,他本人正是导演在影片中哲人式形象的变形。
8岁的洋洋在舅舅的喜宴中就开始苦恼,后来他认为周围的人不相信他,是因为他们不能了解自己的全部;而人们之所以不能了解到全部的自己,是因为人们的眼睛长在前面,只能看到前面的事物,而对脑袋后面的另一半事物就无法触及。为此,洋洋拿起照相机去拍摄别人的后脑勺,希望以此帮助别人看清另一半的事物。
外婆的昏迷是一家人心灵混乱悲戚绝望的导火索。婷婷认为是自己忘记倒垃圾,外婆倒垃圾的时候摔倒才会昏迷的,为此她深深忏悔,无法入睡,只有在深夜悄悄向外婆倾诉自己悔恨与迷茫;洋洋的妈妈发觉几天内向外婆叙述的无非是一些重复的内容,她对着丈夫痛哭自己生命的单调与空虚。NJ,一个非常带有导演自我发掘性质的角色,在片中无法适应物欲纵流,名利熏心的现代商业社会,愤然感慨:“诚意可以装,老实可以装,交朋友可以装,做生意可以装,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尽管他恪持传统的精神操守,却在岳母病床前说:“对我自己所讲的话是不是真心的,好像没什么把握。”既然人们对自我的真实无法界定,既然人们对自我情感的真实性都难以确定,那么,对现实生活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影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信任危机的社会状况:不加节制的物欲和个体的异化。当“先上车后买票”、做生意坑蒙拐骗成为习以为常,导演借此让所有的观众反思都市中的人际关系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是健全完备的,还是根本就岌岌可危。
在《一一》中,有许多镜头是摄影机特意隔着玻璃窗去拍摄的,玻璃窗反光了一重影像,这重影像与窗子后面的影像又交叠在一起。其中,玻璃窗上的影像是根据特定的剧情而精心选择的。当窗子后面的人物陷入焦灼绝望的时候,玻璃窗所反光的影像往往是高耸入天的摩天大楼或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反差极大的两种影像加以叠映,就直观形象地昭显了现代人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世界的苦恼——繁华都市的后脑勺正是个体的扭曲和精神的蒸空。到这里终于理解了NJ无法把握对岳母话语是否真心的原因——人与自身的疏离和隔膜——长年累月地生活在虚伪而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最终对自己情感的真实性都难以确定了。
即使是看到父亲和女儿,分别在东京和台北,同时与初恋情人约会的温馨镜头,我们也只能感叹这是一曲无果而终的悲伤恋歌。以致于NJ在岳母死后诚恳地对妻子说:“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真的没那个必要。”简言之:人活一次,够了。 甚至在影片中最抢眼的洋洋对死后的外婆说:“我好想你。尤其是当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8岁的小孩说出如此老成的话语,很自然地让人唏嘘:天然的生命力在被变态的社会无情地消耗着。
如果仅止于此,杨德昌就不称为杨德昌了。镜头内的洋洋拿着作文本对着婆婆的遗像读着:“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镜头外的杨德昌也对着观众深沉地诉着同样的话。他设置着片中个体种种绝望的方式与心态,进行着着力于道德层面的社会批判,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某种希望的启示:NJ、大田、婷婷都拥有纯真、善良、正直的心灵,他们存在生存的苦恼与悲伤,但从未丢失生命的音乐,并永久地贮存在心里。现代人要想走出歧途,必须拍拍自己的后脑勺,发现并守住自己的善根,由独善其身延伸到矫正整个社会的异化。
影片中的一家人饱尝生活的重压,在艰辛的挣扎中仍努力地活着,外婆的离去,新生儿的来临很具象征意味,从中得到的最直接的“形上”启发是“一一”像生命的绳索,虽遭外物砍扯,时有断痕,却一直延续向前。所以用手“拍拍”自己的后脑勺,用心拍拍生命的后脑勺,回归纯真,善待人生。
(作者简介:孙 薇,苏州大学文学院10级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