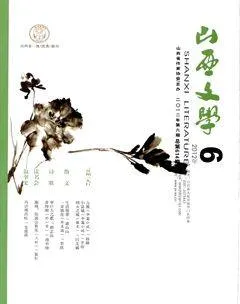剃头过年(外一篇)
民间谚语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过年要剃头,其意义主要在于图个吉利,图个新气。一年忙到头咋也得把自己收拾得干净点、利索点。置一身新衣裳,买一顶新帽子,选一双新鞋子。没钱的这一切都可以省了,但剃头是不能省的。有钱没钱,剃头过年,这是老辈的教导。年关前的理发店生意红火得不得了。打师傅们一大早开门迎客,电推子就嗡嗡地一直响个不停,落发像雪片一般,瞬间铺满一地。服务员忙得团团转,又是洗头,又是洗毛巾。顾客来得早的,坐着,来得晚的,站着,此刻好像都有了耐心。师傅刚理完这个,赶紧让服务员给洗头,马上又叫下一个。就这样一直忙到深夜。不过忙归忙,脸上还是荡漾着满意的笑容。别人剃头过年,他们落个钵满盆满。
记得小时候在乡间过年,剃头都成为一件难事,我最害怕的就是妈妈摁住我的脑袋,拿一把剃头刀子像削苹果似的一点点地给我剃头,那种痛苦至今想起来都浑身打战呢。我小时候的头发特别厚,而且还特别硬,大人就说,头发又厚又硬,长大了是个受苦的命,我也压根没想自己长大要享什么福。剃头是个技术活儿,不是谁的妈妈都能为自己的孩子剃得了头的。记得有一年过年时伯父给他的大儿子剃头,可能是伯父的技术也有限,没有给老大不小的堂兄剃好头,堂兄就又哭又闹,惹得伯父火了,端起地上刚刚洗过头的大铁盆往堂兄的脑袋上砸去。男人生了气实在太可怕了,在与堂兄的脑袋发生撞击后,铁盆破了,堂兄的脑袋也花开了。看到这一幕伯父也傻眼了,把破了的铁盆攥在手里,呆呆地站在原地,半天一动不动。
三不五时,村里会出现挑着一头热的剃头挑子来走村串巷的剃头师傅,师傅把挑子往村口一撂,生火、磨刀,一会儿来剃头的就排起了队。剃个头也没几个钱,除了把剃下的头发拿走再给个三斤核桃二斤枣的就打发了。我们弟兄几个倒是没有去过这种摊子剃头,都是妈妈大包大揽。
印象中,小时候的头发总是长得很快,没有几天时间就长了,妈妈就要剃。每次剃头我都要撕心裂肺地惨叫,妈妈就警告我:老实点别老动弹,我拿的可是很快很快的刀子啊,你瞎动就把你的头割破了。我一听就一动不动地缩着个脑袋龇牙咧嘴发出咝咝的声音。但有时候妈妈的剃刀并不快,实在是疼痛难忍,就要歪脑袋,一歪,剃刀的尖儿就把头皮划破了。妈妈就埋怨:看看,不让你动你就动。然后赶紧在地上捏起一小撮碎发敷在伤口处。剃刀剃出的发型很特别,上下发线分明,齐斩斩的,没有过渡,就是人们常说的盖儿头。其实,妈妈也不想给我们剃头,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看到我们每次剃头时痛苦的样子,她也难以下手。有时候就索性用剪刀剪,剪头发是不疼的,可是很不好看,跟狗咬了似的。但那时候小,并不懂得外表形象多么重要,所以也落得开心。
后来村里有个年轻人买了一把推子,我们就彻底从妈妈的剃刀下解放了出来。每次头发长了,妈妈就给两毛钱让我们到有推子的年轻人那里掏钱让人家来打理。推子理出来的发型果然漂亮,至少不是盖儿头了,明显精干了许多。村里的孩子们也慢慢都从剃刀下逃离了出来,纷纷涌向有推子的年轻人家里。
村子里有了第一把推子,紧接着就有了第二把,第三把了。我爸爸也买了一把,我们弟兄几个就自己学着使用,然后彼此给对方理发。爷爷看见这新鲜玩意儿不错,也让我们给他理。他很高兴,从此再不用每次剃头到村里找人了。妈妈把剃刀彻底收了起来。
村里有个五年制的小学,来了个老师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叫他姐夫,虽是同辈,但年龄很大了,他的儿子只比我小几岁。姐夫的理发手艺特别高,什么样的头他都能理得很好。小学校就在我家跟前,我那时已经上中学了,平时没事时就到学校去玩。姐夫就说,你的头发长了,我给你理吧。然后就在办公室中间摆上椅子,把门上的门帘摘下来,围在我的脖子上。边忙着这些边不停地告诉我说:“我的手艺肯定让你满意,公社主任的头都是让我理的。我在那又大又圆的脑袋上就像摸西瓜一样地摸来摸去。公社主任那可是官呀,大官哩。但他的脑袋也是由咱随便拨弄。”姐夫手不停,嘴也不停。我发现他给别人理发比教书还能找到感觉。紧接着又说起他的儿子如何如何优秀,语文成绩从来都是名列前茅,特别是毛笔字写得好,每年过年村里各家各户的春联都是出自儿子的手。关于他儿子的事迹我也有耳闻,确实不错。姐夫家离我们村不远,再说我们也是亲戚嘛,总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不一会的工夫,我的发型出来了,果然不同一般。我那时候好歹也是个中学生了,对自己的形象还是很在乎的,所以后来只要头发长了就到学校找姐夫,直到姐夫调走。
好多年没见到这个远房的姐夫了,那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在乡间路上不期而遇。他当时已是乡里的教办主任了,听说他的儿子不争气没考上大学,威望多少有些下降,儿子的落榜对他打击很大。他见到从大学回来的我,尴尬地笑了,说,你现在的发型不如以前的好,我以后也没机会给你理发了。我的心好像被针刺了一下。
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是想起了那句老话,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急忙抽出时间上街理发去,好不容易等到个位子坐上去,却听到理发师傅说,先生,你的头发好稀少哦,还有白的了,头皮都快要露出来了,留长点还是短点,要不焗下油?
我顿时感到一种悲哀从心底涌出。
怀念我的美女老师
想写我的中学老师陈晋阳已经很久了,只是众多的头绪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不知从何写起。坐在电脑前集中精力回想那段岁月,陈晋阳老师无论如何是无法逾越的。她可以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此时此刻,她就这样重新走进了我的视野,走进了我的心中。
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陈老师是美女老师。而且是我们高中学校唯一的女老师。我们高中是在当时上级普及乡级高中的精神号召下产生的,教师大多数是高中毕业带高中,有两个教师好像是大专毕业。这是一个土包子云集的学校,陈老师虽然也是高中毕业生,但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从大城市来到我们学校的。她父亲就是我们那儿的人,长期在外地工作,但因右派身份回到了老家,陈老师就这样进了我们的学校。有着城市身份的陈老师在校园里的确与众不同。纤弱、温柔、内敛而且漂亮,这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子绝不会有的一种特质。陈老师给我们带俄语和数学两门课程。她的课上得非常好,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她那标准的普通话。在我们公社的高中,能讲标准普通话的老师几乎难以寻觅到,更不要说女老师了。再就是她那始终不急不躁的语调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但即使她的课真的讲得不错,在那个年代里,真正爱学习的人并没有多少。我们刚刚从开门办学的大环境当中被生拉硬扯地回到了课堂,隔三差五还要再被附近村子拉去支援农村建设。学生的心根本没有从田野上收回来。勉强坐在教室里,学生自然就分为两大块:前面的小个子学生和后面的高个子学生。小个子学生相对爱学习,特别是女生,把陈老师作为榜样,说话学着陈老师的腔调,走路学着陈老师的姿态,总之,一颦一笑都在效仿;而高个子学生相对不爱学习。我属于高个子系列的。但是个例外,还比较喜欢学习。陈老师很讨厌高个子学生,上课时很少提问高个子,巡视时,只在前面转悠,很少到教室的后面。有时候到后面来,也只是为了看看相对爱学习的我等少数几个人。
那是上俄语课,讲完课的陈老师让大家写作业,信步转到了后排来,站在了我的面前,顺手翻看我的作业,表扬了我:“写得挺整齐的。”我对表扬很不自然,随口说了句什么。因为我们这些高个子很少能听到老师的表扬。下课后,我旁边的高个子周锁才就在教室里大声笑着说:“今天陈老师表扬他呢,你们猜他说了句啥?”众生兴趣很浓,赶紧凑上来问:“说啥了?”周锁才使着鬼脸坏坏地说:“他说了个‘毬’。”同学们哈哈大笑。我一下就脸红了,因为我真的那样说了。我们农村娃,从小接受的都是满口的粗话、糙话,张嘴、闭嘴不离那个“毬”字。其实这个字用在语气当中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也就是个语气词而已。说起这个字来,好像在我们晋南一带说话都要带。曾经有一个南方的朋友,在我们山西师大上了三年研究生,总结我们的地方方言,认为最大特点就是,不管说句什么话,中间都要加个“毬”字。比如“麻烦”,往往会这样表述:“麻毬烦”,“真没劲”,就会说成:“真没毬劲”。在正常的话语当中加进去一个“毬”字,就是山西晋南话。这个总结相当有道理。
虽然坐在后排,但还是早早就悟到不好好学习将来还得回到土地上的道理,用老人们的话说就是“打牛后半截”,所以我就发奋读书。要想全面提高成绩,决不能偏科,数学是我的弱项,就得拼命学。要想学好自然就离不开陈老师。我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偶尔还会去主动问她。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受到了陈老师的青睐,成为高个子学生当中的佼佼者。由于数学基础太差,后来高考还是让数学拉了后腿;但也是数学帮了忙,如果不是后来直追,成绩更差,那考大学更是无望了。陈老师是我考大学的奠基人。
陈晋阳老师当时给我们上课时好像已经不小了,依然还是独身一人,我们就不时会议论她,像这么漂亮的女人待在我们这样的乡下,怎么能找到对象呢?我们都为她着急。有一年暑期,有个中等身材,肥头大耳的男人来到了我们学校,走进了陈老师的宿舍,这简直就是学校最大的新闻。一伙儿土包子男老师窃窃私语,一群男生纷纷议论。当有胆大的男生真正走近这个男人,发现这个男人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英俊潇洒,男生们都愤怒了。因为陈老师的美丽支撑了我们乡下男生们的浪漫天空,而如今却被这样的一个男人夺走了,我们纷纷鸣不平。而陈老师的心情颇佳,没事时就和这个男人出双入对,在校园散步。男人带着个120照相机在校园的花池中、操场上拍片,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有次看见他给别人拍照,一边摆弄设备,一边用一口标准的北京话颇有诗意地说着“蓝天白云”之类的文学词语。他原来是个有学问的北京知青啊,我们这才彻底释怀了。
自从身边有了这个北京知青以后,我们男生就把思绪转移到陈老师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乡村高中。她的课依然上得那么好,那么认真,那么专注,但我们脑子里却想象着她站在大城市学校讲台上的样子。还是没有出我们的意料,陈老师终于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乡下,到临汾一中任教去了。我们众男生个个心情郁闷。
1981年秋天,我考入了山西师大,如愿以偿上了大学,离开了农村,摆脱了“打牛后半截”的命运,心中自然欣喜万分。开学不久后的一天,在临汾的新华书店旁边走着,忽然迎面遇到了多年不见的陈晋阳老师,还是原来在乡中时的样子。陈老师开口就说:“我知道你考来了,很不错。”一句简短的话,里面包含着老师对我的信任以及厚望。我还是农村娃那般羞涩,不会表达自己的心情,但这次我庆幸没再说那个“毬”字。在师大上学期间,我一直都没有到一中看望过陈老师,直到有一天听说她调回北京了。我一则为喜,喜的是她这么多年终于能跟爱人团圆了;一则为愧,愧的是和老师同城数载,竟然都没去拜访过,心中留下无限遗憾。
如今,高中毕业都30余年了,人到中年,多少有些怀旧,往事总时时撞击着脑海。陈老师在北京应该过得很好了,只是不知她退休了没。那个在我们眼里不是很英俊的男人,如今应该很优秀地与我心中的美女老师相偕相伴吧。
祝福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