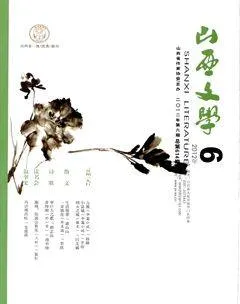再访傅昌旺
今年元月7日,吃过早饭,9点整。我突然决定,利用上午的3个小时,去做一件事情。
这天是星期六,也是我的生日。其实,是不是生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星期六本身。因为每逢双休日,儿子和媳妇起码有一个休息,是有人来照看孙女,而我就可以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看书,比如会友,比如散步。
今天我的计划是去拜访一个人。
我要拜访的人叫傅昌旺。全国劳模、全国首批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十大和谐家园卫士……
在我们西山,全国劳模有六七个,人大代表也有三四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就更多了,他们都是煤矿工人的杰出代表,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像傅昌旺这样退休之后义务植树20年的人却是绝无仅有。
有人说,一个人喜欢、爱好什么,要看他退休以后在做什么。这当然是指有工职的人,不包括农民兄弟在内。从家中出来,路边的棋牌馆里的人进进出出,透过窗户玻璃,可以看到里边的几张桌子上已经坐上了人,还可以听到洗牌发出的哗啦哗啦声。仅在我们这条街,明的暗的棋牌馆少说也有十几家。
来到马路边,旁边那个药店门前的空地已经有扑克摊开张。这里的扑克摊一年四季经久不衰,即使大年三十也有人坚守阵地。在这里打扑克的是清一色的退休职工。其中我认识的几个退休工人,每天吃过饭就背一个包,里边装着马扎来这里报道,一天两趟,比上班还准时。这里的扑克摊少时两三摊,多时七八摊,每摊6个人,还不包括观众。我数过一次,那次的人数高达80多人,像个集会。他们玩的是“争上游”,也叫“三进贡”,俗称“放火”。属于西山人独特的玩法,源于何时,没有考证过,不过,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参加工作时,业余时间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放火”。
我站在马路边,准备乘车去老傅家。我只知道老傅这些年住在西山的建工苑,那套楼房是西山矿务局奖励他的。不过,我从来没去过,当然不知道他住在哪座楼哪个单元的哪一层。
过来一辆蛋蛋车,听司机说是去官地矿的,我便坐了上去。这里说的蛋蛋车,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面包车。这种车在城乡结合部最多。实际上就是没有营运证的黑车。像西山地区,每逢高峰时期,公交拥挤不堪,蛋蛋车在这个时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矿区老百姓的出行提供了便捷。蛋蛋车行走的路线就是从矿务局到某个矿。上车一块,招手即停,再远的地方不去,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当然,如果相互认识,那就另当别论了。在我们矿区,蛋蛋车所以能够生存,同样是因为有它的市场。
待上了车,我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去南山——那儿是老傅义务植树的战场。从1990年退休到现在,二十多年,老傅在那里植了近二十万株树。有松树、柏树,有槐树、榆树,最多的还数椿树。之所以决定先去那里,主要是出于时间上的考虑,另外也想再亲身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然后再去老傅家,两不耽误。
蛋蛋车大约行驶了十几分钟,便来到了老傅每天植树要经过的那道坡,我下了车。
这条长约二百米、坡度在十来度的路我走过好几次。路紧靠着土山,是同南边的高家河连接的枢纽。那边有小煤窑。这些年,凡是有煤矿的地方,必然有小煤窑。这些小煤窑如蛆虫一般,紧紧依附在大矿的周围。像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发生洪灾的官地矿,周边的小煤窑最多时达到二百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没有开采许可证。官地矿被淹就是受了小煤窑的害。一位当年参加过地方政府召开的民营企业经验座谈会的朋友告诉我,一家个体小煤窑的老板在区里把“与大矿(国有企业煤矿)打通”作为一条重要经验来介绍,并且希望推而广之。理由是,在那里(大矿)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小煤窑所以很容易与大矿打通,一是它们之间的距离不太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大矿退休的职工包括大矿辞退了的农民合同工,后来成为小煤窑的主力军,自然而然就充当了小煤窑的“线人”或者“卧底”。
这条通往南山的路以前是土路,来来往往的车辆把路碾得凸凹不平。人在上面行走可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近年才变成了水泥路。我走了几十米,就觉得气喘吁吁。心想,自己比老傅年轻不少,才走几步就成了这个样子,而老傅几乎天天走,一走走了二十年!就在这个时候,听到身后有隆隆的汽车声。回头一看,果然见一辆橙色的大卡车从背后驶来。因为上坡,司机使劲踩着油门,卡车就发出了近乎愤怒的吼叫。这一叫不要紧,灰色的尘土哗哗地扬了起来。这条路不宽,连车也错不开,我赶紧一动不动站在路边,等车过去,也顾不得拍打身上的尘土,加快步伐向上面走去。没走几步,大卡车又来了,这回不是一辆,而是两辆。不是上来的,而是下去的。只见刚才过去的那辆卡车在前边的一个拐弯处停下(唯一可以错车的地方),两辆载重的卡车一前一后呼啸着冲了下来,后边拖着一股灰色的尘烟。我只好如呆子一般,老老实实地站在路边,任凭灰色的尘土哗哗地落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
还好。等我到了坡顶,再没见着来往的大卡车,其间,倒是有两辆小轿车经过。我想,这坐小轿车的,或许就是大卡车的主人。
我顺着那道缓坡一侧的台阶上了铁路。这是一条拉煤的专用线,1935年修的,全长23.3公里。站在铁道中间的枕木上,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使劲地拍打了几下布满尘土的衣服。
这天是晴天,由于气候变暖,冬天也不怎么冷了,虽说已过小雪,但最低气温不超过零下10度。一个多月前刚刚下过的那场大雪,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只有背阴处还留有斑斑驳驳的雪的痕迹。微弱的冬阳下,铁道南面不远处的南山显得更加空旷,安静。
南山是山。说是山,其实是梁。在这道梁上,有三处风景。
一是老君庙。
老君庙就修在那条通向南山一侧的一块平地里。庙的规模很小,坐南朝北的三间房,属于古建筑中的硬山顶,两面坡,最高处横脊两端翘立着鸱吻。庙门不大,可顶部却是那种四面坡的歇山顶。红砖顶端盖着青色的瓦,大门以及庙里门窗的颜色均为朱红色。
这庙是附近一个村庄十几年前才搬上来的,原来的老君庙建在山下的一所学校里。同老君供在一起的还有山神、窑神和几个童子,总共有六七个。院子的中央,摆着一个铁制的大香炉。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五,这儿还有庙会。这个时间与我在资料里看到的不同,资料里写道:“(日本人)借助于‘老君爷’愚弄矿工,一九三九年阴历九月十五老君庙落成‘开光’典礼后,日寇、汉奸、把头常向工人训话:‘老君有灵,保佑的都是好工人,坑下砸死的都是调皮鬼……’”
在另一个矿也见到过一座老君庙。我不明白矿上的人们为什么要供太上老君。至于山神和窑神这倒容易理解。这儿多山,只要睁开眼,首先看到的便是山,近处是山,远处是山,翻过这些山还是山,你不供山神供谁?窑神更与人们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山下都是煤,多少年来,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跟地下的煤打交道,做的是“六块石头夹一块肉”的营生。为了生存,为了平安,为了消灾免祸,必然求助于窑神。因此,凡是有煤窑的地方,就肯定供有窑神。而这儿却偏偏供了个太上老君——一个专门为天上的神仙们炼制长生不老药的老头儿。
那天,在老君庙的围墙上,我看到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条幅:热烈庆祝山西X煤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十周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条标语挂在那个地方有点不伦不类。它挂在那里是给谁看呢?
二是碉堡。
站在老君庙跟前,就可以看到西南方向的碉堡。在灰色的天空下,它像一只冻僵了的野兽,几十年来静静地卧在那里,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现在,它的顶子没有了,把自己的全部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凭风吹霜打,日晒雨淋。周围的墙壁参差不齐,如同老年人走风漏气的嘴巴;碉堡里淤了半截土,长满了杂草。这个碉堡大约有5米高,是用水泥和石头砌的,曾经很坚固。碉堡呈圆形,内径约3米,只是它的墙壁薄厚不一,北边的仅为南边的一半。碉堡的西北伸出一个3米宽、4米长的半圆,看样子是人休息的地方。碉堡的一侧有进出的通道,周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瞭望孔和射击孔。据资料记载,“日寇在矿区修筑大小炮台十五座,拉起双层电网,并在所有交通路口设有岗楼。”眼前的这座残堡,便属于这十五分之一。
三是纪念碑。
碉堡往北不远处,有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在路的两边,除了原来的野蔷薇、荆条以及其他一些灌木外,最多的恐怕就是椿树了。这些高低不一的椿树,粗的似碗口,细的如胳膊。
走在白雪覆盖的小路上,我的脚下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这时,从远处飞来了一只喜鹊,扇动着翅膀,姿势极像一个蛙泳者。那只喜鹊的脑袋冲着我,边飞边喳喳地叫着,好像在向我问好。这声音在空旷无人的山上,显得格外响亮,也十分亲切。
这片椿树林是老傅在山上栽的面积最大的一片。林子依坡而建,呈梯田状,那椿树一棵棵排列齐整,中规中矩,像等待与领导合影的参会代表;而路旁那一株株绿油油的松树,则像是英姿勃勃,精神抖擞的战士,全神贯注地为大山站岗放哨。
那只喜鹊静静地蹲在电杆上,一直注视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友好地朝它笑笑,还轻轻地摆了摆手。
再往上走几十米,就是太原市万柏林区为老傅立纪念碑的地方。
其实,十几年前,我曾拜访过一次老傅。
2000年的某一天,一个朋友同我谈起了全国劳动模范傅昌旺。朋友很是诚恳地对我说,你应该好好写一写老傅。现在,像老傅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回家后,我一直记着朋友的这句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老傅原来是一个矿木料场的扛料工,且不说他从1965年到1987年这23年中累计为国家做义务工5400多个,不拿一分钱的报酬(应得3万多元),还把平时得到的奖励也都交了党费,仅在他1990年退休之后连续十年无偿在荒山上植树造林的奉献精神,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宣传。特别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老傅这种精神更是难能可贵,他的这种举动让许多人感动,让许多人无法理解,也让许多人汗颜!
同朋友谈话后的第三天上午,我决定上山去找老傅。
根据一位熟人提供的线索,我踏上了通往老傅植树的那座山的那条路。这是一座贫瘠的山,薄薄的土层下面全是石头。整座山,除了有土的地上长着些成不了材的灌木和茅草外,放眼全是裸露着的黄的青的石头。即使有几株小树,也如同一个个营养不良的孩子,长得歪歪扭扭。爬了一大段的坡,往东边又拐了几个弯,来到了半山腰的铁路上。我停下来打量一番,视野中看不见那块碑的影子。我决定再找个人问问。离铁路不远,有一位老人正在整修地。我问老师傅,给傅昌旺立的碑在哪儿。老人指着西面告诉我说,在那一片,那儿有座新盖的庙,就在庙上头的山坡上。原来走反了。于是,我返回来沿着铁路线向西边去。大约又走了十几分钟,看到了老人所说的那座庙。顺着小庙旁边的那条小路,没走多远,发现路的两旁有成片的椿树林。已经是农历的九月了,椿树们的身上大多已没有几片叶子,那光秃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