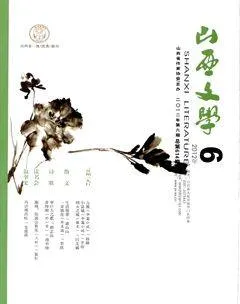剑指人生,反抗黑暗
写作,对于一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打碎还是重建,寻找还是回归?是反抗黑暗与绝望,抑或沿着光与希望一路向前?文学与生活,无外乎归纳、演绎、创造三种状态,归纳生活的写作者站在生活之中,冷静审视,试图揭示本质;演绎生活的写作者站在生活之外,想象虚构,试图重建本质;创造生活的写作者,思行并重,目标在于超越本质。创造力本身就是历史进步的正向力量,于写作而言,既包括谦逊地回到生命的自然与饱满,当然也包括毫不妥协地对生活破门而入。
孙频,手指,闫文盛,这三位年轻作家的文字,近年来读过不少,不过并不知道他们原来有“三剑客”的美誉。大约是中学时代武侠小说读得太多,至今都对剑客怀有莫名的好感。仗剑天涯,倚天屠龙,是不是文学给了他们更多的自由和梦想?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得到致密的现实关怀,沉郁的生命忧思,也看得到灵光一闪的狡黠,和挥洒自如的浪漫,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现实与梦想之间,精神流浪呈现出不同的方向,却有着相似的穿透力。渺小的生存与广阔的世界,本来就没有斩钉截铁的分别,浮生若此,文字有声,倒是让我们看出了他们各自性情的执拗与畅达。
三篇作品给我留下色调各异的印象。两篇小说着力点都在个人与世界的裂痕。没有繁复的因果,那些曲折的人生轨迹最终印证着反抗的无意义,逃离意味着寻找,走上与所渴望的尊严愈去愈远的路途,反证出自我和世界的双重毁坏,作品暗暗的有一种悲悼的情绪在里面。《九渡》浮动着阴郁的味道,《小县城》藏匿着暴力的触角,孤绝的个人,游荡在乡村,小县城,监狱,游荡在童年,少年,和人生末路,小说因此呈现出叠加的空间意识和错位的时间感,八年,二十一年,时光被压缩成内在的空间感,自我迷失在人生的万镜之宫,一切都是破碎的。《烟火之城》也是写城,灵魂在远方,充满烟火气息的喧嚣与浮躁之城,不过是生存的临时站台,是缺少灵魂参与的生活片段,每当记忆重现,往往放映的是剪辑错了的故事。
1
孙频小说近年来频现各大期刊,其文字以细腻见长,情怀幽婉,悲凉中深藏温暖,生死间颇见性情。写女性,尤其是剩女的困境,于无声处听惊雷,生活那么细碎庸常,她竟然写出了步步惊心。那种内在世界的遭遇和折磨,那些看不见的复杂幽暗心理,都在她气韵独具的文字里,一一呈现。《九渡》比起近期的《醉长安》、《隐形的女人》等文要来得复杂,时间的焦虑不仅体现在一个大龄无爱的女性身上,还体现在一个孤独无凭的少年心里。小说写出了存在的多重困境,主人公在命运边缘戴着镣铐舞蹈,作者对于人性,有华丽的遐想,也有不为人知的冒险。现实与想象中纷纷破碎的生活,本ORdsIl4liMivr1dwRD+MJ9PqbD8AbXqITXJ3ATtxZfs=来有着完整的原貌。王泽强和刘晋芳,因为爱,而自毁,而与人世隔绝,读来不禁伤感。时间的漫游,貌似闲庭信步,其实内里无比忧伤。蒋韵曾经评价:“我看到了孙频的悲悯,尽管生活满目疮痍,可她对这个世界,仍然抱着无尽的、赤诚相见的勇气和善意。”孙频自己说:“我喜欢人与人之间那点最微妙最真实的关系,对手的、知己的、情人的,我残酷地、温情地,有时候流着泪写他们,写他们内心里最苍凉、最温暖、最卑微、最执著的东西。我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无论写得多么冷,我内心一直想表达的却是,哪怕一点温情,一点懂得。”
渡,在佛家典籍里,是度化之意,即从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人生是一场劫,渡是过程,也是超越。
王泽强是私生子,是监狱里的犯人,是暴烈凶狠的亡命徒。从小被父母放弃;然后曾祖母和刘晋芳,先后以死亡的方式遗弃他;曾小丽抛下他,嫁给当年毁了他的王兵,他一路走,一路被生活反复抛弃。当他挥起手中的菜刀,扬起手中的皮带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自己能保住最后的一点东西,以便活下去。那一个又一个血腥的瞬间,他抓在手里的是对冷漠尘世的报复,是把整个世界累积在他心底和生命里的冷漠,一并还给了世界。从一个懦弱的被抛弃者到绝望的亡命徒,他只是时光荒野中的流浪者,只是为了拉住自己不被黑暗的世界完全吞噬而已。如果不反抗,那么等待他的永远都是黑暗;反抗了,属于他的还是走不出去的黑暗。他打捞生命深处的黑暗,与身外的黑暗对抗,在生命的湖面如履薄冰,世界时刻都会坍塌破碎,万劫不复,他最终选择与充满邪恶与悲剧的世界玉石俱焚。
刘晋芳曾是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女青年,是个为爱不择手段的偏执狂,是个在黑暗与孤独中清醒的自闭者,是王泽强的生命信念和精神导师。她什么都没有,名声,前途,家庭,爱情,什么都没有。这个人一生都在与绝望感抗争,虚幻的诗意,漂泊的爱情,分裂的精神世界。自杀是一种病态,也是一种反抗,她吃药,投湖,反复尝试和世界永别,当然最后她成功了。作者为刘晋芳安排了一个替身,作为王泽强活下去的支撑。纵然真的隔着万水千山,隔着一片汪洋,人生也不会全部都是空的,暗的,总还是有一点光。这篇小说因此具备了超越性。那么悲剧的两个人,甚至颓废,但是在生的挣扎里,慢慢过滤出一种超越性的透彻和澄明。她对王泽强有过一段生死启蒙:“活到什么时候其实都只有你一个人。你只能一个人往下活,谁都救不了你,因为根本上谁都救不了谁。”这是作者对于存在的理解和态度。依靠外在救赎是虚幻的,只有自我救赎才可能超越心灵禁闭和生死局限。
生与死,抛弃与拯救,两位主人公在广袤的时间和空间隧道来回穿越。刘晋芳收留王泽强,王泽强看护刘晋芳,相互拯救的同时,也意味着自我救赎。世界变幻无尽,那个孤独绝望的少年,只想要一些不变的结结实实的东西,这可以理解为生命的内在信念吧,然而很难,即使痛到绝望,也是他一个人的绝望,时光淘洗到最后,还是走不出去的黑暗,那些生命里的断层,玲珑剔透,然而终究还是空的。作者没有就此否定爱,温暖,还有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其实他知道他是不敢停下来。那是一种多么漆黑的恐惧啊,为了不坠入深渊只有在黑暗中一刻不停地走路,走路,到了后来已经是爬着了,就是这样也不能停。” “时间这只容器太大了,装多少东西进去都填不满它,它始终是饥饿的,这种悲怆荒凉的饥饿把任何东西都吞了进去。”支离破碎地活着,踉踉跄跄地走着,对抗着时间的吞噬,反抗着世界的荒芜。直到八年过去,他走出来,与世界重逢;直到第九渡,还是因为爱,还是为了拯救别人,他选择以自我毁灭的方式,与世界的邪恶同归于尽。
孙频的文字精致华美,不乏妖娆之气,消解了现实写法的边界,暗地里是她对生活和世界的另一种想象和探索。生存关怀,人性剖析,精神追问,心灵投射,生活的幽暗曲折在她笔下如诗如画,直面浮世生死爱恨,灵魂独自歌唱。对她而言,文学探索的那条长路,风景幽深,葳蕤繁茂。她满怀悲伤与悲悯,一笔一笔勾勒,临摹,染色,直到生活的本质跃然画面。
2
古老的乡土中国几乎是一梦醒来,猝不及防地开始了急剧的现代化转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最初,跳出农门进入城市,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后来,这个梦想变成了很多人的噩梦。新文学以来的城市书写,从来都是封闭的,而且往往因光怪陆离的表象淹没了城市的灵魂。对于城市外来者,与乡村外来者一样,都是作家认真关注的主题,祥子是旧时代被城市吞噬的典型。面对陌生的环境,最终不外乎改造自我,或者自我世界的破碎。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叙事,塑造了大量城市外来者形象,然而没有人能够真的把城市变成第二故乡。手指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背井离乡的选择里有多少负面的生命基因,《小县城》是一篇小城人物志。讲述了一些小人物的城市梦。城市改变了他们外貌,改造了他们的性情,给了他们从未有过的东西,也让他们走上回不去的长路。小说沿着出走,写胜利、向南朋友、李丽、建新,这些少年从乡间来到县城,遭遇到陌生的生活围困,他们选择各种方式努力融入陌生的环境。游荡在城市中的这些灰色的小人8a64e7e18cdaa578a3f1b09c0c594381物,他们有名字、没名字都不重要,作者把目光转向他们幽暗的内心世界,放大了他们的挣扎和坠落。
小说抓住少年心中的城市情结,细细剥落,逐层敞开,纠缠一生的心理阴影,即使借助暴力和伪装,内心的空洞仍旧无法填补,说到底,是个毁坏的过程。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冷峻而独特,对人心的把握锐利而幽深。十二岁的男孩,被扔进一个陌生的环境。迷失,仓皇,困惑,孤独,自闭,绝望。他一直在逃避,离开乡村,逃出商场店铺,逃课,逃票,逃出瘦女孩的家……只是为了走进人群,吸引别人的注意,需要别人的感动和温暖,需要被接纳被尊重,这个自闭的少年选择了偷窃。可是,逃课,没有人注意,逃票,没有人注意,偷东西,也没有人注意,他太渺小了。害怕和孤独,这两种情绪跟随了离乡少年一生,在内心深处,因为恐慌,反而一定要抓住一些什么,世界就是被成群结队的老鼠追赶的噩梦。小说写这个男孩内心的渴望和忧惧,焦虑和困扰,以及最终的分裂。作者没有表现少年的罪感,而是让他沉溺于自己创造的王国。明知虚妄,欲罢不能。然而,人生中总会有那样一些时刻,不期然照见真实的自我,原有的幻象全部破碎,瘦女孩家的镜子,让少年看到了自己的虚弱、肮脏和失败。
这些年轻人来到城市,他们背负的人生阴影如此沉重,精神虚无和现实生存构成双重枷锁。与胜利父亲有所期望不同,向南朋友是父亲的玩偶。父亲的残暴,让他时刻想逃离。辍学进城打工,让这个阴郁的少年变成了特别狠的角色,“那只是一小段路,却让旁边的人觉得比任何一个难熬的难眠之夜都要长。”有时候走过短短的一段路,一个人就真的再也无法回到他自己。乡下来的年轻人一把刀征服壮汉的传奇,让这个少年走上了城市混混之路。读手指的文字,让我想起苏童,苏童的香椿树街的故事。少年成长,遭遇生活的迎面阻击,想象,迷狂,暴力,写作者讲述这些故事的心理动因是什么呢?苏童是回忆和沉湎,是无限地靠近生命的真实,手指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异己者反抗的悲剧,面对生命里的漠视和暴力,如何才能找回自我?
较之胜利和向南朋友人生的突然转弯,李丽的蜕变是个缓慢的过程。17岁少女单纯质朴,县城音像店改变了她。乡村的烙印慢慢退去,一年时间她变成了县城里时髦的姑娘。然后和未婚夫——村里小学教师分手,爱上音像店老板,一个很世俗的故事,手指的叙述多少有些怅惘,那些年那些纯真的少女,就这样被城市改造吞噬。而建新则是进城少年的人到中年版。小说至此,给出了叙事的完整结构。九岁进城,建新最初的城市记忆里,下水道的味道,商场的自行车,小饭店的炸酱面,招待所的白墙壁,一切都充满诱惑。那个午后,时间第一次以如此声色鲜明的方式进入他的生命。可是,二十一年后,当他向妻子复述那个烙印在生命里的夏天,妻子并不感兴趣,其实那段往事是一个少年成长的最初动力,建新又一次清晰地看到自己内心的孤独。于是他选择出逃,一个人悄悄回到小城,住进最豪华的宾馆,伪装成成功人士,叫来当年的同学朋友,一板一眼扮演自己想象的角色。小县城一切依旧,所有人都在庸常生活中灰茫一片,他想起那年夏天跟这次几乎一模一样的提心吊胆,伪装的一切转瞬即逝,皆为幻境,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属于他。
小说叙事结构与叙事情感缠绕紧密,县城,身份,命运,叛逃,种种可能的方式和道路,最终都带着各自的想象沉入世俗生活的底部。手指通过不同视角的讲述,把那些懦弱的个人,在弱肉强食的城市丛林,以及刻板平淡的城市生活中的处境,反复放大呈现出来。瘦女孩家的镜子,朋友手臂上的疤痕,李丽对面的城市女孩,建新的县城宾馆,经由空间位移和时间错置,回忆和写实同步,人生的病态,现实的无情,变成一根隐藏的线,把不同人的命运串联起来,故事有对现实的反顾,暗示了城乡转换带给年轻人的虚荣、挤压和挣扎,也带出了存在意义上的乡愁,世事苍茫,如临深渊,作者藏起那一声叹息,让读者在略显颓废的人生美学中,看到生命意义被抽空的所谓生活是如此惊人的雷同。
3
一个作家的写作视野,与时代,与成长环境,大约都是有些关联的,当然,这其实算不上什么定律,虽然丹纳也这么说。或者,主要是因为写作者敏感细腻的心灵,更易于触摸到生活的内在韵律,发之于内,形之于外,难免会带上自身人生背景的烙印和底色,包括对故土家园的眷恋,对故人往事的沉湎。闫文盛这篇长文,以自语的方式,讲述这些年来他的行走和思考,他的经历和感怀,沉静略带伤感的语调,让我们与之亲历了那些漂泊,回望,思索,和喜怒哀乐。“对于生活,我们不是经历得过多,而简直是太少了。”这大约可以看成是他于写作和生活的反省吧。
烟火之城,弥漫着世俗生活的味道。闫文盛沿着自己的人生感怀,一路走,一路思考,文字自然流畅,充满美感。个人的经历和感怀,映照着时代的回声,那些匆匆来去的行人里面,走着你我。叙述里有些人生细节的放大,也有些生命履历的跳跃,淡淡的伤感背后有未曾说出的坚定,沉郁苍凉的静美里饱含着一个人的悲欢,能感受到作者是在生活的深水处呼吸。对生活的无奈,寓居他乡的茫然和感叹,现实的反省和深思,隐约如水波微动。茂密的思想和心灵触角,抓着生活和世界的枝枝叶叶,探索自己与之粘附得最紧密,又偏离得最远的那一部分,那种不能言说的乡愁,是个人的心灵史,也是大时代的文化笼罩。跌落在其中的我们,说到底,也只是一些对生活洪流无能为力的渺小个人。
作者从清晨之思写起:清醒还是梦境:每一天都会反复追问;而感知生存:阅读或者写作早已成为自我生成的方式;眼前这烟火之城:在喧嚣与变异中不断扩张,而我们对它是多么的陌生;那些细碎的日常生活:平淡而迷茫,周而复始,毫无新意;一个人穿越城市:就是穿越他乡与故地;就是穿越记忆:在历史与幻境中寻找自我;作者曾经怀抱自由乌托邦的理想,面对生活,理想滞重,思绪渴望飞翔,而天空常常布满阴霾;这种伤怀:绵延于一切时间与空间之际,回忆与遥望之间。
我读闫文盛的小说,散文,诗歌,各种文字,里面都饱含着属于他个人的乡愁,他的心灵状态,精神世界,常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文学想象中的故乡,是他对外在生活的诠释,也是对内在自我的探询。“这里的生活仿佛一种错误”,他不断地写下各种怀旧,各种在路上,和各种悲伤。写作,是他寻找的出口,走出黑和迷雾,走出冷和疼痛,走出人群和时间的枷锁。他的文字里藏着陈年旧事,藏着搁置的记忆,和努力的遗忘。《人间别久不成悲》、《只有大海苍茫如暮》、《回乡偶书》都是对梦中之乡,心中之乡,灵魂之乡的一再回首和遥望……城市华丽而又张扬,散碎而集约,深沉而喧嚣,是最大的世俗生活,却从不会真的给人心灵安稳和精神安宁。这烟火之城,是多少人的梦想,多少人的流浪,多少人的他乡。“这巨大的生息之所,它本不是我的故地,我在这里,与在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其实无异。九年间所有的记述,都敌不过一次人流中的行走。”漂泊在城市之中,城市,只是生存的寄居地,并无情感和血脉的关联。那些几乎每天都要经过的银行,医院,邮局,小学校,超市,铁路局,酒店和旅馆,菜市场和路边小摊,一切都是生活的表象,丝毫不能与自己的内心产生真正的共鸣。
文中除却空间的伤怀,还深藏着无尽的时间感怀。原乡的恒久情绪来源于无乡或者离乡的痛楚,时光对此有过修复,虚构,强化和改写,作者的努力在于明确的感知,是的,无论是强化,还是淡化,我们都只能眼睁睁看那一切在生命的背景里愈退愈远,唯一能够做到的,是以文字的方式把自己雕刻进其中。“对过去的事件几乎一无所知。那些旧的时空过去存在过,但现在不存在了。那已经消逝的事物,其实不能复原分毫。”的确如此,我们经历人世种种,在内心复制,收藏,总会慢慢模糊,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比我们知道的要强大,没有人真的可以凌驾于生活之上,或者君临世界。文章结尾这一段话:“时间的力量如此博大而惊人,对于万事万物,它都发挥着效力。并非一切都可以提前被预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茫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生命哲学的诗意表达,也是诗意人生的哲学沉思。时间,这个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又严格限定了生死界限的庞大之物,同样让年轻的写作者深感困惑和焦虑,面对生活的重量,他也会愤怒,“为了凝视自己,在黑暗中让往事发出回声”,还有那些黑屋子的记忆,都是他不想于人海和荒野中遗失自我的努力。
和一位作家探讨小说写作时,我提及,或许写作者首先要解决的是历史观,然后是哲学观,最后才是美学观;历史观决定高度,哲学观决定深度,美学观决定力度。虽然这么说未免失之武断,不过如何看待生活,是提笔写作的基础,赋予文字永恒的生命力,是写作的终极追求。当写作者的灵魂活在他的文字中,那些纸上的故乡就成为活动的影像,那些死生契阔就成了人世的博物馆。关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虚构,是一个人的文学地理想象,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地理图谱。生活的底色斑驳杂乱,时代的声音参差嘈杂,今夕何夕,此地他乡,在文学的布景上,这三位年轻的写作者,正凭借文字的引领,一步一步走出自我的局限,走进世界的内心,和生活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