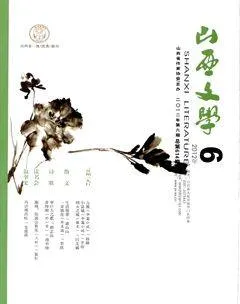烟火之城
闫文盛,男,1978年生。1995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共计100余万字。有作品入选全国数十个选本。曾获2007—2009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新人奖。山西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
1
这一天醒得很早,清晨五点二十,突然睡意全无。索性下了床,洗了脸,蹑手蹑脚经过卧室门,到阳台上,怔怔地站几分钟,天亮,大亮了。時间过得真快。眺望楼下,远山近树,薄雾的清晨,触目皆绿,万物都还是静的。定定神,然后才看见白色的,黑色的,流动的。看见墙头草,已经封顶的楼房,数了好几次,都是十七层。很奇怪,且不去管他。雾慢慢散开。看到脚手架,低矮的民房,公路上零落的行人,极少的车辆,心中渐渐开阔。因为是从黑甜乡回到这律动而将喧嚣的人间。开始短暂的忆旧,想起五年,十年前,想想自己当時住在何处。天南地北,恍惚若梦中。镜头拉回,看到锅炉房的烟囱,楼下草圃前早起锻炼的老年妇女,中年男子。他们转头,甩臂,前行,后退。再想想二十天前,自己在何处。想。有饥饿感来袭。昨晚,妻子偶尔看到的消息让人惊悸不安。消息称,省内某地某公园有上万只青蛙上岸。想不起消息的来源,因为没有亲见,难以辨别。今晨早醒,莫非受惊吓所致?但觉得不是,因为夜里一觉,睡得酣畅,不曾有一梦。
饥饿感愈浓。这些時日,给自己找了好些事做。日子忙起来,有時忙到昏天黑地。真是夙兴夜寐,难得有规律地生活。读别人的文章,看别人的著作,有時沉浸于小小的遐想。想,许多人都有小才华,许多人有功利心。难以控制的自我欣赏,近乎炫耀。但二十年几乎未求一变。可怕的文学生涯局限了他们的生活。我情愿多些時间,回到广阔的人间去。北方的夏天,虽热但不至于让人窒息。我所居住的城市东西两面都是山,只有南北通畅,但再向远处延伸,还是山。有几千年了,在这个自给自足的盆地里,有多少人生老病死。天灾兵祸,人如蝼蚁。我一直在做一种无端的猜想。假如時间在某一处小空间里停滞,让我可以返回商周,秦汉,唐宋,明清,该是多么好。在大的時空的节点上,我定然拥有我的同类。他们在日常里起居,吟诵,沉溺于个人的悠然与欢乐。忙碌,将息。远游,归里。他们在轩敞或逼仄的屋子里写下,大漠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他们自有坦荡襟怀,可叹宇宙浩渺,可造亭台楼阁。兼或如我,有小感叹。
天已亮得耀眼,太阳升起来了。那百十米外,红砖房里的人开始走动。他们私密的小空间里,开始有刷牙洗脸的声音。开始有喊叫起床的声音。开始有拌嘴的声音。开始散发早餐的香味。人影穿梭,光影层次。可以想象他们在夜里肉欲的欢腾,可以想象他们此刻晨起的慵懒,可以想象,生命如一只陀螺,已经再度进入忙碌的循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一代人老去,进入亘古的寂灭。但此前,此前,此前,不管有多少蝇营狗苟,不管有多少琐碎与不甘,大体的轨道已经限定,鲜少有人,能够做那人群外的异类。但凡有困倦,便可安睡,但凡有雄心,便能振拔,但凡有爱恋,便可奋起追寻,但凡有目标,便可达成,似乎只是少数的人生。而我在这早起的晨间,只能从成堆的书卷中迈步过去——那是昨天为找几本书而造成的狼藉——渐渐听到窗外人声鼎沸,渐至于有歌声踊跃,那分明是办婚事的人家,已经开始人生中最大的欢唱。那歌声在肺腑中活跃,却经由别人的嘴巴唱出来。我的思维被打乱了,那不期而至的喧嚣到来。時在清晨八点。
2
像这种反常规的日子并不是很多。我通常睡眠不错,有時简直可说是,睡得过多了;只有偶然的夜间才失眠,偶尔会在凌晨醒转,那些日子记录了我人生的动荡。以前我曾经误解为这些日子将是永久性的,与之伴随的忧伤会贯穿我的终生。但后来觉得自己错了。那是充满了矫情的年代。可我的写作风格却由此界定,那些隐约的,越界的情感,那始终挥之不去的生存的痛感,是所有这一切的由来。后来,这种取向竟然过渡到我的阅读。我似乎有些排斥那种丧失情感的写作。我知道这是理性的判定所致,有時也可理解为曲笔或隐讳。当我经历了年龄的成长,生命中新的磨难种种,这种断然的习性才略有更改。我能够读一些隐藏自我的书籍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如何能够要求所有的写作者都是一副面孔?除非我拥有帝王般的权力且具有统摄众生思想的本领。而这已近于荒诞。我慢慢改掉了自己性格中的部分偏执,力求以一颗和善与宽容之心来对待我的同类。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時至今日,我仍然会为一些事情产生怒火。我知道这是我的文章中存在烟火气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好是坏,但我的确在谋求某种变革。这是艰难的。经过数年的努力,我的情况仍然没有大好转。有的人很不客气地指出过这一点。我知道自己的软肋,基本上每一次都可以安然领受。有時辩解,但自己都觉得是无力的。进而会上升到对自己的怀疑。后来,怀疑一直在持续。它成了一只不断发力的鞭子。我没法子停顿下来,只能以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减轻这种带有自我强迫性的痛苦。年过三十以后,我似乎明白了许多道理。它大概可归结为,我们的文字生涯开始得有些早了,那些人生中的好年华,都被我们磨灭在书斋中。对于生活,我们不是经历得过多,而简直是太少了。在写作的時候,我更多地停留于某种想象,甚至依赖于幻境。我从来没有看到很逼真的一幕,那些阔大雄浑的,与小对立的伟岸時代,从来没有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我只是在翻动纸页的時候会感到血脉激荡,胸怀张得很大,可在合上书的瞬间,万物只向你显示它平常和静止的一面。至于我能够意识到当下的不凡,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但它迄今仍无法作用于我的写作实践中。
我一直在寻求某种变革之力。時至今日,我愈加认定:只有具备某种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的作家才是最好的,但令我懊丧的是,我恰恰总是走在一条相反的路上。我在许多同代的不同代的作家身上都看到了这种情况,这真是让人鄙夷的。有時我甚至觉得应该在一个方向上留下自己的一本书,应该大幅度地使用减法而不是盲目地幻想增值。眼下我只觉得少数的几个人做得不错。我其实在暗暗地揣摩着,使自己变成这少数人之一,但这种坦白只会使人觉得好笑。就像无数次地重复自己,只会使人觉得好笑。它毕竟与日复一日的生活不同,某种程式只会使写作受伤。有一些日子,我在读一些学者写的书,我觉得他们的严谨可以给我启示。我時常督促自己停下笔来,多去读书,多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那异地他乡的风情会让我们改变坐井观天的习性,即使是某一条古僻的巷子,某一座不知名的山头,某一棵经历风雨的树木,都可能隐藏着营养,吸收并消化它们,有助于使我们变得根深叶茂。
我给自己排列了许多事。它使那些原本空空荡荡的日子变得充实起来。以前,我曾经度过了十年居无定所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把我健康的心性带走,它使我变得轻率,经常有浮沉感。我经常希望自己能扎实地居住在大地上,然后,我才会有時间,去仔细地看清楚一些事。那些阅读古书和劳作的日子,是幸福的。那些沉溺于专注的方向里的日子,是幸福的。那不为生计奔波的日子是幸福的。当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爱与悲欢,我知道,这样的時光是幸福的。去除了那些纠结、彷徨、苦闷、担忧,我知道,平常繁复黏稠得像米粒一样的日子,都是幸福的。我知道自己无法使所有的日子像刻度尺一样精准,但与芜杂的岁月构成对立,我知道,对于眼下,我不该有什么不满足的。但为什么,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当那些旧事旧物悄悄地来袭,我却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这一天上午十一時许,屋子里已经很热了,转角阳台被阳光炙烤,更是热得像笼屉。我打开书,读到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只不过是如此一物……》:
你悄无声息地来临,
赐给我敏锐的视觉。
就这样你留下了印痕。
3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座烟火之城……到处都在拆迁,动工,钢筋水泥的森林在争分夺秒地扩张。走在城市的大马路上,混乱的交通使我的步履变得慢下来。有時候刚到楼下便开始堵车,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面包车、出租车,甚至载重的卡车都集中到这条路上。从这里往东可以驶上高速路,六七年以前高速路刚刚通车的時候,我曾经来过一次。站在入口处给同行的人打电话,他们都在后一辆车上;我记得那里有一个土岗子,现在却是一个居民小区了。由于地势起伏,那几幢小六层的商品楼由北向南渐次低下去。刚刚搬来附近居住的去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曾经从这个居民区北面的入口进去,到南边的出口再穿出,然后就到了另一条马路上。相比较而言,南边的这条马路要古老多了,据说它是从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到东边一个贫困县的必经之路。由于年久失修,路况也差多了。那一天我们靠着路边走,沿途有许多装载重物的车辆驶过,在我们的身边荡起一股烟尘。放眼四望,南边有一座军营,门口有岗哨,北边是一条排污渠,渠道的两边,分布着一些平房。这就是我后来在我们家阳台上所看到的,不,它甚至还偏远一些。我们在路上可以看到那屋前挂着的夏季衣物,还可以看到篱笆扎起来的菜畦,里面种着西红柿,黄瓜,南瓜,茴子白,辣椒。偶尔会有一两个小孩子从某一个院落里蹿出来,速度飞快地跑过河渠上的木桥,有時则是一辆电动车或自行车从桥上过来,眨眼便行出老远。照例有烟尘荡起,只不过比大卡车的威力差多了。
这是东城,在它的四面八方,集中了许多工厂。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现在所住着的高层,也曾是一座轧钢厂,只不过败落有年,否则这片土地不会被转让给地产商,被开发成商品楼。这座工厂留了一些年老的和年轻的工人,经常在我们的视野里出没。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成了这个小区的物业人员,整天粗声大气地说话,彼此以师傅相称。许多业主初来的時候都感叹过,这里工厂的气息一直驱之不散。它不仅留下了随处可见的碎铁片,两幢小二层的简易楼房,露天的公共厕所,还留有一幢工人宿舍楼,六层高,就在小区的旁边。许多人都说过这宿舍楼要被拆掉盖高层的事,它将是我们所居住的这楼盘的二期工程。我们希望它可以早一些日子被开发出来,否则,我们居住在这里,单独的一幢楼,总免不了有孤悬城外之感。在很长時间里,这片区域确曾是落后和荒凉的象征。我在来这城市八年之后才真正到了这里,并从此定居下来。但我迄今,对它仍是不熟悉的。那四周的空间对于我,似乎广大无边。某个早晨,因为急着出门办事,又逢周一,向西直抵城中心的马路上拥堵异常,便听取出租车师傅的意见,掉头向高速口方向绕道而行。我们很快离开了我曾经熟悉的路段,穿出了那条古老破旧的大马路,甚至穿越了高速路面下的一个桥洞,一路向东,进入到我从未涉足的一片土地。我曾经误解那里是田野,但在那个早晨,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盯着车窗外的车水马龙,盯着那摩肩接踵的人群,盯着那林立的店铺和逼仄的古街,直觉中,我想自己是来错了地方。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条古街叫什么,但它的繁华嘈杂,似乎与市中心无异。我们在那里绕行了十多分钟,我带着一种诧异和好奇之心浏览街景,但仔细想想,它离我定居下来的那个小区多近啊,至多,也就三站地的路程。在我少年居住的乡下,只不过是从村东头,走到了村西头。
4
似乎到今天仍是这样:我很难明确地意识到,我就居住在这里。尽管为了强化这种印象,我每天都会下楼去走一走。上班,散步,或者送儿子去幼儿园,或者和妻子去菜市场买菜。观察此時此地的生活,有時不免会走神,遥想过去和未来的生活场景。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日子我过得太久了。大概在很久之后我才能够确定自己居住下来的事实,比之遗忘,它差不多得用双倍的力量。我每天所走的路都差不了多少,在人生的某一个時段,生活总是陈旧的,杂乱而铺陈。它到底是轻的,重的,上升的,向下的,红色的,黄色的,我一概地说不清楚。
5
有一天,我从附近的小县返回,却是从城市的西南方向,坐车沿西环高速到这市里来。因为是头一次走这条线路,所以觉得异常遥远。它真是太远了,像我在十年前那个月明星稀之夜,从广州车站一路向深圳方向疾驰,南方的溽热天气,一种浓重的离愁,使我的心情黯淡了一路。我在中途下车撒了一泡尿,抬头看了看异乡的月色,然后继续上车。大约在深夜十二点进入深圳市区,昏茫的光线中,我根本弄不清楚这是到了深圳。汽车停在一条我根本记不起名来的街上,某一个单位的门前,司机去找人借打火机点烟。后来他抛下我们,说,就这里了。然后我才和亲友往另外一个地方赶。凌晨一点,我们到了他的驻地。他安顿片刻后坐车离开,我一个人留在了那里。荒郊野外,和我当時的处境多么相似。他们住简易的宿舍,宿舍后面,是茂密的树木,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才发现那树木遮天蔽日。他们有简易的澡堂子,水在任何時候都是热的,但不是经过人工加温之后,是高温天气导致的自然热源。而今十年过去,我在家乡省城附近的某一条高速路上,眼睛紧盯着长途车司机手中的方向盘,带着一种探究之心向他询问,这趟车的终点站在哪里?他用方言说了一遍,我没有听懂。他又说了一遍,仍是方言,我照旧没有听懂。客车上空旷寥落,只有两个乘客,坐在最后面的大座上咬着耳朵说话,有時还做出亲密的举动,诸如接吻之类。我的眼睛转向车窗外,终于从路边的指示牌上看到了熟悉的地名。车辆转弯,盘旋,擦着西山的山麓下来。路上开始看到正在建设中的高层楼房,开始看到树木,开始看到低矮的厂房,开始看到行人,但相隔遥远,开始看到落在车窗上的细细的雨线,突然想起,忘带雨具了。开始想起曾经听闻的开发西山的市政规划,这毗邻城市的山,很快将与城市接壤。
车辆下了高速,周围的景物渐渐可以分辨出来。那条向西然后向北的路,通往另一个小县城,七年前我曾经去过那里采访,一个多小時的盘山公路,路边松动的土层,挂在半山腰的枝丫细弯的槐树,临近县城時煤灰扑鼻的路面,站在煤灰中疏导交通的警察,路边巨大高耸的工业机械,都在我的脑海中一一显现。向东,才是通往我所居住的城市的宽阔马路。车辆很快进入主干道,我看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小区,我知道这就是那批在建的经济适用房,我的一位旧邻居通过抽签得到了其中的一个名额。不久前,他说已经拿到了房子的钥匙。我的一位同事也曾有意要抽取一个名额,但没有成功。他后来在一个名牌楼盘购买了一套大房子,他家厨房的烟火,离我的居住地很近,我到黄昏時便可看到……车辆很快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我回头望望那个小区,突然觉得它还是太遥远了。它距离我曾经理解的这个城市最西部边缘的那个区域还有好几站地,但那是在四年前,那時,到这个地方没有公交,即使离城市再近一点,也还是连出租车都看不到一辆。但现在,公交车已经笔直地开过来了,它还可以一路东行,直抵火车站。我从长途车上下来,便坐到公交车上。很快,我就看到大马路中间那棵大槐树。那是我此行的终点和起点。一位在京居住的老师为写一篇山西古树的文章,曾经专程跑来这里看它。现在,它像个交警似的,站在那里,将东来西往的车辆分流了。它大约已经站了几百年了,直到有一天,被作为神树,隆重地保护起来。它见证着这个城市长大的历程。而与树木栉风沐雨、吸收天地精华增加着年轮不同,城市的急剧膨胀,似乎更多地可归因于人工的规划与建设。
6
在这城里住了九年,我的岁月与它盘根错节。我写下许多细微感觉,来记载光阴在这里的流淌。前前后后,有十来个地方留下了我生活过的印记,但所有的记录,都已止步于我的回忆。我的确没有为它添加什么,当我行走于人丛,那数百万人口,很轻易地就将我淹没了。如果以数量的庞大来对应个体的生命,那任何伟大的存在似乎都不成立。但这个论断却并非在任何時候都正确,時光越千年,那日常的生活已经难以重现,可是有几个名字,还会留在人们的唇齿间。当个人的意义被发掘、上升,他更近于一个符号被留存下来。時光的更新与汰洗,使多少事情都随风飘散了,当我们在古人曾经活动的地方逗留,那数百年、数千年前的烟火之气,是否曾像今天这般浓烈?我想大半会的,至少每一代人的当下生活,都是唯一的,隆重的,它一往无前而不可逆转。我的一些朋友们,比我更加沉迷于古代,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地回溯,那些被推向从前的時间,既雍容华贵又水流潺湲,是不同于古人的另一种记述。千百年后,我们的后代还会不会试图还原我们的生活?
黄昏時经过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灯火如织,它照耀着形迹匆匆的无数人。很少看到哪怕仅仅有过一面之缘的相识者,或许有过,但彼此的神态转移,所以南来北往的,都是陌生人。这巨大的生息之所,它本不是我的故地,我在这里,与在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其实无异。九年间所有的记述,都敌不过一次人流中的行走。当我稍微留意一下周围的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其实多么相似,那昂头向前、正在拿着手机通话的步行者,上半身略微前倾、双腿屈伸、不断用力的骑车人,双手搭在方向盘上,侧头瞄一眼后视镜或目不四顾的驾车者,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进入了我的生活。我有時混入步行的人群,有時骑自行车回来,路边的居民楼里已经人影晃动,那厨房里的油烟之气漫入空际,使每一天都变得既香醇浓厚又日常守旧。我所经过的地方如许众多,银行,医院,邮局,小学校,超市,铁路局,酒店和旅馆,菜市场和路边小摊,一切都纷繁而简单。极偶尔的下雨的日子,我会在曾经租住的小区附近避会儿雨,那些曾经占据我的记忆的小小角落不知在什么時候发生了变化,理发铺变成了小小的诊所。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眼神狐疑地盯着我看,有時我会注意到他的目光中甚至带着轻微的恶意。大多数日子,我都不会再产生我在这里住过的念头,而是飞快地越过去了。路边经常有兜售水果的小贩,因为把三轮车停在大马路上而受到人们的埋怨,有時是城管的责骂和罚款,但买卖人总是走马灯一般地更换,那里很少有过空寂和寥落的一天。
我曾经的住所占据整个城市的南、北、中各个方位,这些年来,我的生活被容纳其间。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城市,看到先人的居住地,深宅大院或者一间阔大的洞窟,那止不住的幻想便一涌而来。我暗暗比较这其中的异同,像一个孩童般站在那些陌生的地方,有時与那些当下的守护人攀谈几句,但他们摇着头,对过去的事件几乎一无所知。那些旧的時空过去存在过,但现在不存在了。我们只是在影视剧中观看着今人的演绎,那已经消逝的事物,其实不能复原分毫。迄今我们所知的有知觉的生命体,长过百年的寥寥可数,而拥有记忆并能诉诸表达的更何其稀缺?就此而论,我们的生是如此难以定义,所有有机的生命匆匆而逝,如同宇宙间的一个个玩笑。在虚无主义的笼罩下,我们堕入思维的泥沼,只有眼前有形的万物或许可以使存在稍许确定。当我们置身其间,時间又过得多么匀缓,如果没有杂音和速度,它几乎就是停滞的。我曾经无所事事地度过一个个上午或下午,在一间间小屋子里,仔细地聆听光阴的流动。有時,宁静的氛围会突然被现实的事务破坏,焦虑的思绪一旦开始涌动,便很快地泛滥,它变得无处不在。尤其在那些一无所有的岁月里,当无形的绳索被绑缚在身,它把你从虚妄的想象中拽出来,慢慢地与世界接近,是那些日渐增多的获得使你的处境发生着变化。某些外在之物甚至比你的内心更为强大,它们印证着生存的某些铁律,并占据了大半的心灵空间。这便是生活,它更像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某种象征。
7
城市里集中并张扬着最大的俗世生活,越大的城市,便具有越大的现实意味。它是作为现实生命的最大概括。自古而今,城市都是散碎而集约,深沉而喧嚣的。它曾经有过乱纷纷的动荡年代,但更多的则是热腾腾的起居岁月,即使那些并不安定的日子,柴米油烟酱醋茶也是家家户户的必须。可以被省略的只是那俗世之上的生活。对于占据人群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冻饿不着便可以顺顺当当地活到寿终。将生存的需求降到最低,不是追求奢华而不达,便是其思想超凡入圣,我们看到更多的当然是前者。我从外面返回这里之后,年复一年,出门的次数屈指可数,囿于视野的局限,便尽可能地买些书来阅读,以弥补行不足所导致的思想上的困顿。但究其实质,两者却是不可替换的。我每每为自己的生计忧心,在过去的九年中,因为种种原因换过四五个单位,虽忙碌依旧,但捉襟见肘的日子却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可是,长期以来,我一直憧憬着一种自由的生活,希望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墨换来生存的一应所需。它几乎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我始终觉得有一线暂時看不见的光最终会照亮头顶。直到三年前,我整体的生活差不多安定下来,这种理想仍会在我的梦境里出现。摆脱了租房子带来的压力,摆脱了那日日缠绕的漂泊游离之感,我发现自己的生活中依然有很多不足。我自小渴望的那种不为金钱所缚的日子远远没有到来,我至今仍不得不为经济所累。那发自内心的欲望似乎没有穷尽,这大概是我们生活困倦的一大根源。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在我从小生活的村庄,近年来略有余财的农人们向往起了外面的世界,每年或隔年会拿出点钱出门旅游,被我母亲斥为烧包。母亲思想中的守旧并非与生俱来的,她只是数十年生活在乡下,困窘的生活把她生命中的一切欲求都磨蚀殆尽。但是有一年,她幼年的一个玩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来看她,双方谈起了小時候的一些事,母亲才突然地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她们分离的時间已经超过四十年了,这个人现在做了教师,在邻县教书,她这次到我们的村庄是来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她们谈论起母亲早年优异的学业,可惜的是,由于家庭的压力,很早就被迫中断了,还谈论各自的儿女,谈论各自目前的相貌变化,我母亲说,那个人看起来比她年轻多了。她头一次提起,假如自己也能够将书念下去,目前大约也会有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听了觉得心酸,但一切为時已晚。今天的母亲对于城市已经难以适应了,她曾经带着先入为主的排斥心理到省城照看孙子,但不到半个月的時间,便再也住不下去。她觉得那屋子憋屈,出气不畅,她甚至向我埋怨,屋子里冷得她浑身都不舒服,她说卫生间离卧室太近(一墙之隔),总之,她自此愈加认定这城市不是她应该住的地方。她还是喜欢那宽敞的院落。至于我们对城市的亲近,她倒是可以认同。她曾经谈论嫁入县城的妹妹,羡慕她可以很快地融入那里,但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我购买新房后,试图让母亲和父亲来住些日子,但母亲迟迟不能首肯。她被那孤堡式的住宅弄怕了。
8
决定购房的前几天,我曾经早早地醒来一次。妻子和孩子都睡得安稳,我洗刷完毕去了单位,大概是六点半的样子。因为工作变更我很少失眠,即使有过,现在也早已记不清那细微的纠结。但因为其他的事情不能安睡,却時有发生。我在深夜里走过城市的大街,远远地看见那辉煌的灯火,它们如同亘古不灭的星光,如果继续往前,很快便走到那灯火发源之处,某某大酒店的金字招牌,张扬夺目。有時遇到醉酒的人蹲在路边呕吐,路灯会照亮他们那苍白的脸。他们转过头来,眼神依旧恍惚。更多的時候,是在夜间看到情侣。他们在烧烤摊前,某个公交站牌下,或者就在人行道上,手挽着手,或肩靠着肩。他们忘我地投入到了自己的小世界,抚摩彼此的脸,或者吻对方的额头,眼睛,鼻子,嘴唇。还免不了看到争吵,言语飞溅,像离弦之箭。看到无情的殴打,性命相扑,人如同兽类。在离火车站不远的某个小区居住的日子,某个早晨,我七点半醒来,突然动了跑步的念头,然后找出许久不穿的运动鞋,下了楼,跑了十分钟,到车站对面的邮政大楼停下来。台阶上坐着几个外地人,他们的行李放在脚前,他们用我听不懂的方言说话。我看着站前广场上悬挂的大钟,時在清晨七点五十。已经有许多人来到了火车站,他们带着大包小包,有的甚至拖家带口。有的人则是刚从站里出来,急匆匆地来到这个城市。我看着他们,突然不能确定自己的所在,我在这里待了多久。我想起中国铁路开通以前,火车站是不存在c6c51d2c0e0cb3c05c32d605589e582f451dae4441403cfc82a7b9639d08fd94的。那時只有一个个供旅人歇脚的驿站。那時,人们的交通工具是马车。豪华马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某些名车。宝马,奔驰之类。但仅仅百年多的時间,世界已经变化至此。火车站前的大钟突然响了,清晨八点,崭新的一天准時到来。那几个外地人立起身,拿着行李离开。他们拍拍身上的尘土,精神抖擞地奔赴这座烟火之城。
古往今来,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座城市里生活过?怕已不可胜数。他们遇到过怎样的劫难?天灾,兵祸,疫情……世事更迭,物换星移。但许多往事,人们都已归诸遗忘。现今我们谈论最多的,仍旧是柴米油烟酱醋茶,是衣食住行,家长里短,是工作、收入、物价,是儿女情长,诸如此类。自有城市开始,人们日日谈论的,便不外乎是这些事吧。后来流行于世的艳情小说,世情小说,所谓街谈巷议,眼下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肥皂剧,又能有多少逸出常规的东西?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某人的一次婚外情感,当我们在茶余饭后谈论着房价的上涨,当我们为某一次不公抱打不平,当类似的不公落到我们的头上,当我们在这城市的每一条巷子里都跑过了一个来回,那数十年的光景,也就该过去了吧。数十年后,我们何曾会想到那遥远的往昔,我们确曾如此地活过。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就像现今的我们回忆起三十年前,我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刚刚有记忆,就像我们的父辈回忆起他们的而立年华,那時,这座城市的南部还是一片荒凉。我初来这里時住过的民房当時还不存在,离那个地方不远,那著名的学府当時还立于荒郊。从学校到市里,要经过一片广袤的田野,每年夏季,麦浪起伏,像诗心摇动的青春。我听闻一位诗人谈起过这事,而现在是三十年后,诗人退休,麦香已成久远的传奇。在原来的土地上最早建起的高楼已显陈旧,它们疲惫地沿袭着人间的烟火,等待着拆除,并在旧址上建起更高的楼。原先麦田最集中的田野目前成了这座城市最繁华富庶的地段,那里拥有全城最豪华的住宅和酒楼。時间的力量如此博大而惊人,对于万事万物,它都发挥着效力。并非一切都可以提前被预知,在更多的時候,我们都是茫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