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撒哈拉寻找三毛足迹
2012-12-29 00:00:00刀子
户外探险 2012年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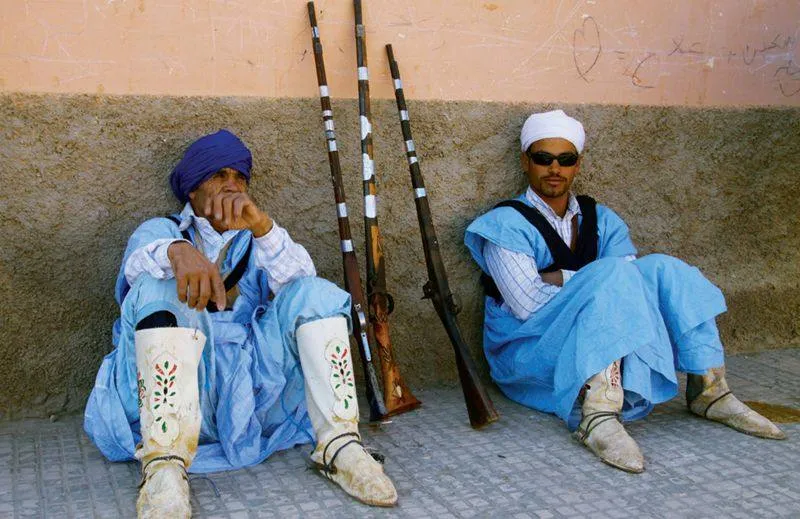




撒哈拉,要追溯这个名字的记忆,已是我遥远的童年时代。那时还读着竖排版的繁体《西游记》,偶然读到三毛那篇《沙漠观浴记》,她生动细腻的文字给我留下了两段不可磨灭的印象—用石头刮“老坑”的浴女和灌海水拉粑粑的女人(“老坑”乃苏州方言,是身上污垢的意思)。于是“撒哈拉”的记忆就这样和“偷看女人洗澡”牢牢地联系起来,虽说不是什么光彩的回忆,但打小就特别念叨着,将来一定要去趟撒哈拉沙漠。
一眨眼很多年过去了,三毛也在1991年过世,而想去撒哈拉沙漠的这个念头却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也曾独自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但比起撒哈拉,总缺少那么一种感觉,大概撒哈拉对我而言已不仅仅是一片沙漠,更烙上了童年记忆中关于三毛和荷西的痕迹。
西班牙教堂 寻找三毛结婚记录
阿尤恩(El Aaiun),在三毛的书中译为“阿雍”的小镇,地处北非西撒哈拉地区,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联合国决议让撒哈拉威人自治,但目前由摩洛哥实际军事占领着。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在摩洛哥投入巨资百万美元后,阿尤恩已成为西撒哈拉地区北方最大的城镇。阿尤恩并无太多旅游资源,城市周围的沙丘也并不壮观,远不如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巨型沙丘。但这里却因为多年前在此居住的一位中国女作家而让人念念不忘,她曾在此写下著名的《撒哈拉的故事》。
翥红色的西班牙教堂并不难找,这是阿尤恩镇惟一的一所教堂。除了南部达卡拉,或许这也是整个西撒哈拉地区惟一的教堂了,现在到处都已换上伊斯兰礼拜的清真寺。钟楼高高耸立,礼拜堂上竖着十字,然而大门却悄然紧闭。如果三毛和荷西是基督徒,当年结婚也应该来此登记才对。
走近紧锁的大门,怯然敲敲门,里面却只传来空洞的回应。四顾茫然,一个路人都没有,似乎连小镇本身都已经遗忘了这所教堂。叹了口气,有点落寞地转身离开,看样子估计不再会有人来这个“遗忘的角落”做礼拜了。
正当我准备离去,背后却突然响起呼唤声。回头一看,居然有个黑女人从旁边侧门探出头来向我招手。她说着听不懂的法语还是什么语,但我大致猜到她让我从那里进去。
或许是神职人员的善意和天性,也许是来这里的人实在太少了,神甫瓦莱里奥热情地带我四处参观,介绍这座当年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教堂虽然只是座小教堂,但穹顶的恢弘气势还是把我震慑住了。手绘的耶稣圣像以他仁慈的双眼俯瞰众生,而他身侧则是追随着他的门徒。二楼摆放着一架古旧的钢琴,等着不知何日再来的唱诗班。阳光透过楼顶无数十字小窗,被五彩玻璃的釉彩染成不同的颜色,如同神谕般投射在远道而来朝拜者的眼中。
我和瓦莱里奥说起前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位当年在这里居住过的中国女子,她在这里和一位西班牙男子结婚,度过最难忘的三年。我希望能在这里查看是否有当年他们的结婚记录,并非为了查证,而是为了怀念。
瓦莱里奥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要来查这位中国女子,难道她是我的亲人?我摇摇头,这是一位让我钦佩的女作家,很小就读过她的书,她的文字她的经历,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瓦莱里奥点点头,说这里的确保管着所有在此登记结婚的人员名单和签名,从1960年到现在厚厚几本。资料保管室比我想像的整洁多了,墙上挂着耶稣的圣像,一张崭新的办公桌摆放着一些资料,一面全金属大橱靠在墙角,瓦莱里奥指指上锁的大橱,“那里保管着所有资料,即使年代久远的也都在。”
厚厚的档案册记录着所有这段时间来教堂举行婚礼的夫妇,还有每一对夫妇的亲笔签名。我屏声静气,书卷翻开时飘起的灰尘在我眼中都那么轻盈美丽。
连瓦莱里奥都急着看想到那份珍贵的结婚记录,如果有三毛的签名那就更棒了。然而档案一页页翻过,“这已经是8月了,没有荷西玛里亚这个名字。你确定是7月吗?”
“那能看看1973年吗?”我从来不放弃希望。
他帮我又重新仔仔细细查看了所有从1973年到1974年的记录,我真是很感谢他的耐心。
“每本档案册后面还有索引,索引也查过了,你确定是在阿尤恩吗?在达卡拉也有教堂。”
“我确定是在这里,她和荷西在撒哈拉一直待在阿尤恩。”
反反复复查了好几遍档案,还是没能找到三毛和荷西的名字。瓦莱里奥和西班牙小伙都有点为我惋惜,“他们应该是在别的地方登记结婚,这里的记录是不会丢失的。”叹了口气,虽然比较可惜,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尽管没有找到三毛、荷西的名字,但我还是很感慨,这座西班牙教堂居然能把这么多年的婚姻记录都保存着。
翻看这些记录,犹如读着旧日的老时光,我不知道在这里签下名的所有夫妇是否都还健在。不知道100年之后,这些签名是不是还是会留在这里纪念他们逝去的主人。
阿尤恩海湾:偷看撒哈拉威女人洗澡
对于撒哈拉的海湾,三毛的《沙漠观浴记》这样描述道:
“蓝色的海水平静地流进一个半圆的海湾里,湾内沙滩上搭了无数白色的帐篷,有男人、女人、小孩在走来走去,看上去十分自在安祥。”
我蹑手蹑脚地走近这片阿尤恩海滩,仿佛走入悠长的记忆,寻找着记忆中散落的撒哈拉威人的白色帐篷。空气中传来阵阵腥臭味,不知道是鱼的味道,还是当年撒哈拉威女人排毒的味道。
一片巨大的沙滩如同梦境般飘了过来,连绵沙丘的弧线让我如梦魇般着迷。或许只有这样的荒芜才配得上她的名字——撒哈拉,这片大西洋岸边的撒哈拉沙漠!
看不到人迹,只有几只流浪狗在漫无目的地游荡,它们来沙漠找骨头吗?继续往前走,才从高处绕过沙丘看到海水,海滩边没有什么人。只看到一对情侣在沙地上踽踽而行,看这情形也不像要脱衣服洗澡的样子。我深深地为这个罪恶的念头而自责,但来这里偷看女人洗澡可是我多年的憧憬啊!
从容不迫地跨过围栏跳下公路,这里不再会有撒哈拉威人气势汹汹地拿着刀来追杀我。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沙子走下沙丘,在沙滩上信步而行。远处的一大群海鸥,一溜儿栖息在海滩上,走近也不怕,自顾自地聒噪着。有个当地人驻足于我的镜头之中,默默地发着呆,真有点“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绝之感。
继续往前走是一大片扇形的海湾,湛蓝的海水倒映着海滩边竖起的高楼。几十年前三毛笔下的阿雍海滩,已被摩洛哥彻底改造。想偷看撒哈拉威女人在沙滩上唱歌排毒的想法,完全成了泡影。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
几叶翠绿色的木舟,翻着大肚子躺在海滩上晒太阳。它们的主人则更悠闲,跨坐在木船上,慵懒而惬意,仿佛一位富有的君王。两个当地小伙,坐在码头的石墩上,听任海鸥在他们身侧上下翻飞,听任时间如眼前的海水般静静流淌。
三毛曾在《素人渔夫》里写到她和荷西在海边抓鱼到小镇上去卖的有趣经历,而在这个港口有的是大把大把的“素人渔夫”。海岸边有一个泊满了小船的小平台,听听贼鸥们嘎嘎乱叫的兴奋劲,闻闻空气中弥漫的鱼腥味,就知道渔夫们打渔归来肯定大有收获。渔夫们正在卖力地把一箱箱的鱼往岸上搬,沉甸甸的样子,封得很严实,我伸长了脑袋还没有看出来有什么鱼。
我在看鱼,他们却在看我。我笑着说“Salaam”,他们回我以朴实的微笑。
有个能说英语的小伙上前来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他认识这里大多数渔夫,要买鱼他可以帮我。我说我想看看有什么鱼,不知道贵不贵。那小伙子转头和忙着搬箱子的渔夫吆喝了几句,那渔夫二话没说就把一个箱子打开,挑了几条鱼摆在我面前。
想起三毛和荷西当年在海边抓到的鱼,“有章鱼,有蛇一样的花斑鳗,有圆盘子似的电人鱼……”果然在这里都看到了,花里胡哨的花斑鳗,纹理像咖啡色的大理石;圆盘子一样的鱼也有,就是三毛说的电人鱼,有点像鳐鱼,但又没有长长的尾巴。后来我查了才知道,这种鱼学名叫做“电鳐”,有着比目鱼一样的单边斗鸡眼。小型电鳐电压可达80伏,大型电鳐发出的电流足以击倒成人,有海中“活电站”之称。还有一条小鲨鱼也在里面,看体型完全属于萝莉幼齿,可怜也被抓上来了。
我问小伙子这条“萝莉鲨鱼”多少钱,他说四五十块,折合人民币再打个七五折。
这里的海水颜色是碧绿色的,不知道是因为船的倒影,还是因为水中的藻类。这种尖头的小渔船,就是当地渔民的生活来源。要是有时间,能和渔民一起出海打趟渔,那就更有意思了。
金河大街:一切都曾那么汹涌
这就是当年“撒哈拉最美丽的家”吗?站在金河大街(即卡泰罗尼亚大街)44号门口,我不由得感慨万分。
如同赵章云老师的描述,“44号是个粉笔写的数字,旁边只有42号有个正式的门牌。”
三毛也曾经写过,“这个家里里外外粉刷成洁白的,在坟场区内可真是鹤立鸡群,没有编门牌,也不必去市政府申请了。”
门外的土墙已斑驳不堪,土黄色的墙粉也开始剥落了,墙上安着几个电表也有种年久失修的感觉。
“一切都曾那么汹涌,什么都敌不过时间。”正当我怔怔地想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远远地跑过来,靛蓝色的小头巾,淡蓝色的碎花衣,橘红色的小皮鞋。她就这样蹦蹦跳跳地从门口跑过,扭过头去呼唤她的妈妈。
那一刻我几乎想脱口而出,“姑卡!”
当年三毛的小邻居姑卡只有10岁就成了娃娃新娘,“那时的姑卡梳着粗粗的辫子,声音清脆而活泼,俨然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
细细端详,隔壁46号也是一扇没有门牌的小门,同样用黑色油漆写的门牌号,门内有楼梯通到二楼。沿着楼梯拾阶而上,楼道非常狭窄,只够一个人将将通过。到了二楼,我想着能不能上三毛《芳邻》里提到的那个神奇天台,去看看“飞羊落井”和“天台盗水”的发生地:
“我抓起菜刀就往通天台的楼梯跑去,还没来得及上天台,就听见木条细微的断裂声,接着惊天动地的一阵巨响,木条、碎玻璃如雨似的落下来。当然这只大山羊也从天而降,落在我们窄小的家里。我紧张极了,连忙用扫把将山羊打出门,望着破洞洞外的蓝天生气。”
可是到处却找不到上天台的路,只有一扇天窗赫然在头顶,用铁栅栏封了,只有阳光透射下来。
难道这就是那扇落过羊的天窗?
带着疑问,我去敲二楼人家的门,看看能否带我上天台。开门的是一位警觉得像小鸟一样的撒哈拉威女人,没有戴面纱,很秀丽的脸,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躲在她身后。
我试着向她解释,很久以前有位中国女孩在此地住过,我想来拜访一下故居。她似乎完全听不懂,不住地摇头。看来从这里上天台是没希望了。
我灵机一动,能不能爬到旁边更高的楼上去看这里的天台,就像刚才在路口俯瞰墓地。下了楼,右拐进了靠东侧的一条小巷子里,像作贼一样四处查看地形。果然不出贼眉鼠眼的我所料,在后一排就有一栋三层的楼房。从三层楼的正门上去,我这算不算是“私闯民宅”?
万能的主啊,请饶恕我的罪过吧,摩洛哥警察们,千万不要抓到我吧。
三楼的楼顶,有一扇拴上的木门,这对我而言不是问题。爬上高高的楼顶,三毛故居的天台全部呈现在眼前,这就是三毛和荷西那么多动人故事发生的地方啊!天台很大,角落一隅有个棚子,似乎喂养着牲畜。平台上飘着几件晾晒着的旧衣服,随风舞动。刚才看到的那面铁栅栏天窗也在一角,天台中央用水泥封了一大片。不远处的清真寺传来悠扬的祷告声,而马路对面院子里有头骆驼在悠闲地散步,时不时抬头,远远地望着我。
根据赵章云老师的描述,也找到了三毛《爱的寻求》提到的那家杂货店——“我住的小屋附近,在七八个月前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里面卖的东西应有尽有。”
这是故事的主人公沙仑工作的那家店铺,的确离三毛家很近,就只要走几步路过一条小街,在街角就到了。然而当年这家应有尽有的杂货店,摇身一变成了仓库。门口站了个年轻人,似乎是在履行保安的职责,当年的沙仑也早已不在这里住了。
正当我四处张望时,一旁一位老人走上前来和我打招呼,他指指我的相机不住地点头微笑。
原来又是一位自告奋勇要拍照留念的撒哈拉威人啊,看来他们再也不怕魂被收走了。我试着问他中国女孩的事,可是他一句英语都听不懂,只是对着我微笑。
三毛曾在《娃娃新娘》中提到过撒哈拉女人的“哈那”,这是一种涂在手上的花纹。通常是女子要出嫁时,用一种特殊植物磨成汁,绘抹在手上的祝福图腾,呈现出墨绿色的样子,猛不丁看到还有些吓人。就在三毛家对面的小巷子里,遇到一个小女孩也是双手涂满了“哈那”。见我拿起相机,她还很兴奋地张开双手展示给我看。难道这么小的女孩子也要出嫁了吗?
对面街上,一位佝偻着身躯的老妪,拉着一个小童缓缓走过。突然有一种苍凉的感觉,几十年过去了,这里场景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年的故人却早已人去楼空。
荷西意外失事去世了,三毛也过世了,房东罕地发达了搬走了,姑卡嫁走了,沙仑也不在这里卖杂货了。只有这房子还在,只是换了主人,或许只有房子自身才会记起当年的那些欢声笑语吧。
只是朱颜改。
废弃法院
我翻出网上找到的只鳞片爪的信息,又在地图上仔细察看。已经想好了去寻找下一个三毛的足迹,那就是她和荷西结婚的法院。在教堂没有找到他们的记录,那么他们当年很可能就是在法院登记的。
当我在老城里找到那座在邮局楼上的法院,这才发现这里比他们的结婚记录销毁得更彻底。旧法院早已被废弃了,这座西班牙时代的破楼,已经陈旧不堪,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成了老鼠和蝙蝠的家。
当年三毛和荷西就是到这里的二楼,郑重地签下撒哈拉小镇的第一份婚姻法律文书。然而现在别说当年的文书,连当年的法院都没有了。
就在废弃的法院旁,有家小小的门面,挂着黄蓝相间的标志,是一个小人飘然欲飞的样子。
门面很陈旧,看来也有点年头了,连上面插着的几面摩洛哥国旗都有些褪色了。
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
没错!这正是当年三毛天天往来的那家镇上的邮局。
三毛《结婚记》中提到,“我因为住的地方没有门牌,所以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每天都要走一小时左右去镇上看信。来了三个月,这个小镇上的人大半都认识了,尤其是邮局和法院,因为我天天去跑,都成朋友了。”
或许是过了上班时间,邮局铁门紧锁,想去问问是否还有三毛相识的故人,这想法也成了泡影。如今这条僻静的小道路人稀少,更不要说来邮局看信的了,只有一位流浪汉蜷缩在角落,警惕地四处张望。
三毛当年的信箱还在不在?心念着这个问题,我真想写一张明信片寄给当年的三毛。问一问她在那里还好吗?是否还能重新与荷西携手同行?又怔怔地想起,荷西笑言来世再也不想和三毛做夫妻了,只是想过另一种生活,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舍得?
梦游般地走近邮局,就像当年三毛一样坐在石阶上,望着不远处的沙漠发呆。
拖着步子向街道南面尽头走去,那里是一个高坡,可以远远地眺望这座法院和邮局,明黄色的摩洛哥邮政标识很显眼。而在街道北面的尽头,耸立着巨大的沙丘,仿佛转眼就要吞没一切的沙丘。似乎听到尖锐的沙鸣,又似乎是骆驼的悲鸣,抑或者只是我的幻听。
不是我,而是风。
国家旅馆
国家旅馆依山而立,据说是参照西班牙古城格拉那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建造。靠着曾经多次到四季酒店大堂小便的胆识,我径直步入这座看上去气派十足的旅馆。正对着大门的是一间会客室模样的房间,几张大沙发,两具铜像,还有墙壁上的摩洛哥国王的画像,略显陈旧却不失气派。
这里的前台并非如花似玉的少女,而是一位有点年纪西装笔挺的绅士。我上前问他能否在这里吃一顿晚餐,他有点歉意地告诉我,晚餐时间还早,要7点开始,需要我等一下。我问他能否先到餐厅看一下菜单,他马上叫来一位年轻侍者陪着我去餐厅参观。不过他提醒我,帕拉多尔旅馆的晚餐是自助餐,每个人170DH(折合人民币130元不到)。
侍者领着我在宽敞明亮的旅馆走廊里穿行,折了好几道弯才看到了最里面的这间餐厅。下午时分还铁门紧锁,只能透过栅栏看个究竟,里面一排华丽锃亮的铜质餐盆,而淡蓝色的餐桌分列两边。餐厅虽然不大,但装潢的格调却处处透着精致。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三毛和荷西,还有他老板一起享用荷西抓来的鱼的地方?我仿佛看到三毛和荷西苦逼憋屈的苦笑,忍不住想笑,却又忍不住伤感。
国家旅馆的中庭是一个小花园,植满了棕榈树,似乎原本有喷泉,但现在水池已经干涸了,谁让这里是撒哈拉呢。隔着天竺葵的叶瓣,看着中庭院落,或许最适合这里的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碎大理石镶嵌的石桌旁,空无一人,只有我和我的影子才是这里惟一的客人。在昔日西班牙殖民时代,这座国家旅馆可是名流云集的宴会场所,如今依然绚丽的只有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正惆怅间,那厢的人声却传了过来,我赶忙躲到树后面偷偷观望。原来是一群身着正装的官员,有身穿西服的谢顶绅士,也有一身阿拉伯长袍的当地人士。他们看起来似乎刚开完什么重要会议,手里还拿着文书交相讨论。
不敢造次,偷偷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装模作样地踱步赏花附庸风雅,免得被人误以为是撒哈拉威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