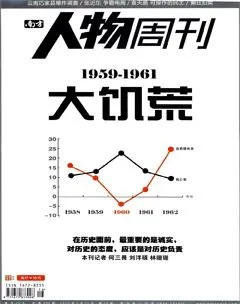敦
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李若兰在民生公司管运务和船务,和童少生并称卢作孚的左右手。
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得了肺结核,要打盘尼西林,那时候“一两黄金一支针”啊,谁打得起?卢作孚对他真是很好,让民生公司美国办事处买药寄回来,救了他的命。
他1959年就去世了,这其实是个好事,他胆子不大,身体也不好,真要赶上“文革”,吓都吓死了。
我高中毕业后就参军了,出身不好,在部队也没啥前途,后来就退役上大学了,念的是兰州大学中文系。
我去敦煌工作是个偶然。1960年,甘肃省委把兰大中文系划出来,跟师范大学音乐系、美术系合并,成立了兰州艺术学院,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兼任艺术学院的院长,我被选去给他当秘书。
两年后,艺术学院撤销了,我本来要回兰大工作,但常院长不让走,把我带到了敦煌。那时候我们受的教育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服从党的需要。就这么过去了,一边当秘书,一边在考古组里当组员,从头学起。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点,当时交通极为不便,信息也很阻塞,我们看的报纸都是一个星期前的。敦煌研究院现在的影响力很大,规模也发展得很大,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员工只有十来个人。我去的时候,那里也只有三十多个人,是个小单位。
人少,又偏远,人跟人之间比较单纯,关系都不错。“文革”全面爆发后,这里也有震动,但基本是“文斗”,没有闹得太过火。冥冥之中,给我这样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极大保护。
“文革”中的群众心理其实是很复杂的。
“四清”开始时,一些同志对常院长的工作方式不满,主动邀请工作组进驻敦煌文物研究所,希望利用运动,把他揪下台。没想到工作组来了以后,把我们都给套进去了。我们私下开玩笑,本来是请神来的,结果把鬼给请来了。
常院长一直被批斗,腰椎也因为一次意外折断了。我因为做过他的秘书,被说成是他的亲信,是他的“黑班底”,先是被定性为“三类半分子”,后来又被打成“五一六”,白天开会交代问题,晚上还要劳动。
敦煌天黑得晚,我们要干活干到晚上9、10点钟。我那时候三十多岁,不怕累,但一些老先生还是很吃了些苦。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爱养花养鸟,就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他拿来整。他被派去挖防空洞,一两丈深的洞,用根绳子把人放下去,饭都不让上来吃,一挖一天。有一次他还挨了造反派一拳,正打在腰眼上,差点死了。
但总的说来,我们那里的左派,还算是相对温和的。地方小,人又少,大人之间左中右地斗,孩子们还是在一起玩,我记得一个左派的爱人还经常做些吃的,给我的孩子们吃,这在外面是不可想象的。
挨批斗时,造反派有些话很可笑的,我们想笑但是不敢笑,怎么办,就假装咳嗽,或者弯腰吐痰,低着头笑完了再抬起头来。搞到后来,大家完全疲掉了,无所谓了,你愿意怎么搞怎么搞,愿意搞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每天不是开会就是劳动,劳动是大家最喜欢的时候。大家一边薅草、种树、浇水,一边讲笑话,或是弄点恶作剧取乐。
我不是整天都想着捡烟头嘛,有几个人就弄个驴粪蛋包在纸里,弄得像根烟卷似的,说老李,你不是想抽烟嘛,这根拿去抽吧,我真点着了吧嗒吧嗒抽半天,旁边的人都笑惨了。所以人类能延续下去,是人本性里头有种向上的乐观的东西,不论情况如何,人们都在尽力寻找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我一直感到很对不起孩子。我7岁的大儿子负责带他1岁的弟弟,受的罪很多。对长辈,我也没有尽到任何责任,父亲去世时我不在身边,母亲去世时,左派横行,我请假他们都不准假。
话说回来,就是准我假,我也没法去,没路费。就那么点钱要养两个孩子。我那时走路都低着头,走哪儿都想着要是能捡个烟头就好了。
最大的遗憾是我爱人没等到“天亮”,她在“文革”快结束时因病去世了。她十三四岁就参军,尽管出身不好,但她待人诚恳,做事踏实,还立了功。她后来也上了大学,毕业时因为我,放弃专业,到了甘肃,在我们院当会计。自打跟了我,每次运动都担惊受怕,最后把命丢在那里了。
她是1976年11月份去世的,我当时在武汉大学学习。那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我给她写信报告喜讯,她吓得要死,回信叮嘱我,千万不要乱说。敦煌消息就是那么闭塞。我安慰她不要怕,武大都开会作报告了,说“四人帮”如何如何……
这么好一个人38岁就走了。她走后,我一个人完全没有办法应付两个儿子,只好把他们送到外地亲戚家。我没怎么管他们,更不要说给予什么父爱了,简直是个浪荡父亲,真的。现在两个儿子都很有作为,他们总是安慰我,说不怪我,因为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但我心里总觉得很难受。我时常回想旧事,特别希望他们的妈妈能够被医治、救活。
我今年八十多岁了,一个人活了下来,还活到这个岁数,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奇怪得很。我把这段记忆说给你听,希望你记录下来,留给我的孙女还有小孙子看看,让他们知道,爷爷奶奶曾经经历过多么惨淡的生命光景,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经历这些,永远幸福地过活。
(实习记者乔芊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