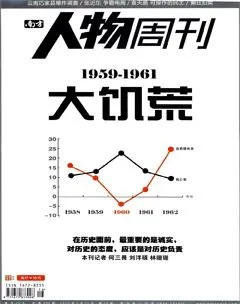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2012-12-29 00:00:00刘洋硕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16期



没事的时候,68岁的吴永宽喜欢骑上三轮车,从村里跑到光山县城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下,给人摇签算命。
这天下午来算命的女孩,显然不太相信这套把戏。她求了一签姻缘,却又说,“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吴永宽不说话。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给他算过—卦:命里八字相冲,少年克父;老得贵子,却离他很远。几十年中,皆已应验。
父亲吴德金死于1959年的大饥荒,那一年吴永宽15岁。
对于那场饥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献称它为“信阳事件”,教科书称它为“自然灾害”,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关口”:过去的,算是幸存;过不去的,成了饿殍冤魂。
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纪念。
一个月后,清明,“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立起来了。帮忙操办的人图省事,把碑建成了两座,一座吴姓,一座外姓。外形简陋,跟普通的墓碑没什么两样,与伫立在县城里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将军尤太忠题字的“烈士纪念碑”,相差甚远。
“谁跟你讲理?”
43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吴永宽感觉到的仍然是恐惧。
《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
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
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
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起来特别黏、扎嘴,有一股‘青’(涩)气”。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吴永宽的记忆里,村里第一个饿死的人是吴德刚,按辈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十多岁,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放现在算是‘五保户’,即使死了也无人过问。”
堂伯父死后,是几个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时候一天能死几个。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儿了,“没准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对于死亡,吴永宽总是轻描淡写。他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身子歪着,翻个白眼,“很简单地”死了。
那时候,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但吴永宽也不怕了。即便轮到他的亲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是三叔吴德才。因为饥荒,他从湖北逃回吴围孜,却发现村里同样没得吃。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吴永宽从饥饿中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三叔“不动弹了”,一摸,人已经凉透了。
父亲负责料理后事,但他同样饿得没劲,卸了块门板,把三叔拖出去,挖个小坑、铺上浮土,算是坟。
人人都知道村里饿死人,但没人敢往外说。直到农历十月下旬,村里的副队长吴永冠饿极了,和一个姓李的社员一起杀了生产队的牛。牛肉没吃多少,两人就被生产队抓住。吴永冠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的大帽子,又被生产队队长吴永寿带人在会议室一顿殴打。
吴永冠一怒之下说了实话:“老百姓饿死了,我对北京首都有意见。”他当过兵,“脾气暴得很”。
村民们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谁也没吃到。吴永宽只记得,他们看到吴永冠跌跌撞撞从生产队出来,后来就听说他从小桥上跌下去,摔得了。
在那场饥荒里,因为杀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数。时任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孙广文在1960年撰写的一份《我的错误交待》里提及,“1959年冬,农村发生杀牛问题后,当时把这一问题错误的分析为两条道路斗争、富裕农民破坏生产的花样,像这样情况经我批准法办也冤枉不少的人。”
带头打人的队长吴永寿是吴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队里的吴德荣因为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吴德桐也因为骂了句脏话,被活活打死。
吴永宽的父亲吴德金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里人饿得皮包不住骨头,斗胆说了句“老百姓快饿死了”。因为这句实话,他也差点被打。村干部碍于他在村里威望高,只批了他一顿,轰回家去。
吴德金又气又饿,流着眼泪回到家里,一屁股瘫倒在地上。看到父亲饿得不行,吴永宽只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里惟一值钱的木桌子抬到镇上卖了3块钱,换回了两碗稀菜汤。
他们赶回家里,父亲已经在地上断了气。吴永宽捏着父亲的嘴灌了一口菜汤,却已无力回天。
三叔饿死一个月后,15岁的吴永宽像父亲埋三叔那样,卸下块门板,把父亲抬出家门。同样,挖个小坑、铺层浮土,便是坟。
吴永宽记得父亲死的那天,自己并没有哭。直到很久以后,心里那股压抑已久的难过,才不断涌上来。他想起饥饿的父亲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村里的长辈吴德琴,本想到县城投奔大儿子,但没走到县城,便饿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见尸。
吴永宽也差点成了同一条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回来的路上,一阵风吹来,他一下子栽倒路边。不知昏迷了多久,挣扎着爬起来,接着一个踉跄又栽倒在路边。
他本该这么饿死,但偏偏“八字”里说他命不该绝。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城里人发现了他,偷偷帮他叫来了城里的亲戚。那亲戚赶紧跑来给他灌了口稀饭。吴永宽这才算是捡回一条命,身体却从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点饿死,但谁也不敢明说。在那年月,这样一句“错话”便可能招来大祸。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
吴永宽记得,当时吴围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队干部抓回来批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出去。关键是,“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到了农历十月下旬,天寒地冻,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况谁还有力气走出去?”
村里剩下的人,就那么瘫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
吴永宽并不知道,他们躺在炕上“等死”的时候,《河南日报》却登出了头版头条——《今年我省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他至今也说不清,这条喜讯背后,光山埋葬了多少饿殍。
《光山县志》记载,1959年、1960年全县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这一数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县的死亡率高达270.6‰,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真实的情况比县志上的数字更严重。
吴永宽已经记不清是1959年底还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终于又响起了钟声。
“听说上面解决粮食了,老百姓喜欢得不得了”,几个庄的活下来的人,撑着木棍从家里慢慢走出来。吴永宽已经饿得走不动道,母亲拿着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带着糠渣的米糊汤。虽然稀得只能“当开水喝”,但终归可以救命。
喝了几天“米糊水”,吴永宽的手脚开始浮肿,一摁一个坑。养了一个多月,身上的浮肿慢慢退去,这条命也就保住了。
吴永宽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来到光山,在县一中的操场上开了一场万人大会,旁边还站着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那天,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亲耳听到当时那位个头很高的省长向全县人民道歉:“我对不起光山60万父老乡亲,我这个省长当得不好。”
可人都死了,“检讨还有什么用?”吴永宽表情漠然。
在那场灾难中,吴永宽家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本有128人的吴围孜,有73人遇难,其中四十多人绝后,17家绝户。
由于村里死人太多,无人种地,第二年吴围孜只打了几万斤粮食。直到1962年前后,从安徽阜阳来了不少逃荒的人,村里收留了这些外乡人,让他们下地挣工分。
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河南省委改组了光山县委,派出工作组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和强迫命令风)错误。但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却把饥荒的原因归结为“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主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这期间,信阳的8位县委书记被捕,除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外,其余几人被判2-3年徒刑。
这在当时被视为又一场“斗争”。马龙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过街老鼠”。县里从此流传一首童谣:“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吴永宽曾看到,马龙山的儿子“马大头”被学校里的大孩子们追着打。
毛泽东最终对“信阳事件”作出批示,称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这场“民主补课”一级一级补下来,到了吴围孜,便是把队长吴永寿和村里的干部关起来,开会学习。“课”还没补完,“四清”运动又开始了,紧接着,“文革”的火苗开始点燃。
“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村里死去的那七十多条性命,吴永贵始终难以忘却。
1960年,被吴永宽称为“休养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结了婚,和父亲一样在村里当会计。1968年,有了大儿子吴晔——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吴晔考到南开大学;4年后,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后他常常寄回钱来,给村里挖渠、修路。
吴永宽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出国前,听吴永宽讲起当年村里的惨状,吴晔哭了。他以前并不明白,在父辈们所说的那场‘粮食关’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开始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坏人”马龙山造的孽,后来读到当代史专家丁抒写的《人祸》,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吴永宽时常会担心,“再过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没有人知道了。”他觉得,在子女中吴晔最像他,“良心的驱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为那些死去的人立个碑。
2004年,吴永宽从天津回到吴围孜养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难者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然后掏了3200块钱,刻碑、做法事,请村里人帮忙操办。
那年清明节,吴永宽自家的庄稼地里立起了两块“粮食关纪念碑”。刻碑之前,他记得当时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来两个,但其中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
他写了篇祭文,写上那72个名字,寄给美国的儿子。吴永宽觉得自己不会讲漂亮话,他在祭文中写道:“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当年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眼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过,让为官者都来看看这两块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应该忘记老百姓。 ”
碑立起来,麻烦也来了。当地有干部对此有看法,说他这碑“不该搞”,“是跟国家作对。”后来,信阳安全局、县安全大队真就找到家里。对方查了几天,“没说你不该建,也没说你该建。”
这些事让吴永宽有些后怕,他想着自己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办了坏事”。但那些想法他还是坚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脏东西就好好洗一洗,这样才好”。
后来的几年里,吴永宽总觉得,这两块普普通通的纪念碑,立得其实有些“不尽人意”。他本打算立块高两米的大碑,底下堆个高高的土堆子,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到,再在台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吴围孜田里的麦子已经微微泛黄,水稻正等着插秧。2012年5月7月,旱了两年的光山总算下了一场痛快雨。
吴永宽在家里喝了点酒,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国家开始反思当年的大饥荒,他就真的掏钱把纪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写一副更有意义的对联”。他觉得那时候国家应该不会反对。说着,他又开始顾虑,“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在68岁这一年,他没有想到为此再给自己算上一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