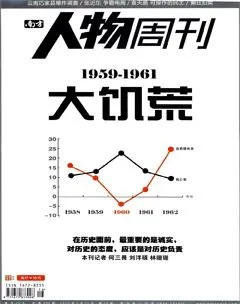记者眼
坚守的人生
本刊记者 赵佳月
以工作的名义理所当然地回趟南京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在那里虚掷了7年大学时光后,对于故地重游,总有种束手无措的尴尬:回去做什么呢?
采访的地点在这座“黄金陵地”之城西南角的殡仪馆,但我照例在校园附近走了走。
午后三四点,学校北边的汉口西路,车辆不多,树荫影影绰绰。靠近力学小学的时候,安静被打破了,守着接孩子的家长在聊天,为夜市准备的小贩开始搭起货架。小学的闸门一开,孩子们摇晃着书包飞奔出校门。
初夏的阳光透亮透亮,连梧桐叶尖上也挂着金色欲滴的阳光。4月开始的梧桐飞絮一直持续着,连续打了几个喷嚏之后就撞见了“熟人”。
她依旧坐在校门口,那张木质小板凳被她臃肿的身躯吞没。佝偻的背充满了卑微;白发像一顶帽子扣住她额头沟壑分明的皱纹;脸上鲜有表情,目光失焦地投向路对面的校门;小碎花的白色衬衫好像还是七八年前的模样……我听说过她的故事,连起码的“5个W”都不明,只说她的孙子在某次放学回家时遭遇车祸,老人从此每天准时在放学时坐在校门口等。
我从没有勇气停下脚步问她,不知道她已等待多久,也从不见她与路人有过任何言语。她像这条路上准点的摆设,像路边的梧桐树,像树旁的公交车站牌……有时适逢雨季,她的不同只是披了件蓝色雨衣。
每次从她身边路过,都屏息静气,生怕打扰她。这时我总想起那句:“等过第一个秋等过第二个秋,等到黄叶滑落,等等到哭了为何爱恋依旧。”可就连这样的歌唱都比不过她坐在那里惊心动魄。尤其是8年后重逢,她几乎成了一面镜子,照见我的变化和她的坚守,而此时我的心里是否也有所坚守?
联系着南京市中心三所高校的汉口西路一度盛传拓宽拆迁,若是这样,力学小学或将搬迁……真是难以想象,若此成真,她将去哪里继续她的等待?诸如此类我们对变迁的热衷和追逐,在她对生命的不变坚守面前,都显得如此浅薄。
梦回唐朝
本刊记者 王大骐
窄巷内,艺妓们化着浓白的妆容,身穿花费一小时缠裹而成的和服,头顶着更为耗时耗力盘缠而成的发髻,全身唯一裸露的细白后颈则被称为日本女人的“第三条腿”,留给男人想象的空间。
3个艺妓里最小的只有19岁,从14岁开始诗书琴艺的练习。她们由已褪去妆容的“姐姐”们带着,其中一个还曾是田中角荣及稻盛和夫每来必点的红牌。金色的屏风被撤去,我们被要求不得照相和说话,只需静静欣赏。
舞蹈中艺妓的动作很小,面无表情,似是极简主义的写照,反映的是京都近郊农田里农家女孩耕作的场景,一旁的老艺人手捧日本鲦笛,吹着乡间小调。第二个舞蹈则反映了艺妓的生活,她们清晨即起,练习歌舞,午后开始梳妆打扮,夜晚为客人助兴。最后老艺人开始独奏,是一首名为《鲫鱼》的曲子,我们被要求紧闭双目,寻找曲子中鲫鱼跃起的那一瞬间,座中一位年轻人留下了眼泪。
由于不通日语,无缘见识艺妓们千锤百炼的谈话艺术,与她们的交流也仅限于杯盏交错之间。喝到一定份上,艺妓会温柔地问你可不可以交杯,这时你要豪迈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伸出右手托付空杯于她,并大声说一句拉长音的“好”(伊伊哟)。
正当我们频发穿越时空、梦回唐朝之感时,一位大叔站了起来,走到前面的榻榻米上,不顾众艺妓的惊愕之情,攥着拳头,眉目紧锁,气运丹田地朗诵起《送元二使安西》,接着又唱了一遍,然后默然回到座位上。原来这是他小时入睡前,母亲总会对他吟诵的诗歌。
回酒店路上,他痛斥了我们对自己文化已然消亡的悲观论调。在他看来,日本清酒与白酒相比,不适合下咽;艺妓表演过于简单,毫无中国戏曲的丰富性;漆器、和服等传统工艺,更只学到中国的皮毛。他说我们这代年轻人宁愿选择卡拉OK和泡吧,也不愿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文化的消亡又能怪谁呢?
大巴穿梭在京都的道路上,这座仿制唐长安城修建而成的日本精神文化之都,如今依旧最大限度地保存着昔日的模样,城里的居民以从事传承千百年的祖业为傲,市区内的1877个寺院和神社随时能让你驻足、出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