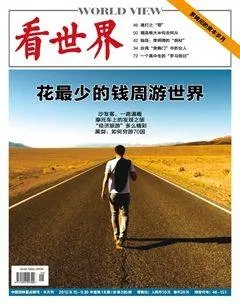巴黎,愤怒的移民社区
2012-12-29 00:00:00编译/宇帆
看世界 2012年18期



一个郊区小城市的案例
艾克萨维尔·莱莫尼翻了翻办公桌上那本薄薄的、记载治安方面的记事簿,作为蒙特佛梅尔,巴黎市东北部一座小城的市长,这是他每天上午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昨天夜里还是相当安静的:一个家庭的住宅发生了火灾,一辆轿车着了火,一群青少年偷了一辆汽车,两名妇女相互斗殴。“还不错。”他啜了一口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莱莫尼,面容严肃、头顶光秃、戴着一副眼镜的市长,注视着旁边墙上一幅蒙特佛梅尔的鸟瞰照片。它显示出一座座住宅、公园和商业购物中心,而在其中,有一个小小的灰色圆形物体,它就是莱波斯克一座破旧的大型公寓楼,2005年10-11月蔓延到法国各地的严重骚乱的事发地。
莱波斯克的面积只占蒙特佛梅尔市的3%,却居住着该市全部25000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来自土耳其、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以及马格里布(包括利比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的沿海平原和阿特拉斯山地),绝大多数人都是虔诚的穆斯林。
这些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失业者,但一种由毒品贩运和假证支撑的地下经济却迅速蔓生出来。“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都由这几种交易支撑,”市长指出,“在2005年,这个城市的80%的犯罪案件来自于‘公共项目楼’(安置贫民和移民,房租很低的住宅楼)。”
据莱莫尼的说法,一部分问题源于居住在‘公共项目楼’的大批人仍然青睐于自己的原始文化,而不愿意融入法兰西的世俗文化。他们的大多数人不会说法语。它意味着这个社区以自己的语言和传统对外部社会进行自我封闭。“然而法国并不是一个多文化的社会,”莱莫尼说道,“我们是开放的。我们喜欢北非小米,但我们不想要头巾和布卡(穆斯林女性的全身罩衫)。”
在距离蒙特佛梅尔市政厅几个街区远的一个小广场上,有一处原本是花坛的地方。远看上去似乎生长着茂密的花丛,但走近一看,则发现该处散落着无数的空瓶子,压扁的饮料罐,香烟头和腐烂的食物。尽管位于西南方的巴黎圣母院距离这里仅仅15公里,而这个小广场让人感觉与旅游者要去的景点和高档酒吧相比恍如隔世。
广场上站立着一堆堆的人,年纪稍大的是一些失业的人;而年轻的则从来就没有工作过。还有一些人没精打采地站在附近建筑物的门道前,边抽着烟,边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来往的行人。“你是flic(警察)?”有人操着俚语问道。这些人曾多次寻找工作,但是在这个以姓名、肤色、穿戴和居住社区来判断求职者的国家,他们往往无功而返。
“当你说你的居住地点是蒙特佛梅尔或者克里奇索波伊(附近的另一个小城市)就必然被歧视。”已当了父亲,有一个1岁女儿的穆罕默德·加达尔说道。他正与一群无所事事的同伴在当地的咖啡馆消磨时光。在过去的18个月,加达尔一直在找工作。“可是要改变对我们的成见是很困难的,我们被视为小偷或者贩卖毒品的骗子,虽然我在法国出生,说着流利的法语。”
右翼排外力量的兴起
现今的法兰西共和国在进行人口调查或统计时禁止对种族或宗教实施单独列项,但是据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公布的出版物《全球穆斯林人口的未来》透露,如今在法国的穆斯林约为470万,到2030年,将增加到690万。不仅是法国有这种趋势,该研究资料预测,从现在开始的40年期间,穆斯林的数量将逐渐占到欧盟国家全部人口的20%以上。
这种人口的增长引起了欧洲极右翼排斥多元文化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不仅在法国,在瑞典、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由于种族之间不信任,移民自由和高失业率等问题引发的对立观点变得更加尖锐。
莱波斯克是法国750个被认为是城市贫困和犯罪案件高发地点之一。这里的人们明显地感到被划分成“我们”和“他们”,即富有人群和贫困人群,白人和非白人。这些地方被视为Voyous(法语:小流氓)的聚集地——失业的年轻者在街头兜售毒品,烧毁汽车,相互斗殴……
这种形势也给予了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勒庞(极右翼的反移民政党,其父亲基恩-马里·勒庞为该党创建人)机遇以进一步推进该党的行动纲领。作为一个长着亚麻色头发,谈吐优雅,说话直接的女士,她代表了支持她的法国新一代公民的观点:那些穆斯林在巴黎街道上进行他们的祷告,不啻是一种“入侵”。
右翼势力的兴起以及民众间的辩论使得法国出现了对立的派别。前任总统尼科拉·萨科齐的政府早些时候就通过一个法令:即凡是具有法国公民身份的女性如果无视禁令,在公共场合穿裹身长袍,戴面纱(据悉在法国,大约有2000人穿这类服装),会被罚款150欧元,并接受法国公民课程教育。在欧洲其他国家,一些领导人,如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曾宣称他们社会中的多种文化融合,但至今仍未见成效,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以及荷兰等国,极右翼政党人士已经进入了各国的议会。荷兰自由党领导人基尔特·威尔德甚至公开地将《古兰经》比作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确实,那个去年7月自诩为“完美骑士”的安德斯·布雷维克,曾在挪威大开杀戒。他的行为导致了75人死亡,而其所谓的“理由”之一,就是要挑起一场针对伊斯兰的征战。他在自己的狂妄言论中曾引用过威尔德与其他作者发布的一个长达1500页宣言中的内容。这些人警告说伊斯兰的宗教信仰者很有可能在欧洲效仿“9·11事件”发动恐怖袭击。
移民生活面面观
对于一些移民来说,在法国的生活还不错。阿卜杜拉克曼在阿尔及利亚找不到工作,所以12年前来到了法国。尽管生活艰辛,现在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一家伊斯兰肉店有了全日制的工作,并与当地的社区融为了一体。“我在这里过得还可以,”他一边为顾客服务,一边说道,“我喜欢这里。”
然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生活却具有悲剧色彩。今年春季的一天,在阿斯尼里苏塞尼,离巴黎城区很近的西北部郊区,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帮派分子与来自附近根尼维列地区的另一群人发生大规模冲突,结果是:一名15岁的少年因胸膛被刺穿而当场死亡;另一个成年人背部被刺了一刀,导致重伤,后死于医院,伤者则更多。当地警方随后在这一地区对青少年实施了宵禁。
在巴黎东北部,距离蒙特佛梅尔不远的一个社区,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41岁的妇女,每天不但要为什么地方能停泊她的小汽车发愁,而且也为孩子放学后做什么而抱怨。这个移民家庭的经济状况只能勉强糊口,尽管她的丈夫是为通勤火车系统工作。有时,她会感到移民法国是个错误:“我的丈夫是一名工程师,很想在这里继续他的学习,然而我们到达后才明白他必须从头开始。每个晚上,我们都谈到孩子们。在这里的生活只是一种存活而已。”
再看巴黎的北郊,圣德尼地区附近的情况。麦迪·斯利曼姆与他的表兄豪辛·基基正站在一条人群熙熙攘攘,布满购物者、孩子和吉普赛乞丐的商业街上闲聊。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26岁的斯利曼姆仍未能找到一份工作。不过他目前正在学习中文,期望在将来找工作时能有所帮助。这位胡子修剪得很整齐的年轻人认为政治家们和媒体所关注的事情与他们这些阿拉伯移民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关系,却同样不乏种族成见。例如,法律禁止了戴面纱,实际上在法国,裹长袍、戴面纱的女性以前也是不多见的。
正面与负面并存
30岁的基基算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在这个地区拥有好几家面包店,但他已有了离开这里的打算——因为担忧逐渐走向分化的法国会影响到两个孩子,18岁儿子和3岁女ovPV6if3Y42p1WFIW4/uqg==儿的前途。“我孩子的前途是我要申请移民加拿大的重要原因,”他说道,“这里的政治空气正日益复杂。”
蒙特佛梅尔居民马尔科·亨利和米丽阿姆·皮卡德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现实问题。2010年4月,他们居住在法国南部的帕尔皮格南,有一个8个月大的女儿。他们平时在社区里小心翼翼,因为一些阿拉伯人和黑人青年常在街上惹是生非,开着小摩托车乱闯,搞街头聚会,制造高分贝噪声。一天晚上,夫妇俩让女儿在床上入睡后正在看电视影片,街上又传来了声音很强的喧闹。
马尔科·亨利打开窗户,要求小青年们安静一点,结果适得其反,这些小痞子愈发起劲地将喧闹声搞得更响。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下,他将一罐水浇到了这伙人的头上。这一举动无疑是捅了马蜂窝。街头小混混们立刻涌到马尔科·亨利的家门口,拼命砸大门。随后这些人还用泥灰乱扔房子的墙壁和窗户,并把手伸进门上的一个孔洞试图拉开门栓,而马尔科·亨利则用尽全力抵住了门。米丽阿姆此时抱着女儿,躲进了卫生间,用手机拨打报警电话。门外的暴徒疯狂地叫嚷着,扬言要杀死这家男主人、强奸女主人的声音不断传来。几分钟后,警车呼啸而来,小混混们立刻作鸟兽散。由于有了这一经历,他们知道必须马上搬家。
于是马尔科·亨利在蒙特佛梅尔市政厅找到了担任市长通联主任的职位。这个职务是市长计划改变市政形象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当我们来到这里时,人们说我们是刚出油锅,又入火坑。”米丽阿姆说道。她如今正在照料新出生的第二个孩子。“这里的形势也很紧张。我的丈夫几周前又遭受攻击。但是在蒙特佛梅尔存在着真正的政治意志,即努力将整个穆斯林融入社区。”
蒙特佛梅尔的市政改造计划包括将莱波斯克等破旧的居民楼拆掉,建造一种低层的公共项目住房来提供给低收入移民。在这些公共住房附近还将设立社区中心和警察站。社区中心将向移民们提供免费的语言学习,而警察站则努力在民众和法治机构之间构筑相互信任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