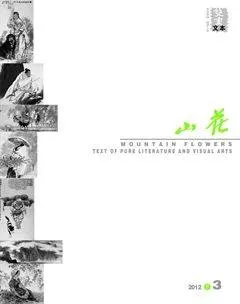论“评点式”小说理论的美学价值
一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县”乃古“悬”字,高也;“令”,美也。意思是说举着细小的钓竿和钓,奔走于用于灌溉用的沟渠之间,只能钓到小鱼,想获得大鱼就难了。靠修饰琐屑的言论,来求取高明美誉,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就差得非常远了。所以,“小说”一词,最初是指浅薄琐屑的言论和小道理,这与现代的“小说”观念相去甚远。庄子针对春秋战国时的学人策士,多用比喻、神话、寓言等故事,来修饰自己的言说,增强文章表现力的现象,认为这些都是“小说”,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些“琐屑言论”和“小道理”的小说,却又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
《荀子·正名》中说:“故智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2]其意是智者只论大道,而那些百家异端邪说就会停息。在东汉桓谭时,“小说”的概念有了较大变化。《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3]“短书”是相对于“长书”而言的,古代编简成册,经类简长二尺四寸,称为长书;杂记之类的长度为经书的一半,称为短书。分析可见:在形式上,小说是零碎琐细的言辞写成的短篇体制;在内容上,它于治身理家有道理;在手法上,通过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等形象化比喻来说明道理;在社会功能上,可以为人们提供一定的经验教训。于此,桓谭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肯定小说价值、探索小说文体特征的第一人,并影响了后人对小说的认识。
《汉书·艺文志》列“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将“小说家”看做独立成家的学术流派,于此,“小说”成为一种文体的专名。“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4]班固认为“小说”是民间稍有知识者所创造的,而居高位的人是不屑于此的,其内容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带有夸饰虚诞的色彩,这种小技艺创造也有可取之处,也是它存而不灭的原因,但它会妨碍大事业,故君子不为。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根据西汉刘向、刘歆的《七略》删定而成,刘向、刘歆在汉成帝、汉哀帝时期担任朝廷藏书室校书,所以,班固的观点可以反映两汉时期人们对小说的看法。他既继承了庄子小说为小道的观点,又吸收了桓谭小说有“可观之辞”的正面肯定,将小说列为十家之一,使它有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地位。《汉书·艺文志》中的十五家是由诸子、史传和巫术三部分构成,班固从子书的角度来肯定小说的价值,虽过于狭隘,但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的历代正史大都将小说归于“子部”,将“小道”与“可观”作为“小说”的核心观念,直至清代,依然没有多大的变化。
纪昀主持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漫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故不必以冗杂废矣。”[5]这里,将“小说”的功能定位在“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之上,是典型的儒家“小说”观,它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影响了小说的创作实践。“寓劝戒”的观念,使小说一直处于经籍的附庸地位,作为社会教化的工具。但是,它也肯定了小说创作没有停止,一直在向前发展,直到明、清,小说的创作空前繁荣,进而产生了关于“小说”的艺术理论。
二
明、清两代,随着中国传统诗歌创作高峰的转向,诗话批评方式的转变,原属于民间艺术的小说和戏曲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随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形式——小说和戏曲的评点兴盛起来。评,是批评、评价和判断;点,是圈点、指点和说明。明代李贽开始评点白话小说,并把小说批评和社会批评紧密地结合起来,运用小说批评来宣传反道学、反传统的思想。因此,“评点式”批评理论可以看做诗话批评在小说和戏曲活动中的另一种应用,也是社会批评的一种方式。
“评点”本来是古代典籍评注形式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古人读书,常在正文旁圈点批注,以记述其阅读过程中的会心之意。宋代诗文多用评点,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特样式,它继承了钟嵘《诗品》中的多种批评方式,并将笔记小说的体制借用过来,逐步形成了以谈论诗艺为主要内容,并带有漫谈和随笔性质的笔记体批评方式。笔记体的批评内容比较庞杂,包括了“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6],作者将它们搜集起来,主要是“以资闲谈”用的,在体制上,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其优点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缺点是“凌乱琐碎,不成系统”[7]。尽管如此,但它似乎更适合普通文人的需要,影响和引导他们参与到具体的文学阅读活动中来,使它逐渐成为宋、元、明、清艺术批评的主要方式。明代杨慎在《丹铅总录·诗话类》中说:“世以刘须溪为能赏音,为其于选诗李、杜诸家皆有批点也。”随着小说和戏曲的流行,诗文评点逐渐渗透到小说和戏曲评点中,成为明、清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
从现存资料来看,最早的小说评点本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万卷楼刊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它的评论基本上是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事实分析与道德评价,有史注和史评的印痕。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容与堂本和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袁无涯刊本的《水浒传》的相继问世,以及明末清初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和《西厢记》的刊行,将小说和戏曲的评点推向了高峰,它使中国的文学批评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些评点对作品中人物的分析、结构的勾勒和叙事模式的探索,有力地展示出批评理论中的新思维和新方法,推动了中国通俗文学的阅读和传播。
“评点式”小说理论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研究,使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从边缘进入中心,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小说和正统的诗文有同样的价值,是“六经国史之辅”,有益于“世道人心”。按照目前文艺学的观念,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其成熟标志应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在表现形式上,以散文写作,也可有一定数量的韵文,将写景、描绘和议论融为一体;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环境;在性质上,它是虚构的,或至少是以虚构为主。中国小说可以分为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两个系统,前者比后者更接近现代小说观念,但它们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依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评点”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有效方式,它可以提高读者的欣赏能力,使读者充分理解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意图。袁无涯刻本的“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卷首《发凡》中说:“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侮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敻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所最贵者耳。”阅读优秀的评点作品,就好像跟着一位非常熟悉作家和了解作品的人一起阅读,他帮读者逐字逐句逐段逐回地讲解,使读者对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手法和文辞表达的优美都能很好地了解。金圣叹认为“看书要有眼力,非可随文发放也”[8],他评点的《水浒传》和《西厢记》流传三百年后,仍有不朽的魅力,足见其影响之深远。金圣叹的评点就是要发现“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9],帮助读者提高眼力,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作品。因此,“评点式”小说理论更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特点,评点中所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都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它以具体的创作实例作为依据,具有很好的示范性。
三
完整的小说评点体制具体包括三部分:一是全书的序文、读法和凡例等,它们是评点者对全书的主旨、结构、艺术手法、人物形象、创作特点等的分析和介绍,具有总论全书的性质,是对作品进行宏观把握和阅读前的提示,可以让读者形成一个阅读前的期待心理,能够帮助读者很好地进入作品之中,因此,它是评点理论中比较完整的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正文中的眉批、夹批和侧批等,它是评点者把阅读时的感受印象,在正文的空白处随手记写下来,有的以一两个字提示其思想意义和艺术特征,如“画”、“妙”、“真”、“传神”、“活写”、“奇文”等;有的则发挥其中的深层含义,如金圣叹评武松打虎,则联系赵松雪画马、苏轼画雁诗论“无人态”,以此来说明这段文字的描写和诗画美学之间的联系。这些内容是评点者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体验和艺术鉴赏的角度对作品进行的把握和思考,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种评点方法灵活多样,是一种自由交往式的阅读、思考和表达方式。三是回前和回末的总评。它是评点者抓住这一回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主要特点,进行阐释和发挥,其问题一般比较集中,理论色彩比较鲜明,篇幅也比分散在正文中的零星评语要多,有时候,它可以是一篇批评专论。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需要将评点、序跋、笔记杂注中的有关内容综合起来加以分析,才能全面地反映小说理论批评的全貌。
“评点”实践是随小说情节的发展,逐步揭示出作者的创作目的和艺术表现手法的,使读者对任何一个细节的描写、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词语都不会轻易放过,它就像近代西方“新批评”学派提出的“细读式”批评一样,一点点地读出文字背后所隐藏的秘密,体现出中华民族在艺术赏析上的独特方式。
“评点式”理论探讨了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从小说的源头到稗官野史的记述来看,史学对小说的创作实践有很大的影响。六朝的葛洪将自己辑录的《西京杂记》看做“以禆《汉书》之阙尔”。在历史上,小说和历史有很深的渊源,特别是《史记》的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将历史事实系于人物,对小说艺术的成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小说也多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进行虚构和想象,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因此,小说可以是历史文献的补充,但它却能显示出艺术真实的独特价值。
总之,“评点式”小说理论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能够帮助作家更好地创作,读者更好的阅读。它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特色,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丰富了文学理论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渭南师范学院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10YKZ043。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