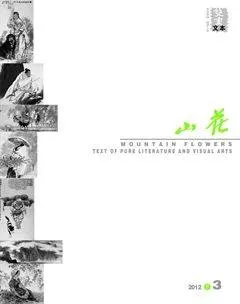现代文学作品新型故事程式
“第三者”形象与“第三者”意象
我们首先从历史发展角度来探讨“第三者”。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婚姻的生命历程总体来说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与蒙昧时代相对应的“群婚制”;第二次是与野蛮时代相对应的“对偶婚制”;第三次是文明时代,即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的“一夫一妻制”。通观三次变化,我们发现,只有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产生的“一夫一妻制”才为“第三者”的出现提供了逻辑和制度性前提。
在启蒙主义文学和先锋主义文学盛行时,“第三者”形象是作为群像出现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往往是讲相爱的两个年轻人不顾封建礼法,冲破媒妁婚姻的牢笼,放弃原配而追求真挚爱情。其中很多作家就是先驱者,徐志摩与林徽因,鲁迅与许广平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爱情而或了与原配的关系。而在先锋文学中,叶灵凤、穆时英等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第三者”身上所蕴涵的道德、伦理色彩并不十分突出,很少涉及对传统观念、制度的批判和颠覆,而是以“颓废”、“浮躁”的形象传达出作家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认识和反思。
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作品中的“第三者”形象被延伸扩展了。我们通过由时间线索串联而成的王海鸰的“婚姻三部曲”,来简析一下“第三者”的时代变迁和多重含义。《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三部曲,有着相似的悲剧因素——离婚(如果我们把离婚看成悲剧的话),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夫妻感情不和。而多重因素中既有真正第三者插足的原因,也有女主人公臆断“第三者”而猜忌丈夫的原因,甚至有由外在因素所形成的“第三者”差异性因素,确切地说,应该是“第三方”因素[1][2]。
至此,我们所讨论的“第三者”形象就扩展为“第三者”意象了。在这里之所以定义为“意象”,不是特指文学概念,而是本文涉及的一个泛指的概念。它不仅指一个具体的人,还指存在于夫妻一方头脑里的影像,以及离间夫妻感情(爱情、亲情)的社会的、家庭的、伦理的差异性因素。其实,从表面上看“第三者”的出现和对其的讨论似乎削减了现代女性的家庭安全感,增加了危机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对“第三者”的重视与探讨也是对现代女性意识的一种关注和对家庭天平失衡的一种反思。因为只有到了文明时代,在法律上已经确定了男女平等的前提下,女性在现实中的弱势地位才会受到关注。
“第三者”意象程式与传统故事程式的联系
当代学者刘慧英在她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列举了古今中外三种故事程式来印证她的主题——女性形象“自我”的空洞化。三种故事程式分别是才子佳人程式、诱奸故事程式以及社会解放程式,深刻剖析了在文学作品中女子对男子物质精神方面不自觉的依附和女性自我定位的偏差。
其中“才子佳人”、“男才女貌”式的故事多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戏剧、小说中,以《莺莺传》为开端,到后来的《李娃传》、《霍小玉传》。虽然结局有所不同,但是男为“色”倾倒,女为“才”仰慕却是定式。但是“这种表面的‘相映’和‘相兼’潜存着一种极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它直接将外在的美貌作为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砝码,作为女子取得幸福爱情和美满婚姻的根本性条件;而男子的才气既是婚姻的砝码,又是女性终生依附的根本性条件”。[3]
以诱奸故事程式创作的作品往往出现于19世纪西方和俄国的文学中。这类故事大都通过这样的程式展现主题:“年轻单纯、贫穷善良、温柔美貌的女子受到老爷恶少的引诱而失身,从被玩弄到遭抛弃,身心俱遭摧残,女主人公痛不欲生,不是步入歧途就是亡命丧身,总之是走向不幸,从而构成悲剧,锋芒直指贫富悬殊的等级社会和养尊处优的有产阶级。”[3]这类程式不乏世界名作,像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德莱塞的《珍妮姑娘》等。
发生在新时期阶级斗争和革命潮流中的社会解放程式,则是指在革命形势和政治力量的影响下,同为受苦受难的底层阶级的女性和男性一起来推翻统治阶级,在阶级独立以后,女性本身似乎也取得了与男权抗争的胜利,但实际上这是对女性自我的回避。家喻户晓的《白毛女》则是一个脱胎于“诱奸故事程式”的个例。实际上,《白毛女》将对女性生存和命运的探讨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那就是妇女个人的命运一旦与某种政治力量或社会变革力量结合在一起,并献身于政治斗争或社会解放运动,她自身的一切也就为这种外在的力量所决定和包容”[3]。诚然,女性首先是作为“人”来争取做人的权利的,其次才是女人的权利。在人权和阶级权利得到认同之后,女性要去争取与男人平等的作为女人的权利。此时,女性意识的抬头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上述三种故事程式,均反映出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关系,女性从未作为独立的个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她们习惯了自主意识的缺失,习惯了作为男人的参照物。她们往往忽略自己,而把幸福寄托在一个与她们有同样缺点的男人身上。
前文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印证了“第三者”意象。基于当代家庭伦理剧中反复出现“第三者”意象,本文顺接刘慧英的三种故事程式提出一种新型程式——“第三者”意象程式。
它与前三种程式的关系在时间顺序上大致是承接的。我国古代的小说戏剧中多出现才子佳人模式,原因是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和男子以取得功名为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心理。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作家想要通过妇女个人的悲剧来揭露社会黑暗、批判社会制度,有意无意地牺牲妇女的尊严而使她们屈从于男人的诱奸。到了现代的社会解放时期,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抗争成了作品的主题。在与同属于被压迫阶级的男人一起站起来反抗阶级压迫之后,妇女取得了与男人相等的权利和义务,但却失去了“自我”独立的意识。“它同样将人物形象的命运发展划归为外部力量,从而将人物形象、作品构思框架刻板化和模式化。”[3]而到了当代,在近一二十年的文学作品中,又频频出现“第三者”的角色,而且大多数的第三者都由女性扮演,这又为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为何第三者多为女性,为何女人在婚姻中容易怀疑丈夫有第三者。这同样代表了当代女性自我意识的不觉醒。
“隐形男权”与现代女性自觉意识的缺失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男人永远不会以性别为起点去表现自身,他不用声明他是一个男人。”[4]但是,女人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是一个女人。”随着当今社会法律和制度的健全与人们思想的进步,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女性也渐渐扮演起“半边天”的角色。但事实上现代社会仍是男权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男性还是有着许多易被忽略的特权。由于时代的发展有其关联性,现代社会多少会残留一些旧社会的糟粕。而随着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盛行,原来的“显性男权”被现在的“隐形男权”所代替。较过去而言,“隐形男权”更具有迷惑性和危害性,因为这种思想也同样存在于大多数女性的观念里。虽然教育和法律规定一夫一妻制,夫妻双方要对彼此忠诚,但是一旦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女性们又不自觉地认为是“第三者”在作祟。女性对“第三者”所产生的这种恐惧、忧虑的心理也从一个方面上表现了女性自觉意识的缺失和对“隐形男权”的屈服。
产生“隐形男权”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传统文化心理,自父系社会以来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心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成为一种不被人发觉的“隐形男权”,渐而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劳动分工中女性本身对男性的依附,由此造成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无论在社会地位、经济权利上,还是在两性心理、精神层面上都处于绝对优势;而女性则常常处于弱势地位,艰难地挣扎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于是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的依附心理,从而放弃了追求独立人格的权利。
“女性之所以为女性,并不是天然如此,女性是被社会历史及男权中心的社会文化建构而成的。”[5]诚然,上千年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造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男人和女人的思想里都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默认的意识——男人理应坚强勇敢,女人则应温柔善良;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则要从一而终;男人永远是以俯视的姿态关照女人,而女人永远要以仰慕的神情注视男人。一直以来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使这种意识得到流传和延续。从现代家庭伦理剧中已婚男性选择第三者女性而放弃结发妻子这一行为的引申意义来看,“第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男性对理想女性想象的“集体无意识”,她们具有“阿妮玛”的原型意义。荣格指出:“‘阿妮玛’也是男性心灵中理想的女子模式,一旦现实生活中异性的形象与这一模式相左,心理上就可能出现剧烈的冲突。”[5]“首先,从‘第三者’与男性之间感情产生的起点来看,男性标准下的理想女性首先应该是崇拜并肯定他……其次,从‘第三者’与已婚男性产生感情的基础看,男性需要的理想女性是乖巧服帖,她们的爱要无所附丽,具有纯粹为爱而爱的浪漫主义气质……最后,承担第三者功能的女性大都曾得到或需要男主人公的帮助和拯救。”[5]而上述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意识的不自知恰恰默许了这种现象的存在。
女性意识应该觉醒,外在的美貌不是自己努力争取来的,大都是天然获得的。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用通过自己努力取得的东西来提高自己的身份,而不是“才子佳人”中的美貌和“诱奸故事”中的性吸引。“爱情是一种人人皆有的情欲,在这种情欲中偶然的感性认识取代了谨慎选择和理性认识……这种情欲因悬欲不决和遇到困难而自然增强,并使心理失去常态,更激发出热情;但是婚姻的保障能使爱情的狂热渐渐平息下去……这是,也必然是自然的趋势,继爱情之后必定是友情或者是冷淡。”所以说,在爱情消退之前建立起彼此的尊重,在消失之后就会留下友情,这种坚固的联系会对“第三者”的介入起到一种防御作用。或许,当女性通过知性与独立人格取得了男人的尊重后,“第三者”的问题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吧。
此外,社会劳动分工中女性本身对男性的依附也是女性意识不能充分觉醒的一道屏障。王海鸰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说是男女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不平等。就是说,女人上班时间要上班,下了班之后还要上班;男人是退了休就退了休,女人是退了休还要上班。”[6]繁杂的家务占去了女性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致使她们更依赖于男人成功的事业。对于这一问题,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