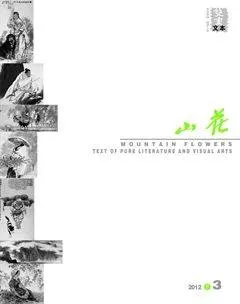试析二十世纪初“美术摄影”观
20世纪初的中国摄影
据史料记载,1839年达格雷照相术公布后仅十余年即传入中国,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少数人垄断了摄影术,身怀绝技者秘而不宣,流传到中国的摄影术并没有像它在西方的发展一样走向民主化。直至晚清,中国才出现了一些研究摄影学、宣传摄影术的文人墨客,他们开始从事摄影实践,总结摄影经验,撰写摄影著作,传播摄影知识。19世纪70年代上海编印出版了摄影专业书籍;清末出版的摄影书籍多为编译,刻版或石印,但数量有限。而首创精神是成功的保障,由西方引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摄影术来到中国时面临着重重困难,因而导致了如此局面:“吾国最初之摄影家。鲜有以研究学术之精神临之者。大都从西方之来华传教者或商人。略得一二简易手续以为谋生之计。其时传教者或商人。对于斯道。未能深明其学理技术。可断言也。而得知者,复视同枕秘,不肯轻以示人,师徒相承,辗转传播,以讹传讹。遂致毫无新知。”①
20世纪初,随着专业摄影和商业摄影在中国的发展,一批业余摄影师也随着西方的炮舰政策和商业扩张来到了中国。鸦片战争时西方用大炮顷刻间轰开了中国的港口,紧接着以照相机撩开了中华帝国神秘的面纱。当时中国旧的封建统治被摧毁,新的共和国又风雨飘摇,军阀纷争,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新的民主思想在孕育,新的救国道路在形成。
20世纪2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初创期和转型期,一些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的政治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为中国现代文艺创作方向定下了基调和范例。1919年之后,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文人学者、有识之士加入到摄影队伍中来,以他们广博的学识、深厚的艺术素养和探索精神,在摄影艺术处女地上披荆斩棘。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20年代的文艺研究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了我国早期摄影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国摄影艺术随着摄影术的传入开始萌芽;从开始被视为异端邪说到新奇玩意儿,为宫廷里极少数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所赏玩,到高级知识分子和中等文化阶层中传播,成为摄影爱好者传情达意的工具,以至“美术摄影”在群众中兴盛起来,经历了半个世纪。
刘半农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勇将,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语言学家和摄影家,积极倡导摄影这门新兴学科,并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和探索。1927年9月,刘半农撰写了《半农谈影》,该书在1928年、1930年两次再版。1927年,他积极参加了北京光社,在发表《半农谈影》之后的两个月又为《北京光社年鉴》作了序。刘半农作为光社最活跃成员之一,也是北京影坛的中坚人物。鲁迅将刘半农喻为“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打了几次大仗”,因而许多人亦认为刘半农在当代摄影界鸣锣开道,为摄影进入艺术之宫扫除障碍,为摄影和摄影工作者正名打了漂亮的一仗;而《半农谈影》即中国摄影理论的奠基之作。
被国际摄影界赠与“亚洲影艺协会之父”的郎静山,继刘半农组织北京光社之后倡议组织了摄影团体 “中华摄影学社”,进一步把摄影艺术推向社会。1928年,郎静山应聘成为上海时报的新闻摄影记者,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摄影记者;1932年他在上海组织“三友影会”;次年,他向《新闻夜报》争得一个版面,创办《摄影艺术》周刊,登载摄影技术、影展评介、影坛动态、摄影史话、器材交换等方面的文章,共出了二百三十多期。20世纪30年代的相机技术落后,焦距长,景深浅,胶片感光慢,不能收缩多级光圈,郎静山对此作了多番考虑,试制集锦照片加以补偿。早年的郎静山就意识到摄影是形象逼真、传递迅速的一种艺术手段,并力争全国美展要包括艺术摄影在内。他把西洋摄影技巧与国画的写意手段完美地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摄影风格——集锦摄影。
1929年9月,中国美术刊行发行了郎静山出版的《静山摄影集》,当时著名的摄影家都纷纷为其撰写序言,溢美之词此起彼伏。在陈万里、吴伯翔、陈山山、佛青为其摄影集作的序言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洒脱豁达的文人身影,看到了这位摄影爱好者为理想而奋斗的心路历程,也从中了解到当时的摄影思潮与人们评价摄影的标准。在郎静山推出这本《静山摄影集》之前,陈万里于1924年出版了个人摄影艺术作品集《大风集》,并于1926年在上海举办了个人摄影艺术作品展览,这些在中国摄影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岁月有序,时节如流,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郎静山和他的摄影集、陈万里和他的序言也都成了历史,我们不妨如陈万里所愿,仔细梳理一下摄影术传播之初的“声浪”,努力回顾一下当时的“艺术的摄影”,或曰“爱美的摄影”,平心解读一下郎静山如何促使摄影发展成为“一种高尚的娱乐”。事实上,这些问题解答的正是郎静山摄影观的构架。
鉴于北京光社在当时摄影界影响之大,笔者选取《北京光社年鉴》序言的撰写人、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摄影家——刘半农为代表,与郎静山的摄影观作比较,进一步分析上述问题,具体探讨一下何为“美术摄影”。
美术摄影
郎静山在1930年出版的《华美影集》中发表了《何谓美术摄影?》一文,该文总结了“美术摄影”的共通处,那就是:无不承认美术摄影正如绘画般是美的感情产物,是美化人生,创造人生的工具;而从另一方面讲,美术摄影就是他的记录,就是他的各种活跃与迈进的姿态缩影。
郎静山为“美术摄影”下的定义特别强调了“美”与“摄影”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观念的形成恰恰是由于当时人们脑海中所建立的摄影与美术之间的暧昧关系所致,当时人们对摄影的定义大都以“美术”为基准:
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是我国摄影艺术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也是早期摄影艺术评论的开创者。当时他称优秀的摄影艺术作品为“模范图画”, 1923 年,他在上海摄影家欧阳慧锵编著的《摄影指南》的十三幅照片上逐幅写了“画意”的评语。
我国美学、美育的倡导者、开拓者蔡元培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中这样提到摄影:“摄影术本是一种应用的工艺,而一入美术家之手,选拔风景,调剂光影,与图画相等;欧洲此风渐盛,我国现亦有光社、华社等团体,为美术家所组织。”
刘半农在1927年撰写了中国第一本摄影艺术专著——《半农谈影》,在书写过程中他已经习惯把“照片”等同于“美术”,因而还为“照片”加了很多美术法则,其手段称为——“美术的手腕”。
郎静山1931年在《文华影展》上题词曰:“有美皆备。”这时候,与刘半农、郎静山同时代的很多摄影评论都以“美术”法则评价照片。郎静山在分析“美术h8gBjTM0YDSHu/wbTTsi5A==摄影”时,提出了三个重要元素,也就是摄影作品成功的关键所在:一、光调;二、色调;三、构图。好的照片必须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来考究,如果一张照片在这三点上都无可指摘,那么这样的照片就完美无缺了。同样,刘半农在书写《半农谈影》时也不惜重墨大篇幅分析如何用光、如何构图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构图方面,刘半农还引用了诸多透视原理仔细阐述。
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以这样的标准来分析绘画作品又何尝不可呢?从古到今,不少绘画大师不也是在苦心追求画面的构图、色彩,甚至是光影效果吗?
1931年郎静山出版了《桂林胜迹》摄影集,在序言中他开宗明义:“摄影尤绘事”。这样的观念贯穿了郎静山摄影观的始终,郎静山丝毫不回避摄影模仿绘画这样的关系,言语之间甚至有些自豪。所不同的是同样坚持“美术摄影”的刘半农却十分忌讳有关摄影模仿绘画的说法,他在《半农谈影》中这样提道:
“有许多人以为照相是模仿图画的,这实在是个很大的错误;至少至今,我个人总不愿这样主张。因为画是画,照相是照相,虽然两者间有声息相通的地方,却各有各的特点,并不能彼此摹仿。若说照相的目的在于仿画,还不如索性学画干脆些。”
刘半农为当时社会上从事摄影工作的人所受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他企图为摄影正名,为摄影在艺术宝殿上争得一席之地而呐喊。因而,他明确否认了摄影模仿绘画的动机,试图为摄影寻求独立的身份。然而,之后刘半农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摄影的目的即“造美”,拍摄好的照片的秘诀即“结构完美”。如此说法似乎又回到了郎静山“摄影尤绘事”的论断上去了。因为得出这样观点的前提是:摄影图像是模仿绘画的。
坚持绘图法则的摄影师背后有其固定的理论依据,即摄影仅仅是一部生产作品的机器,而机器产生的作品不是艺术。他们企图用特殊的艺术法则与摄影过程中的机械化的本质抗衡,郎静山和刘半农正是其中的典型。以1931年起,郎静山开始参加国际摄影沙龙活动,提倡把摄影技术和中国传统绘画六法相结合,用中国画理创作集锦摄影,1939年发表《集锦照相》,将东方艺术融入摄影创作,他的照片甚至在画幅的格式上都沿袭了中国的绘画传统。以至于许多评论认为,郎静山恬淡如菊,静穆超脱,深受老庄哲学影响,达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尚境界。
同样具有传统文人气质的刘半农企图对摄影作为艺术设立一道防线,而内心对“摄影将成为艺术”的惴惴不安的矛盾心理促使刘半农建立了“写真”和“写意”照相分类法。刘半农在《谈影》中一方面对“照相总比不上图画”的看法进行辛辣的挖苦,另一方面提出了“把作者的意境借着照相表露出来”的“写意”摄影法。刘半农将“写意”和“写真”严格地划分了界限,认为 “写真”照相需要有个“术”字,而“写意”照相在“术”字之外还要有个“艺”字。他无形中暗示了“美”、“艺”、“术”这三者的关系。我们在《北京光社年鉴》中可以看到其中的照片大都是以浑柔的线条和影调表现山山水水,颇有国画的意味,深受中国传统艺术家美学观念的影响。作品的趣味仅仅来自于画面的形式美和光影效果,前人的流风余韵在这些作品的回味中久久不能散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摄影爱好者在探索创造性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传统理念来指导他们,不久,他们开始从画家那里挪用现成的图画法则。这种信念慢慢形成,以至于摄影成为一种新形式的绘画,拥护者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使照相机制作出像绘画一样效果的图片。或许这种误解正是由于恐惧触犯艺术的名称而形成的。摄影以新方式揭示新事物的巨大能力被绝大多数摄影拥护者疏忽了,照相机先天的忠实性竟成了它的局限性。在摄影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期,摄影家揣着继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沿袭画家的传统,以建立“美术”的标准来抑制任何有独创性、有活力的视觉征兆的出现。这些“美术的手段”和“写意”手法都成为“画意摄影”的渊源。
兴起的声浪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文艺研究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我国爱好摄影者之团体以1923年冬建立的北平光社为之先,南方华社相继而为之创,各学校摄影学会均应声而起。当时的许多摄影团体除举办展览外,还编辑出版了各种形式的摄影书刊。这一时期源自西方的摄影艺术在我国出现了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也就是陈万里所说的“近五年来新发的声浪”。
北京光社原名“艺术写真研究会”,后因名字太长才改为光社。它的建立被称为我国摄影艺术经过漫长的技术准备和摸索阶段,进入发展时期的标志。而光社本身则被视为我国摄影艺术的发源地,中国美学思想和摄影展览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摄影艺术团体。1924年 6 月,光社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了第一次公开影展,每日观众足有两三千人之多。从此每年一次,每一会期观众至少有万余人。
1927年北京光社出版了年鉴,刘半农为其作了序言。由于年鉴的销量出人意料的好,第二年,光社年鉴又义不容辞地出版出来,刘半农继续执笔为其撰写序言,然而这篇序言的声音显然尤为低沉。刘半农总结出光社的“情绪不佳”,言语中透着让人哭笑不得、爱恨交织的说不出的滋味,他是如此形容光社的面貌的:
“就整个儿光社说来,它原是去年的老样子,好像一只疲瘦的骆驼,全身沾满了尘埃煤屑,一拖一拖的在幽冷的城墙根下走;你要他努力,他努力不来;你要他急进,他急进不得;他只会一拖一拖,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如此萧条暗淡的描述恐怕光社中任何人都不愿在年鉴的序言中见到,似乎也为光社后来的消亡埋下了一个伏笔。于是,刘半农传出了影界新的希望,即上海成立了华社。对于这同气连枝的团体,刘半农充满憧憬,对于华社虽然不必说“太阳出来了萤火该消灭”那一路的客气话,却也不妨说“太阳出了我们身上也有光”。既然刘半农称华社和光社是“同气连枝”的团体,为何他对于两个社团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呢?我们在光社序言中又看到:
“但华社光社的目的虽然相同(这目的简单言之,只是弄弄镜箱,送两个钱给柯达克或矮克发,无论如何,总说不出什么天大的道理来),态度却不无小异。在我们这方面是昏庸老朽,愈腐愈化,愈化愈腐。在他们却是英气勃勃,不住的前进。所以华社虽然成立了还不很久,已在南方博得了极好的声响。我们在种种方面,可以看得出他们这一年中苦心努力的痕迹。”
华社真的能给影界带来希望吗?刘半农的摄影观能在华社找到自己扎根生长的土壤吗? “华社”全称为“中华摄影学社”,是 1928年年初由郎静山、陈万里、吴伯翔、黄振玉等发起,经上海《时报》主人黄伯惠等赞助,联合报界和摄影同人成立的摄影团体,他们定期举办摄影展览,每星期聚会一两次,交谈研究,相互观摩作品。《华社简章》规定:“本社以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
位居华社会计一职的郎静山在华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在1939年出版的《郎静山摄影专刊》上看到郎静山摄影作品入选国际沙龙的“丰功伟绩”,郎静山是用照相这一“奇技淫巧”,千方百计地弄出中国画的味来,来圆他的绘画之梦和撬开他的国际奖牌之门。华社中展出的摄影作品题材内容多为风光、人物、静物、花卉、建筑等。这些物质和精神条件都较为优越的知识阶层,都认为摄影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把摄影当做满足个人兴趣的途径。
张篷舟1931年在《文华影展》序言中这样呼吁道:“艺术摄影团体的小组织又忒多,缺少巨大的活跃。有力量分散的毛病,甚者门户之见很深,取不到前进的联络。”华社提出“该社诸君虽抱发扬东方艺术、提高生活兴趣之伟旨,但欲入会者,须讲作品在展览会中陈列多次,对于摄影术有相当研究,而须有高尚的品格,故持严格主义”。这种近乎关门主义的态度,使华社逐步失去了活力,无形中慢慢走向消亡。刘半农寄予华社的厚望也在无形中破产了。
高尚的娱乐
郎静山将他的摄影观与“为人生而艺术”的世界观始终联系在一起,直到他九十六岁高龄在摄影学会成立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上他依然强调说摄影和人生有密切关系,他个人研究摄影的原因,就是希望借摄影艺术影响世界,以期达致和平。而在郎静山1929年出版的《静山摄影集(一)》的自序中他却如此道来:
“静山玩习摄影,于兹有年,第以娱乐为旨趣,非事职业者也。职业者其器精,制作也巧,必求照相之征于优美,静山并非以此为职业,所事全反乎是。凡天下事物,不问其可摄与不可摄,只以个人之兴趣之所至,取而摄之。”
另外,在陈万里为郎静山摄影集作的序言中也是如此赞美他的:“静山在上海,为开发这一种新的动机倡导者,同时把这微弱的声浪,扩大成功为一种强有力的一种高尚的娱乐,同簇新的学说之研究,静山实为其中最努力的一个人。”
当此国难之际,郎静山游踪诸名山大川,以一位“业余摄影师”的身份,在暗房红灯下精心拼对山高水远和小桥流水的集锦作品,琢磨揣测西方人的审美口味,制作出一幅幅清妙缥缈、别开生面、迥异时流的照片。他用照相机拍了许多的山影树景的素材,然后再找若干演员,装扮成仙风道骨的老人或村野樵夫抑或田野牧童拍成照片,再用暗房拼放的技法洗印合成。这样,一幅幅中国人眼熟耳闻的,酷似水墨山水画的照片就诞生了。这样的照片比用笔绘制的水墨画更逼真,能让想象中的神仙真身再现,让虚无缥缈的梦想又接近真实一步。这又何尝不是刘半农所追逐的呢?!刘半农在《谈影》中提到他摄影“……为的是消遣,所谓消遣,乃是吃饱了饭——或者说:吃不饱饭——寻些事做,把宝贵的光阴在不宝贵中消磨了”。这不就是刘半农所提倡的“消遣”摄影的结果吗?
以郎静山、刘半农为首的一批物质和精神条件都较为优越的知识分子把摄影视为一种消遣,一种娱乐,把摄影当做满足个人兴趣的途径。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行动是个体的,追求的结果也是个体的,乃是纯粹的“为己者”。拍的照片“敝帚千斤”,每个人都可置身事外,真正达到“消遣”摄影的心态了。然而真正的现实逃避得了吗?摄影充当的只能是聊以慰藉自己心灵的附属物吗?相机拍摄的只能是风花雪月般的抒情篇吗?
这样,一面激烈地反对将摄影和绘画混为一谈,一面在实际创作中以绘画的方式“造美”的摄影行为滑稽而尴尬地并存于中国影界。摄影作为一种书写人类历史的独特方式,其忠实性,其镜头的特权被人们遗忘了。摄影师实践活动的真正价值与他们留下影像的历史价值是成正比的,释放快门的瞬间在历史中演变成历史的永恒。若忽略摄影的传播功能,把摄影简单地看做另一种绘画,或类似于下棋一般的娱乐方式,那么摄影只是局限在小圈子里的赏玩方式而已。如果我们释放快门仅仅为了得到瞬间的快感,或美学上的享受,这样的出发点往往是无力的。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北平光社”、“华社”的结局正是一面明镜。当年刘半农呼吁的“为己的精神”正是对在沙龙摄影中迷失了自己的摄影师的一番苦心呼唤。只是他提出的“消遣”观走向了极端,成为脱离社会的摄影者从事摄影的一个借口。如今大批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围着奖牌走,对身边的现实生活却熟视无睹。就像当年的刘半农一样,认为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美就足以心旷神怡,国家大事和人民命运都可以置之度外了。如果说当年的刘半农还承受着战事的痛苦、政治的重担,需要以摄影来“慰藉”心灵,那么,现代人还在年复一年地拍摄雷同的题材,进行着重复的劳动,孤芳自赏,那就是与时代脱轨了。这也是中国摄影的发展仍然落后于他国媒体,落后于时代需求的原因。
启示
进入了21世纪,电子媒体日益普及,计算机与数字影像已经逐渐威胁到传统摄影的生存空间。传统摄影更应该探索出新的生存理念。希望这篇论文能够唤起摄影媒介的研究者和那些严肃的、从传统中获得概念知识的摄影师潜在的兴趣。思索只有通过批评才能进行下去,也只有通过警示,懂得批评既存的观念,新的观念、新的实践才会诞生。刘半农与郎静山的摄影观是整个中国摄影界理论状况的一个缩影,八十年前中国摄影理论存在的问题,今天仍然悬而未决。这也昭示人们必须告别以摄影表现方法论为主的对待摄影的态度,重新激活一度兴盛的摄影创作激情,我想郎静山、刘半农之后的摄影理论需要更多,更雄壮,更新鲜的声音。
注:①上述言论载自《中华摄影杂志》1931年10月发刊辞。
②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寿彭,后改名刘复,字伴侬、瓣秾、半农,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同时,他也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
参考文献:
[1]刘半农.半农谈影[M].上海:上海开明书